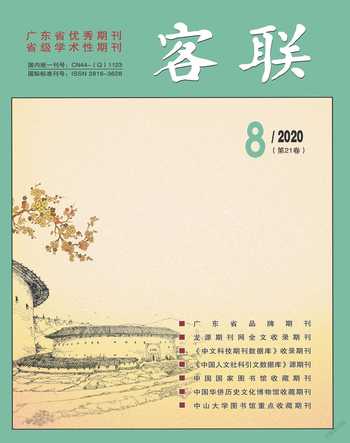紈绔的第四代
任程宇 楊鑫鑫
【摘 要】本文將通過悲劇的誕生,悲劇的形成,悲劇的終結三個方面對《布登勃洛克一家》與《紅樓夢》文本中漢諾和賈寶玉兩個典型人物的比較,試分析在不同的社會環境與時代背景下,兩人在時代浪潮和家族使命下形成悲劇形象的原因及異同。
【關鍵詞】《布登勃洛克一家》;《紅樓夢》;賈寶玉;悲劇;漢諾
漢諾是德國作家托馬斯·曼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布登勃洛克一家》中的主要人物之一。這部小說描述了布登勃洛克一家歷經四代由盛而衰的全過程,但時間跨度只是從1835年到1877年。從情節和內容看,全書寫的盡是家庭瑣事。托馬斯·曼在創作時充分利用了自己資產階級家庭的歷史資料,以現實主義的藝術手法,通過對一個資產階級大家族的日常生活細節以及婚喪喜慶一類活動的描寫,反映出布登勃洛克一家的衰亡史。而這不得不令人聯想到了中國的四大名著之一,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家曹雪芹創作而成的《紅樓夢》。曹雪芹的家世和個人經歷也是他創作《紅樓夢》的直接歷史資料,通過描寫一個封建貴族大家庭賈府的日常生活畫面,反映其衰亡過程,進而揭示封建社會必然滅亡的歷史趨勢,這一點與托馬斯·曼的作品《布登勃洛克一家》有著異曲同工之妙。本文將通過布登勃洛克家族第四代繼承人漢諾與《紅樓夢》中賈府的第四代繼承人賈寶玉進行比較,探討他們殊途同歸的悲劇命運。
一、悲劇的產生——家族使命的千鈞之擔
作為歷經百年的大家族的男性子嗣,賈寶玉和漢諾都負有相同的家族使命,這是由他們在各自家族史上的地位所決定的。賈寶玉是《紅樓夢》的核心人物,對賈府的興衰具有決定性意義。賈府最初由寧國公和榮國公創下基業,成為遠近聞名的“鐘鳴鼎食之家”。此后,賈氏家業逐漸呈現出衰敗之象。到了第四代,則逐漸衰敗蕭疏,再也不比先時的光景。整個賈府到了第四代只剩賈寶玉聰明靈慧,心腸樸直,于是賈府中興的重任就順理成章地落到了他的肩上。
無獨有偶,在被譽為德國“紅樓夢”的《布登勃洛克一家》中,同樣有著百余年歷史的名門望族布氏家族也發生了與賈府極其相似的后繼乏人的情形。布登勃洛克大家庭最初依靠老約翰·布登勃洛克在拿破侖戰爭年代販賣糧食發財致富。老約翰之子小約翰繼承家業時,德國資本主義已經進入大規模發展的階段,商業競爭日趨激烈,社會上投機成風。而第三代布登勃洛克的情形則更不妙,長子托馬斯為了維持家族產業殫精竭慮,悲觀絕望之余,試圖在叔本華哲學中尋求解脫,最后因牙病猝死。此前,托馬斯和全家人很早就把繼承家業、重整旗鼓的期望寄托在漢諾身上。因此,小漢諾作為第四代布登勃洛克唯一的子嗣,和賈寶玉一樣,同樣面臨著繼承祖業、挽救家族衰亡命運的重任。橫向上來看,賈寶玉和漢諾都是含著金鑰匙出生,但也恰恰正在享受家族最后的紅利,家族的大廈都或多或少出現了裂縫,正在朝著反方向滑落,而他們顯赫的家族最終也以各自的油盡燈滅而宣告破滅。
二、悲劇的形成——在劫難逃的使命烙印
盡管賈寶玉主要生活在有“女兒國”之稱的大觀園內,他的生活面卻十分廣闊,因為賈府貴公子的現實身份使他情愿或不情愿地與外界發生著各種各樣的聯系。而漢諾的生活面則十分狹窄,他基本上是在家庭和學校活動,與外界的接觸極少,只有一個同性朋友凱伊。書中著重描寫了漢諾的精神世界,尤其是他對音樂的熱愛和迷戀。雖然封建貴族公子寶玉和資產階級少爺漢諾確實過著兩種完全不同的生活,但他們的存在方式在本質上是相通的,因為音樂之于漢諾恰如大觀園里的女孩兒們之于賈寶玉。
賈寶玉內心深處積聚著有時連黛玉也無法了悟的悲涼和難以言說的孤獨。既然現實世界對他來說無異于身外之物,而生活之中又知音難覓,甚至連他最鐘愛的黛玉有時也不能理解他,因此他逐漸變得悲觀和多愁。這一切都是賈寶玉隨著時間的流逝體味到的,是在他的成長過程中發生的,是他悲劇人生的重要環節。
而漢諾的生活遠不如賈寶玉那么浪漫而富于詩意。他從小體弱多病。之后他在音樂中發現了自我,發現了存在于他心中的某種無法言說的理想境界。賈寶玉在殘酷、污濁的現實生活中,只有見了女孩兒才覺得清爽,而一貫無精打采、終日誠惶誠恐的漢諾則只有傾聽或是演奏音樂時,才變得聚精會神、容光煥發。他們作為各自家族精神的叛逆者,憑著自己的“真性情”和對冷酷現實生活的深刻感受和理解,拒絕自己“理應”肩負的家族使命,承受著來自環境的巨大壓力,心中有著朦朧的理想,在深深的孤獨中尋求他人的理解和自我表達的方式。在本質上他們二人是如此的相似,甚至于是相通的,對漢諾和寶玉來講,音樂和女孩兒既是同質異形的審美對象和審美理想,同時又是他們在無感現實世界里僅存的寄托和在家族使命重壓之下少有的喘息空間。這種深刻入骨的使命烙印使得漢諾和賈寶玉刻不容緩的被家族機器一步步的塑造、轉型、被迫逃避甚至扭曲,這也為之后他們的抉擇和命運埋下了必然的伏筆。
三、悲劇的終結——家族大廈的轟然倒塌
賈寶玉和漢諾堅守自己獨特的個性和思想,以拒絕的姿態同他們所處的社會環境保持著距離,時刻感受著成長過程中無法掙脫的羈絆和日益深重的壓抑及苦難。這種與家族意志背道而馳的“成長”,相對于社會環境對他們的要求而言,更多的是自發的逆向生長。這實質上是個人存在同社會與時代精神的背離,在任何時代都可能導致個人在世俗生活中的悲劇和災難性的后果。賈寶玉和漢諾的人生就是這樣的悲劇。理所應當的,我們可以預見到,他們的結局定會以悲劇的高潮作為個人乃至家族生命的完結。
曹雪芹為賈寶玉的悲劇人生安排遁入空門作為結局,正是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一種具體體現,也自此為榮極一時的賈氏家族拉上了告別的帷幕。而托馬斯·曼則讓苦難深重的漢諾死于傷寒,沒有讓他自殺或因意外事故死去,這個結局也不是偶然的。漢諾十分明白,面對無法逃避的可怕未來,音樂和友誼都救不了他。他虛弱的身體和軟弱的個性不可能產生抗拒的強力,在絕望之中他想到的唯一可以自救的途徑便是死去。同賈寶玉不同的是,漢諾的苦難生活本身包括兩個方面,即精神的和肉體的。精神方面的痛苦是,他的特定“身份”使得他和寶玉一樣無法擺脫家族意志的壓制和追迫,以至于他只能通過音樂暫時逃避和自慰,直到最后再也無法承受巨大的精神壓力,終于悲觀厭世,想一死了之。漢諾看似偶然的“病故”,無論是就小說的情結發展還是漢諾本人的生命歷程而言,其實都是具有必然性的。漢諾的悲劇雖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個人性格和志趣同生存環境之矛盾的產物,卻也表明了有藝術才能的人或者說藝術家同資本主義社會環境之間的不可調和的矛盾關系。
四、結語
從以上分析可以發現,賈寶玉和漢諾這兩個人物,其悲劇命運的發生發展以及結局都有諸多相似或相通之處,呈現出一種同構性。《紅樓夢》和《布登勃洛克一家》兩書的作者能在不同時代、不同地域和不同歷史文化背景下創造出如此類似的文學形象,絕不是偶然的,這也說明寶玉和漢諾這樣的人作為時代精神之叛逆,具有超越時代的意義。
【參考文獻】
[1]傅惟茲譯.《布登勃洛克一家》,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
[2]余匡復著.《德國文學史》,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1年.
[3]游國恩等編著.《中國文學史》(四),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
[4]曹雪芹.《紅樓夢》,岳麓書社,1987年。
[5]黃燎宇.《進化的挽歌與頌歌——評〈布登勃洛克一家〉》,《外國文學》,1997年第2期.
[6]方維規.《“病是精神”或“精神是病”——托馬斯·曼論藝術與疾病和死亡的關系》,《北京大學學報》201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