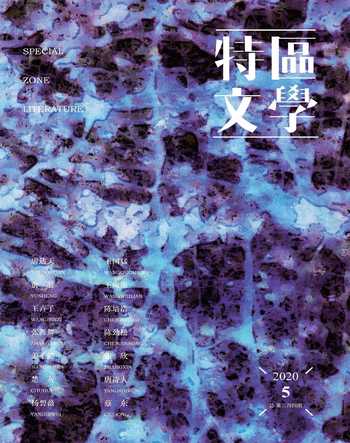深圳孕育著最富現代性的城市文學形態
陳勁松 蔡東
一、個人創作及閱讀:以寫作捍衛一個更好世界
陳勁松:蔡東老師,你好!前些時候,青年作家王威廉來信告知,他和青年批評家陳培浩今年在《特區文學》共同主持“大灣區文學地理”專欄,欲邀請我和深圳作家做一個對談。得知訪談對象是你后,我欣然接受了邀約。一則,有幸認識并關注你的寫作十多年了,盡管我們曾經在不同場合也有過各種交流,但像今天這樣鄭重其事的訪談還是第一次,我們正好可以借此機會就彼此感興趣的話題再深入聊一聊。二則,我從研究生時期即開始閱讀深圳作家作品,并持續跟進其創作態勢。粵港澳大灣區成立后,我又將關注視野延伸至香港、澳門及珠三角其它城市的文學創作及發展,在此過程中,我對深圳文學乃至粵港澳大灣區文學產生了諸多思考,亦伴隨著不少困惑,我愿就此和你進行分享和探討。我想,我們的對談大致可以圍繞你的個人創作與閱讀、深圳文學及城市寫作、粵港澳大灣區文學現狀和未來等話題展開,當然也不局限于此,可以盡量輕松活潑一些。你看如何?
蔡東:說真的,一聽說要做訪談,抵觸、擔憂、害怕一起涌上來。很多話題翻來覆去說,難有新意。另外,作家重要的永遠都是作品。訪談做得多,心慌意亂,小說寫出來,心里才踏實。
糾結是有的。但正如勁松兄所言,相識多年還是第一次做對談,機緣到了。看到你發來的幾個對談話題,花了很多心思,這些問題也很有展開談的必要。
陳勁松:我至今記得最早邂逅你作品時的情形。2014年前的那個春季,我尚念研究生,某天去學校圖書館翻閱文學期刊時,偶然讀到了你發表于《人民文學》2006年第3期“新浪潮”欄目的《嘿,天堂》,一部以深圳為故事背景的中篇小說(雖然作品沒有出現深圳字眼,但從其中的場景不難辨識)。彼時,在導師的影響下,我正有意鼓搗一篇類似的小說,所以特別留意相關作品。可是,當我讀完這篇精彩小說,尤其看到文末的作者簡介,發現你居然也只是和我同齡的在讀研究生,而非想象中的成熟作家,我內心的沮喪莫可名狀,隨之放棄了這個念頭。說實話,那個年紀的你,在這篇小說中表現出來的從容與嫻熟,讓我刮目相看。因此,我們的對談不妨從回顧你這篇小說開始。還能想起當時的創作背景嗎?
蔡東:《嘿,天堂》應該寫于2005年,讀研時期。2003年研究生入學的時候,我有了一臺電腦。父母知道我喜歡寫東西,經常在學校外面的網吧待到很晚,他們就給我買了一臺。我家是普通工薪家庭,談不上富裕,尤其母親生活挺節儉。現在想來,買電腦是一筆意外且不小的開支,但家里為我想得周到,鼓勵我發展自己的興趣。家庭氛圍也寬松,很多事情是我自己做決定,沒有感受過管束和逼迫。我以為同齡人的成長經歷是類似的,工作后接觸到更多人,同事,學生,了解到更多樣的家庭關系。腦子里有了這根弦后,跟以前的同學也開始聊這些話題,了解到家庭內部人際關系的勢利和殘忍,長輩怎么逼子女,有條件的愛,精神虐待,掙脫、逃離甚至切割,感覺挺震撼,震撼下也寫了小說《來訪者》。
那會兒宿舍里有電腦,寫小說就不用出去了。寫《嘿,天堂》時,用一條床單做簾子圍住書桌,寫得天昏地暗,是忘我的境界。這種寫作狀態很少有。寫作的緣起是去深圳游歷了一趟,受到很大沖擊。此前的人生經歷很簡單,就是一直上學,沒操心過生活,從山東的校園到深圳,打個比方就像家養動物進了叢林,回學校后就寫了這篇小說。
陳勁松:在你的《嘿,天堂》之前,我讀過作家慕容雪村的《天堂向左,深圳向右》,一部同樣以深圳為故事背景的長篇小說。較而言之,《嘿,天堂》和《天堂向左,深圳向右》均以“尋找”為主題,且有著異曲同工的創作歸旨:兩者都寫出了一代青年在深圳這座現代化城市(天堂)追求理想和愛情,卻最終都化為泡影后的迷惘和虛無。不過我以為,和《天堂向左,深圳向右》的粗獷喧囂相比,你的《嘿,天堂》由于采取的是女性化視角,故而顯得更加細膩溫和。你讀過雪村那部小說嗎?你自己如何評價《嘿,天堂》對于個人早期創作的價值和意義?
蔡東: 慕容雪村的作品很有名,當年這個句式挺流行,但小說至今還沒讀過。《嘿,天堂》是很早的作品,當然有很多問題。但我喜歡這篇小說的敘述,有生活質感,豐潤不干枯。《人民文學》的寧小齡老師讀了初稿,給出修改建議,定稿后只等了幾個月小說就發表了。那時還在讀書,小說在喜歡的刊物上發出來,是莫大鼓勵,一下子有了信心。
陳勁松:嗯,我理解你那種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感覺。提到作家的個人創作史,“創作動機”往往是一個繞不開同時非常有趣的話題。譬如,作家莫言多次憶起自己寫作的最初的原動力,“就是為了改善自己的命運,為了改善自己的社會地位,說得更俗,就是為了天天能吃餃子。”作家閻連科也一再強調自己年輕時的寫作動機多么功利:“能提干。”他坦承:“最開始寫作很純粹,就是想到城里去。”對于莫言、閻連科那一代作家來說,這樣的創作動機顯然帶有深深的時代印痕,雖現實卻無奈。后來,在你的創作手記《寫作:天空之上的另一個天空》中,我讀到了這樣的句子:“我寫作的隱秘動力,來自于靈魂深處的矛盾。”“寫作成為了一種調和,或者說,是一個自救的辦法。”“寫小說是一次美妙的誤入歧途,且很難迷途知返。”具體說來,你是如何踏上文學之路的?其中又有哪些難忘經歷?
蔡東:我是生活型的人,愿意沉下心來過日子,也能在家庭生活中找到樂趣。人活在世上,既有愉悅和享受的時刻,也必然要承受生活的壓力。對我來說,沒有比讀小說更好的解壓方式了。拿起一本小說,讀進去,人就去了另一個地方,這是最好的休息。人到中年,特別能體會弗羅斯特詩歌《雪夜林邊小駐》的滋味,“睡前還有很多路要趕”,讀本小說,就像是趕路途中在雪夜林邊的暫時停駐。
我算不上表達欲很強烈的人,一篇小說要醞釀很久。讀書的時候喜歡看小說,也嘗試著寫一寫。寫作初期找不到感覺,不是很快受到關注的作者,寫了很多年,漸漸有心得,也漸漸有人注意到我的小說。
陳勁松:大學時上文學理論課,講過英國浪漫主義詩人華茲華斯,我至今記得他的一句話:“適合自己的生活才是美好而詩意的”。或許這也可以用來對應你的生活和寫作,恰如他的另一句話—“樸素生活,高尚思考。”聽了你剛才的講述,我充分體會到作家創作背后的種種艱辛,也完全理解作家針對批評家過于吹毛求疵乃至刻意貶損其作品時,發出“站著說話不腰疼”的嘲諷。事實上,自文學批評誕生以來,作家和批評家之間的處境始終非常微妙,不少人還專門撰文討論兩者之間的關系。譬如茅盾,就在《作家和批評家》一文中談到:“作家們抱怨批評家們‘不負責任’,只會唱高調,可是總說不出個所以然來叫作家佩服。”而與此同時,“批評家也是同樣地抱怨著”。對此,茅盾認為“互相抱怨是無聊的,要互相幫助。”這種彼此相互成全的境界固然值得向往,不過現實或許沒有那么令人樂觀。我比較好奇的是,身為作家的你,如何看待作家和批評家之間的關系?交往過程中,是否遇見叫你佩服的批評家?他們的文字對你的創作有無真正影響或啟發?
蔡東:有啟發,會在有些評論家的評述里發現自己未曾覺察的東西,變得更自覺。小說寫出來,當然希望收獲贊美,而中肯的批評就像難喝的良藥,只能表情痛苦地往下咽,咽下去了就有好處。其實評論家蠻溫和的,看到毛病,點到為止,后來我自己更深地參悟到了,心領神會,也明白這是一份善意。
陳勁松:你的心領神會何嘗不是一種相互理解的善意!某種意義上,好的批評家和好的作家一樣,可遇不可求。魯迅曾說:“批評家兼能創作的人,向來是很少的。”但在閱讀你作品的過程中,我發現除了創作小說,還寫了不少創作談和評論文章,譬如你對作家鄧一光和遲子建的論述,就非常令人賞心悅目。細讀之后,我感覺你的評論文章靈氣斐然,迥異于某些專業批評家尤其是學院派批評家的佶屈聱牙。你如何看待自己這種“創而優則評”的雙重身份?你心目中理想的批評家是什么樣子?
蔡東:謝謝勁松兄夸贊。這些年寫的評論很有限,不算學術文章,“感受派”的寫法,稱作藝術隨筆更貼切。理想的批評家是什么樣子?前段時間讀到岳雯的一篇文章,太喜歡了,有真氣,有性情。岳雯說:“我們視批評為寫作。這是另外一種形式的抵抗。盡管我們中的大部分人出身學院,或就職于學院,但我們不滿足于論文式的寫作方式。”說到理想的批評家,大概就是愛惜自己的文字,不在乎多一篇少一篇,拒絕樣式陳舊的“論文”—這類論文跟機器寫的一樣,感受不到作者的靈性,不慎讀到是浪費時間,而炮制者大概就是在浪費生命了。
陳勁松:岳雯的這篇文章,我也讀到了,對其觀點,深表認同。我們再聊聊虛構和非虛構的話題吧。作為近年來較為流行的探討文學寫作的兩種不同手法,盡管兩者并無高下之分,但還是在作家之間尤其是學術界引起了一些爭議,爭議的焦點,在于實際寫作中兩者究竟應該涇渭分明,還是應該互為一體。我以為,虛構也好,非虛構也罷,回應的其實都是文學和現實(世界)的關系問題。譬如,法國作家菲利普·福雷斯特認為,小說就是回應現實。他強調,真正的文學應該是基于個人經歷的一種“真實”,這種真實只能通過文學的再現而存在。作家梁鴻則將寫作與世界比喻成魔術師與真相的關系,在她看來:“文學世界是一個既不同于現實世界,但又一定誕生于現實世界的世界,它與現實世界之間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關系,是看似一個面像,但其實卻是由無數面像組成的關系。”你在寫作過程中如何處理文學和現實的關系?或者說,你怎樣理解虛構和非虛構的關系?
蔡東:非虛構我了解不多,讀過一些,寫法很講究,敘事上有藝術價值。虛構和非虛構看起來手法迥異,其實都是洞察世界和世相、人和人性,都必然是帶著主觀色彩的對現實的再創造。對非虛構來說,再創造不是扭曲捏造,也不是作者需要什么就留下什么,而是以真實為前提的藝術表達。說到底,虛構也好,非虛構也好,不管什么姿態,終極目的不都是為了抵達真實,抵達更深刻及被遮蔽的真實嗎?虛構和非虛構也面臨著同樣的挑戰:如何抵抗時間。這方面,非虛構可能風險更高,寫作不可能回避現實,非虛構尤其長于擁抱“熱點”,時過境遷,易于過時,這就對寫作的藝術和思想的穿透力提出更高的要求。
陳勁松:你說的沒錯,較之虛構,非虛構關注更多的可能是“此時的事物”,能否經得起時間長河的淘洗,作家們對此應有所考量。一般而言,作家創作經驗的獲取不外乎兩條途徑:閱歷和閱讀。其中,閱讀的作用尤為重要。因閱讀其他作家作品而在自身創作時深受影響的例子不勝枚舉,譬如契訶夫之于魯迅、勞倫斯之于張愛玲、奧威爾之于王小波、馬爾克斯之于莫言、川端康成之于余華、博爾赫斯之于格非、卡佛之于蘇童、卡夫卡之于殘雪……影響的結果,大多體現在作家的創作觀上。你也說過:“一個小說作者的文學觀,隱含在寫作里,也體現在閱讀上。”那么,你有著怎樣的閱讀旨趣?古今中外哪些作家作品給你的創作帶來了不可磨滅的影響?
蔡東:我在閱讀方面是雜食者,讀經典,也讀新書,讀笨重型的作家,也讀輕盈型的作家。但不喜歡故弄玄虛的小說,把寫作變成雜耍和游戲,還自以為有創意、很實驗。舉個例子,讀《幾乎沒有記憶》這樣的小說,既感受不到作者的誠懇,也感受不到作者的才華。
陳勁松:莉迪亞·戴維斯的《幾乎沒有記憶》嗎?我沒有讀過,無法評價。但我想,每一個真正有抱負的作家,都應努力成為讀者和批評家心中的好作家。然而,究竟什么樣的作家才算好作家?在批評家謝有順看來:“如果一個作家缺乏深刻的憤怒和敏銳的同情,那他的寫作就很容易為工具理性所劫持,缺失那種足以看清罪惡、喚醒美善的忠直力量。在此之外,他還要有對敘事探索的不懈熱情,對藝術語言的不斷打磨,對個體命運的持續關注,對內心世界、生存困惑的執著追問,唯其如此,寫作才能根植現實而超越現實,并在學習經典的同時也創造出自己的藝術世界,進而為寫作加冕。”。這實際體現的是一個作家對于真善美的追求。作家龍應臺更是從三個不同層次將作家分成三種:壞的作家暴露自己的愚昧;好的作家使你看見愚昧;偉大的作家使你看見愚昧的同時,認出自己的原型,而涌出最深刻的悲憫。讀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巴爾扎克、卡夫卡、曹雪芹、魯迅等偉大作家的作品后,我對龍應臺的上述觀點感同身受。當然,關于壞作家、好作家和偉大作家的評判標準或許還有很多,正所謂“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部《哈姆雷特》”。那么,你認同龍應臺關于作家的三分法嗎?對于她心中三個層次的作家,分別有何相近或不同理解?
蔡東:龍應臺的三分法主要從認知“愚昧”的角度來談,有特定的語境。我認同謝老師“喚醒美善”的說法,我心目中的好作家,勇敢又一派天真,不憚于書寫人間的苦厄、丑陋、殘酷,同時又有勇氣建構,以寫作捍衛一個更好世界的可能性。
陳勁松:的確,在書寫黑暗和苦難的同時,不忘光明與救贖,這誠然是一個好作家的固有情懷。在我有限的閱讀視野中,發現存在這樣一種現象:不少作家寫到一定時候,有意無意陷入了自我重復的怪圈,包括寫作風格、人物形象、故事情節等,我總會在他們后面的作品中找到前期作品的影子,這似乎也可視為作家的“中年危機”之一。對此,你怎么看?你目前的寫作是否有遇到上述窘況?一個優秀乃至偉大作家,如何才能突破此類瓶頸,超越自我,創作出經典作品?
蔡東:寫作歷程中有自我重復,也有對重復的突破。幾乎每個寫作階段都有瓶頸,這伴隨著寫作本身。我覺得一直寫,不斷自省,就會慢慢提升和改變。沒有一勞永逸,萬事萬物都在變化,寫作也是如此。
二、深圳文學及城市寫作:天才的發現和表達從來都是稀有的
陳勁松:《特區文學》將我們對談的這個欄目命名為“大灣區文學地理”,比較前瞻,富有遠見。從你個人的創作和閱讀中,我們也不難看到深圳這座城市對你的影響。接下來,我們不妨將話題轉到深圳文學及城市寫作這個方向吧。2020年適逢深圳經濟特區成立40周年。從40年前的邊陲小鎮到今天的國際化大都市,深圳的發展成就有目共睹。“來了就是深圳人”這是深圳近年廣為流傳的開放標語。你南下深圳并生活于此快15年了,按理說早應與這座城市融為一體,但你在2016年接受中國作家網采訪時提到,“來深圳的前幾年,感覺自己和這個地方互為異物”“在小說里,深圳是一個讓我們的內心風聲鶴唳的地方”。你感覺是什么原因導致“自己和這個地方互為異物”?這種“風聲鶴唳”的感覺至今有什么變化嗎?
蔡東:定居南方后,我并不適應這里的氣候和生活節奏,經常想家,也一度回避書寫當下經驗,仍以家鄉的人、事、情感、記憶為寫作之源。近年間我意識到,不管內心是否抗拒,情感是否疏離,畢竟已進入到全新的生活中。門在某一刻開啟了,深圳孕育著最富現代性的城市文學形態,它可以成為情感和想象的載體。我既是生活者也是寫作者,無論生活還是寫作,都需要投入地感受、體驗正在發生的一切。我嘗試書寫與居住地有關的小說,一些具有南方氣息的作品。
陳勁松:可能北上廣深的不少作家都有著和你一樣的心路歷程吧。伴隨著改革開放40年的宏闊歷程,深圳文學也取得了長足發展,先后誕生了“移民文學”“打工文學”“新都市文學”“青春文學”“新城市文學”等多種文學思潮,代表性作家作品更是相繼涌現。對此,批評家李敬澤曾指出,“放在全國范圍去看,深圳這個群體的實力相當突出……‘深圳青年作家群’確實改變了我們的文學地圖。”批評家謝有順亦認為,深圳青年作家群的寫作實績“即便放在全國的視野里來觀察和定位,也是有競爭力和影響力的。”兩位批評家對深圳文學的看法不謀而合。你平時關注其他深圳作家的創作嗎?你眼中的深圳文學是何種樣貌?當前處于怎樣的發展態勢?
蔡東:問題有點大。說說我的觀察,十幾年前剛來深圳時認識或知道的作者,大部分人仍在寫,工作之余寫,生活的間隙寫,作品紅不紅都在寫。在一個充滿世俗焦慮的大城市里,還有一小撮人為寫作焦慮,這里面孕育著文學的可能。
陳勁松:“還有一小撮人為寫作焦慮”,用時下流行的話說,這才是真愛啊!不知你有沒有注意到,深圳近年一直在傾力打造“文學之城”。談到一座城市的文學,我們常常會從文學生態、文學思潮、文學精神等方面予以觀察。我以為,真正重視文學的城市,除了營造良好的文學生態,為作家提供更好的創作環境,同時要形成頗有創造性和生命力的文學思潮,還要塑造和城市相得益彰的文學精神。豐富的文學生態、引領時代的文學思潮、令人耳目一新的文學精神,無疑更能體現一座城市的文學格局。三者之間,文學精神尤具標桿性價值,蓋因文學精神乃文學之靈魂。那么,深圳的文學精神是什么?有人說敢為天下先,也有人說兼收并蓄,你認為呢?
蔡東:“敢為天下先”是深圳城市發展歷程中重要的精神價值,說到文學精神,似乎還需要沉淀和成形,或者可以說,年輕、不穩定、難以概括也是深圳文學精神的棱面。最棒的是,大家生活在深圳,但大家寫的小說都不一樣。
陳勁松:就如那首歌所唱的:“我們不一樣,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境遇。”當然,由于觀察視角有別,咱倆關注的層面稍微有些差異,但有一點可能所見略同,那就是,看到深圳文學這些年取得一定成就的同時,我們還必須正視其可能存在的某些缺失。譬如,和北京、上海、廣州、西安、武漢、南京(中國首個世界“文學之都”)等文學傳統深厚的城市相比,深圳文學根基尚淺,整體較弱,尤其在全國視域下匱乏有影響力的大家名篇。有論者甚至指出,深圳文學成就和這座城市的經濟發展成就嚴重不匹配,至今沒有產生反映改革開放波瀾壯闊景象的史詩性作品,更遑論具有文學史意義的傳世之作。對于上述問題,我也有過一些粗疏的思考和建議(詳見拙文《在傳承中尋求嬗變—新都市文學的歷史、現狀與前瞻》《深圳文學的當下處境與前景》《當我們談論新城市文學時我們在談論什么?》等),綜而觀之,深圳文學的羽翼確實還不夠豐滿,但也不必妄自菲薄,若真是大鵬,終有一日同風起,扶搖直上九萬里。不知你如何看待這些問題?隨著深圳城市化的進一步發展,你覺得深圳文學將會面臨哪些新的問題?身處其中的作家們又該如何應對?
蔡東:不好一概論之。其實鄧一光已經提供了一系列城市小說文本,跟《都柏林人》放在一起,毫不遜色。不能一說經典就崇古和媚外,經典為什么不能誕生在此時此地呢?
目前面臨的問題,仍然是寫作者感覺的鈍化,對真實生活的麻木,面對復雜的現實和快速的變化,茫然迷惑,喪失了察覺能力,符號化的寫作居多。這也正常,天才的發現和表達從來都是稀有的。
陳勁松:是的,對此我們要有耐心。從早期的《嘿,天堂》到后來的《凈塵山》《通天橋》《出入》,再到近期的《來訪者》《照夜白》《朋霍費爾從五樓縱身一躍》,你的小說創作多以深圳為故事背景,且深受好評,譬如,作家魯敏就認為你是深圳城市文學的代表性作家。就你這么多年的創作實踐來看,你如何看待作家與城市之間的關系?或者說,你怎樣評價自己關于深圳的小說創作?
蔡東:深圳是居住地,是工作和生活的地方。這么多年了,居住地總會對寫作有所觸發。《凈塵山》《通天橋》《出入》《照夜白》等小說寫出了深圳的某種特質,或者說,“深圳”也相當于小說里的一個重要人物,抽掉這個人物,小說可能就不存在了。在另外一些作品里,深圳雖然出現了,但只是一個單純的地名,換成其他城市名字也未嘗不可。
陳勁松:這也許是你慢慢融入這座城市后的一種收獲吧。縱觀古今,一時代有一時代之青年,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2020年5月底,中國作家協會青年工作委員會聯合《南方文壇》,以“新時代青年寫作的可能性”為主題召開青年作家批評家研討會。我比較喜歡這種“一切皆有可能”的敞開性話題,這個時代的青年(時髦的稱呼謂之“后浪”)及其寫作,和前輩們的寫作早已有著天壤之別,因為“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東西都被褻瀆了,人們終于不得不冷靜地直面他們生活的真實狀況和他們的相互關系”。現代性不僅深刻影響了“后浪”們的生活和相互關系,而且極大改變了當下文學的生產和傳播途徑,以及“后浪”們對于文學傳統的認知、接納與承繼方式。不過,在青年批評家李壯看來,“相比于中國現當代文學歷史上曾有的時代,今天的青年寫作者,似乎處在一種較為罕見的、與時代現狀充分融洽的相處狀態里”。作為青年寫作者中的一員,你如何理解李壯的這一判斷?進而言之,我們如何理性、客觀地思考青年寫作尤其是深圳青年作家的困境與未來?
蔡東:傳播和接受方式當然不一樣了,可以說發生了深層次的改變。但對我來說,困境仍然是文學本身的,也很具體,那就是怎么把一篇篇小說寫出來,把觸動自己的東西傳達好,找到有意味的表現形式,盡可能讓小說的生命力長久一些。
三、粵港澳大灣區文學現狀和未來:海洋氣息與開放性
陳勁松:從個人到深圳再到大灣區,這不僅意味著觀察視角的變化,更意味著思考的深入和升華。隨著粵港澳大灣區以國家戰略的高度提出來,“粵港澳大灣區文學”作為一個整體概念開始浮出歷史地表。2017年12月21日,第一屆粵港澳大灣區文學發展峰會在深圳舉行,首次提出“粵港澳大灣區文學”這一概念,并從粵港歷史、港澳經驗、深港個案等角度對粵港澳大灣區文學的歷史與現狀、共性與個性深入論述。你在創作之余是否關注“粵港澳大灣區文學”?和深圳之外的其他灣區城市作家有過交流或互動嗎?就當下粵港澳文學發展現狀來看,你認為這一提法是否存在概念先行的問題?能否成立?如果成立,依據是什么?是否可視為新時代出現的中國當代文學的一個新品種?和過去的移民文學、打工文學有何異同?
蔡東:對文化戰略和文藝批評來說,概念先行不是問題。對小說創作來說,概念不重要,概念既不是寫作的障礙,也不是寫作的靈丹妙藥。
陳勁松:你的回答言簡意賅中透著一種哲思啊。事實上,“粵港澳大灣區文學”這一概念提出三年來,粵港澳三地紛紛舉辦各類文學活動,以期從實質上推動大灣區文學融合發展,譬如,召開“粵港澳大灣區文學發展峰會”“粵港澳大灣區文學筆會”,啟動“粵港澳大灣區文學工作坊”“粵港澳大灣區文學周”,成立“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聯盟”,出版“粵港澳大灣區文學叢書”等,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人們對于大灣區文學的關注和討論。但不置可否的是,“粵港澳大灣區文學”這一概念從內涵到外延至今尚未形成共識。通行的觀點有兩種:有些人認為,唯有粵港澳地區作者書寫的作品,才能納入“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范疇;另一些人則認為,只要是描寫粵港澳大灣區人和事的作品,都應視作“粵港澳大灣區文學”。你認為“粵港澳大灣區文學”最核心的特質和要素是什么?如果可以,你能否結合自身經驗對其進行界定或下一個相對確切的定義?
蔡東:我傾向于認為,描寫粵港澳大灣區人事的作品,可視作“粵港澳大灣區文學”。我喜歡的美劇《億萬》,片頭是灣區的場景,很現代的美,高度的城市化,灣區大概是人類城市建設最杰出的樣本和形態了。《億萬》是金融題材的劇集,最初因為戴米恩·路易斯才追這部劇,后來被劇情的節奏和張力所吸引。而灣區文學的特質,也許就是海洋氣息和開放性吧,人們在此聚集離散,自然也延伸了文學書寫的空間。
陳勁松:延伸書寫空間這一點很重要,也很有意思。2018年舉行的“第二屆粵港澳大灣區文學發展峰會”,一致通過了《粵港澳大灣區文學合作發展倡議書》,除了倡導建立粵港澳三地十一城市文學合作長效機制、加強文學交流互動、共建城市文學活動載體、互通文學作品發表渠道、完善文學交流平臺、推進文學聯動,構建粵港澳三地文學界交流合作新格局,倡議書還特別提出要“培育清新剛健、多元蓬勃的大灣區文學生態,形成粵港澳大灣區文學共同體,使之成為華語文學走向世界、走向未來的重要樞紐”。從“粵港澳大灣區文學”到“粵港澳大灣區文學共同體”,這或許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人文灣區的重要途徑之一。你認為是否存在這種“文學共同體”?或者說,你認為建設這樣一種“文學共同體”是否可行?如果可行,你能否從一個作家角度提出相關建議?
蔡東:寫作說到底是個性化和創造性的勞動,但命名和交流自有其意義。
陳勁松:說的是,作家和批評家考慮的畢竟各有側重。在批評家謝有順看來,“粵港澳大灣區文學”概念的提出,提供了一個前瞻性的視角,去思考“現在”和“未來”。而從文學的角度來說,大灣區開創了藝術、審美和想象的空間,將會提供更多書寫主題。記得你在創作手記《寫作:天空之上的另一個天空》中提到,你的故事大都關乎女性,在關于《我想要的一天》創作手記《在全世界找到一張桌子》中進一步指出:“我關注的,不是一時一地的具體的困境,而是日常生活的悖論和近乎無解的精神格局。”“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視域下,你未來的寫作有何規劃?是否考慮過其它主題?變與不變之間,你內心是否有一種始終堅守的小說精神?
蔡東:考慮過其他主題,比如多走出去看一看,多了解更年輕的人是怎么活著的,希望能駕馭更多樣的題材。說到堅守的小說精神,似乎有悲壯感,其實也就是自己對寫小說的態度吧,不粗制濫造,每一篇都細細打磨,品質好一點吧。
訪談的尾聲,我想謝謝勁松兄,你為訪談下了大工夫。聊的過程中一些問題想得更清楚了,很受益。
陳勁松:也謝謝你接受我的訪談,和你交流非常愉快,也讓我深受啟發。期待你寫出更多好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