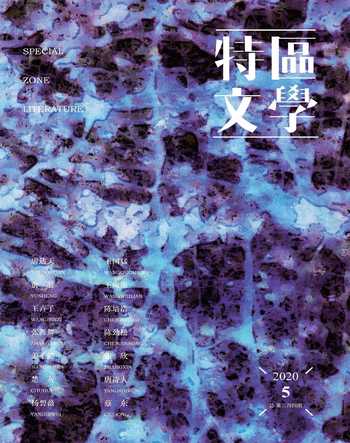現實的真相,及其詩意的翻轉
夏漢
相對論
孫文波
巨大反差:陽光下黑暗的話題,
把我們引向心靈的最深處。在那里,
有一些東西是不能觸動的—分離,
或者死亡,總是把我們朝絕望的方向推,
為了應付它,需要我們徹底懂得虛無。
但是誰又能真正懂得。因此,我更愿意談論
生活的表象。譬如今天,我愿意談論
戶外的陽光,明晃晃的光線下,
人們在矮樹叢曬花花綠綠的衣裳。你看一下
這樣的景象吧!我總是從中感受生活,
它們從來不哲學不神秘,不把人引向想象的黑暗中。
也許我可以因此告訴你:生活,是一次次洗滌,
在絕望時洗盡絕望;在沮喪時洗盡沮喪。
它使我哪怕冬日午后沿著河岸散步,
不論走在青石砌的小徑,還是踏入枯黃草坪,
都在努力地尋找讓心里輕松的感覺;
看見河水清亮非常享受,看見不知名的雀鳥
從樹叢中飛起,也能從心底涌出喜悅。
或許,你會說這些仍然無法留住我們的生命,
死亡終將到來—死亡!我不否認它。
但我希望,活著時,享受活著的樂趣
—我知道死亡絕對,我們不過相對地活。
我與山相對,與水相對,與鳥相對
在相對中,用相對的喜悅,反對絕對。
按照波德萊爾的觀點,一切好的詩人都是現實主義的—盡管在某種境況下,僅僅只是一種在否定敘事中再現文化和審美與之對立的社會現實的激情(參見高名潞《波德萊爾的現代性與浪漫主義思想》,王志亮譯);而從詩的發生學的角度,詩又是無中生有的。那么,怎樣在二者之間尋找一種平衡,的確成為一個問題。以此觀察孫文波近期的寫作,正好是一個入口—就是說,從內容看,其寫作取向一直都在現實的維度上,而且是那樣地投入與真誠,不妨說他在寫作中杜絕了虛假與造作。而同時,他的每一首詩卻又是在對于詞語的辨認中趨于完成—或許詩人深信“那種真實的詞即是這樣的事物”(伽達默爾)的詩訓。
當然,一個時期以來,文波面對社會現實的態度幾乎是悲觀的,這在某種程度上應該歸于時代的“饋贈”,但他可以把這種持久的感覺融入詩里,“加入到他的詞語方陣之中,開始抵抗”(希尼)。同時,在持續閱讀中,能夠感覺出來,詩人盡管對于政治是在意的,但卻在寫作中有意疏遠或淡化,或者說不屑于把政治牽扯進來,而這種轉化顯然給他的詩帶來了新的樣態。故而,他的詩在很多情況下都是靠剔除了某些觀念后的真實生活細節來推動,總是以情緒隱蔽起來之后的平靜語調進入詩的鋪述。比如在《偶像的作用》里,通過對于某些細節的尋找、忽略與排除,陷入復雜的沉思,直到“重新回到我們的現實”,但那已經不是之前所經歷的,“我們需要小心地,就像繞過路上的水洼一樣”繞過,從而在與現實的疏離中“重新定義自己”。詩人還會在“學校、車輛、疫情。/瓜果、蔬菜、飲料、酒水”的細節鋪述里,“變化著組成詩句”,而且做出 “某一次災難也到來”(《每一天,都有新》)的預言性判斷。
緣于對于現實的詩學認同,我在文波的幾乎每一首詩里總能看見其獨異的身影—或許這也是作為一個見證者的預設。詩人可以在讀書之際有所感:“我讀過后,很感興趣”(《讀<高適集>作》);可以沉醉于某種風景:“這讓我一個早晨全用在/盯著那棵樹看了”(《眼前有景》);自然也可以對于自己生活的有所覺察:“每一天,都有新的事情發生。譬如說/今天,從痛疼中醒來。仿佛從地獄中返回”(《每一天,都有新》)在這樣的“有我”之境里,其實也意味著一種詩人的自覺,同時也構成了策蘭意義上的對于一首詩的“自我忘卻”的反證。
著力于現實,必然含括人物,所以,當看到詩里關涉人的事由,就有幾分親切—況且那是一種游離于小說虛構的懇切。比如在《讀<高適集>作》里,“有一件事,/人們一直詬病于你,朋友落難,有求于你,/你卻沒有幫他。而你的朋友大名鼎鼎。/因為你沒有幫他,差一點死于非命”無疑,這是對于高適的傳記性表達。隨后的“官場云詭風譎,/每一步必須走得如履薄冰。你必須格外/小心謹慎”則予以寬厚地理解,不啻說,這是作為詩人間的惺惺相惜,是穿越久遠歷史的獨屬于詩人間偉大的體諒。同時,如此的表達還在“應和之作”中呈現的友誼和“詩壇佳話”的體例之中呈現出了某種寫作的駁雜與復合—這才是文波作為一位現代詩人的藝術僭越。
作為詩歌,似乎人們的基本期待首先就是審美的想象,在文波看似粗糲、樸拙而并非唯美的文字里—這恰恰是其審美性選擇—自然不缺乏想象力,在《眼前有景》里,詩人如此寫到:
學校操場邊的鳳凰樹開出了
殷紅的花,遠遠望去,猶如一灘血。
懸掛在空中的血。
接下來,詩人聯想到曾經的年代,武斗中脖頸涌出的血,在農村過年時豬羊身上噴出的血,這種恐怖的景象顯然跟死亡關聯起來。而“花朵是植物的血”與“火山噴發出的紅色熔液,/是不是可以稱之為大地的血”的詰問則引向生存的深入,從而“世界上我不清楚的事太多了”的感嘆才顯得有力而自然。有時候,詩人甚至可以將想象逼近夢幻之中:“從天空中下墜,穿過云霧的迷陣。被閃電擊中/左胸三次,或許更多,摔倒在石頭堆中,/還沒有爬起,一群豹子、鬣狗、野豬圍了上來。”這時候,詩人已經在日神的護佑之下窺見了詩的“美麗光輝的尊嚴”(尼采)。
文波的詩里有著一個頗為穩定的文體特征,那就是其思辨性,在近期寫作里,這種思辨色彩愈加濃重。這是一種成熟的寫作所擁有的知性與詩性智慧,能夠體現出詩的力量與“隨時間而來的真理”(葉芝)。在《春風不度》里:
自從艾略特寫下“四月是一個殘酷的月份。”
盛開的意識便凌亂的盤繞在人們疑惑的頭腦里。
就像此刻,一只鷹從我的眼前飛過,它已經不再是鷹,
而是一只恐怖。帶著巨大的不祥。
顯然,文波從艾略特這句詩里截取了“殘酷”的蘊涵,而用于描述親臨的生活感受—這是那個時間里很多人的共同感受,恐怖與死亡隨時會降臨到頭上。而不同的是詩人通過聯想與想象強化了這個感受,最終轉化成一個審美的詩性表達:“我分明看到天空裂開了口,/傾刻之間,會有什么墜落?一口鍋,或者是/籠罩我們的謊言。都不是……而是,末日的景象。”而一首《瘟疫思》通篇都沉入思辨之中,“看不透空氣。懷疑主義開始流行。那些明亮/都是假象,那些清新隱藏著致命的殺機”“人的確是人的敵人”,在作出“一切都在必然中”之后,依舊讓思辨慣性般地潛行,從而跌入“另一個幻想”的虛無。在《短是長的收縮……》這首詩里,詩人的思辨則始于一種語義上的虛無裂變和“詞成為詞的衍生物”的游戲,而最終在揭示語言秘密的途中,達至詞與物意義上的詩意翻轉與生命的指向。
在對于文波寫作的觀察與反思中,始終有一個直覺:他在開始寫作的某一刻,或許并沒有一個明確的表達,尤其沒有一個現實的清晰概念,或只有一個詩的萌芽促動著他?這樣,反應在他的詩的語調里就有著某種猶疑和不確定性,盡管他的敘述是肯定的,“每一個詞都落到實處”(啞石語),可以說,他幾乎沒有對詩的最終生成抱有先在的預設。他只是從一個原點—生活中的或語言的—開始,悠然地寫下去,或跟著潛意識,或跟著想象,有時候就是跟著某個詞語的連綴—就這樣寫下去,直到最后,他似乎意識到了詩已經出來,才順其自然地罷手。但這種生成是有其內在的合理性,記得艾略特在《詩的三種聲音》里,談到貝恩關于“不對任何人說話”的詩的作者從哪里著手寫作的問題,大意是:首先是有一個不活潑的胚芽或者“創造的萌芽”,另外就是擁有語言。有某種東西正在他心中萌發,他必須為它找到詞句;但在他找到他需要的詞句之前,他無法知道他需要的是什么樣的詞句:在他把這個胚芽轉換成正確的詞句以前,他無法確定這個胚芽是什么。當找到這些詞句后,那個不得不為之尋找詞句的“東西”卻消失了,代替它的是一首詩。文波的《鯨落》這首詩,或許就是如此產生的。首先出現了一個鯨魚的形象?或一個詞語:大海王,然后,詩人展開想象性捕捉;
龐大的縱橫家。油脂的產出者。
一生在逃避人類追捕。有時候撲向沙灘找死。
接著,描述噴出的水柱,被太陽染成霓虹;其啼鳴,像夜半歌聲在空曠的大海間“猶如海妖被喚醒。足以讓聞者心驚”;繼而論及鯨魚之死,“亦帶有神圣的純美的意味。垂直的下落,緩慢而莊重。/向著黑暗深處(絕對驕傲的過程……)/一點點滑向徹底的虛無”,最終演化為對于死亡的禮贊—詩篇完成得漂亮而凝重。
在孫文波近期的寫作里,能夠確定一個詩學判斷,便是他的一個明確指向—個體與世界的關聯,這一點構成他寫作的一個意涵顯在,我們也就在他的文本里始終領略到這一點,而他的每首詩又反應了不同的側面,這種持恒成為其寫作的德性,也為其寫作確立了最終的意義,或者說詩人“仰仗自己的機智”(奧登語)完成了作為當代詩人的使命。概言之,孫文波在貌似散亂卻是自如、自洽的寫作中,針對生存及其時代現實的并非樂觀的描述里,顯現著詩的真意或真相,或許從這里可以看得出詩人信奉著曼德爾施塔姆的觀念:“存在是藝術家最大的驕傲。除了存在他不渴望別的天堂”,“因為他知道藝術的現實更無限地令人信服”而“在詩歌中這現實恰恰正是詞語”(楊青 譯)。這也是作為一個詩人的當代寫作的全部詩學價值。
(欄目責編:朱鐵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