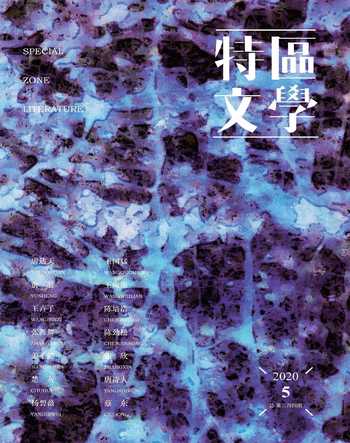潔凈的詩寫者或孤獨的“他者”
納蘭
姚輝在《詩意之外的斷想》中如是說:“一個潔凈的詩寫者可以成為某種獨立的‘他者’。”從他的這本以《另外的人》命名的詩集,也能管窺出他作為一個獨立的“他者”的觀念和用心。他不僅是一個潔凈的詩寫者,同時也是一個獨立的“他者”,潔凈和獨立既是他的人格特質,也是詩歌特質。借用伯恩斯坦的說法:“我從不認為我用的詞語表現一個既定的世界;我用每一個詞去創新作品。詩歌既是錯覺也是啟示的產品,既是幻想也是現實。”姚輝的詩歌也有這樣的錯覺幻想和啟示現實的功效,他不是表現既定的世界,而是描述一個動態的變化著的世界和動態的心靈世界。除此之外,姚輝還處理另外的人和另外的時代的關系,如果這個時代不甚美好,那處于這個時代的就不是自己,而是一個“他者”;如果這個時代不甚理想,那他就是一個“另外的人”。換言之,在詩歌里他有了輾轉騰挪的時間和空間,他用自己的分身去感受不同的經驗。他對這個時代有深切的感受,他的詩歌里有這個時代的脈搏和自己的心跳,作為一個他者的自我,他已經跑到了時代的盡頭,而這個“時代的盡頭”即另一個時代的前端。
一、潔凈的詩寫者或獨立的“他者”
潔凈的詩寫者,意味著姚輝蚌一樣的生命存在,咀嚼人世的苦難、荷擔現實的重負、承受精神的試煉,體現了他把痛苦轉化為美和含沙孕珠的詩學凈化觀。
每一個詞語都經過了詩人的擦拭和浸潤,因此,每一個詞都是潔凈的。這些由潔凈之詞匯聚成的詩篇,就如蓮葉上的晶瑩泛光的水珠。潔凈的詩寫者,寫出潔凈之詩,實屬必然。“一滴水確立了整部濤聲的流向。”(《開始》)潔凈的詩寫是從“一滴水”開始的,“一滴水”和“整部濤聲”構成了一個單獨者和整體的一致性,“一滴水”不是一種從眾心理,恰恰相反它遵從的是自己的內心。我們從一滴水里感受到一種左右“流向”的意志,一滴水的微小之中潛藏著“濤聲”的啟示性的力量和“殷紅的遼闊”,一滴水也可以照見大海。
馬里奧·J·瓦爾德斯在《詩意的詮釋學》中寫道:“自我的恒久性對每一個人來說都是生活的總和,如是,一個人的他者才能認識并承認作為個體的這個人。”獨立的“他者”,使姚輝獲得了“反觀自照”的他者視角,對我進行審視和省察,“另外的人”對這一個人進行詩意的糾正。“另外的人”對這一個人形成鏡子式的洞見和燈一樣的燭照,“另外的人”成為這一個人的傾訴的對象,“另外的人”消解這一個人的孤獨,“另外的人”增添這一個人抵制虛無的侵蝕的積極力量,自我和他者的雙重身份在對話和理解下,達成詩意的和解。
正如保羅·利科在《解釋的沖突》一書中說:“對于一個存在而言,理解便是想象自己置身于另一生命之中。”姚輝成為了一個作為他者的自我或作為自我的他者的復合體,潔凈的自我理解了獨立的他者,獨立的他者也理解了潔凈的自我。作為一個“他者”,姚輝得以跳出肉身對心靈的約束,得以逃脫社會秩序、自然秩序和心靈秩序對個體的規約和束縛,從而可以從感受力的約束走向想象力的解放。
姚輝在《另外的人》一詩中塑造了一個“他者”,詩中有“隱入蒼翠的石頭”“多變的棱角”等句子,好像是作為自我的他者和作為他者的自我在自我把脈和診治。“他說出那些命定的水勢與憂郁”,從詩中出現的“憂郁”一詞,就判定姚輝是一個有憂郁氣質的詩人,未免有些武斷。但憂郁在詩中出現,焉知不是那把心中之憂“放置”在詩中的舉動呢?況且詩人的“放置”行為還有“他把歧路放置在浪潮中 雨滴漫長”。“另外的人”約等于“詩人”,得出這個結論也很恰當。“將鳥影捏制成雨滴”“他有云的疼痛 或者螢火之遠”等句,非詩人之魔術手不能為也。“他在風的緘默里 寫下我們不變的質詢”,他不僅是有憂郁氣質的詩人,也是一位“從‘無人祈禱’的塵世質詢美學的天空”(耿占春語)的質詢式的詩人。姚輝在《烏鴉》一詩中也寫到:“難以放棄的夢境墜入泥濘/質疑的人 為值得質疑的時辰活著”。
“另外的人”是更為理想化的自我,是一個“閃射光亮”的自我。“他讓那塊無辜的石頭/再次擁有 艱辛的勇氣”,或許,這也就是另外的人存在的意義吧。
二、另外的人和另外的時代
從姚輝的詩中,能看到一個詩人的“憂天下”的情懷。“從脂粉到典籍/從暗疾到酒/一個時代揭開了自己的隱痛”,這是屬于他的“時代之痛”。他曾經身處一個不甚理想的時代,表現出一種兀立的品格,一如他的詩所表明的“而一朵花兀立/鐵鑄的芳香/凜冽如刃”。詩人的所見是“我看見巨石挪動了自己的陰影”,在這里巖石和陰影之間是一種隱喻性的關系,那是詩人的一體兩面,是一個人身上的自我和身上的他者之間的角力。在《猜測》一詩中詩人說:“你好像來自另一個時代。血滴毛羽遍布/你好像與另一種遺忘密切相關/你/好像只能讓無辜的飛翔/不斷重復”,通篇都是“你好像”作為起始,符合“猜測”這個題目。作者雖不太肯定,但已經隱隱約約感受到了“另外的時代”的風了。作者筆下寫出了“血滴”“毛羽”“無辜的飛翔”“隨雨聲蜷曲的某種疼痛”“燃燒的塵土”,而這些經歷并不是白費,因為“苦難帶來啟示”。面對著“那樣的時代”,渴想著“另一個時代”。作為一個“挺住意味著一切”的詩人,他既能夠聞弦歌而知雅意,也能洞悉“淚水中掩映的全部門秘密”。作為“他者”的個人,他既是一個受難者,也是一個施救者。就像他在詩中所寫:“歌者自篝火邊緣歸來/一次歌詠/便是一次牽魂的救贖”,他本身就是那個從篝火邊緣歸來的歌者,他不僅帶回來了“救贖”,也帶回來了“篝火”,“他”便具有了歌者與救贖者的雙重身份。“格格不入的風”,是他與“那樣的時代”的一個錯置和錯位。
在《守護篝火》中,他寫道:“為守護篝火/我已征用了/三種滾燙的身影—”。朗西埃在《詞語的肉身》中寫道:“彼得潛進湖中以求重返救世主門下,而救世主現身在岸上,使徒們發現岸上有一小堆篝火,這篝火既是烤魚的炭火,同時又是降入世界的光。”姚輝守護的火,也就是“降入世界的光”或“篝火成為似是而非的啟示”。他不再是一個普羅米修斯式的盜火者,而是篝火的守護者。他被篝火所啟示,也被它溫暖和照亮。守護篝火不是一種遠觀和守望,而是經歷了近距離地“卷過篝火”,以身體為襁褓以篝火為嬰兒般的裹緊,再到篝火為襁褓而自身成為進入篝火的襁褓的嬰孩—進入篝火“撐起過火焰虛無的往昔”,仿佛他已經過篝火的凈化,成為了浴火重生的鳳凰。篝火不只是“世界的光”,在詩人這里,“篝火在我們銳利的矚望里探出身來”,篝火已經成了人格化的篝火,而守護篝火的人,已經勝過了篝火對他的考驗和試煉。他是篝火懂得者,“我懂得篝火枯落的理由”。
正如《守護篝火》中所言,第一種是“翠綠的身影”,第二種是“像赤紅的眷顧與緘默—這種身影”,第三種是“暗黑的身影”。“三種身影交替出現”,構成了一個多樣性的自我。“三種滾燙的身影”也可以看作是詩人的一種自我分化的能力和非同一性主體意識。阿多諾的非同一性概念是這樣說的:“從同一性中發展而來的非同一性,并不試圖將事物歸于一個統一的起點或參照系,也不追求一個最終的確定的歸一。非同一性重視同一性中的個別性,強調非連續性、自我改寫,意味著主體的自我建構和生成。”耿占春明確地提到“非同一性主體”的問題,“認為純粹認知領域的自我非同一性對敞開封閉已久的集體心智有著重要的作用”。詩的結局是“像三根吱呀燃燒的骨頭/發出 篝火哽咽的回音”,“三個身影”在對篝火的守護中,“我”近乎于完成了自我的構建和生成。生命的意義正如篝火,是一種燃燒與耗盡。“篝火哽咽的回音”,正是“我”完成的自我認知的明證,篝火的回音在某種意義上等同于希尼所說的“黑暗的回聲”。希尼說:“我寫詩,是為了認識自己使黑暗發出回聲。”查爾斯·伯恩斯坦在《回音詩學》中說:“回音詩學是美學的星叢中一個母體反彈到另一個母體所產生的非線性的共振。……它是暗指缺席情況下對暗指的感知。換而言之,我所找尋的回音是一個空白—一個缺席的本源的陰影,一個臨時替代品組成的網”。姚輝的這首《守護篝火》,無形中契合了伯恩斯坦的回音詩學。姚輝的“篝火哽咽的回音”,昭示出“我”與篝火之間的守護,產生了伯恩斯坦所謂的“非線性的共振”,“我”對篝火的守護,已經讓“我”成為了“美學的星叢”中的一顆星。或者也可以這么說,篝火只是一個“缺席的暗指”,它是不存在的,“我”的守護也就是對感知到的暗指的守護。“我”傾聽到的篝火哽咽的回音,只不過是“傾聽到了自己”。在另一首《火焰之舞》中,篝火有了另外的情狀,“篝火在夢境邊喘息”,“骨頭”也有了不一樣的結局,“那堆骨頭 沉默夠了就會吐露霞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