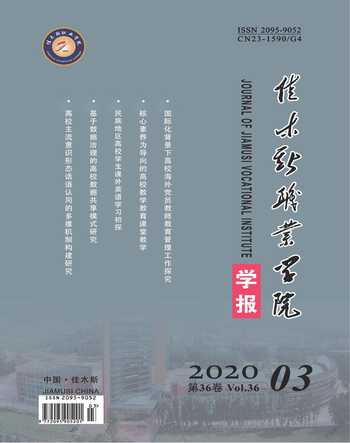略論無(wú)證搜查的最低限度及證明標(biāo)準(zhǔn)
何成兵
摘 要:無(wú)證搜查在刑事偵查實(shí)踐中應(yīng)用極為廣泛,因其略過(guò)了審判這一制約而極易造成權(quán)力失控。正是有基于此,我國(guó)關(guān)于無(wú)證搜查的規(guī)定極其嚴(yán)格,既有時(shí)間限制,又有時(shí)機(jī)限制。立法規(guī)定的過(guò)左與司法實(shí)踐的過(guò)右形成極大背離,無(wú)證搜查的正當(dāng)性基礎(chǔ)需要事先厘定。就正當(dāng)程序的要求而言:無(wú)證搜查既要符合刑事搜查的目的,即設(shè)置最低限度;又要符合刑事訴訟的目的,即設(shè)置證明標(biāo)準(zhǔn)。
關(guān)鍵詞:無(wú)證搜查;正當(dāng)性;最低限度;證明標(biāo)準(zhǔn)
中圖分類號(hào):D918;D915.3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文章編號(hào):2095-9052(2020)03-0289-03
由于刑事搜查集中體現(xiàn)了國(guó)家公權(quán)力與公民私權(quán)利的直接對(duì)抗,世界各國(guó)都對(duì)其運(yùn)行程序進(jìn)行了嚴(yán)格的規(guī)制。其中,在偵查實(shí)踐中,無(wú)論在國(guó)內(nèi)還是國(guó)外,無(wú)證搜查又是搜查中占比最大的常態(tài)。較之有證搜查,無(wú)證搜查略過(guò)了審批這一制約,更易造成權(quán)力失控。與此同時(shí),無(wú)證搜查又是刑事訴訟中越來(lái)越倚重的搜查手段。這種實(shí)踐的亟需與理性上控權(quán)形成天然的緊張關(guān)系。如何化解張力,尋求平衡,與刑事搜查目的相切合,與刑事訴訟目的相一致,是本文探討的邏輯起點(diǎn)。同時(shí),為無(wú)證搜查設(shè)置最低限度及證明標(biāo)準(zhǔn),能夠最大限度實(shí)現(xiàn)搜查權(quán)與公民權(quán)的平衡,實(shí)現(xiàn)程序正義的法治追求。
一、無(wú)證搜查的正當(dāng)性基礎(chǔ)
無(wú)證搜查的條件限制頗為嚴(yán)格:一是時(shí)間限制,必須在執(zhí)行拘留逮捕的時(shí)候;二是時(shí)機(jī)限制,必須在緊急情況下,二者缺一不可。換言之:在非拘留逮捕場(chǎng)合,遇到緊急情況不可以無(wú)證搜查;而拘留逮捕場(chǎng)合,非緊急情況亦不能無(wú)證搜查。這實(shí)際大大壓縮了無(wú)證搜查的空間,對(duì)于拘留逮捕時(shí)非緊急情況下和緊急情況下非拘留逮捕等情形都無(wú)法展開(kāi)及時(shí)搜查,不僅會(huì)隨時(shí)帶來(lái)風(fēng)險(xiǎn),等到時(shí)過(guò)境遷,即使申請(qǐng)到搜查證再行搜查,很多物證都將湮滅,反而貽誤了偵查犯罪的最佳時(shí)機(jī)。這種擔(dān)憂體現(xiàn)在實(shí)踐中,偵查人員常常會(huì)繞開(kāi)法律規(guī)定,利用慣用做法搜集物證等線索,來(lái)保障刑事訴訟的順利開(kāi)展。但這又將對(duì)被搜查人的人權(quán)保障帶來(lái)風(fēng)險(xiǎn)。立法目的的過(guò)左與司法實(shí)踐的過(guò)右形成極大背離,無(wú)證搜查的正當(dāng)性基礎(chǔ)需要事先厘定。
(一)無(wú)證搜查須符合刑事搜查的目的,設(shè)置最低限度
無(wú)證搜查也好,有證搜查也罷,最終這一偵查手段的目的是為了搜索與犯罪有關(guān)的人或物,從而追究犯罪,懲罰罪惡。因此,立法在預(yù)設(shè)無(wú)證搜查權(quán)時(shí),就應(yīng)當(dāng)在考量有證搜查已經(jīng)對(duì)搜查權(quán)制約的基礎(chǔ)上,適當(dāng)傾斜于搜查本身的目的,即盡可能為偵查提供有效的合法手段,同時(shí)為實(shí)踐中偵查權(quán)的擴(kuò)張預(yù)留緩沖,使之既不至于淪為任意搜查,也不會(huì)為偵查實(shí)踐提供過(guò)高壁壘。因此,界定合理的適用范圍是實(shí)現(xiàn)無(wú)證搜查正當(dāng)性的首要基礎(chǔ)。對(duì)此,鑒于有證搜查已經(jīng)涵攝了一部分的搜查手段,并對(duì)之進(jìn)行了較為嚴(yán)密的程序規(guī)制,形成了較為完整的能夠自洽的閉環(huán),無(wú)證搜查則相應(yīng)的可以設(shè)置成開(kāi)放式適用模式,即設(shè)置最低限度來(lái)保障不至于過(guò)分侵?jǐn)_人權(quán)。
(二)無(wú)證搜查須符合刑事訴訟的目的,設(shè)置證明標(biāo)準(zhǔn)
立法之最初目的,毫無(wú)疑問(wèn)是把懲罰犯罪擺在第一位的,把保障人權(quán)同樣視為刑事訴訟的目的,體現(xiàn)了追究犯罪過(guò)程中對(duì)人權(quán)價(jià)值的考量抑或妥協(xié)。事實(shí)上,刑事訴訟中,追究犯罪和保障人權(quán)是一對(duì)天敵,存在此消彼長(zhǎng)的關(guān)系。意大利法學(xué)家貝卡利亞在《犯罪與刑罰》一書(shū)中指出,在法官判決之前,只要還不能斷定他已經(jīng)侵犯了給予他公共保護(hù)的契約,社會(huì)就不能取消對(duì)他的公共保護(hù),如果犯罪是不肯定的,就不應(yīng)折磨一個(gè)無(wú)辜者[1]。這種無(wú)罪推定的思想反映到刑事偵查中,即是要把嫌疑人去犯罪化,偵查機(jī)關(guān)在依法行使偵查權(quán)時(shí)應(yīng)當(dāng)對(duì)嫌疑人的權(quán)利予以充分關(guān)注和尊重,尤其是基本權(quán)利,這不僅僅是道義要求,更是職責(zé)所在。無(wú)證搜查的隨意化實(shí)踐恰恰沖擊了公民基本權(quán)益,與刑事訴訟目的相悖,與刑事訴訟尊重和保障人權(quán)原則相悖,有必要在無(wú)證搜查設(shè)置中通過(guò)證明標(biāo)準(zhǔn)約束搜查權(quán)的恣意。
二、無(wú)證搜查的最低限度
如前所述,我國(guó)無(wú)證搜查的適用需要在執(zhí)行拘留、逮捕時(shí)且遇到緊急情況,這兩個(gè)條件都符合的情形下才能進(jìn)行。這在理論上大大限縮了無(wú)證搜查的范圍,而實(shí)務(wù)中又大大突破了立法規(guī)定,無(wú)證搜查被無(wú)序?yàn)E用。據(jù)筆者調(diào)研發(fā)現(xiàn),實(shí)踐中在執(zhí)行拘留逮捕時(shí)幾乎都會(huì)伴隨著無(wú)證搜查,無(wú)論是否有緊急情況,不執(zhí)行拘留、逮捕但情況緊急時(shí),往往卻無(wú)法搜查。同時(shí),起贓這一廣泛運(yùn)用的偵查手段實(shí)質(zhì)就是無(wú)證搜查,但卻沒(méi)有法律依據(jù)。總體而言,現(xiàn)有無(wú)證搜查制度立法過(guò)嚴(yán)、實(shí)踐過(guò)寬,解決這一難題需在搜查程序正當(dāng)性基礎(chǔ)上,確定無(wú)證搜查的最低限度,并據(jù)此設(shè)置無(wú)證搜查的啟動(dòng)要件。隨著法治現(xiàn)代化的深入推進(jìn),一些主流的刑事訴訟理念和制度也漸漸趨于一致。其中,有關(guān)無(wú)證搜查的制度設(shè)計(jì),大都秉承了程序正當(dāng)原則。
(一)得到被搜查人同意
在沒(méi)有司法令狀或緊急情況下,原則上國(guó)家權(quán)力不能貿(mào)然侵犯公民權(quán)利,除非得到公民同意。例如:法國(guó)法律規(guī)定,在初步偵查中,搜查人身或住所時(shí)必須經(jīng)過(guò)被搜查人同意才能進(jìn)行;德國(guó)法律規(guī)定,在執(zhí)行留置時(shí),經(jīng)過(guò)搜查相對(duì)人同意可以搜查人身及隨身物品。
在我國(guó),常常用到的一種偵查手段叫起贓。這是實(shí)踐中的慣用做法和稱謂,指通過(guò)訊問(wèn),在相對(duì)人交代了相關(guān)物證線索(通常是贓款、贓物、作案工具等)后,將其帶到有關(guān)地方起獲相關(guān)物品的偵查手段。其實(shí),在犯罪嫌疑人交代有關(guān)線索之后,大都符合了有證搜查的條件。但偵查人員往往不愿意通過(guò)審批獲取搜查證進(jìn)行搜查,因?yàn)檫@樣更耗時(shí)耗力,且有可能沒(méi)有收獲甚至要承擔(dān)一定的風(fēng)險(xiǎn)或責(zé)任。相較之下,起贓是更優(yōu)方案。如果起獲證據(jù),則直接扣押,繞開(kāi)搜查程序;如果沒(méi)起獲證據(jù),則無(wú)其他法律手續(xù)和風(fēng)險(xiǎn)。起贓不需要辦理搜查手續(xù),只需要嫌疑人的確認(rèn)和陪同前往即可進(jìn)行,換言之,需要嫌疑人相當(dāng)程度的配合,而非純粹的強(qiáng)制性偵查措施。因此,其既具有一定的現(xiàn)實(shí)必要性(合理根據(jù)),也具有實(shí)質(zhì)上的正當(dāng)性(犯罪嫌疑人同意)[2],是一種實(shí)質(zhì)上的同意搜查。
從司法政策上講,同意搜查措施本來(lái)就是一種把本應(yīng)對(duì)公權(quán)力的約束轉(zhuǎn)嫁給了公民進(jìn)行私權(quán)處分。而這種處分又涉及到公民的基本人權(quán):隱私權(quán)、住宅權(quán)等。故而,考量同意是否自愿,應(yīng)該是同時(shí)搜查的關(guān)鍵性要件,也是無(wú)證搜查合法與否的重要判斷標(biāo)準(zhǔn)。
(二)存在合理根據(jù)
無(wú)證搜查原本就缺少了審批制約,故其實(shí)施必須有合理根據(jù),且這種合理根據(jù)應(yīng)當(dāng)以足以影響到警察安全或刑事訴訟的正常開(kāi)展。比如懷疑其身邊或住處有兇器或其他證據(jù)、作案工具等。在美國(guó),無(wú)論是聯(lián)邦還是各州,都將嫌疑人可能持有武器且具有危險(xiǎn)性作為無(wú)證搜查的合理根據(jù)。大陸法系國(guó)家中德國(guó)、意大利、日本等國(guó)都有合理根據(jù)的規(guī)定。
(三)情況緊急
情況緊急主要是指在來(lái)不及申請(qǐng)搜查證而不搜查又將導(dǎo)致證據(jù)滅失或造成其他危害的情形,大都體現(xiàn)在抓捕現(xiàn)行犯場(chǎng)合。無(wú)證搜查中的情況緊急與存在合理根據(jù)往往是相伴相生的關(guān)系。通常緊急情況下搜查時(shí),需要存在合理的根據(jù),而情況不緊急時(shí),則不必產(chǎn)生無(wú)證搜查,可等申請(qǐng)到令狀后再行搜查。就世界范圍而言,大多數(shù)國(guó)家都立法規(guī)定了緊急情況下可以沒(méi)有搜查證進(jìn)行搜查。
根據(jù)無(wú)證搜查最低限度的世界通行標(biāo)準(zhǔn),我國(guó)無(wú)證搜查制度應(yīng)當(dāng)進(jìn)行梳理重構(gòu):將起獲物證行為附加被搜查人同意這一條件,使之成為法律意義上的搜查,同時(shí)增設(shè)其他情形下,被搜查人同意也可以無(wú)證搜查,形成完整的同意搜查制度;把執(zhí)行拘留、逮捕時(shí)和緊急情況下這兩種條件拆分開(kāi),作為兩種搜查形式,來(lái)緩解立法過(guò)于苛刻的緊張關(guān)系,即執(zhí)行拘留逮捕時(shí)可以不經(jīng)同意無(wú)證搜查,緊急情況下也可以不經(jīng)同意無(wú)證搜查。由此,我國(guó)無(wú)證搜查可重構(gòu)為三種形式:同意搜查,拘留、逮捕附帶搜查,緊急搜查。
三、無(wú)證搜查的證明標(biāo)準(zhǔn)
將我國(guó)無(wú)證搜查以三種形式予以重構(gòu),擴(kuò)大了無(wú)證搜查的范圍,增強(qiáng)了實(shí)踐偵查手段的合法性。但同時(shí)基于程序正當(dāng)性基礎(chǔ),還應(yīng)當(dāng)對(duì)無(wú)證搜查提高門檻,厘定標(biāo)準(zhǔn),才能兼顧偵查效率和公民權(quán)益,實(shí)現(xiàn)刑事訴訟目的。無(wú)證搜查的證明標(biāo)準(zhǔn)即是解決這一問(wèn)題的根本所在。
(一)拘留、逮捕附帶搜查的證明標(biāo)準(zhǔn)
在執(zhí)行拘留、逮捕時(shí),雖然沒(méi)有搜查證,也可以搜查,這是很多國(guó)家立法規(guī)定了的附帶搜查制度。如美國(guó)聯(lián)邦最高法院認(rèn)為,只要具備合法逮捕和同時(shí)或緊接其后兩個(gè)條件即可展開(kāi)附帶搜查。而加利福尼亞州、阿拉斯加州等則認(rèn)為,即使上述兩個(gè)條件,仍須依客觀情形進(jìn)行判斷,只有同時(shí)具備相當(dāng)理由而有搜查必要時(shí),方可進(jìn)行無(wú)證搜查,否則會(huì)有警察濫用職權(quán)和違反令狀原則之虞。例如,因違反交通規(guī)則而被逮捕之人,除有其他的事實(shí),如手指有血跡等可認(rèn)為有附帶搜查的必要,不可因逮捕即對(duì)之為附帶搜查[3]。
嚴(yán)格而言,我國(guó)刑事訴訟法中并沒(méi)有規(guī)定附帶搜查制度,但在執(zhí)行拘留、逮捕等司法實(shí)踐中卻常常伴隨著理所當(dāng)然的搜查行為。這種立法的缺漏和司法的過(guò)激是一個(gè)硬幣的兩面,解決問(wèn)題的關(guān)鍵在于立法接納。
刑事附帶搜查即拘留、逮捕時(shí)的搜查如何設(shè)置,是一個(gè)需要綜合衡量的問(wèn)題。因?yàn)樗巡榈哪康闹饕谟谒鸭C物,故證據(jù)保護(hù)應(yīng)當(dāng)是目的之一,同時(shí),執(zhí)行拘留、逮捕時(shí)往往險(xiǎn)象環(huán)生,所以安全保證也應(yīng)當(dāng)是目的之一。因此應(yīng)當(dāng)以證據(jù)保護(hù)和安全保證為目標(biāo)來(lái)設(shè)置附帶搜查標(biāo)準(zhǔn)。同時(shí)不能忽視的是,搜查的范圍也應(yīng)當(dāng)有所限制,不能過(guò)于寬泛,應(yīng)當(dāng)以立即可控為標(biāo)準(zhǔn)予以界定,即緊急搜查的范圍應(yīng)當(dāng)限定在被搜查人立即可控的范圍內(nèi),比如隨身物品、所在處所、身體等,反之則需要有證搜查來(lái)介入了。這種必要性的界限便是搜查得以合法展開(kāi)的證明標(biāo)準(zhǔn)。
如前所述,附帶搜查存在于合法的刑事拘留、逮捕之后,因?yàn)榫辛舸端枰淖C明標(biāo)準(zhǔn)相對(duì)已經(jīng)較高,對(duì)之后的搜查不應(yīng)當(dāng)重設(shè)過(guò)高的證明標(biāo)準(zhǔn),這樣不利于犯罪證據(jù)的獲取,同時(shí)增加風(fēng)險(xiǎn)。對(duì)此,應(yīng)當(dāng)在拘留逮捕后有懷疑即可啟動(dòng)無(wú)證搜查,即附帶搜查的證明標(biāo)準(zhǔn)為單純的懷疑。這種主觀標(biāo)準(zhǔn)外化體現(xiàn)的客觀要件:一是可能隨身攜帶兇器的;二是可能隱藏爆炸、劇毒、放射性、急性傳染病毒等危險(xiǎn)物品的;三是可能隱匿、毀棄、轉(zhuǎn)移犯罪證據(jù)的;四是可能隱匿其他犯罪嫌疑人的;五是其他突發(fā)性緊急情形[4]。
(二)同意搜查的證明標(biāo)準(zhǔn)
同意搜查是上文提及的我國(guó)應(yīng)設(shè)的搜查新類型,它可以解決沒(méi)有司法令狀或?qū)徟O(jiān)督時(shí)證據(jù)的搜集問(wèn)題,可以提高偵查效率。但同時(shí),由于同意搜查中同意的意思表示主觀性較強(qiáng),事后較難判斷是否真實(shí)或有無(wú)受到脅迫等,使其極有可能成為偵查人員濫用權(quán)力的合法通道。因此,如何規(guī)范同意搜查,成為全世界各國(guó)都必須關(guān)注的一個(gè)問(wèn)題。
要論證同意的真實(shí)性,必須立足于被搜查人視角。一般而言,每個(gè)人對(duì)于被搜查都會(huì)下意識(shí)的抗拒,因?yàn)楫吘箷?huì)遭遇一定程度的強(qiáng)制,還有就是隱私的可能暴露、財(cái)產(chǎn)的可能損失等。但搜查相對(duì)人在考量上述因素后依然同意(假定真實(shí)同意)被搜查,一定是經(jīng)過(guò)了利益權(quán)衡,即如果不同意,會(huì)有更不利的后果。這種利益權(quán)衡是人基于利益最大化的本能選擇,立法應(yīng)予以尊重。這也是同意搜查能夠被全世界大多數(shù)國(guó)家認(rèn)可的重要依據(jù)。因此衡量自愿同意與否的關(guān)鍵問(wèn)題是外部影響,即是否有偵查人員的外部強(qiáng)制或威脅,以及這種強(qiáng)制或威脅與被搜查人同意之間有沒(méi)有因果關(guān)系。如果沒(méi)有,則同意具有合法性。正如美國(guó)聯(lián)邦最高法院的法官在1976年美國(guó)訴沃森案中所指出的,被告被拘禁這一事實(shí)并無(wú)礙于其同意的任意性。同樣,在我國(guó)臺(tái)灣地區(qū)的司法實(shí)務(wù)中,犯罪嫌疑人被逮捕后同意“帶同警方前往其住處起贓”的做法,并不違背同意搜查的原則[5]。
如何設(shè)立一個(gè)相對(duì)科學(xué)合理的判斷標(biāo)準(zhǔn),來(lái)證明搜查相對(duì)人的同意不是受脅迫或強(qiáng)制。因?yàn)閭€(gè)體差異、個(gè)案差異、同意本身的主觀性等因素,導(dǎo)致很難有一個(gè)相對(duì)精確的標(biāo)準(zhǔn)。目前世界各國(guó)規(guī)定雖然略有不同,但基本上都是根據(jù)個(gè)案的具體情況來(lái)進(jìn)行判斷。例如,我國(guó)臺(tái)灣地區(qū)在判斷搜查相對(duì)人是否自愿時(shí)往往是依具體個(gè)案綜合情況認(rèn)定之[6]。而在美國(guó)的司法實(shí)務(wù)中,聯(lián)邦最高法院對(duì)同意搜索的審核通常是綜合一切情狀進(jìn)行判斷,即在進(jìn)行判斷時(shí)綜合考慮當(dāng)時(shí)的環(huán)境,如警察訊問(wèn)的方式是否有威脅性,同意者主觀意識(shí)的強(qiáng)弱、教育程度、智商等。有鑒于此,要判斷“同意搜查”是真實(shí)的自愿還是被迫的結(jié)果,必須結(jié)合諸多情況進(jìn)行綜合考慮,以對(duì)憲法所保障的眾多利益加以調(diào)和[7]。
綜上,同意搜查的自愿性是保障其合法性的關(guān)鍵因素。把同意搜查的證明標(biāo)準(zhǔn)界定為,單純的相信比較合適,也即無(wú)證搜查主體本能的相信被搜查者是自愿的。由此所要求的外在實(shí)質(zhì)要件:一是警察沒(méi)有展示武力或進(jìn)行言語(yǔ)威脅;二是沒(méi)有眾多警察的出現(xiàn),使搜查相對(duì)人產(chǎn)生同意與否都無(wú)法阻止搜查的進(jìn)行;三是根據(jù)搜查相對(duì)人的年齡、性別、文化程度、社會(huì)閱歷、精神狀態(tài)等綜合判斷,其意志沒(méi)有被警察所壓制。
(三)緊急搜查的證明標(biāo)準(zhǔn)
情況緊急時(shí),如果申請(qǐng)搜查證則會(huì)延誤打擊犯罪,甚至帶來(lái)危險(xiǎn),可以不必具備搜查證這一形式要件,但要具備相當(dāng)?shù)恼?dāng)性基礎(chǔ),即不是所有緊急情況下都可以進(jìn)行緊急搜查的。這種正當(dāng)性基礎(chǔ)應(yīng)當(dāng)是基于刑事搜查目的乃至刑事訴訟目的權(quán)衡后的價(jià)值取向,是在已經(jīng)考量過(guò)人權(quán)保障目標(biāo)下的搜查權(quán)的特許。
綜合上述規(guī)定可以看出,一般而言緊急搜查的實(shí)質(zhì)理由有如下三種情形:一是抓捕罪犯需要;二是證據(jù)保全需要;三是人身安全需要。
同時(shí),緊急搜查最易侵害到的法益是人身權(quán)和住宅權(quán),而這兩種法益容易受到侵害的可能程度是不一樣的,所以有必要單獨(dú)考察兩種情況的緊急搜查。
關(guān)于人的緊急搜查,分兩種情況:一是對(duì)住宅外的人的搜查,也即緊急搜身,在追蹤現(xiàn)行犯、可疑分子或逮捕通緝犯等情形時(shí),搜查相對(duì)人本身危險(xiǎn)程度較高,現(xiàn)場(chǎng)瞬息萬(wàn)變,來(lái)不及也很難進(jìn)行預(yù)判和心證,此種情形下應(yīng)當(dāng)允許立即搜查;二是對(duì)住宅內(nèi)的人進(jìn)行搜查,這需要判斷是否有必要通過(guò)侵入住宅的方式實(shí)現(xiàn)對(duì)人的搜查,此刻涉及到兩個(gè)法益,而住宅權(quán)必須成為考量的因素之一。對(duì)上述現(xiàn)行犯、可疑分子、通緝犯等對(duì)象,在追逃的過(guò)程中躲進(jìn)住宅,則符合第一種情形,可立即進(jìn)行住宅內(nèi)緊急搜查;如果是住宅內(nèi)正在犯罪或有線索指向追逃對(duì)象正在住宅內(nèi)的,則需要搜查人員有相當(dāng)?shù)睦碛上嘈牛@種相信的程度不必達(dá)到百分百確信,只要有相當(dāng)理由相信即可。比如住宅內(nèi)傳出呼救聲或暴力擊打等異常聲音,或有鄰居等熟人指認(rèn)住宅內(nèi)有追逃犯等情形,都屬于生活中大體可信的相當(dāng)理由,據(jù)此可以對(duì)住宅進(jìn)行無(wú)證搜查。
關(guān)于住宅內(nèi)物的搜查。由于住宅內(nèi)的物一般沒(méi)有緊迫的危險(xiǎn)性,而住宅權(quán)又是公民的憲法基本權(quán)利,所以可待簽發(fā)搜查證后進(jìn)行搜查。但是,如果有線索指向住宅內(nèi)的物極具現(xiàn)實(shí)的危險(xiǎn)性,比如炸彈、毒氣等足以危及公共安全的情形,或者有證據(jù)證明不緊急搜查證物將可能永久性滅失、毀損或被轉(zhuǎn)移的,比如毒品等關(guān)鍵性物證,則可以進(jìn)行緊急搜查。而這種也需要有相當(dāng)?shù)睦碛上嘈拧?/p>
四、結(jié)語(yǔ)
綜上,我國(guó)緊急搜查的證明標(biāo)準(zhǔn)應(yīng)當(dāng)略高于附帶搜查,略低于同意搜查,把它界定為合理的懷疑較為恰當(dāng)。外化為無(wú)證緊急搜查的實(shí)質(zhì)要件:一是可能危及偵查人員或其他公眾的人身安全的;二是可能導(dǎo)致罪犯或犯罪嫌疑人逃匿的;三是可能毀滅、轉(zhuǎn)移證據(jù)的。
參考文獻(xiàn):
[1]貝卡利亞.論犯罪與刑罰[M].黃風(fēng),譯.北京:中國(guó)法制出版社,2002:35.
[2]周洪波,潘利平.無(wú)證搜查:立法與實(shí)踐的背離及其完善[J].西南民族大學(xué)學(xué)報(bào)(人文社科版),2008(8):198-202.
[3]劉世興.附帶搜索要件及范圍之比較研究[D].臺(tái)北:臺(tái)北大學(xué)碩士論文,2002.
[4]陳光中.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刑事訴訟法再修改專家建議稿與論證[M].北京:中國(guó)法制出版社,2006.
[5]林山田.刑事訴訟法改革對(duì)案[M].臺(tái)北:臺(tái)灣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0:486.
[6]林鈺雄.搜索扣押注釋書(shū)[M].臺(tái)北:臺(tái)灣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1.
[7]李學(xué)軍.美國(guó)刑事訴訟規(guī)則[M].北京:中國(guó)檢察出版社,2003.
(責(zé)任編輯:李凌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