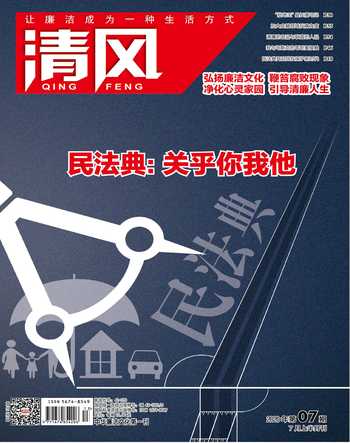美國大選年觀察之三:特朗普、拜登比誰對中國更狠
闕維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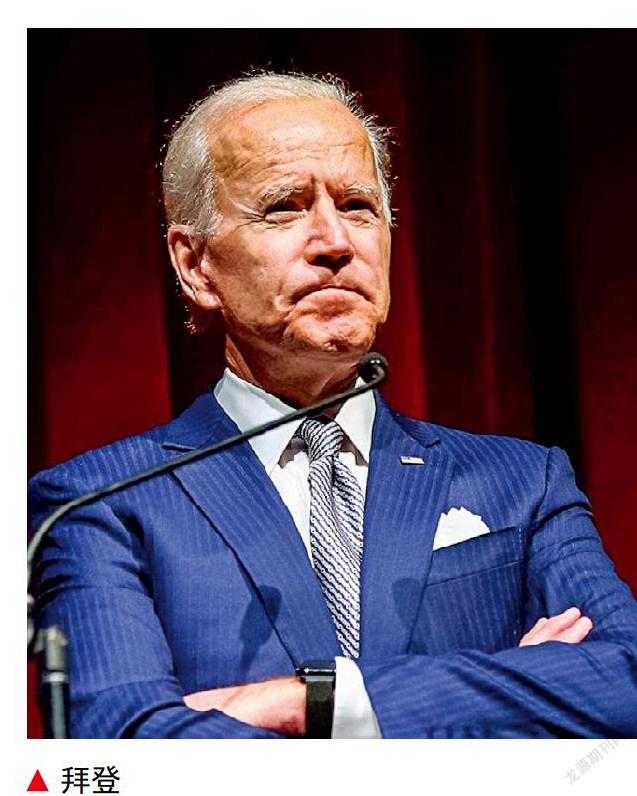

早在6月共和、民主兩黨各自舉行全國委員大會之前,美國現任總統特朗普和前副總統拜登,就已經被確認為各自黨派參選總統的候選人,因為他倆在各自黨內都已然沒有了競爭者。美國共和、民主兩黨的正面廝殺,也早早地于4月就開始了。
互相攻擊的廣告輿論戰
拜登競選陣營4月17日推出一系列廣告,辯解自己系被特朗普陣營指稱“支持中國”,并反指特朗普在新冠病毒蔓延時過于信賴中國,“令人不安的事實是,特朗普讓美國處于脆弱狀態,無視衛生專家和情報機構警告,反而信任中國領導人”。揶揄特朗普“沒有讓中國負上責任”。
特朗普那段時間幾乎每天下午站在白宮電視攝影機前,將新冠病毒大流行歸咎于中國,并試圖傳遞拜登在其副總統任內對北京友好的政治信息。自1973年就當選為聯邦參議員的拜登,是美國政治風評中的“友中派”,其傾向自由主義的外交邏輯,希冀以對話、交流與合作溝通,建構中美兩大強權的“伙伴關係”。拜登的這一風格,在奧巴馬總統任內即已被視為“對中軟弱”,加上其次子杭特屢屢牽涉在華投資爭議,因此被政壇保守派視為民主黨內的“親中派系”。
特朗普連任政治行動委員會“美國第一行動”投入1000萬美元,在賓夕法尼亞、密歇根、威斯康星三個搖擺州投放廣告,播出重點是展示拜登“說中國好話”的資料錄像片,直批拜登曾經說過“中國不是美國的競爭對手”,稱他“不會站起來對抗中國”。旁白是:“美國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更需拒絕中國,而要拒絕中國,必須拒絕拜登。”而聯系到當下的抗疫,該競選廣告則批評拜登曾多次反對特朗普宣布的對華旅行禁令。
民主黨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美國大橋”撒了1500萬美元,只為推廣一個電視廣告——抨擊特朗普“信任”和“贊美”中國,在美國國內醫療用品欠缺時還將裝備送給中國。而拜登在其住家地下室借遠距視訊,回應特朗普陣營指控——自疫情蔓延以來,特朗普一直未能與中國領導人溝通,以致美國沒有充分準備好應對危機。
這些現象表明,疫情下的總統大選,兩黨候選人的交鋒,廣告輿論戰打頭陣,幾乎都在比誰對中國更狠,都是在打一副所謂的“中國牌”。
頻打“中國牌”伎倆不新鮮
美國大選期間候選人頻打“中國牌”,既是不爭的事實,也是早就不新鮮的伎倆。自中美建交以來40余年,里根、老布什、克林頓、小布什、奧巴馬、特朗普,幾乎每位上臺的美國總統在其競選期間,都毫無例外地攻擊前任或對手的對華政策。
然而被疫情沖擊的本屆大選,距離11月3日的投票日僅有5個月左右之際,特朗普和拜登之間的較量,居然乞靈于誰亮出的“中國牌”更狠,更能夠抓住選民的眼球;卻缺乏實質的內涵和政策表述,亂了競選策略的章法。
“在美國陷入危機時,拜登卻在顧忌中國的感受。” 4月9日,特朗普在其YouTube賬號上發布了一段競選廣告視頻,指責前副總統拜登在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前后為中國出聲。
長約1分鐘的該視頻文字說明聲稱:在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之前及其期間,拜登一直維護中國,不認同中國是(美國的)經濟威脅,并反對特朗普總統對華實施的旅行限制。視頻隨即出現有關拜登反對“因疫情對華實施旅行限制”的新聞報道截圖,以及拜登在集會上提到的“歇斯底里地排外(hysterical xenophobia)”的言論。在繼續質疑拜登的視頻中,還配有拜登與中國合作伙伴、中國官員會面的場景和報道截圖等畫面,指出那“又或者是為了在華的投資”。
5月間,特朗普陣營在美國社交媒體臉書上與媒體推出競選廣告,其中包括引述拜登過去對中國的稱贊,試圖以“中國傀儡”比喻拜登,并且直接稱他是“北京拜登”。一張拜登低著頭在懸掛中國五星旗的白宮前的圖片也一度出現在社群網站,暗示這是“親中派”拜登上臺后的白宮,以此警示美國選民。
拜登陣營毫不示弱,首先指責特朗普對中國“說一套做一套”,嘴上強硬但態度軟弱,對華政策是“一系列災難性失敗”。拜登5月12日透過外交政策幕僚放話,承諾將提出更有效、具體的“對中國硬起來”政策。拜登競選團隊聲言,特朗普任內面對貿易戰、新冠肺炎病毒等問題,總是“色厲內荏,光說不練”;唯有豐富外交經驗的拜登,才有辦法重整昔日戰略盟邦,于戰略上重整“中國包圍網”。
因拜登陣營的指責,也為了自我開脫新冠病毒疫情在全美爆發的責任,特朗普不斷擴大對中國的指責,口氣愈來愈強硬,并考慮與中國這個最大的貿易伙伴“切斷關系”。
顯然,特朗普自知,疫情失控、經濟崩盤,是尋求連任的“死結”,他必須為疫情蔓延尋求免責理由,給受疫情所傷民眾找出一個發泄的出口,還得盡力啟動經濟快速反彈,否則如何能夠讓選民對他投下信任票?前者,“甩鍋”中國成了捷徑;后者,試圖豪賭經濟重振,卻依然是未知數。
重彈“中國威脅論”老調
自特朗普入主白宮以后,他把眾多鷹派人物羅致到自己身邊,2017年發表國家安全報告時,更直接定位中國為“戰略競爭對手”,猶如復制、擁抱里根時代的冷戰氣氛,喚醒美國政界乃至社會對中國崛起的深潛憂慮,拋起了全美從上而下對中國強硬、遏制中國的一波波浪潮。
在這樣的氛圍下,美國所謂《國防授權法》《臺灣旅行法》《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都一一出籠,甚至罕見出現兩黨聯手推動、白宮國會目標一致的情勢,且暢通無阻。
而今,新冠肺炎疫情儼然又成了中美關系惡化的一帖催化劑。共和、民主兩黨候選人以“斗罵中國”為主旨的比狠戲碼,就在這般混沌、繁復的氛圍下相繼登場,堪為今年大選兩位老人對決的白熱化一幕。
特朗普、拜登各自手舉的“中國牌”,聲嘶力竭地互相對罵,互揭瘡疤,其實只是重彈“中國威脅論”的老調,是想用鷹派的觀點綁架或左右民意,也是想以鷹派的自我包裝,與對手比狠。
拜登陣營指責特朗普在貿易戰、外交戰中“只圖大嘴巴過癮”,盡管時常嗆聲中國,但兩國貿易談判談了4年,迄今都沒有具體的“結構性”獲益;在相關國安戰略議題上,各種制裁法律也都由國會主動先導,特朗普基本沒有具體作為,且與歐盟交惡。
拜登陣營認為,特朗普在對華政策上不僅無法有效拉攏德國、法國等傳統盟邦與美國行動一致,在日本、韓國與菲律賓等東亞傳統盟友的戰略經營上,也屢屢因為駐軍經費、貿易問題而多有摩擦。因此,如何重整歐洲與印太的“中國包圍網”,也成了拜登陣營的主要政見。
拜登陣營還發布近2分鐘長、標題為“準備不足”的廣告,抨擊特朗普應對疫情不力、過于信賴北京,指其在1~2月間至少15次稱贊中國政府的疫情應對。
“中國威脅論”近幾十年來一直是美國政客喜歡鼓噪的話題,在大選年自然成為熱門招數,這就是兩黨政客都高調鼓吹的緣由。縱然是商人出身的特朗普,浸淫政壇這幾年,也未能免俗而成習慣,并且深知非如此難以抗衡對手,也難以忽悠選民手中的選票。特朗普和拜登競相在對華問題上展現強勢,也就成了如今電視、視頻里不時出現的畫面。
據《紐約時報》5月的一篇文章表述,共和黨人迫切希望掩蓋特朗普應對疫情的失敗。近10萬美國人死亡和3600萬人失業的現實,讓特朗普在競選策略上除了打“中國牌”,似乎沒有更好的選項了。
就特朗普而言,抨擊前副總統拜登并把他和中國扯在一起,至少起到如下作用:抑制民主黨人的投票率,轉移自身應對疫情的致命錯誤而不承擔任何責任,試圖重新包裝自己在中國問題上的立場,變成“政治正確”的化身。
而拜登陣營,在攻擊特朗普對中國示弱、防疫抗疫不力之外,也竭力撇清被對手攻擊的“親華”立場及形象。在2019年黨內總統初選辯論期間,顯然為了競選和拉攏選民,拜登一改以往的“友中立場”,在初選辯論中公開批評中國領導人,并質疑特朗普的對華政策。
拜登競選陣營的幕僚還為之設計出一套競選策略,稱“拜登前副總統”有兩件事情需要處理:一是追究特朗普對一連串災難性“中國政策失誤”的責任;二是填補特朗普在“嘴炮的巨人、行動的侏儒”之間所留下的巨大鴻溝。拜登的幕僚認為,特朗普執政以來,美中兩強對抗日漸激烈,但除了各種口水戰,雙方的拉鋸消耗戰并沒有具體的成果與進展。言下之意就是,只有拜登上臺,才能夠改變這一切。
“斗狠”無異于喪失政治格局
特朗普近年來在經貿問題上對華強硬,疫情期間對華表態反反復復。他的種種焦慮與矛盾表現,仿佛是一位意氣用事的商人,勉為其難地為國家大事操心,卻終歸落實不到點子上。疫情陰影籠罩下的大選緊迫關頭,特朗普亟須嚴厲抨擊中國,挑起并附和選民對中國的強烈不滿,以謀求競選優勢。
拜登雖然是老政客,但在對華立場上左右搖擺,一看就是為了競選總統刻意做出的姿態——既要洗白“親華派”的固有形象,又要樹立對華強硬角色的新立場,其實也是勉為其難的一場作秀。
這兩位總統大選的對手,為了忽悠選民的選票,為了擊敗對手,就只能顯示自己比對方對付中國更狠,就只能竭盡全力抹黑對手,以彰顯自己的強硬狠勁和“政治正確”。事實上,與拜登為人詬病的家族利益相似,特朗普的女兒伊萬卡曾經獲得大量中國商標,幕后的交易也往往遭遇媒體調查。
兩位候選人的言行,除了比狠斗狠,恍若把高舉的“中國牌”當作長矛的新唐吉訶德,非常搞笑之外,既了無新意,又沒有切實可行的政見,幾乎就是喪失政治格局的兩個粗人,在總統大選的戲臺上說那些老掉牙的臺詞。如果不是在疫情下飽受煎熬,美國選民們根本無暇看兩位年邁的演員表演,這樣的套路與戲碼,怕是早就要被觀眾喝倒彩了。
他倆不約而同地扮起了鷹派頭領的狠角,幾乎不顧及進退失措的各種辭令可能擦槍走火,不顧及毫無章法地“甩鍋”、斗狠徒然喪失政治格局,只在意亮出“政治正確”的旗號,在乎如何有效煽動起民族主義情緒,就可以乘勢而為,把“中國牌”舉得更高更高,從而撈取盡可能多的選票。
兩黨競爭對手如此高調而無節制地斗狠,在當下中美關系低落的階段,可能會愈演愈烈,將導致未來的當選者在對華強硬政策上的沖突難以剎車,也可能打破以往當選總統較快調整政策立場趨于溫和的慣例,會不得不延續對華強硬態勢,這是尤其值得警惕的“斗狠后遺癥”。
因此,有觀察家分析指出,當下這種特殊的政治氛圍如延續下去,11月大選無論是特朗普抑或拜登當選,都極可能要延續一段時間的對華強硬路線。因為他倆都依然要繼續博取選民的信賴,都要顯得比對方更狠更硬,其實還是更唐吉訶德般的自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