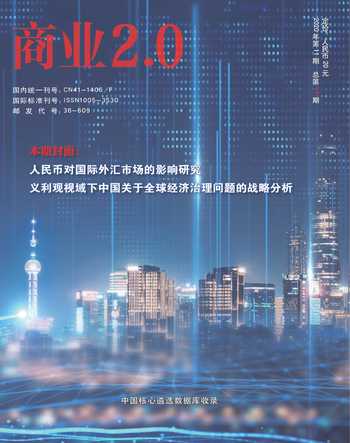人民幣對國際外匯市場的影響研究
摘要:隨著我國綜合國力的提升,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逐步完善,人民幣的影響力也在逐步遞增,在這樣的背景下,本文對人民幣國際化對國際外匯市場的影響進行研究,同時對我國目前人民幣國際化存在的問題及障礙進行了分析,為推動我國人民幣地位的進一步提升,我國還應加強金融領域的改革開放,促進人民幣三大貨幣職能的均衡發展,推動在岸—離岸市場的良性互動。
關鍵詞:人民幣國際化;貨幣職能;在岸-離岸金融市場
1.引言
近年來,隨著我國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逐步完善和金融開放,外匯市場調節能力和市場成熟度逐步提升。面對復雜多變的外部環境,我國經濟運行總體平穩,人民幣匯率彈性增強并基本穩定,國際收支保持基本平衡。中國作為世界經濟第二大國和第一貿易國,同時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也迎來了新的發展機遇。伴隨著中國經濟的平穩增長,人民幣匯率機制的不斷改革,人民幣跨境結算的穩步推進,金融基礎設施的逐漸完善,在岸-離岸市場的良性互動,人民幣對國際外匯市場的影響也在不斷的加深擴大。
2020年初新型冠狀病毒在全球的快速蔓延,海外股市大幅波動,得益于國內疫情防控措施的有效,快速,疫情獲得極大的緩解,同時,外資加速流入中國資本市場勢頭明顯,全球主要經濟體競相降息,進一步凸顯了人民幣資產的配置價值,此時人民幣資產在全球范圍內性價比快速提升。與此同時,自2001年年底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以后,我國經常賬戶順差與GDP之比從2001年的1.3%升至2007年的9.9%的最高值;隨后逐步回落,2016年以來一直維持在2%以內,表現了我國內部經濟結構逐漸優化,與外部經濟逐步平衡。
本文之后部分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紹人民幣國際化進展以及對國際外匯市場產生的影響,第三部分人民幣國際化帶來的問題及對國際外匯市場帶來的風險,第四部分為本文的結論以及相關的建議。
2.人民幣國際化進展及對外匯市場的影響
人民幣國際化“從無到有”,其支付結算功能不斷增強,投融資功能不斷深化,儲備貨幣功能逐步顯現。
2.1人民幣可能將會成為主要國際貨幣之一
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的次貸危機,在“特里芬難題”的約束下全世界意識到過度依賴美元的國際貨幣體系所帶來的嚴重危害。當前特朗普政權的不確定性,更加加劇了人們對于美元作為世界主導貨幣的擔憂。2016年人民幣被正式納入特別提款權SDR的貨幣籃,占比達到10.92%,僅次于美元和歐元[1]。人民幣作為新興發展中國家唯一“入籃”貨幣,增加了SDR的穩定性,同時提高了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貨幣體系的地位。隨著中國經濟持續穩定增長,通過完善“一帶一路”金融基礎設施的建設,貨幣互換合作的加深,人民幣跨境結算的穩步推進,人民幣將逐步發展成為全球關鍵貨幣之一[2]。
2.2人民幣的國際支付結算及計價功能逐步增強
近年來,跨境貿易支付結算快速增長,人民幣結算業務金額從2010年的5063億元增長到2018年的51100億元,年均增速為33.5%。且根據人民銀行披露的數據顯示,與我國發生人民幣跨境業務的國家和地區達242個,發生業務的企業超過34.9萬家,銀行超過386家。目前已有30多個貨幣當局與中國央行簽署了貨幣互換協議,超過60個國家或地區將人民幣列為外匯儲備[3]。
2.3金融領域不斷進行改革開放
人民幣跨境使用基礎設施不斷完善,截至目前,人民銀行已在美國、德國、法國、南非、韓國、日本、俄羅斯等25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人民幣清算安排。滬港通、深港通、債券通等管道式開放深入推進,并且隨著人民幣跨境使用的不斷擴大,離岸人民幣產品逐步增多,香港作為人民幣重要的離岸金融中心,與上海相互促進,境內外金融市場互聯互通穩步推進。同時人民幣資本賬戶開放度不斷提高,合格境外投資者(QFII),人民幣合格投資者(RQFII)的投資額度都有顯著的增長。跨境投融資快速增長,金融市場體系投融資功能的不斷完善,極大地促進我國形成一個集國際化與多層次一體的金融市場。
2.4人民幣匯率改革趨于市場化
從1994年匯率形成機制市場化以來,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逐步完善和金融開放,匯率彈性不斷增強,人民幣匯率將呈現雙向波動,有升有貶的走勢,有助于分化市場預期,促進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穩定。外匯市場調節能力和金融改革開放市場成熟度也將繼續提升。
3.人民幣發展存在的問題
3.1人民幣不同貨幣職能發展不均衡
近年來我國過于重視人民幣結算職能,而忽視人民幣計價和價值儲備職能的發展。目前人民幣的計價功能較弱,跨境貿易投資和國際金融產品仍主要采用美元計價,中國的海外資產存量還十分有限;另外,人民幣的國際官方儲備貨幣地位與其他國家相比仍有較大差距,據IMF于公布的2019年第三季度官方外匯儲備貨幣構成,在全球官方外匯儲備資產中,人民幣外匯儲備資產約合2196.2億美元,占比僅為2.01%,美元仍是全球占主導地位的儲備貨幣,未來人民幣官方外匯儲備地位的提升任重道遠[4]。
3.2金融市場發展不完善及交易成本過高
境外投資者在主體資格、投資額度、產品種類等方面還存在一些限制,較高的交易成本制約了人民幣的順暢回流。另外,國內金融市場改革有待深化,目前缺乏與美元、歐元等貨幣計價的金融產品相競爭的人民幣金融產品。目前在跨境貿易和投資的計價中大部分國家仍對美元有較強的依賴,特別是在大宗商品領域,“石油-美元”機制鞏固了美元作為主要計價貨幣的地位。相比之下,人民幣在大宗商品計價、外匯衍生品等方面仍與美元等國際貨幣有較大差距。
4.結論與建議
總體而言,隨著中國經濟平穩增長,國際收支項目的穩定,金融領域改革開放持續深化,人民幣的地位也將進一步提升,人民幣國際化還將穩步前行。中國也應把握住機會,結合“一帶一路”建設中的廣闊機遇,進一步發展,讓人民幣成為國際外匯市場中舉足輕重的一員,增強世界貨幣體系的穩定性。
4.1推進以人民幣計價的大宗商品交易
中國作為全球最大原油、天然氣進口國,大宗商品人民幣計價將增強大國因素對全球大宗商品交易的定價權。同時,全球大宗商品交易計價貨幣一旦形成之后就具備很強的制度慣性與網絡特性,有助于使人民幣更快成為國際支付結算及計價貨幣。目前“一帶一路”沿線石油,天然氣,礦產等能源資源豐富,在能源合作中推進人民幣計價的大宗商品期貨和現貨市場前景廣闊。
4.2加強金融基礎設施建設,促進“在岸-離岸”市場良性互動
我國應充分利用現有條件,提升國際化層次。綜合利用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提升國內金融市場完善程度,提高香港離岸金融中心的國際地位,大力發展人民幣離岸市場,豐富離岸市場人民幣金融產品的種類,拓展人民幣投資與儲備功能,逐漸放松對與資本交易相關的金融服務和外匯兌換的控制。
4.3改善人民幣的穩定性和流動性
加快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有序實現資本項目可兌換、加強政策協調并處理好開放的次序;提高金融信息處理和風險監測能力,完善危機預警體系和應對預案,建立健全人民幣資本市場的相關法律與監管規則及高效、安全、統一、便利的離岸人民幣清算系統。加快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并最終實現中高速的經濟增長,為人民幣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提供堅實有效的支撐。
參考文獻:
[1]方磊.人民幣加入SDR后發揮國際貨幣職能的理論思考和路徑探索[J].當代經濟研究,2020(01):92-102.
[2]王喆,張明.“一帶一路”中的人民幣國際化:進展、問題與可行路徑[J].中國流通經濟,2020,34(01):100-111.
[3]王新.人民幣國際化與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基于外匯儲備的貨幣功能的視角[J].金融理論與教學,2019(06):23-26.
[4]馬草.人民幣國際化發展趨勢及其影響[J].合作經濟與科技,2020(04):54-55.
作者簡介:鄭佳佳(1996-),女,研究生,研究方向:國際商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