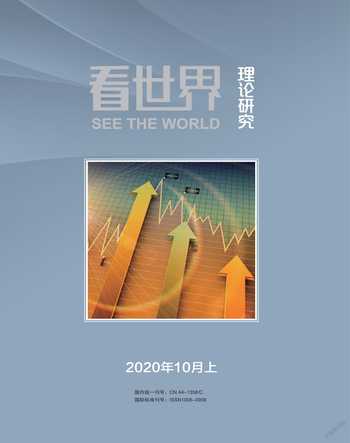行政國時代的言說:讀私有財產、公共行政與法治
李欣
摘要 :在愛潑斯坦看來,2010年頒布的《多德——弗蘭克法案》和《患者保護和平價醫療法案》中所透露出的龐大的管制野心,引發了他對政府因此而享有巨量行政裁量權的擔憂。作為古典自由主義的“偏愛者”,他認為這一切與私有財產權的保護及法治理念相背離,于是,他就意圖創造出一種良好的公共行政模式,私有財產、公共行政和法治三者能夠實現良性互動。
關鍵詞:私有財產;公共行政;法治;古典自由主義
基調:作為一位古典自由主義者,愛潑斯坦對個人權利、私有財產和自由市場極為鐘愛。在本書開篇愛潑斯坦便提出法治與私有財產和個人自由似乎存在著某種緊密聯系——“自由和財產必須在強有力的法治保障下才能運作”,但與此同時,法治亦不能被僅僅局限在競爭市場的邊界內運作,愛潑斯坦對古典自由主義者所堅持的小政府與法治之間存在必要的邏輯聯系這一觀點并不贊同,他認為法治的概念是寬泛的,不能僅僅將其與市場拴在一起,因為這將意味著將下層人民拋棄在法治的保護以外。
愛潑斯坦筆下的法治沒有一個確定的概念,相反他認為法治的概念性差異無礙于對其的追求。回顧法治的歷史進程,愛潑斯坦書中提到的古典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哈耶克、洛克等人,洛克以權利作為自由的基礎,而哈耶克以法律規則作為自由的基礎,但他們的終極目標都是為了實現自由。
富勒在論證法律的道德性時提出的八大原則,也可被認為是形式上的法治:普遍性、公布、非溯及既往、明確、不矛盾、可為人遵守、穩定性、官方行為與法律的一致性。愛潑斯坦則認為僅僅依靠這種形式上的法治控制政府無限制的裁量權是不夠的,“因為最高貴的程序有可能服務于最丑惡的政治。”實質上的非歧視性條文也應是法治的一部分,只是這種中立性的條文又會帶來嚴重的差異性影響,“要處理敵人,就要將朋友作為人質。”這種規則在一些情形下運行良好,但在另一些情形下,如應納稅的行為可能對對手的經濟生存甚為關鍵,但對你和你的支持者卻不是這樣,差異性影響便顯而易見。
將法治的程序性要素與一種健全的個人權利觀念結合便可以更好的解決上述問題。自然法與社會福利的關系漸漸浮出水面,“用現代博弈論的話語,競爭和發展給社會的所有個體生成正收益,限制和強迫生成負收益。”
不過個人偏好總有不同,為了將社會期許和個人愿望聯系起來,愛潑斯坦試圖尋找一條通過非恣意的方式將不可通約的個人偏好相整合,并且兼顧社會整體結構的社會安排路徑。帕累托標準和卡爾多——希克斯標準提供了將主觀偏好與社會福利連接的路徑。盡管在是否支付補償上有差別,但這兩個標準都毫不含糊的譴責所有主觀上減少社會整體福利的體制。但讓每個人都變得更好還不夠,愛潑斯坦又提出了第三個標準,每個人必須在同等程度上變得更好。
他認為,現代行政國熱衷于以盡可能確保所有利害關系人和組織參與公開、協商程序的立法來取代強大個人權利,但被高估的公共協商、專家參與以及個人權利和政治權力關系的顛倒,使得行政國沒能通過社會福利三個標準的考核,“現代行政治理體制不如已被取代的更為謙遜、更為聚焦的古典自由主義體制。”
于是,我們跟隨愛潑斯坦的腳步,來到了古典自由主義的核心——財產權。愛潑斯坦筆下的財產權也有公共財產和私有財產兩個面向,他贊同洛克關于財產權的立場:財產權是自下而上產生的,國家的主要功能在于保護這些財產。財產權人享有的權利包含排斥他人進入其財產的權利及進入自己財產,即占有、使用及處分的權利。雖然愛潑斯坦熱衷古典自由主義,但他也并未將財產權推向極致,在古典自由主義的框架內,財產權要遵守“讓自己活也要讓別人活”的互惠原則。財產權體系清楚配置了對物的全部權利,權利所具有的清晰、穩定和事先知曉的特性,進一步堅定了愛潑斯坦以財產權來限制威脅法律體系長期穩健的政治裁量制度。為了檢驗這一概念,他接著將目光轉向了在現代行政國被寬泛構思的征收權,意圖揭露行政國藏在“法治”之下的不堪。
“征收”意味著公共所有權超越私有財產權,其授權政府只要補償損失就可以為了公用強迫私人所有者放棄財產。如何規制征收權使其與私有財產權并行不悖是愛潑斯坦所想回答的問題。憲法第五修正案規定“未經補償,不得因公用征收私有財產。”在此基礎上愛潑斯坦接連追問:征收私人財產意味著什么;何時征收是為了公共利益;是否給予了公平補償;政府如何用其警察權的行使為征收辯護。
在需要支付補償的前提下,政府更樂于將“征收”的內含限縮,以達到更便于管制的效果,這種政府行為在愛潑斯坦看來是披著“征收”之名的管制行為,與前文私有財產權利束概念相違背。愛潑斯坦對此憂心忡忡,對財產權的限制如此隨意和“管制性征收”的范圍一再收縮,都是在為“政治陰謀開放空間”。
更加糟糕的是,政府對被征收者進行補償所依據的是公平市場價值補償的原則,愛潑斯坦認為這忽視了對個人主觀價值損失的賠償,他認為補償甚至應包括律師費和評估費等間接損失。一個良好的征收體制,愛潑斯坦認為應該是雙贏的,政府權力的運用既能達到正面功能亦能避免其權力濫用。
談及古典自由主義的另一支柱——契約自由,愛潑斯坦提到了著名的“洛克納訴紐約案”,在愛潑斯坦看來,它重申了司法的謙抑性和契約自由的重要性,公共過分自信的對自由利益進行干預反而會招致負面影響,正如古典自由主義的格言“要合作,不要強制。”
擔憂:雖不愿看到,但愛潑斯坦也不得不承認行政國的昂首闊步仍未止歇。他用了“法治式微”來表達對行政國的失望,行政國給司法機構帶來一系列壓力,對行政行為的司法審查出現了大反轉。行政國下,法院在對行政行為進行審查時,對內含于其決定中的事實問題上過度干預,對專業范圍內的法律問題反而尊重行政機構的解釋,“這將我們推向遠離法治之境”。謝弗林案件所反映的法院在疑難案件中讓與行政機構寬泛的解釋權,使愛潑斯坦再次強調最終的解釋權應當在法院,行政機構所能做的是“說服”而非解釋。除此之外,有溯及力的立法同樣對法治提起挑戰,它干預了市民有權仰賴的確定預期。面對輕視固定規則和頌揚自由裁量的行政國,財產權變得不再強硬,自由交易也不再自由,法治難以生存。“沒有理由認為行政國和法治兼容”,愛潑斯坦終于說出了他的心聲。
愛潑斯坦對奧巴馬政府的醫療改革法案和金融改革方案提出了批評,藏在這兩部法案背后的是政府龐大的管制野心,他們試圖證明:高水準的政府干預也許可以振興國家低迷的經濟。在經歷了自由市場經濟創造的眾多奇跡之后,人們面對“市場失控”造成的經濟災難手足無措,于是轉而寄希望于政府及其行政權。但插手那些本不該由政府插手的事,反而使政府在真正屬于他的政治責任問題上變得效率低下。
堅守:愛潑斯坦面對“政客毫無章法,經濟體制飄忽不定”的現狀,對他曾經的篤信也變得不那么確定了。他明白堅持法治就意味著消滅政府在日常事務中的裁量權,這不過是白日做夢,關鍵點在于將任務分配給有限且邊界清晰的政府,只有這樣良好的公共行政才能與充分的財產權相嫁接。這可以看作是愛潑斯坦的讓步,只是這樣良好的公共行政“從未降臨人間”。
行政權作為一種權力,它本身并沒有“善惡”,只是由于行使方式的不同帶來不同的結果。愛潑斯坦將所有的政府行為一律推定為非或許帶有“偏見”,他將政府的權力限定在消極被動的保護個人自由權利上,那些積極主動的想要促進個體幸福的行為背后都有可能是以公共利益和道德的名義對個人自由權利的侵犯。面對行政國的登堂入室,愛潑斯坦痛心疾首,他仍高揚有限政府、權利和自由的古典自由主義旗幟,哪怕這些東西在新的時代背景下顯得互相之間有些沖突。
作者單位:西北政法大學行政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