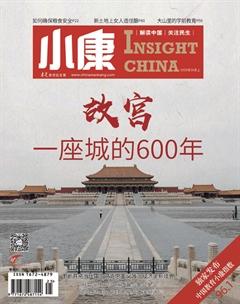分類探索撤縣設區不同路徑
行政區劃作為行政體制的空間投影,是構建現代國家治理體系的基本載體和重要手段。作為縣級行政區劃調整的一種類型,撤縣設區是指將縣(縣級市)改設為相應城市的市轄區。撤縣設區主要發生于城鄉接合部,主要目的是擴展城市的發展空間,減少協調成本,統籌市域發展,推動城鎮化進程。
近期,隨著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階段性勝利,我國的行政區劃調整工作也開始步入快車道。2020年6月至7月,國務院先后批準了山東煙臺、四川成都、河北邢臺和安徽蕪湖四個城市的撤縣設區方案,短時間內新設立了6個市轄區,引起各界的廣泛關注。
撤縣設區曾經歷兩次高潮
實際上,包括近年來的撤縣設區熱潮在內,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先后經歷了兩次撤縣設區高潮:從改革開放以來一直到2003年,隨著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和城鎮化的加快推進,尤其是市管縣體制的普遍推行,大量新設立的地級市通過撤縣設區的方式增設了市轄區,引發了第一次設置高潮。在這一階段,市轄區數量增加了437個。但在2004年至2012年,相關審批被收緊,市轄區數量僅增加了15個。
近年來,隨著新型城鎮化的快速推進,部分大中城市由于中心城區人口、資源的過度聚集,規模不經濟現象開始凸顯,產業和人口紛紛向周邊區域擴展。而通過撤縣設區等形式擴展城市的發展空間,被認為有助于區域協同發展和基礎設施的統籌規劃,促進城市功能疏散和產業轉移。于是,從2013年開始,撤縣設區的第二次高潮出現,并迅速成為縣級行政區劃調整的主導類型。

趙聚軍南開大學政府發展聯合研究中心研究員,民政部行政區劃調整論證專家
截至2020年7月,我國城市市轄區的數量已經由1978年的488個增加到了970個,增長近一倍,其中絕大多數是通過撤縣設區而來的。目前,北京、上海、天津、廣州、深圳、武漢、青島、南京、蘇州、鎮江、無錫、常州等大中城市的原轄縣(縣級市),已經全部通過撤縣設區的方式改設為市轄區。與之相伴的,則是1978年以來“縣”數量的持續下降,以及縣級市數量的先揚后抑。
值得注意的是,2013年以來的撤縣設區高潮存在一定的區域差異:東部發生頻次最高,西部次之,中部和東北最低。具體來看,2013年至2019年,東部共出現了50起撤縣設區案例,西部為32起,而中部和東北則分別只有20起和5起。東部地區出現較多的撤縣設區案例,主要源于自身較高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和活力,尤其是較高的城鎮化水平。而西部地區較高的發生頻次,則在較大程度上源于重慶、成都等少數大城市較高的撤縣設區強度。不僅在西部地區,在全國范圍內,從撤縣設區的強度來看,直轄市、副省級市和其他省會城市都要明顯高于一般的地級市。
有序推進撤縣設區彰顯我國制度優勢
通常來看,城鎮化的持續推進,必然導致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在空間和人口規模上的繼續擴張。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城市發展的實踐也證明:不宜將城市規模作為制定城市發展戰略的主要依據,長期以來對大城市規模擴展的嚴格控制,已經無法適應新時代社會經濟發展的要求。尤其是近年來天津、武漢、西安、成都等特大城市紛紛加入“搶人”大潮,同時對比部分中小城市面臨的人口和經濟收縮,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視為我國城鎮化發展的一個重要節點:城鎮化進程已經開始步入大都市區化的階段,區域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無疑已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源。在這種情況下,大中城市通過撤縣設區等途徑擴展發展空間,也就成為一種必然的調整。
從另一個層面來看,適時的行政區劃調整也是提升城市,尤其是大都市區治理效能的必要保障。大都市區的產生和成長是現代社會城鎮化進程中的一個重要特征,也是全球性的普遍態勢。就西方國家的普遍情況而言,長期以來大都市區在行政區劃設置方面存在的主要癥結之一,就是地方政區數量繁多、種類龐雜所導致的地方政府“巴爾干化”(又稱“零碎化”“分散化”),并由此引發區域統籌發展困境、公共服務和施政效益低下等問題。相比西方國家,由于行政區劃手段得到了有效和適時的運用,我國的中心城市和城市群能夠始終堅持單中心廣域市制。在有序的行政區劃調整下,各類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的轄域普遍比較廣闊,發展空間比較充足,從而避免了政區結構體系的零碎化趨勢,消除了大都市區有效治理的一個潛在體制性弊病。
當然,也應該看到,雖然說必要的行政區劃調整有助于解決城市發展空間不足、統一的區域發展規劃難以實施等問題,但過猶不及,城市空間和人口的過度聚集也有可能誘發“大城市病”。總體來看,我國自上而下的行政區劃體制具有一定的制度優勢。在政府職能轉變不到位的情況下,考慮到行政區劃的相對穩定性,為了更好地提升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承載力,優化資源配置,更好地發揮其輻射作用,適時推進撤縣設區,也是改革的題中之義。

圖1? 2013年以來的縣級行政區劃調整情況

圖2? 1978年以來的縣級政區變化情況

圖3? 2013年以來撤縣設區的區域分布差異
應以優化城市空間規模為基本目標
整體而言,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行政區劃調整的制度紅利得到了充分釋放,提升了要素的流動效率,為城鎮化,特別是大中城市的快速發展創造了良好的外部條件。同時也應看到,雖然撤縣設區能夠在短期內迅速擴大城區的人口規模與面積,但也存在一些普遍的問題。
第一,城鄉邊界模糊加劇了土地城鎮化快于人口城鎮化的問題,造成了比較突出的“假性城鎮化”現象。特別是那些新設置于中小城市且遠離中心城區的市轄區,由于地理位置偏僻、人口集聚不足,市政基礎設施建設水平更是與中心城區存在巨大鴻溝,與市轄區的建制性質名不副實。
第二,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意識依然對撤縣設區有較大的制約,以致城鎮化和經濟發展水平、政府管理的現實需要等基礎性因素,在一些情況下依然要讓位于行政級別因素。
第三,撤縣設區在部分地區加劇了市縣矛盾。對上級市而言,撤縣設區大大增加了城市發展空間,不僅可以短期內迅速提升主要經濟指標,也為域內公務員的交流晉升提供了更順暢的渠道和更寬廣的平臺,因此多持積極態度。但對縣(縣級市)而言,則是誘導性因素與約束性因素并存。在此情境下,現實中因撤縣設區引發的市、縣博弈案例雖不多見,但也會不定期地出現。
鑒于上述問題,黨的十八大以來,行政區劃工作開始顯示出統籌兼顧發展與治理的雙重導向:優化行政區劃設置不再僅僅服務于經濟發展,亦已成為完善城市空間治理體系的主要政策工具。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優化行政區劃設置,提高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綜合承載和資源優化配置能力”,以黨的重要文件的形式,明確了行政區劃在提高城市綜合承載力、優化城市資源配置能力方面的基礎性地位。
期待有效發揮撤縣設區等行政區劃手段在提升城市空間治理中的作用,必然會涉及城鎮地區行政區劃調整的一個核心問題,即城市發展的最優空間規模。空間規模對中心城市發展的影響并不是簡單的正相關,而是呈現出N型的變化曲線:當城市的空間規模較小時,適度的空間擴張可以促進經濟要素的聚集,從而發揮規模經濟效益;然而,城市規模的不斷擴大又容易誘發交通通勤成本過高、生產生活成本上升等一系列“城市病”,導致集聚經濟在城市的空間規模達到一定程度后出現邊際遞減;隨著城市空間和人口規模繼續擴張并在所處區域處于絕對優勢和中心地位時,就會形成區域性的城市結構,進而由中心城市的單邊發展轉變為區域性整體提升,最終擺脫由集聚經濟邊際遞減帶來的“效率瓶頸”。也就是說,撤縣設區對城市承載能力和資源配置能力的影響,一定程度上取決于城市規模是否已經達到最優。
從實踐層面來看,隨著近年來撤縣設區的大規模展開,許多城市不同程度地出現了“大城市病”。這在一定程度上與部分城市正處于集聚經濟邊際遞減帶來的“效率瓶頸期”有關。因此,進一步適度地撤縣設區有可能助推其突破發展瓶頸,更好地發揮對周邊區域的輻射帶動作用。這表明,在近年來的撤縣設區實踐中,直轄市、副省級市和其他省會城市調整的規模和強度均明顯高于一般的地級市,是存在其合理性的。鑒于此,有必要根據城市的類型和等級對撤縣設區的政策目標和具體路徑進行分類探討:由于撤縣設區的主要政策目標是通過擴展城市空間的方式促進城市和區域發展,因此應著重考慮城市發展的最優規模、城市在區域發展中的定位等因素。
具體來看,一方面,應繼續推動中心城市撤縣設區。從城市規模對城市發展影響的N型曲線來看,區域中心城市繼續通過撤縣設區的途徑擴展城市的發展空間,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強化中心市區與撤并縣市之間的聯系,促進城市功能的擴展和基礎設施的統籌規劃,提升城市的承載力和資源配置能力,最終推動市域的整體協調發展。當然,通過撤縣設區等形式擴展城市發展空間,只是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還有賴于合理的城市規劃、科學的區域合作與協調機制等其他政策的配合。
另一方面,適度限制中小城市撤縣設區。不同于中心城市在區域發展中的龍頭地位,作為中小城市的一般地級市由于其城鎮化水平、區域輻射水平、發展前景等均無法與中心城市相提并論。因此在今后的調整中,應以城市發展的合理空間規模為核心指標,綜合考察經濟發展和城鎮化水平、區域經濟發展的關聯度等因素,嚴格審核中小城市的撤縣設區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