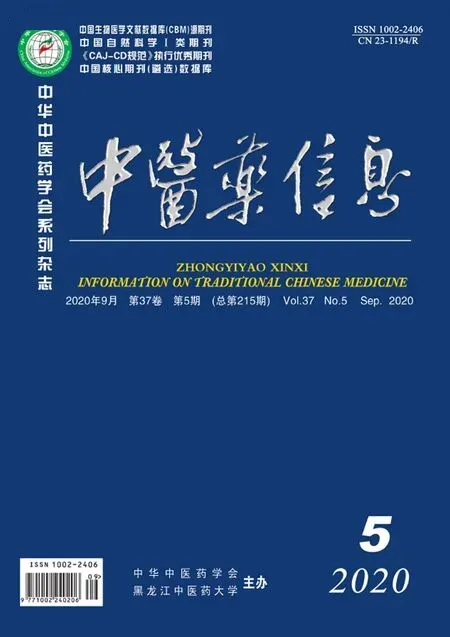李光榮教授治療更年期綜合征經驗
張娜,李光榮
(安陽市中醫院,河南 安陽 455000)
更年期綜合征又稱圍絕經期綜合征,是指女性由于卵巢功能逐漸衰退,雌激素水平下降引起內分泌失衡,植物神經功能紊亂從而出現的一組癥候群[1],臨床主要以月經紊亂、潮熱出汗、頭暈、頭痛、耳鳴、心悸、失眠、煩躁易怒、焦慮不安、抑郁腰背酸楚、面浮肢腫、感覺障礙等為主要癥狀,嚴重者甚至影響患者的正常工作與生活[2]。中醫學中有關該病的記載多見散于“絕經前后諸證”“年老血崩”“臟躁”“百合病”等論述中。調查問卷發現,更年期綜合征發病率高達92.1%,其發病與社會環境和自身心理狀態密切相關[3]。
目前我國大約有1/5的女性步入更年期,其中約有2/3會成為更年期綜合征患者[4]。
李光榮教授是第六批全國名老中醫藥專家學術經驗繼承工作指導老師,從事婦產科臨床工作40余年,對圍絕經期綜合征的治療療效顯著,筆者有幸成為李教授的學術繼承人,跟師侍診左右,現將恩師治療更年期綜合征的經驗總結如下。
1 以陰陽立論,調節人體陰陽平衡
《素問·上古天真論》曰:“女子七歲,腎氣盛, 齒更發長。二七而天癸至,任脈通,太沖脈盛,月事以時下,故有子”,說明腎精充足,天癸按期泌至,是女子月經按時來潮以及生長,發育和生殖功能正常的根本。而腎精和天癸屬于人體的陰類物質。《類經·十五卷·疾病類·腎風風水》亦言:“夫人生于陽而根于陰,根本衰則人必病,根本敗則人必危矣。所謂根本者,即真陰也”;《素問·上古天真論》載:“七七,任脈虛,太沖脈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壞而無子也”,說明更年期是女性的特殊年齡階段,其生理特點為體內腎精,天癸等陰類物質不足和耗竭,所以其病理特點也必然為“真陰不足”。陰陽本為一體,二者互根互用,互為平衡,陰液不足,打破了體內原有的陰陽平衡狀態,從而導致機體不能適應變化從而出現了一系列的病理癥狀,如月經紊亂等。因此李師認為,本病的病因是機體的陰陽失調,而“陰虛”是本病的基本病機,在陰虛的基礎上出現本虛標實的表現,其治療應以填補真陰為主。而腎陰為人體一身陰液之根本,所以補陰液,常以補腎陰為主。臨證時常常選用大補陰丸、二至丸、四物湯、左歸飲之類的滋補腎陰和陰血的方劑治療。陰虛嚴重者,可選用龜甲、鱉甲等血肉有情之品。根據陰陽互跟原理,陰虛者不能制約陽,陽亢于外,則見各種火熱之象,如潮熱,心煩,失眠等,治療還應選用清熱之品,李師常選用黃芩、黃連、黃柏、梔子、澤瀉等藥,清上、中、下三焦之火,直折火熱,釜底抽薪。但臨證中強調清熱莫過于寒涼,須中病即止,并加大滋陰甘潤之力,曲線救國。如加大生地黃、知母、白芍、麥冬、石斛、女貞子、墨旱蓮等藥的用量。總之,對于更年期癥狀的治療,李師強調以滋陰為主,清熱為輔,滋陰不過用滋膩,清熱不過用寒涼,以恢復肌體的陰陽平衡為治療大法。
2 立足五臟,糾正人體臟腑功能偏頗
關于本病的病因病機,歷代醫家論述豐富。古代醫家公認本病發生根本原因為“腎陰虛”。《景岳全書》中講:“五臟之陰非腎不能滋,五臟之陽非腎不能發”。《傅青主女科》載 :“經本于腎”“經水出諸腎”。現代醫家國醫大師夏桂成認為該病本質上是腎陰虧虛,癸水不能上濟于心,導致婦女更年期心-腎-子宮生理生殖軸功能的紊亂[5]。現代醫家班秀文認為本病關乎五臟,總責于腎[6]。而滿玉晶認為腎虛精血虧虛是圍絕經期綜合征的病理特點,腎氣衰天癸竭的過程中加深腎陰陽失衡……而出現一系列癥候群[7]。傅金英認為本病以腎陰虧虛為主,絕經前后婦女由于腎陰虧虛,陰損及陽,使陽浮于外,最終導致腎陰陽兩虛,見乍寒乍熱等[8]。總而言之,對于本病病機的認識,古今醫家大多以腎虛為主,尤其是以腎陰虛為主。
李師認為,本病的發生主要是因為腎虛,但五臟在生理上是相互關聯的,病理上是相互影響的,腎虛, 必會累及其他臟腑;同樣“五臟相移,窮必及腎”,其他臟腑功能失調,最終也會引起腎虛。因此更年期綜合征是以腎虛為主,五臟功能失調而出現的一組癥狀。婦女年老,腎陰虧虛,天葵漸絕,氣血生化乏源,故月經紊亂、量少、漸至閉經;腰為腎府,腎精不足,失于濡養,故腰膝酸軟;腎主骨,通髓,腦為髓海,腎陰虧虛,髓海乏源,腦竅失養,則頭暈、耳鳴、健忘;腎陰虛不能制陽,虛火內生,則潮熱、盜汗、口干、便秘、尿赤。火迫血妄行,則崩漏下血;虛火上炎,心火偏亢,擾動心神,則失眠、五心煩熱。陰損及陽,久之腎陽也虛衰,失于溫煦,則畏寒怕冷;腎陽虛,不能運化水濕,則面浮肢腫、帶下異常;腎陽虛,氣化失司,故尿頻,性欲低下。最終導致腎陰陽兩虛,諸病雜至。治則應以補腎為主,腎陰虛者應滋陰養腎,以左歸飲為主加減治療;腎陽虛者應溫腎助陽,以右歸丸為主加減治療;腎陰陽俱虛者應陰陽并補,以二仙湯為主加減治療。
李師認為本病的發生和肝相關。肝和腎關系密切,中醫學中有“乙癸同源”“肝腎同源”“精血同源”之說。肝藏血,腎藏精,精血同源,互相轉化,故肝腎陰血之間可以互相滋生,互相轉化;肝主疏泄,腎主閉藏,兩者相互制約,共同調節著女性的生殖功能保持正常。更年期女性腎陰虛,水不涵木,而致肝血不足,肝腎陰虧,藏泄失常,故表現為月經量少、紊亂。肝體陰而用陽,肝陰不足,則肝陽上亢,可表現為煩躁易怒、抑郁、多疑等情志異常、頭痛、頭暈、血壓波動等癥狀。因此李師臨證時,常在補腎的基礎上加入疏肝之品,如玫瑰花,柴胡,郁金,牡丹皮等。
李師認為本病發生和心相關。心和腎關系密切。心為君主之官,正常生理狀態下,心主火,心火下降,腎主水,腎水上升,兩者相交,稱為“水火既濟”。更年期婦女腎陰虧虛,腎水不足,不能上濟心火,導致心火獨亢于上,則見心悸、怔仲、失眠、焦慮不安等癥狀。正如《景岳全書·雜病·不寐》云:“腎水不足,真陰不升,而心陽獨亢,亦不得眠”。因此臨證時,李師強調在補腎陰的基礎上加入寧心安神或鎮心安神之品,如蓮子心,茯神,梔子,百合,煅龍骨,紫貝齒、磁石等。
李師認為本病的發生和肺相關。肺與腎的關系也很緊密,二者在五行上屬于“金水相生”的關系,兩者陰液相互滋生。肺腎陰虛,則可出現骨蒸潮熱、盜汗、月經量少等癥狀。因“肺主皮毛”,腎陰虛導致肺陰虛,則見面目憔悴、毛發干燥枯萎、皮膚蟻走感等癥狀。另肺為水上之源,腎為水下之源,兩者共同通調水液。腎虛,導致肺虛,水道失調,則見水腫,面部浮腫等癥。《丹溪心法·六郁》 指出:“人身之病,多生于郁。”《景岳全書·婦人規》 曾言:“婦人幽居多郁,常無所伸,陰性偏拗, 每不可懈。”李師認為在腎虛基礎上,氣機不暢是更年期綜合征中的常見病因,可見抑郁、失眠等癥,氣機上逆也可見煩躁易怒等癥。肝主疏泄,調理氣機;肺主氣,司呼吸,主宣發肅降,兩者共同作用維持人身氣機的升降運動。因此李師臨證時,下病取上焦,強調調暢氣機,肝肺同調,在理氣疏肝的同時,不忘宣通肺氣;強調宣肺利水以提壺揭蓋,消除水腫;強調肺腎陰血同補,以金水相生。常喜用桑白皮,桔梗、枇杷葉、杏仁等藥。
李師認為本病的發生和脾相關。王肯堂在《證治準繩》曰:“婦人童幼天癸未行之間,皆屬少陰 ;天癸既行,皆屬厥陰 ;天癸既絕,乃屬太陰經也。”即指出了在天癸將絕之時,是太陰脾經所主導的生命過程。脾為后天之本,脾主運化,為氣血生化之源;腎為先天之本,“先天”腎氣, 必賴“后天”脾的不斷滋養,才能發揮其生理效應。后天脾胃可以頤養先天腎氣[9]。且腎陽虛時多致脾陽虛,脾土不暖,溫運失司,水濕困阻,則見腹脹、納呆、疲乏、面浮肢腫等癥。故治療更年期疾病時,更當以健脾為要,因脾胃為后天之本,氣血生化之源,氣機升降之樞,唯有調理脾胃之氣,才能使水津四布,五經并行,和調五臟六腑, 使氣血生生不息,令水谷之精可以源源不斷地輸注于腎[10]。腎受陰精之奉養,又得水谷精微之助,五臟始能安和。因此在臨證時,李師強調在補腎的同時,注意補養脾胃之氣、調理脾胃的功能,從而有助于腎氣的補充,常用陳皮,焦三仙,雞內金,砂仁等藥。
綜上所述,李師認為,更年期綜合征發病的原因,是以腎虛為主的,五臟功能失調,其病機為本虛標實,本虛為腎虛,尤其是腎陰虛,標實為心、肝火旺。在治療中強調調理五臟,以恢復五臟的整體功能,達到陰陽平衡。
3 善用經方
中醫學中沒有更年期綜合征這一病名,但根據其心煩,失眠,潮熱盜汗等癥狀,于古代醫典中散在記載。《金匱要略》曰:“婦人臟躁,喜悲傷欲哭,象如神靈所作,數欠伸,甘麥大棗湯主之”。《金匱要略·百合狐惑陰陽毒病脈證并治》云:“百合病者,不經吐下發汗,病形如初者,百合地黃湯主之。”《金匱要略·人產后病》:“婦人乳中虛,煩亂嘔逆,安中益氣,竹皮大丸主之”。《傷寒論》:“血弱氣盡,腠理……往來寒熱,休作有時”之特點,可以看出,少陽病的發病具有時間規律性,這與更年期綜合征表現的陣發性往來寒熱有相似之處,因此,后世很多醫家在治療更年期綜合征時多從少陽入手,以小柴胡湯和解少陽之樞機,進而調和陰陽,失眠多夢時,可加入龍骨、牡蠣等重鎮安神之品[11]。《傷寒論》曰:“虛勞虛煩不得眠,酸棗仁湯主之”:“煩熱,胸中窒者,梔子豉湯主之”“少陰病,得之二三日以上,心中煩,不得臥……黃連阿膠雞子黃湯主之”。李師熟讀經典,善用經方。根據上述經典內容所述,臨證時常常選用甘麥大棗湯、百合地黃湯、竹皮大丸、柴胡加龍骨牡蠣湯,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酸棗仁湯,梔子豉湯、黃連阿膠雞子黃湯等經方,只要辨證得當,方證對應,很多處方都會有應用的機會,這就是經方魅力之所在。
4 善用易醫八卦臍針
易醫臍針療法是以易學理論、臍全息理論為指導,在肚臍即神闕穴實施針刺的一種新型針刺療法[12]。八卦原義是用8個符號(乾、兌、坤、離、巽、震、艮、坎)來表示8個不同的方位、不同的節氣(見圖1)。因為八卦與五行相關而,五行與人體臟腑有密切的聯系,所以八卦與人體臟腑有對應的醫學聯系。八卦臍針療法就是把肚臍視為一個后天八卦圖,八卦圖的12點處為上,為離為心為火,在人體對應心臟疾病、血脈疾病、眼目疾病、女性乳房疾病等。6點處為下,為坎為腎為水,在人體對應男女泌尿生殖系統疾病、耳病、視力病、水腫病等。9點處為左,為震為肝為風為陽木為雷,在人體對應肝膽疾病、眼目疾病等。3點處為右,為兌為肺為金為澤,在人體對應肺和氣管的疾病、口腔咽喉、皮膚疾病。1點處為坤為脾為土為地,在人體對應中氣不足的疾病、腹部 、腸 道、肌肉、四肢疾病等。5點處為乾為大腸為陽金為天,在人體對應著首腦、脊骨、關節疾病,畏寒、腎冷、腰背疾病。7點處為艮為胃為陽土為山,人體對應脾胃疾病、鼻口疾病、腫瘤、硬腫癥、結石、痤瘡及疣等皮膚疾病。11點為巽為膽為陰木,在人體對應肝膽疾病、血管、氣管、神經、風痛痹癥。臍針是由齊永教授發明的,在臍部實施針術,從而達到平衡陰陽、祛除疾病的目的[12]。李師研讀易經,熟練應用八卦臍針,臨證時常選用四正位,補腎三針,水火既濟,雷風相薄等卦位來治療更年期癥狀。
四正位就是指“上下左右”四個位置,即震、離,兌、坎四卦,在臍八卦全息中,四正就是心、肝、肺、腎四個藏,即五行里的火、木、金、水,是人體內的“十全大補”,主治人體全身性疾病,故有“四正位調全身”之說。如此則四維升降而生中氣,樞機運轉,木升金降,火水交濟,輪行軸運,四維既圓,中氣自旺,回歸身體“和”之道。治療上把四正位第一針扎在坎(水)位,第二針在震(木)位,第三針在離(火)位,最后一針落在兌(金)位,在“四正位”里面,其中坎離兩針又形成“水火即濟”,可調節陰陽。水火既濟就是指“坎和離”二位,為心腎所對應位置。坎為水為陰,離屬火屬陽,而水火既濟就是水與火的交融,是陰陽相交的具體體現,也是調整人體陰陽最基本的大法,落實到人體就是心腎相交,陰陽調和。補腎三針依序為“坤卦、乾(兌)卦、坎卦”的組合,形成土生金、金生水的相生格局,用于補先天之本。因坤土生乾金,在配伍過程中,坤卦加乾卦形成“地天泰卦”,引寓天地交而百病自消之意。乾金生坎水,藉以化生腎陰,使心火得腎水上濟而不至過旺。雷風相薄就是震卦、巽卦相配,震巽皆為木,是雙木相合的格局,其中震就是雷,在人為肝。巽就是風,在人為膽。雷屬陽木,巽屬陰木,雷風相薄就是調理肝膽,調暢全身的氣機。

圖1 易醫八卦臍針圖
李師讓患者取仰臥位,暴露肚臍,常規消毒后選用規格為0.25 mm×25.0 mm的毫針,根據癥狀選取不同的卦位相配,沿皮膚呈 15°,配合捻轉手法進針,進針深度約13~25 mm左右,留針35或55 min,每日1次,5次為1個療程,治療3個療程。
《周易》載:“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故留針35或55 min,寓陰陽相交,化生萬物之意。
5 輔助五行音樂療法
在中醫學中,五音入五臟,并且可以調節五臟。五音調和搭配,就成了一套養身大典。李師對更前期綜合征的治療,常常根據患者的不同癥狀,在針灸的同時,配合播放不同的音樂曲目,來輔助調和臟腑的陰陽。一般用《紫竹調》補心,《梅花三弄》補腎,《十面埋伏》補脾,《陽春白雪》補肺,《胡笳十八拍》補肝。總之通過播放不同的音樂,調整五臟的功能失調,恢復臟腑陰陽平衡。除此之外,老師還重視飲食和運動療法,建議患者應少進食溫熱香燥、刺激性強和肥甘厚膩之品,宜多選用滋陰補血的食物,積極參與體育鍛煉,多社交,通過豐富多彩的業余生活,增強體質,轉移注意力,輕松度過更年期。
6 典型病例
劉某,女,48 歲,2019 年 10月 12 日初診。主訴:停經2月余,潮熱、汗出、失眠3月。患者近1年來月經紊亂,經期20~90 d先后不定,量時多時少,多時需要服用止血藥出血方止,色紅,有大血塊,無腹疼。平素腰痛,膝軟,頭暈乏力,哈欠頻作,偶見耳鳴,視物昏花,心煩失眠,心悸易驚,情緒易于激動,看電視劇喜悲傷易哭,與家人交流,煩躁易怒,情緒不能自我控制。近3個月出現面部潮熱,盜汗,乏力,勞累后耳鳴,5~6 s自行消失,手腳心熱、口渴,納差,小便發黃,大便時干結。現停經2月余,諸證加重。舌紅,舌上可見細小裂紋,苔薄黃,脈弦細數,無力。查彩超:子宮正常,雙卵巢體積縮小,子宮內膜線樣。性激素六項:FSH:89 IU/L,LH:68 IU/L,E2:25 pg/mL,P:0.69 ng/mL,T:0.88 ng/mL。診斷: 絕經前后諸證 (肝腎陰虛,虛火上亢) 。治則:滋腎養心、疏肝解郁。處方:浮小麥30 g,炒酸棗仁30g,大棗10 g,百合15 g,生地黃15 g,女貞子15 g,旱蓮草15 g,白芍30 g,柴胡6 g,山藥15 g,當歸15 g,山茱萸15 g,枸杞子15 g,澤瀉10 g,炙甘草10 g,5劑,每日 1 劑, 水煎至400 mL分早晚2次口服。
2019年10月17 日二診:潮熱盜汗有所減輕,悲傷感減輕,哈欠減少,心悸緩解,仍難以入睡,睡后半夜易醒,醒后不能再睡,情緒易于波動,心煩躁,二便調,舌尖紅、舌上細小裂紋,苔薄白,脈弦細數。仍從上法,加重養陰清熱、鎮心安神之力。處方: 上方去大棗,枸杞子,加鹽知母15 g,鱉甲10 g,梔子10 g,紫貝齒(先煎)30 g,繼服5劑。同時加上八卦臍針,取水火既濟,補腎三針,雷風相薄,每日1次,每次35 min,針灸的同時,配播放音樂《梅花三弄》。
2019年10月27日三診: 藥后諸癥減輕,幾乎消失,自行停藥5 d后,癥狀又作,但程度減輕,近3 d來乏力,納呆,納呆,聞肉欲嘔,眠可,但時心煩懊惱,舌尖紅、舌上裂紋消失,苔薄白,脈弦細。治以滋補肝腎、健脾益氣、養心安神。處方:二診方減去酸棗仁,百合,澤瀉;加太子參6 g,桔梗15 g,焦三仙各15 g,雞內金15 g,淡豆豉15 g,繼服5劑。并繼續原臍針方案5 d。
2019年11月3日四診:藥后潮熱、汗出、心悸消失,眠可,心情愉快,舌淡紅、苔薄白,脈細。續服三診方3劑以鞏固療效。
按語: 此例患者年至七七,腎氣漸衰,腎陰不足,天癸漸竭,沖任虛衰,精血不能按期到達胞宮,故月經先后不定,量多少不一,終至絕經。腎陰為全身陰液的根本,五臟之陰液非此不能滋。腎陰虛外府失養則腰痛,膝軟。腎開竅于耳,腎虛精血不能上榮,則見頭暈,耳鳴。腎陰虛虛火上炎,則見潮熱、汗出。肝腎同源,腎陰虛導致肝陰虛,肝血不足,肝目失養則見視物昏花;肝陰不足,肝陽上亢則見頭暈,煩躁易怒、情緒激動不能控制。肝腎陰虛,血不養心,心失所養,則見心悸、怔仲、喜悲傷欲哭;心陰不足,心火上炎,則見心煩、失眠。氣陰不足則乏力。盜汗,口渴,手足心熱,尿黃、便秘、舌脈為陰虛有火,虛火上炎之征象。李師認為此患者出現典型更年期典型癥狀和臟燥的表現,《金匱要略·婦人雜病脈證并治》曰:“婦人臟躁,喜悲傷欲哭,象如神靈所作,數欠伸,甘麥大棗湯主之”。陳修園在《金匱要略淺注》中曰: “婦人臟躁,臟屬陰,陰虛而火乘之則為躁…… 所以然者五志生火,動必關心陰,臟既傷窮必及腎是也”。 故其病機為腎陰虛,陰虛火旺,虛火上炎,影響心肝所致,治療應以滋陰清熱,補腎、養心、疏肝為主。初診方選用甘麥大棗湯合左歸丸合二至丸加減。甘麥大棗湯為治療婦人臟燥的經方,方中,以浮小麥代替小麥,養心液安心神,專門斂汗治療盜汗。酸棗仁養心陰,補肝血,寧心神,斂汗生津。女貞子、旱蓮草為二至丸,配生地黃,專事養陰,陰液足則火熱消。山藥、山茱萸、枸杞子、當歸仿左歸飲之義,補陰養血,專門補養腎陰不足。白芍養血柔肝,柴胡疏肝解郁,澤瀉清泄三焦之火,直折火熱。百合潤肺清心、益氣安神。二診方證對應,諸證減輕,但仍以失眠為主,陰虛火熱證仍明顯,繼續用甘麥大棗湯加減, 并增強滋陰降火,鎮心安神之力。上方中去大棗、枸杞補益上火之品,加鹽知母補腎陰,并入血肉有情之品鱉甲,專入陰分養陰,增加養陰液之功。梔子入心、肝、肺胃、三焦,起清熱、除煩之功。紫貝齒咸,平,歸肝經,可鎮驚安神、平肝潛陽、清肝明目。同時用八卦臍針,取水火既濟,補腎三針,加強補腎作用,化生腎陰,使心火得腎水上濟,水火既濟,陰陽平衡。取雷風相薄,調暢全身的氣機,疏肝解郁。音樂《梅花三弄》具有“水”的特性,入腎,配合針灸,起補腎陰的輔助治療作用。三診服藥后諸證消失,說明方證對應,辨證準確。停藥后再復發,仍心煩失眠,心中懊惱說明病機仍在;納呆,乏力說明患者年高體弱,脾肺氣虛,應在繼續滋補腎陰的基礎上,加強健脾益氣之力。故在二診方的基礎上,減去滋膩的酸棗仁,百合,減去苦寒的澤瀉,加太子參氣陰雙補,桔梗開宣肺氣,焦三仙、雞內金健脾益氣,以肺脾雙補,增強益氣之功。加淡豆豉和梔子仿經方梔子豉湯之義,清熱除煩助眠。并繼續用臍針補養腎陰,交通水火,疏肝解郁。如此則腎陰充盛,虛熱得清,心陰充足,肝血得養,脾肺得補,故四診則諸證得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