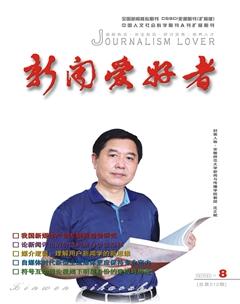公共理性視閾下的輿論沖突與融合
張月月 唐遠清
【摘要】輿論在演變過程中會因輿論生態失衡而出現輿論分化與沖突的情況,這與媒體報道方式、輿論環境、受眾媒介素養與心理等元素息息相關。一方面,輿論沖突違背了公共理性,但另一方面,輿論沖突也是為了維護公共理性。以孫楊拒檢事件為個案,論述輿論沖突與公共理性的關聯性;深層次、多角度反思與分析輿論沖突的成因;進而基于公共理性和規則意識,從多層面提出輿論融合與引導策略。
【關鍵詞】輿論沖突;孫楊事件;公共理性;融合與引導策略
一、輿論沖突與公共理性
輿論是利益相近或相同的人們在政治、經濟和其他交往活動中對公眾事務發生的意識反射,是社會各種力量交互作用的結果。輿論沖突表現為人與人、階層與階層、國家與國家間發生的輿論對撞。如果輿論訴求得不到滿足或受到打壓,將出現輿論激化和沖突。[1]新媒體的快速發展增加了媒體報道的及時性、多樣性、影響力,網絡議程設置主體的多元性和復雜性,使得網絡輿論常常呈現出與傳統大眾媒體上的輿論所不同的景觀,也極大地改變了輿論格局。[2]新媒體技術的發展和沖擊顛覆了傳統媒體的結構與運作模式,民眾輿論表達常處于情緒先于真相的無序狀態,信息安全與信息公開間的沖突交鋒日趨嚴重。[3]輿論演變整體呈現復雜多變、沖突加劇、撕裂的趨勢。在輿論演變過程中,不同輿論主體的利益訴求不一致,思想涵養不同,難免會出現非理性的輿論風向,公眾社會認知與表達過程中的種種問題,又反過來加劇了網絡社會的輿論沖突和激蕩。因此,需要通過探究輿論沖突的成因來尋找應對策略。其中,公共理性在輿論演變中擔任著類似于“審判官”的角色,影響著輿論的演變方向,把本身不屬于一個哲學范疇的元素巧妙嫁接在一起,成為處理輿論沖突的重要關鍵。
公共性與公眾性是輿論的內在價值,不可偏廢。輿論的公共性價值強調個人理性、權利本位和公共利益,即公共理性。[4]新康德主義者羅爾斯在現代政治哲學的意義上正式提出并系統闡述了“公共理性”的概念。他認為:“公共理性是一個民主國家的基本特征。它是公民的理性,是那些能夠共享平等公民身份的人的理性。這是法政公理觀念對社會基本制度結構的要求以及這些制度所服務的目標和目的所在。”[5]介于工具理性的“理性經濟人”與注重道德和價值理性的“有限理性存在者”之間,他還曾提出了“理性道德人”一說。引申來看,中國近年來日益重視國際合作,同時積極倡導與推動國際合作中的公平正義理念,這是個體理性與公共理性、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統一。但單個個體的努力仍需要在互動中對其他行為體產生影響,進而達到塑造整體環境的目的。[6]這種互動在互聯網領域的表現之一就是輿論的互動,因而公共理性視域下的輿論沖突與整合對象不僅包括新媒體社會中的個人和媒體,也包括國內外輿論。此外,哈貝馬斯在《交往理性》中提到交往理性具有語言性、程序性和主體間性等基本特征。在此意義上,人們在公共領域的交往中形成的一種具有特定價值共識的實踐理性就是交往理性,它對公共領域中人的行為、話語方式予以規范和引導。而此種意義上的交往理性也契合了公共理性的理論旨趣。[7]
公共理性在當代社會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中扮演著重要的“調解員”角色,能有效調節社會規范與個人自由之間的博弈與平衡。這里的“公共領域”是指在社會生活中形成的政治與文化的公共空間,是一個客觀存在的范疇,而非價值判斷的理性范疇。在孫楊拒檢事件中,媒體或網民自發形成的網絡公共領域——輿論場正是一個客觀存在,其中包括對涉事各方不同評價在內的沖突輿論,主要表現為主流媒體和自媒體輿論立場分歧、國內外媒體的慣性輿論沖突、自媒體內部不同平臺的輿論沖突,且輿論不斷分化反轉。
二、公共理性視閾下孫楊事件輿論沖突的成因
(一)部分國內主流媒體欠缺公共理性的偏頗報道
主流媒體影響力大,主導社會輿論。在孫楊拒檢事件初期和中期,部分國內主流媒體對孫楊整體持力挺態度,渲染一致抵外的輿論氛圍,卻未以擺事實講道理的態度客觀理性地報道和分析孫楊團隊自身行為的不妥。這些國內主流媒體欠缺公共理性的偏頗報道,助長了跟風輿論的偏頗態勢,為輿論沖突埋下了隱患。在事件后期,尤其在2020年2月28日孫楊裁決結果公布以后,不少自媒體開始反思報道孫楊團隊拒檢行為的不妥及對國際規則的違背,受眾開始反省和理性回歸,輿論開始反轉。此時,輿論焦點已經不是孫楊是否真的服用了興奮劑,而是孫楊團隊對規則的違背、對聽證會準備的不足、輿情應對的失敗。此前積極報道的部分國內主流媒體卻選擇了“低調”,缺乏及時有效的輿論引導。不難看出,在該事件中,國內一些主流媒體沒有堅持公共理性,對國際規則、法理實踐原則強調不足,違背客觀公正原則的偏頗報道造成了許多國內受眾對事件的錯誤認知,成為造成輿論沖突的重要原因。
(二)自媒體群體動員下非理性的“輿論狂歡”
目前自媒體傳播的極端化、碎片化、傳播下沉及輿論市場的活躍導致了傳播市場“劣幣驅逐良幣”的效果顯現,對主流媒體的公信力和傳播力起到分解作用。技術賦權的自媒體,賦予了每個人、每個群體充分的發言權,具有與生俱來的“親民性”,帶來了人際傳播和群體傳播效應。勒龐在《烏合之眾》中提到“群體的無意識行為取代了個體有意識的行為,這是現時代最顯著的特征之一”。同時指出,人們一旦形成群體,就會表現出智力下降、自信倍增、情緒激動等特點。[8]在孫楊拒檢事件中,國內微博、微信、知乎以及國外的Facebook等社交媒體上的言論滿天飛,“輿論狂歡”造成明顯群體極化現象。技術賦權和群體動員使不少缺乏新聞專業素養的所謂“公民記者”,缺乏對公共理性的基本尊重,在自媒體平臺上根據主觀臆斷評述此事,并非公正的情緒傳播超過了對事件真相的核查。而作為圍觀者的普通網民也在幾乎不受約束的網絡表達中宣泄著對事件的偏頗認知、偏激情緒,為輿論沖突奠定了非理性的群體心理基礎,最終造成缺乏公共理性的沖突性、群體性的“輿論狂歡”。
(三)狹隘民族主義裹挾下的盲從
從當下現實看,領土爭端、貿易摩擦、跨國公司涌入,再加上國內社會矛盾,成為極端民族主義行為的溫床。[9]違背公共理性、忽視客觀事實、避重就輕地盲從跟風,是“狹隘民族主義”的典型體現。從國內來講,在孫楊拒檢事件中,首先,部分主流媒體因缺乏理性反思的片面言辭,激發了國內民眾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其次,民眾被激發起來的熱情必然要尋找表達的路徑,不理智的盲從行為和網絡發泄就成為成本最低的選擇,他們通過各種社交媒體平臺踴躍發聲,脫離了就事論事、公平公正的公共理性的正常表達軌道。
(四)國內外輿論環境與應對理念的迥異
國內外政治環境和媒體制度的不同,造成了國內外輿論環境和輿論應對理念的迥異。長期以來,我國政府對于社會情緒的引導重在安撫疏導,主流媒體報道也跟著政府走,這與西方國家和媒體的路徑有較大差異。美國媒體極具商業化色彩,是與政治層面相對獨立存在的,在商業利益驅動下,美國新聞的理念與我國嚴格堅守新聞黨性原則的中國媒體有著巨大區別。這也是為什么中國媒體及官方近年來不遺余力地在反興奮劑問題上嚴防死守,但國際輿論仍然出現了很多對中國不利聲音的原因。本次孫楊拒檢事件又把中國泳壇推上國內外輿論的風口浪尖,可在萬眾矚目之下,國內主流媒體對事件避重就輕的片面報道,難免會引發國外輿論的批判,這成為該事件引發國內外輿論沖突的重要原因。
三、公共理性視閾下的輿論融合與引導策略
(一)重建媒介倫理體系,增強公共理性表達
獨立、公平、正義、責任、服務公共利益等原則,是長期以來新聞媒介應該堅守的倫理準則。伴隨著社會轉型和新聞行業自身的發展變化,在新媒體時代,媒介倫理的內涵和外延也在不斷更新發展,除了進一步堅持傳統媒體倫理價值體系之外,還需要融合基于技術和平臺的新媒介倫理要求,增強解決現實問題的建設能力。因新技術而生的自媒體、社交媒體一方面會對新聞倫理產生沖擊,但另一方面也能夠讓主流媒體意識到重建媒介倫理體系的重要性,警惕民粹主義等因素影響下的輿論分化與沖突,這需要主流媒體與非主流媒體的共同努力。作為權威媒體,主流媒體應堅守媒介倫理精神,要承擔反映主流意識形態、引導主流輿論、傳播主流價值觀等職責,以伸張公平正義、解決實際問題、強化公共服務與社會責任為目的,而不能僅僅強調堅持“正面報道”為主。當普通網民面對大量不知真偽的網絡信息和一些偏頗的極端言論時,主流媒體就需要設置“意見領袖”來為其分析、解惑,從而避免輿論的盲目性。[10]
美國心理學家帕特里夏·華萊士曾言:“一旦人們相信自己的行為不會被追到個人頭上,他們就會變得不那么受社會習俗和戒律的約束。”[11]這也是網絡新媒體及網民缺乏公共理性表達的原因之一。因此,主流媒體以“弘揚社會責任,堅持正確輿論導向”為價值指向,關鍵在于要堅守和增強公共理性的表達方式。在孫楊拒檢事件中,主流媒體應引導輿論,重建媒介倫理體系,堅守公共理性原則,客觀全面報道事實、維護正義、主動發聲、敢于發聲,對孫楊團隊拒檢違規問題進行反思與揭示。只有將建立在公共理性之上的表達方式和內容傳遞給自媒體參與者和普通網民,才能引領他們把現實利益問題如實地通過輿論客觀、理性地表達,承擔起社會責任,遵從公共立場原則,對輿論進行理性反思和實踐檢驗,努力化解主流媒體輿論場與自媒體輿論場的輿論沖突。
(二)貫通“官民”輿論場,強化協同輿情治理
中國當下輿論場可分為由主流媒體支撐的官方輿論場和由非主流媒體支撐的民間輿論場。[12]官方輿論場的主體通常包括政府及相關權力部門、主流媒體及網民,民間輿論場的主體包括第三方機構、自媒體及網民。近年來,中國官方輿論場與民間輿論場的輿論沖突此消彼長的趨勢愈演愈烈。新媒體時代,相互制約又相互促進、融通融合、平分天下的輿論新格局已經形成。但這并不代表官方輿論場就失去了公信力和職責使命,反而更應彰顯官方輿論場主動發聲、協調議程的“主人翁精神”。為了化解官方輿論場與民間輿論場的輿論沖突,政府及相關部門和主流媒體應該擺正自己的位置,多管齊下貫通“官民”輿論場,強化協同輿情治理。為此,要堅持公共利益為導向,公共利益是兩個輿論場整合和共振的前提,也是公共理性的共同目標,在此基礎上形成的輿論力量,能夠消解和糾正輿論場中偏激和消極的部分。其中,政府及相關部門應直面問題,通過主流媒體主動理性發聲,協調媒介議程與公眾議程,達成二者基于公共利益的公共議題認同;及時進行有針對性的輿論引導,加強政府、官方機構當事人與民間輿論場的意見溝通和協調,形成良性循環。
在孫楊拒檢事件中,主流媒體應盡早正視問題,主動設置議程,引領客觀、公正、正確的輿論風向。同時要尊重公眾邏輯,真正“俯下身來”,在發揮官方輿論場核心作用的同時,也應激發民間輿論場的話語活力,吸取網絡時代的傳播方式及運營模式,第一時間關注民間輿論場焦點,及時調整媒介議程,攜手自媒體及第三方機構協同治理輿情,在互動中提升正面輿論的影響力和引導力,打通并推動官方輿論場和民間輿論場相互配合、協調發展。
(三)堅持以“理”為本,避免狹隘民族主義
堅持以“理”為本,以理服人,這個“理”不僅指新聞媒介倫理,還指公共理性、規則意識、同理心等,其針對的對象既包括政府、主流媒體等,也包括自媒體及當事人在內的普通網民。雖然中國當代的政治體制和核心價值理念與西方社會不同,但對于道德原則和法律原則的區分與融合,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的平衡與協同,社會公平正義的理論與實踐,公共理性與交往理性的反思與確證,同樣是中國現代性公共領域建構過程中必然經歷的現實環節。[13]
另外,“網絡民粹主義”思潮影響了公民正確愛國主義價值觀的生成和鞏固,對此必須引起足夠警惕,既要將民粹主義話語表達和思維方式對愛國主義價值觀的消極影響加以明晰,又要警惕將樸素的愛國情感打入民粹主義陣營。[14]就自媒體來說,因其具有自發性、草根性、非理性、易傳性的特點,故需要兼顧行業自律和相關部門的他律;需要遵循媒介倫理和公共理性,不斷提高媒介專業素養,不造謠、不傳謠、不攻擊,堅持客觀理性傳播。對于普通網民來說,在互聯網社會圈層細分化的現狀下,觀點越分化,就越需要專業看法的從容表達、正視問題的理性回歸、規則的遵守與尊重,不被所謂的情緒所綁架,這是對新媒體信息時代每一個公民的要求。
在孫楊拒檢事件中,作為新時代的偶像和網絡大V的孫楊,對粉絲文化、社交情緒、民族主義的調動都反映了時代的需求。但在社會契約和規則的大背景下,需要熟知和遵守規則。不可否認的是,孫楊團隊的拒檢行為違背了國際規則和公共理性,這或許源自個人長期以來對規則的輕視或懈怠態度;另外,孫楊團隊在聽證會上的準備不足、對法庭程序的藐視等,也是造成后來不利裁判結果和輿論危機的原因。除了孫楊一案,中國體育此前沒少吃輕視相關行業規則和法律法規的虧,如當年中國足協與卡馬喬的合同糾紛、舉重選手黎雅君因“無視”規則丟掉奧運會金牌等事件。而國安和恒大之所以能打贏“國際官司”,無外乎他們吃透了規則、應對專業,掌握了于己有利的完整“證據鏈”。由此可見,不論是網絡空間的媒體還是公眾個人,均需撇開身份差異和輿論偏見,避免狹隘民族主義,在一定的約束條件和行為準則下行使網絡權力,堅守以“理”為本,遵循共同的行為尺度,才會減少網絡輿論沖突。
(四)審視國內外輿論環境,提升輿論引導的時度效
在如今全球化語境與新媒體蓬勃發展的媒介環境下,國內國際輿論相互影響,通過媒體傳播、文化交流等多種方式發生“溢出效果”。即兩者產生“共焦點”,由國際輿論場“由此及彼”的作為和延伸報道后,又“溢回”國內輿論場,也就是人們常說的“出口轉內銷”,再次形成新的輿論焦點,從而對中國的國際形象和國內社會情緒都產生影響。[15]隨著中國國力的提升,雖說近年來國際涉華輿情正面和積極的聲音明顯增多,對敏感問題的報道有所減少,但依然存在“不和諧音”。
在這種背景下,我們需要全面認識國際輿論的多元復雜性,順應國內外輿論融合的趨勢,謹防過度引導和議程設置的反效果。尤其在涉及國家利益的媒介事件中,我國官方和主流媒體的態度應理性冷靜,沉著應對。既要清醒審視國際輿論中有誤讀和歪曲報道中國的內容,也要客觀認識正面呈現中國形象的內容。對于“不和諧音”,我們要找到問題所在:一方面,國內社交媒體正在成為國際輿論的“指南針”,尤其當外媒難以從官方渠道獲得第一手信息時,這種傾向就愈加明顯;另一方面,國內部分媒體的報道有失偏頗。因此,首先要自我審視,以強公信力的主流媒體和官方機構設置好議程,暢通信息渠道,消除國內非理性輿論。其次,應當堅持國內外互動下的理性對話,盡力提升網民媒介素養,勿讓非理性言論成為國外輿論的“笑柄”。再次,應加大對外傳播力度,及時扭轉信息流進流出“逆差”,爭取更多理解和支持,讓正面、積極的輿論成為國際輿論場的主流聲音,提升輿論引導時度效。
在孫楊拒檢事件中,倘若主流媒體正確引領民間輿論場,堅持從公共理性出發主動發聲,對孫楊拒檢行為的不妥及時進行反思,給國內外受眾一個圓滿交代,或許對于建立中國反興奮劑的國家信用和美譽度都將大有幫助,也能夠震懾那些心懷不軌、企圖給運動員使用興奮劑的教練及其他相關人員。同時,這次事件也是對中國運動員和體育界的一次提醒,提醒我們如何正確指導運動員面對興奮劑檢測的態度,合法合規地保障運動員權益;如何在發生國際訴訟糾紛時更好地把握規則、贏得主動;如何在國際糾紛中傳遞好中國聲音,塑造好中國形象……這些都是需要反思的問題。
四、結語
隨著社會公共理性的提升和媒介權力的釋放,在國內外復雜輿論形勢下,轉型期的輿論更加活躍,無論是主流輿論還是非主流輿論,輿論高漲是由社會矛盾不能或長期沒有解決而激發的,因而輿論在演變過程中的輿論分化與沖突趨勢日漸明顯。此時,各輿論場“硬碰硬”不是良策,“刪禁堵瞞”不是出路,“避重就輕和模棱兩可”更不可取,主流媒體要樹立“主人翁精神”,以“公共理性”為基點,以“客觀全面”為方針,以“解決問題”為目的,以“共情傳播”為效果。同時,尊重和親近新媒體技術下自媒體支撐的民間輿論場,逐漸實現輿論整合與引導方法的轉變。最后,針對國內公眾和國際社會輿論,不能任憑“沉默的螺旋”自個兒轉,而要主動牽引、有效把向,以消除主流媒體輿論場與非主流輿論場、國外國內輿論場和自媒體自身輿論場內的輿論壁壘,以追求公共利益為導向,使新時代的輿論分化與沖突日趨融合。
[本文為中國傳媒大學教改項目“新建專業新聞學(新聞評論方向)建設”項目(編號JG180502)成果,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重大輿情和突發事件輿論引導機制創新及應對策略研究”(編號20ZDA059)成果]
參考文獻:
[1]劉建明.從輿論混沌到民變的輿情演變及模型[J].新聞愛好者,2014(11):54.
[2]金兼斌.社會化媒體時代網絡輿論需要把脈[N].社會科學報,2008-04-26(006).
[3]童兵.新媒體時代輿論表達和輿論引導新格局[J].新聞愛好者,2014(7):5.
[4]郭小安.輿論的公共性與公眾性價值:生成、偏向與融合———一項思想史的梳理[J].新聞與傳播研究,2016(12):53.
[5]康德.歷史理性批判文案[M].何兆,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25.
[6]劉雪蓮,桑溥.新型國際合作理論:國家理性二元統一的視角[J].國際觀察,2018(3):8-9.
[7]梅景輝.“公共理性”的現代性反思與建構[J].江海學刊,2015(5):75-81.
[8]法斯塔斯·勒龐.烏合之眾[M].董強,譯.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18:6.
[9]張淑娟.批判與反思:對狹隘民族主義的再認識[J].學術界,2016(12):96-106.
[10]關梅.“蝴蝶效應”與網絡輿論引導[J].新聞界,2012(3):56.
[11]Wallace Patricia.The Psychologyofthe Internet[M].Britai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124-125.
[12]張濤甫.兩大輿論場:從競爭到融合[J].新聞與寫作,2019(4):58-59.
[13]梅景輝.“公共理性”的現代性反思與建構[J].江海學刊,2015(5):75-81.
[14]崔聰,張勵仁.“網絡民粹主義”思潮影響下愛國主義價值觀培育的挑戰與應對[J].理論導刊.2020(1):112-117.
[15]劉小燕,李云翔.國內政治議題的國際溢出效果研究[J].國際新聞界,2015(8):20-32.
(張月月為中國傳媒大學新聞學院博士生;唐遠清為中國傳媒大學媒介評議與輿論引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海南師范大學新聞傳播與影視學院特聘教授)
編校:董方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