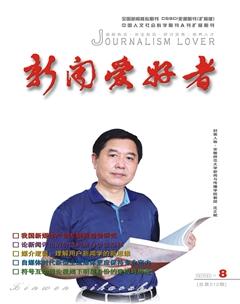增強健康意識的網絡媒介功能研究
任偉榕 郝雨
【摘要】在新時代的中國,健康已經被擺在以人為本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在日常生活中增強人們積極正向的科學健康意識越發重要。由于健康意識是一種在認知和行動基礎上對待健康的態度,網絡媒介能夠通過影響人們的認知與行動來增強人們的健康意識,發揮的主要功能包括通過信息傳遞機制和社會支持機制對增強健康意識產生積極效應。因此,需要構建良性的網絡媒介氛圍與健康的社會網絡環境,提升社會網絡資源的質量,從而為人們積極正向的科學健康意識維系發揮重要功能。面對健康風險的持續存在,網絡媒介與人們健康之間的關聯研究將是今后需要持續探討的重要課題。
【關鍵詞】健康意識;健康風險;媒介傳播;社會網絡
當前中國經濟社會水平已得到極大提升,人們對自身的健康也越來越重視,進入到新時代的社會,如何在日常生活中維系科學的健康意識日益成為人們實現美好生活的重要需求。隨著人們通過網絡媒介獲取健康知識及社會資源變得越來越重要,網絡媒介與健康獲得之間的關聯討論也成為重要話題。各類媒介新聞中越來越多地報道“癌癥”“心梗”“猝死”等,直接在那些最健康最無關的年輕人中產生著心理陰影。與此同時,“養生文化”“全民健康”“健身保養”等也悄然興起,并受到熱捧,盡管媒介數據和新聞報道更偏向于告訴社會大眾或許健康意識的增強只是相對性的、暫時性的、小范圍的,但同時這樣的媒介傳播又在無形中影響了人們對健康的認知與態度。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無論從所探究的一些起因、居民的防范意識,還是從零零散散出現的一些采購醫療物資小熱潮等來看,實際上都表明網絡媒介與健康意識之間存在緊密關聯。
一、增強全社會應對健康風險的健康意識
現代社會是風險并存的社會,其中的健康風險尤為重要。健康風險既可能來自外部環境,也可能來自人們的主體認知。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帶給人類的健康風險,深刻表明了外部環境與主體認知的不同維度采取應對健康風險策略的重要意義。如果說外部環境具有諸多不確定性,那么人們對健康的主體認知則會通過一定的方式改變或增強,正如當人們充分了解到新冠肺炎疫情的科學知識后,就能夠采取積極正向的健康意識以應對疫情帶來的健康風險。因此可以講,增強人們科學的健康意識對應對健康風險是十分重要的。通俗來講,健康意識表示的是人們對日常生活方式與健康問題聯結程度的認知、態度及理念等,如生活中的飲食習慣、運動保健、體檢預防、疾病應對等能影響到健康的諸多內容[1],人們對于日常生活方式的關注程度就取決于對自身健康重視的自覺程度。一個人若具有積極正向的科學健康意識,在日常生活中就會持續關注自己的健康狀態,具體表現為在不同的資源條件中積極收集和靈活運用各種健康信息,并經常參與各種健康活動,從而始終保持活躍的健康動機[2]。
然而,人們應對健康風險的健康意識會受到諸多因素影響,因而形成積極正向的科學健康意識并不容易。盡管2017年《中國家庭健康大數據報告》顯示國民的健康意識正在逐漸增強,但在與2013年的數據對比中發現,2017年一線城市白領階層中高血壓患者的平均年齡下降了約0.8歲,其中存在著不可忽視的兩大問題:既有慢性病的增加中顯現出的患者年輕化趨勢,也有一線白領階層出現的健康狀況下滑。之所以會產生如此社會問題,一方面可以從“快節奏、壓力大”的工作勞動中尋找原因,但另一方面就在于人們對于健康生活與健康風險的認知意識仍存在不足。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發的初期,人們由于相關知識信息的不具備造成的健康恐慌,也揭示出人們積極正向的科學健康意識仍有不足,更加表明增強健康意識對應對健康風險的重要意義。
二、網絡媒介對健康意識培育的功能分析
從影響健康意識的因素來看,除去個體自身與環境特征因素外,人們通過所擁有的網絡媒介及其建立起的網絡資源會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媒介化、信息化、網絡化持續發展的現代社會,人們的日常生活已經越來越緊密地關聯于網絡媒介,使得網絡媒介的健康意識功能效應更為明顯。其中的網絡媒介不僅包括了可以進行知識和信息傳遞的媒介方式(傳遞各類健康知識和信息等),更包括了深層次上的社會網絡資源(為人們形成健康生活方式提供支持),以此培育人們的健康意識、產生健康知識信息的傳遞功能和健康網絡資源的支持功能。
(一)健康知識信息的有效傳遞
從健康傳播學的視角來看,在健康意識的形成過程中,網絡媒介等的健康知識信息傳遞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健康傳播即是通過政府、醫療機構和專家、民間等各種渠道,運用多樣傳播媒介和方式,為維護和促進人們的健康而將醫學研究成果和健康信息等收集、制作、傳遞、分享的過程。在有效的健康傳播中,人們會獲得與健康相關的知識和信息等,同時因為大多數人會下意識地通過健康信息來確認自己健康所處的狀態,人們對于健康的關注度也就越發提高[3],從而喚醒自身的健康意識。例如應對疫情風險時通過“健康碼”的媒介信息確認,就能夠引起人們對于健康狀態的關注程度。在健康傳播的過程中,正是傳播媒介和傳播方式的存在,才促進了健康知識和信息的流動,而這又恰是網絡媒介的重要組成和功能之一。已有研究對此驗證,經常通過網絡媒介傳遞的健康知識和信息會影響到個體對健康的關注程度,個人使用網絡媒介共享和獲取健康知識信息的方式是形成健康意識的重要因素[4][5]。
進入到信息化時代,在信息技術的持續發展中,移動互聯網的接入、社交媒體等新媒介的普及使人們構建社會網絡更為便捷,傳遞健康信息和共享健康知識的渠道也更加多元。具體來說,人們通過廣泛的網絡交友、積極的網絡討論、大量地瀏覽健康信息網頁,從而對健康有一定的認知和理解,并通過論壇、微博、微信等促成健康群體活動,出現健身、保健、養生、綠色生活等重要社會熱潮,維持著人們健康動機的活躍。由此可知,在當前的社會發展中,網絡媒介的信息傳遞機制更是促進健康意識的重要渠道。經常能夠看到,人們想了解某一關于疾病或保健的知識信息時,在尋求專業的醫院機構或醫師之外,通過網絡媒介就可以滿足相關的需求。即便面臨紛繁復雜的信息捕捉狀況,但在對互聯網、社交媒體等的充分利用下,依然能更為快捷地獲取關于健康的信息,解決相關的健康訴求。相關數據也在說明健康知識的關注量和互動量顯著上升,如2019年今日頭條發布的健康大數據就分析出,今日頭條平臺的健康科普信息瀏覽量達550億次,健康咨詢信息收藏數量超過7億次,點贊數近3.3億,評論量也較上年上漲近140%。在這之中,年輕群體尤其是“95后”對健康知識和信息的興趣指數增速明顯。因此,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只要善于利用網絡媒介傳遞或獲取健康知識和信息,就能夠增強對科學健康意識的培養,從而培育有利于健康的生活方式習慣及積極應對健康風險。
(二)健康網絡資源的全媒體支持
網絡媒介對健康意識影響的重要性更多體現在構建社會網絡及獲取網絡資源功能上。社會網絡是一種基于“節點”(個人或組織)之間相互連接的“網絡”,是關注人們之間互動、聯系、關系的社會結構,相互連接起來的聯系即為各種社會關系,被視為“線”,這些“節點”和“線”形成的一個個網絡狀結構成為人類社會形成的基礎[6],影響到人們的意識和行為,對人的成長與發展起到了重要的動力學作用。在前述知識信息傳遞中發揮關鍵作用的各類知識信息傳播媒介和知識信息發出者以及公眾個人,實際上都可以看作是網絡中的“節點”,“節點”相互聯系后就構成社會網絡,健康知識和信息在這些社會網絡中沿著“線”進行傳遞,實際上就轉化為各類健康資源,公眾則在“網絡”中接觸和獲取到這些健康資源,使得健康意識得以培育。已有研究指出,社會網絡的規模和結構會影響到健康知識信息的傳遞[7]。也就是說,健康知識信息傳遞已經給予健康意識培育的基礎,網絡媒介的信息傳遞、知識共享等的達成又離不開人們構建的社會網絡。構建高質量的社會網絡對于人們的科學健康意識培育是有益的,社會網絡的質量較差則可能給予健康意識負面或消極的影響,社會網絡的瓦解甚至會破壞形成的健康意識[8][9],體現出社會網絡對于健康的重要支持功能。
健康社會學的研究領域強調了人們的社會網絡資源對于健康維系的重要性,指出人們所擁有的不同社會文化傳統、所屬的不同社會網絡對健康的態度和行為存在重要影響。諸多研究更是直接將社會網絡視為影響健康意識的重要中間機制,即社會支持、社會資本等社會網絡可以充當社會經濟地位等主體特征與健康意識之間的一條途徑[10]。尤其是當人們的物質生活條件達到一定水平后,從社會網絡資源中所獲得的社會支持以及對于生活的參與機會和自主性甚至將成為健康意識的決定因素。即與社會網絡成員長期互動,會形成一種對資源獲取方式和資源可得性的固定心理感知模式,對于健康意識的培育至關重要,即人們可以從社會網絡中認識的成員、結交到的關系中互相交換分享健康知識信息、共同監督參與有益健康的預防性行為,可以在遇到健康問題時采取規避、解決和分擔等方法,對健康維系提供直接有效的社會支持。當健康知識信息的傳遞和共享為人們健康意識的培育創造條件,直接的物質與精神的社會支持就會在健康意識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產生影響,結構化下的網絡支持在潛移默化中更進一步影響了人們的健康意識,使人們的健康意識逐漸趨同化。例如,在新媒體和社交網絡的“造勢渲染”下,諸多被稱為“中產階層”的群體,都不約而同地將“跑步”作為自身的健康“慣習”,出現了諸如“跑吧”“跑圈”“跑團”等各種小型社交網絡,這些網絡資源為個體的健康意識培育起到了重要的支持作用。
三、增強健康意識的網絡媒介對策
從前文分析可以看出,網絡媒介對健康意識培育的主要功能體現在:一是網絡媒介中的信息傳遞功能,即傳遞健康信息、分享健康知識,使人們不用再依靠專業機構或專業教育等方式就能夠關注健康及認知健康;二是表現為構建社會網絡的社會支持功能,即通過網絡媒介構建起的社會網絡資源及結構會影響到健康意識的培育過程,其中既包含健康資源的獲取,更包含健康生活圈的建立,從而使健康意識趨于良性且穩定的維系。為此,構建良性的網絡媒介氛圍與健康的社會網絡環境,能夠提升社會網絡資源的質量,從而為人們增強積極正向的科學健康意識發揮重要功能。
(一)構建網絡媒介的良性氛圍
構建良性的網絡媒介氛圍對于人們健康意識的增強會產生積極影響,不論是主流媒體抑或自媒體等,都需要在健康意識的積極正向引導方面共同努力。身處信息化的社會中,很多時候人們會通過網絡媒介尋求健康知識信息,一旦網絡媒介釋放錯誤或消極的健康知識信息,就不但會對尋求者帶來困擾,更會在社會層面引發危機。如出現過的將某些食物視為健康之寶,而實質上是誤導公眾;又如疫情初期紛繁雜亂的關于治療疾病的一些媒介傳播,導致公眾急切的社會心態,進而導致恐慌行為的產生。因此,應規范網絡媒介對于健康知識信息的科學傳播,構建起網絡媒介的良性氛圍。網絡媒介傳播健康知識信息既需要政府部門的引導與規范,更需要科學傳遞與汲取,需要政府、媒介及公眾的多方共同努力。
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中,網絡媒介將疫情最新數據信息和新冠肺炎的預防、診治、科研成果等專業知識及時準確地傳遞給公眾,喚醒了公眾的健康意識,讓公眾自覺采取隔離和防護措施,并且加強對流行病學的了解度和警惕性,作用十分明顯。在這一過程中,不僅有電視新聞聯播節目、廣播電臺、新華社及《人民日報》等主流媒體發布國家決策和部署、對話專家進行疫情分析,出版社等傳統媒介及時出版預防手冊、防護指導等,《新京報》、澎湃新聞、《三聯生活周刊》等媒體則發出實地探訪的深度前線報道,而且有疾控機構、醫療部門、醫生個人的網站、微博、公眾號的疑問回應和健康科普,抖音、快手等當紅媒體和直播、短視頻等新興方式不可忽視的傳播度和便捷性。傳統媒體在收集、發布大量權威健康知識和信息的同時,新興網絡媒體進一步擴大了健康知識信息受眾面和及時更新健康內容,促進了公眾健康意識的增強。可以看出,網絡媒介的多方聯動,共同圍繞公民健康的積極正向引導,有助于人們獲取更為豐富且科學的健康知識,從而在日常生活中增強健康意識。
(二)擴展健康的社會網絡環境
在網絡媒介的積極正向引導以外,人們自身生活于健康的社會網絡環境中同樣十分重要。在健康的社會網絡環境中,人們能夠獲得包括信息交換、行為監督、物質精神支持等諸多網絡資源的支持,從而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以此培養起積極正向的科學健康意識。在日常生活的健康關注方面,如果缺乏健康的社會網絡環境,不僅無法深入了解有益健康的健康行為和相關的健康知識,更缺少社會網絡中成員的支持與協助,積極正向的健康意識就難以建立。在現代社會中,盡管追求個體化的趨勢日漸明顯,但如果失去社會支持,個體在諸多方面將無法保障,健康即是如此。當個體面對健康風險時,高質量的社會網絡資源能夠給予很大支持。因此,需要充分通過網絡媒介方式,建立起自身積極健康的社會網絡環境,以此獲得更多的健康支持。
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應對過程中,可以看到人們通過多元化的網絡媒介渠道構建起維系自身及家庭的健康網絡體系,不僅分享了健康知識,更獲得了健康支持。由于在公共衛生危機中,個體的力量是很微弱的,在應對疫情的全民總動員中,人們通過微博、微信等媒介渠道構建起共同的防疫社會網絡,也從中獲得了健康支持并增強了戰勝疫情、健康生活的信心。在當今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從“線上線下”的網絡環境中獲取健康信息及尋求健康支持也越來越常態化,建立起健康生活方式的社會網絡圈就顯得尤為重要。不難理解,構建健康的社會網絡環境,對于積極正向的健康意識培育能夠發揮積極的社會功能,人們通過社會網絡環境直接或間接地聯結起來,也將健康意識嵌入健康社會網絡環境的日常生活中。
(三)健康管理從“治已病”向“治未病”轉變
風險社會的來臨使得健康風險持續存在,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的發生和擴散,讓人們對于“健康中國戰略”所圍繞的“疾病預防和健康促進”核心有了更切實的體會。這對廣大民眾提出的健康要求是,不僅要已病后能夠治愈,更要在未病時增強預防能力,在健康管理中從“治已病”向“治未病”轉變,培養自身主體的健康意識,提升個人的健康素養。在此方面,良性的網絡媒介氛圍與健康的社會網絡環境,能夠提升人們所處的社會網絡質量,從而對增強健康意識產生積極效應。對于網絡媒介越來越豐富的未來,這一功能或許會越來越顯著,而伴隨健康風險的持續存在,網絡媒介與人們健康之間的關聯研究將是需要持續探討的重要課題。
四、結語
當前中國社會已進入新時代,在人們追求美好生活的過程中,健康已經被擺在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國家公布《全民健康素養促進行動規劃(2014—2020年)》和實施《“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旨在通過多種方式將居民科學健康觀和健康意識樹立起來,實現以“心動”促“行動”,從源頭推動健康發展。中國民眾仍面臨著預防疾病、增強體質等為健康投資和提高健康意識這一嚴峻的局勢,只有真正將自己作為自身健康的第一責任人,擁有并不斷提高積極正向的健康意識,才能提升健康素質,培養健康的生活方式,把健康融入生活的方方面面。
參考文獻:
[1]Rama K.Jayanti,Alvin C.Burns.The antecedents of preventive health care behavior:An empirical study[J]. Journal of the Academy of Marketing Science,1998,26(1):9-15.
[2]Hyehyun Hong.Scale Development for Measuring Health Consciousness:Reconceptualization[J].http://www.instituteforpr.org/research/measurement_and_evaluation,2009.
[3]高北晨,王施施,廖曉梅.身體“在場”與心靈的“缺席”:我國新媒體抑郁癥健康傳播現狀與路徑探索——以癌癥健康傳播微信公眾號系列推文為例[J].東南傳播,2020(4):11-17.
[4]Iversen A.C.,Kraft P..Does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health consciousness influence how women respond to health related messages in media?[J].Health Education Research,2006,21(5):601-610.
[5]Rodgers Shelly,Chen Qimei,Duffy Margaret,Fleming Kenneth. Media usage as health segmentation variables[J].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2007,12(2):105-119.
[6]John Scott. Social Network Analysis:A Handbook[M].London:Sage Publications Ltd,1991.
[7]趙延東.社會網絡與城鄉居民的身心健康[J].社會,2008(5):1-19.
[8]郭慧玲.由心至身:階層影響身體的社會心理機制[J].社會,2016(2):146-166.
[9]DebraVandervoort.Quality of social support in mental and physical health[J].Current Psychology,1999,18(2):205-221.
[10]Uphoff Eleonora P,Pickett Kate E,CabiesesBaltica,Small Neil,Wright John.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social capital and socioeconomic inequalities in health:a contribution to understanding the psychosocial pathway of health inequalities[J].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Equity in Health,2013,12:54.
(任偉榕為北京工業大學文法學部、北京社會管理研究基地研究人員;郝雨為上海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編校:王 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