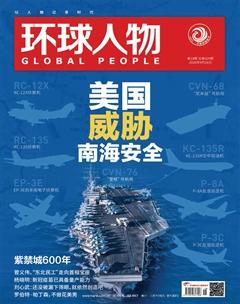王安石家族,才女無德禍事多
李開周
有宋一朝,多出才女,最著名的當數李清照,其次是朱淑真,再次便是今日不太知名但當時頗有影響的幾位才女,比如王安石的妻子、妹妹和幾個女兒。
先看一首七言絕句:西風不入小窗紗,秋氣應憐我憶家。極目江山千里恨,依前和淚看黃花。
這是王安石大女兒的詩作,寫于出嫁后,表達了對娘家的思念之情。詩意淺白,意境雖不甚高遠,但平仄工巧,韻律舒緩,是非常規整成熟的七言律絕。尤其是“極目江山千里恨”,相當大氣,格局一下子上去了。
還有一些沒能完整流傳下來的詩詞片段,分別出自王安石的妻子、妹妹和侄女之手。“待得明年重把酒,攜手哪知無雨又無風。”這是王安石妻子的詞;“草草杯盞供君笑,昏昏燈火話平生。”這是王安石妹妹的詩;“不緣燕子穿簾幙,春去春來哪得知?”這是王安石侄女的詩。與王安石同時代的魏泰曾在《臨漢隱居詩話》寫道:“近世婦人多能書,往往有臻古人者,王荊公家最眾。”意思是說宋朝多出才女,王安石家尤其多。
但是,才和德是兩回事兒,文采了得,品德未必一定高尚。王安石的妻子吳氏出身仕宦之家,祖父吳敏、父吳芮、叔父吳蒙皆為進士。耳濡目染之下,她自幼聰穎,文采綺麗,宋人筆記多處記載“荊公妻吳夫人最能文”。但在德上,吳氏實在有負名門閨秀的聲望。
據宋人筆記《萍州可談》記載,王安石罷相之后,曾被貶到江寧任知府。后來,他自請退休,一家人需搬出知府衙門,回自家私宅。衙門里有一張藤床,系公家所有,吳氏甚為喜歡,讓下人搬回了家。王安石是清官,從不吞占公物,勸妻子把床還回去,吳氏不聽。后來,知府衙門的差役趕到家里索取,百般求情,吳氏還是不理。王安石無計可施,只能穿著鞋子躺在那張床上——吳氏有潔癖,見床已被弄臟,便嫌棄了,這才還給了公家。
除了貪小便宜,吳氏還護短,甚至視國法于不顧。宋人筆記《東軒筆錄》記載,吳氏的弟弟吳生到南京(時稱金陵)游玩,住在某寺行香廳。那行香廳又寬敞又雅潔,南京官府經常借用此廳舉行儀式。有一天,皇帝生日,南京官員要在行香廳集合,為皇帝祝壽,好言好語請求吳生先搬到別屋,等儀式完畢再搬回。吳生嫌麻煩,不搬。不但不搬,還破口大罵,因此犯下了辱罵官長的罪。
大部分官員礙于吳生是王安石的小舅子,不跟他一般見識。但也有人忍不下這口氣,等儀式一結束,就對他簽發了逮捕令。吳生嚇壞了,一溜煙兒躲進王安石府里。幾個官員去拜見王安石,訴說吳生辱罵官長的經過,王安石聽后很生氣,準許他們進屋抓人。吳氏卻攔著不讓進,并大聲呵斥這些官員:“相公罷政,門下之人解體者十七八,然亦無敢捕吾親屬于庭者,汝等乃敢爾耶?”我們家老王雖說不是宰相了,老部下們也大都退休了,但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再大的官兒也不敢到我們府上放肆,你們竟敢捉拿我家屬,莫非是吃了熊心豹子膽?這劈頭蓋臉一頓罵,使得南京官員不敢還口,只得作罷。
有其母必有其女,吳氏的潑辣、蠻橫也被女兒繼承。查《宋史·蔡卞傳》:“蔡卞妻王夫人,荊公女,頗知書,能詩詞。蔡每有國事,先謀之床笫,然后宣之廟堂,時執政相語曰:吾輩每日奉行者,皆其咳唾之余也。”說是蔡京的弟弟蔡卞娶了王安石的二女兒,這二姑娘知書卻不達禮,既寫詩填詞,又搞裙帶關系。蔡卞當副相時,每有重大決策和重大任命,都要先回家跟老婆商量,老婆怎么說,他就怎么辦,老婆說讓用誰,他就升誰的官。

戴紅倩/繪
據南宋文獻《容齋三筆》記載,王安石的二女兒讓蔡卞提拔一個人——王安石連襟的外孫,蔡卞趕緊跑去找哥哥蔡京,一番說辭,最終讓那人做了大官。
王安石的大女兒王堇,乳名伯姬,嫁給了王安石同年好友的兒子吳安持。兩人生下一子,取名吳侔。這孩子眉清目秀,聰明伶俐,備受外公王安石的喜愛。王安石曾為其賦詩一首,就是著名的《贈外孫》:南山新長鳳凰雛,眉目分明畫不如。年小從他愛梨栗,長成須讀五車書。意思是說小外孫就像南山上新生的小鳳凰一樣,眉目清秀得比畫上的還好看。在他小時候,想干什么就讓他干什么,但是年紀大些時就必須讀很多書。
吳侔兄弟造反事件成了王安石家族命運的轉折點:此前,王安石家族蒸蒸日上,他的兒子、侄子、侄孫相繼進入官場,并受到重用;此后,王家子孫不得不揖別政壇,甚至文壇,再也沒有任何一個名人出自這個家族。
不幸的是,這樣一個被寄予厚望的外孫,最終竟誤入歧途。
吳侔有一個堂兄叫吳儲,宋哲宗時期出任某地知州。吳儲迷信相術,道士張懷素給他看相,夸其相貌“貴不可言”,有朝一日能在關中平原稱王稱霸。張懷素此人號稱“落魄野人”,喜歡說大話,自稱“道術非常神通廣大,即使是飛禽走獸,也可以呼喝差遣”。他往來于京師,以“左術”游說于仕宦之門,與蔡京、蔡卞等人皆有交往。吳儲聽了他的一番話,既興奮又緊張,將之告訴吳侔。吳侔年輕,不知深淺,竟勸吳儲造反。
就這樣,兄弟二人開始密謀劃策,招兵買馬。公元1107年,正在他們預謀起事之際,被人告發,張懷素、吳儲、吳侔當即被逮捕,隨后被關進天牢,凌遲處死。造反事件發生時,王安石早已去世,但王安石的女婿吳安持和女兒王堇還健在。身為造反者的親生父母,他們也受到牽連:吳安持知情不舉,被判死緩,剝奪一切官職和稱號,后減為徒刑,發配到長沙(時稱潭州);王堇對兒子失于管教,從輕發落,被軟禁起來。
問題在于,吳侔為什么要造反?一是因為迷信,竟然相信相士的信口雌黃;二是因為狂妄,竟然認為他們堂兄弟二人有能耐掀翻大宋王朝。這狂妄的個性,跟他的生活環境有很大關系——外祖父王安石當過宰相,祖父吳充當過副相。他從小到大錦衣玉食,受人追捧,怎會知道天高地厚呢?除此之外,他還缺乏理性的家庭教育。說到家教,其母親王堇自然難辭其咎。
王堇有才,以她的聰穎和見識,絕對不會蠢到去攛掇兒子造反。但是再追溯到她的生活環境和家庭教育,也就不難理解了。王堇的母親,也就是王安石的妻子,貪婪、護短、潑辣,能指著鼻子將知府級別的官員罵得狗血淋頭,事后不承擔任何責任。她的女兒們看在眼里,依樣學樣,自然也就把任性和張狂傳給了下一代。
吳侔兄弟造反事件涉及的案犯多是王氏至親,加上變法失敗后政敵的報復,王安石家族再也沒有立足的底氣了。這件事由此成了王安石家族命運的轉折點:此前,王安石家族蒸蒸日上,他的兒子、侄子、侄孫相繼進入官場,并受到重用;此后,王家子孫不得不揖別政壇,甚至不得不揖別文壇——從北宋末年到南宋滅亡,再也沒有任何一個名人出身于這個家族。
平心而論,王安石本人在道德上堪稱完人。他不貪財、不好色,不倚仗權勢欺人,也不喜歡下屬溜須拍馬。若有人反對他的變法主張,他力圖用道理和實效來說服對方,實在說服不了,也絕不會打擊和陷害反對者。但是他的家風實在成問題,不然怎會有一個貪婪、護短和暴戾的妻子,之后還有一個不斷向丈夫吹枕邊風、搞裙帶關系的女兒(蔡卞之妻)。
但這僅僅是家風有問題嗎?恐怕不是,真正的病根兒在整個官場的風氣上。
北宋文獻《東軒筆錄》載有一段故事,說是王安石執掌相權時,“每生日,朝士獻詩頌,僧道獻功德疏以為壽,輿皂走卒皆籠雀鴿,就宅放之,謂之放生。”每年過生日,百官紛紛獻詩,僧道紛紛祝壽,連商販都提著鳥籠子到門前放生。有一個京官名叫鞏申,渴望得到王安石的提拔,“以大籠貯雀,詣客次,搢笏開籠,且祝曰:愿相公一百二十歲。”用大籠子裝上許多麻雀,來到王安石的壽宴上,一邊給王安石祝壽,一邊打開籠子放生。
王安石變法,反對者多,擁護者少,那為什么文武百官、小商小販和出家人都來給他祝壽呢?說到底是因為他手中的權位。誰手中有權,就向誰拍馬屁,這是歷朝歷代都有的慣例,也是權力缺乏制衡之時的必然現象。王安石的妻女和后世子孫在這種環境下生活,很難不走上囂張的道路,曾經光芒萬丈的王氏家族也由此敗落。
王安石(1021年-1086年)
字介甫,號半山,撫州臨川人。北宋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改革家。1042年進士及第,歷任揚州簽判、鄞縣知縣、舒州通判、參政知事等職。曾兩度拜相,主持變法。著書立說,文采斐然,名列“唐宋八大家”。1086年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