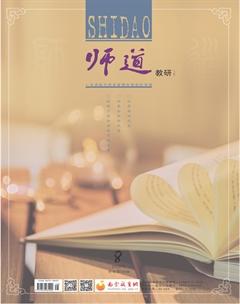自我的力量:有關自我同情的研究簡述
肖巧韻 向英華
近些年來在正念(mindfulness)相關的研究領域中,來自美國德克薩斯州大學奧斯汀分校的Neff教授經過多年臨床工作經驗于2003年提出替代自尊的積極自我態度,自我同情(self-compassion,也有譯作自我關懷)。她認為自我同情包含3個基本成分:(1)自我仁慈(self-kindness),即在個體失敗或處于痛苦中時,對自己表達寬容與理解,而非苛責自己;(2)共通人性(common humanity),即將個體自身的經驗看作是人類整體經驗的一部分(尤指痛苦經驗),而非感到孤立無助;(3)正念(mindfulness),即平衡自己內心的痛苦感受并加以調整,而非耿耿于懷。這三個成分雖然在概念上存在區別,但它們之間是關聯的。正念覺知有助于個體對自己的境遇表現出友善、仁慈的態度,且認為這并非是個人獨有的;同樣,認為自己的境遇并非個人獨有的個體也更愿意對自己表現出友善和同情,以不批判的態度看待自己內心的情緒和感受。不同于單獨的正念,自我同情還包含了很重要的自我仁慈與共通人性,這對于自我認同與人際關系不斷發展的青少年而言也許會有很強大的潛力。相應地,Neff于2003年發表了自我同情的評估工具,self-compassion Scale。自我同情量表包含26個條目,包括自我仁慈/自我評判、共通人性/孤立無援、正念/過度沉浸的3個維度6個方面的內容。該量表具有良好的心理測量學結構指標,內部一致性系數為092,重測信度為093。
需要指出的是,自我同情并不等同于自我中心。自我同情的詞根,compassion,在本質上是一種演化賦予人類的社會情感或動機,是以人際互動并促進個體的社會適應為基礎而存在的。因此,自我同情是一種將自我置放于人類群體之中,并接納和承認個體過去、現在、未來的消極境遇的一種健康的自我態度,從而避免了自我中心。自我同情也不是自我縱容和自我可憐。自我同情并不是對個人境遇的妥協或自戀,反而是一種接納和鼓勵自我改變的態度;相反,那些缺乏自我同情的人則更為自怨自艾。
近十幾年來開展了大量的自我同情相關實證研究。兩份元分析研究顯示自我同情能夠有效促進個體的幸福感并保護個體遠離心理適應不良。在我國青少年群體中的研究發現也同樣支持這個結果,自我同情能夠有效地幫助青少年從容應對來自學習生活中的壓力,并保持身心健康發展。
為此,Neff教授的研究團隊有針對性地開發了一套主要針對提升自我慈悲能力的訓練項目,Mindful Self-compassion (MSC)。該項目不僅適用于臨床工作,也適用于非臨床群體。MSC包含為為期8周,每周2~25小時的課程,外加半天的冥想靜修訓練。在每一次課程中,包括體驗式練習與討論,之后還有家庭作業作為日常訓練。實驗數據表明,與控制組相比,MSC顯著提高了參與者的自我同情、正念、對他人的同情及生活滿意度,并降低了參與者的抑郁、焦慮、壓力和情感回避。個案報告也顯示八周的訓練讓被試者對未來更有信心和希望,并且學習到了應對困難的方法。這種效果持續到訓練結束后的6-12個月。楊琳等人在MSC的基礎上稍作小小改動,驗證了該訓練方式對于中國樣本具有同樣的效應。在對40名(實驗組和控制組各20名)具有抑郁心境的大學生進行了同樣是為期8周的MSC訓練之后,結果發現,與對照組比較,實驗組的自我慈悲水平、自我友善維度有了顯著提升,而自我批判、孤立感、過度認同三個維度和抑郁水平顯著降低。實驗組的前后測表明,經過團體干預后,被試的自我同情及各維度水平均顯著改善,抑郁情緒顯著減少。也就是說,自我慈悲團體訓練可以有效改善大學生的抑郁狀況。在青少年群體中,Bluth的研究團隊于2016年的研究也證實了MSC對于普通青少年同樣適用。在對34名青少年進行了為期8周的MSC訓練之后,結果發現這些孩子們在自我同情、焦慮抑郁癥狀、社會聯結感、生活滿意度等諸多方面均表現出顯著的積極提升。Biber和同事分析了7項自我同情干預訓練對個體健康行為的促進作用研究發現,自我同情訓練有助于提升個體的自我調節能力,進而減少出現健康風險問題。
責任編輯邱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