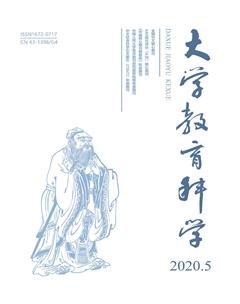排名:大學的“增壓泵”
劉信陽

摘要:程瑩博士撰寫的《大學的壓力之源是競爭而非排名》一文中把“大學的壓力之源”歸結為“競爭而非排名”,歸因結論值得商榷。其一,大學壓力的根源不是“競爭”。大學的壓力源自于其走出“象牙塔”邁向社會中心過程中在政府、市場、社會多方需求與期待下所建構的多種角色與多重社會責任。其二,文章顛倒了“排名”與“競爭”的邏輯關系。排名通過改變競爭結構從而激化競爭。如今世界大學排名已將隱性、零散、零星、局部的競爭演化為顯性、全球、頻繁、系統性較量。由“需求/資源-排名-競爭-壓力”發展鏈可知,大學壓力激增,排名難辭其咎。
關鍵詞:排名;競爭;評價;壓力;高等教育
中圖分類號:G649.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0717(2020)05-082-07
程瑩博士《大學的壓力之源是競爭而非排名》(以下簡稱“程文”)一文闡述道,“大學的壓力增大了”,“有些評論將人才的‘東南飛、人文社會科學地位的削弱,乃至學校之間辦學資源的巨大差距等問題都歸結為排名的影響,恐怕經不起理性的分析。大學遭遇的排名壓力實質上來自于大學為了獲取更多資源或者維持原有資源狀況所面臨的競爭壓力”[1]。的確,現階段大學的壓力增大了,從大學組織到作為要素的學科、團隊和教師都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壓力。然而,細品“程文”,對于作者提出“大學的壓力之源是競爭而非排名”的結論,筆者不敢茍同。另外,還有一大缺憾是文章屬于“筆談”性質的短文,僅僅呈現了一個觀點,還缺乏對此問題的透徹分析與嚴謹論證。據此,本文承接“程文”的話題,梳理“排名”“競爭”以及“大學壓力”之間的邏輯關系,探尋大學壓力的生成機制,尤其重點分析排名在激化大學競爭和引發壓力中的影響,以就教于程瑩博士及學界相關同仁。
一、大學壓力之源:需求之下大學的多種角色和多重社會責任
在工程學中,壓力指作用于機體的外部力量;生理學上,壓力被用以描述“人體對外部需要的適應性反應”;心理學中認為壓力是當個體沒有足夠的能力應對面臨的需求時而產生的個體反應;認知交互作用理論綜合工程學、生理學、心理學等眾多學科的觀點,指出壓力是當機體感知自身能力無法應對外部需求時所產生的困難感[2]。壓力源自于外部需求,機體感知需求并以實際行動對需求做出反應,當需求大于機體的應對能力時壓力便產生了。總的來說,壓力是一種源自于機體外部的作用力。“競爭”是機體對外部需求的一種應對策略,是由機體自身發出的行為活動,并不能作為大學壓力的根源。“程文”中將大學的壓力之源歸結為“競爭”這一結論有失偏頗。
大學的壓力源自于社會對大學的需求和期待以及社會賦予大學的多種角色。角色是由機體的社會地位和身份所決定的符合社會期望的一套社會行為模式。它意味著公眾及角色扮演者對機體在社會規范、責任、義務等方面的期待[3]。根據角色壓力理論,角色及附著其上的期望和需求是壓力的重要來源[4]。威廉·古德(William J.Goode)將角色壓力定義為“在履行角色義務時感到困難”的感受[5]。布魯斯·比德爾(Bruce J.Biddle)等人認同角色壓力理論并剖析了角色需求和期待作為外部刺激引起機體內部壓力反應的機制[6]。從封閉的“象牙塔”走向社會中心的大學,在適應外部環境變遷及滿足社會需要中扮演了多種角色,承擔了從傳統教學、科學研究到社會服務等更多的社會職能和責任,同時也承受了更大的壓力。
中世紀大學職能相對單一,主要以教學為主。11世紀以后,歐洲封建社會進入鞏固發展時期,穩定的社會環境孕育了工商業的發展、城市的復興以及新興市民階層的形成,中世紀大學應運而生并在專注于生產、傳播高深知識的同時培養了教會、政府以及世俗社會發展所需要的人才。此時的大學具有受教會或國王特許的受法律保護的自治權,包括免除大學成員的兵役和財產稅、確定課程、審判和懲罰行為不端學生以及組織罷工等權利[7]。大學無需對外界負責,教授是教學和學術方面的絕對權威,甚至可以挑戰教會和國王;教育質量的解釋權歸屬于大學內部。
19世紀德國柏林大學的創立,使科學研究成為與教學相統一的大學的重要職能。此前,科學研究只是教學的“衍生物”,服務于教學。18世紀末期,以教學為主的大學因墨守成規和脫離實際逐漸走向衰敗。從1792年到1818年不到30年間,半數以上的德國大學被迫關閉[8]。在新人文主義影響下,德國知識分子和貴族提出了創建組織獨立、學術自由的新大學的設想。這一設想恰好符合耶拿戰役中失敗的普魯士政府發展民族主義哲學、歷史和文化的意愿。在政府的支持下,作為新式大學的典范——柏林大學于1810年成立。以此為標志,德國創建了一批研究型大學并且豐富和完善了習明納制度。德國研究型大學重視純粹科學研究,應用科學研究一度被排斥在校園之外[9]。研究型大學拓展了大學職能,直接或間接地滿足了德國工業化時代科學創新和技術進步的要求。柏林大學的研究型大學模式在世界范圍內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它后來也成為主導美國大學的發展模式。大學科學研究職能的發揮為創新人才培養、知識生產與創造以及世界各國的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作出了巨大貢獻。
19世紀中后期的大學增加了公共服務的職能。德國柏林大學以純粹教學和科學研究為目的,服務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充其量是其上述職能衍生的“副產品”。大學服務社會的價值理念及其公共服務的職能肇端于美國,是19世紀美國大學發起的民主化運動的產物[10]。一方面,大學以推進社會民主以及服務于民族國家的個人為職責。美國建立起州立大學、贈地學院、社區學院、師范學校、女子學院、黑人學院、成人學校、開放學校等形式多樣的學校,并通過取消學費、降低入學標準等舉措使婦女、少數族裔及貧窮學生獲得了較為平等的入學機會。隨著大學及學生數量增多,美國高等教育實現了由精英到大眾再到普及的轉變,知識面向普通大眾廣泛傳播,大學成為個體社會階層流動的“輸送帶”。另一方面,大學致力于研究和解決社會問題,服務于社會發展。1986年頒布的《莫雷爾法案》推動了贈地學院的建立。贈地學院鼓勵研究和傳授農業、機械等實用知識,成為人類歷史上最成功的應用性研究計劃。隨后,服務城市發展為目的的州立大學建立。威斯康星大學承諾為該州的所有人口提供服務,“州的邊界就是大學的邊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大學研究數量及成本的增加迫使其與政府、企業和社會建立起更密切和廣泛的合作。創建校辦企業、催動科研成果轉化以及增加國際學生招收等都成為大學創收的渠道。在此過程中,大學的科學研究從基礎和軍事轉移到民用領域;教學內容由高深知識變為實用知識和技能;服務性學習納入學生課程體系;公共服務納入教師考核和評價系統[11]——大學已經成為社會發展的“服務站”,服務社會的價值理念滲透到高校辦學的方方面面。美國高等教育在走出“象牙塔”與時代契合、與社會互動中獲得了豐富的資源,取得了巨大成功,成為世界其他國家效仿的典范。
在變化是唯一不變的世界里,大學的角色和職能也在與時俱進地變化。大學的角色和職能反映著不斷變化的經濟水平、政治體制、哲學思想、教育政策、社會文化。大學在悠久的歷史進程中表現出極強的社會適應性,大學或在其職能之間進行重點的轉移,或衍生出新職能以適應變化的環境。如今正值“知識經濟”時代,知識與土地、資本、勞動力等傳統資本要素一并成為推動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引擎”。經濟和社會對知識的依賴使大學備受矚目,政府、企業、學生、家長等多方主體都對大學寄予了殷切期望:政府期望大學成為政治的“穩定和增強劑”、經濟的“動力站”、文化的“培養皿”和“揚聲器”;市場需要大學成為人才的“孵化站”“篩選器”、以科技創新提升企業效益的“發動機”;家長和學生期望大學成為獲得高薪職位的“敲門磚”、階層流動的“傳送帶”……大學在滿足社會的諸多需求和期望中塑造了多種角色,也肩負了沉重的責任和巨大壓力。
二、排名給大學“增壓”:排名激化競爭和壓力的作用機理
如果說多方利益相關者的需求和期待是導致大學壓力的深層次原因,那么更加富有市場色彩和重視績效的高等教育資源分配和管理方式的轉變即是形成壓力的重要來源。而排名作為治理工具運用到新的資源分配和管理方式中,將原有的壓力生成鏈由“需求/資源-競爭-壓力”演變為“需求/資源-排名-競爭-壓力”,進一步激化了壓力。如壓力生成鏈所示,“程文”所主張的“大學遭遇的排名壓力實質上來自于大學為了獲取更多資源或者維持原有資源狀況所面臨的競爭壓力”這一論點顛倒了排名和競爭的邏輯關系,忽視了排名在影響資源配置及激化大學競爭和壓力過程中所起的作用。
(一)排名引入新的競爭機制進一步激化壓力
多方利益相關者對大學的需求和期待賦予了大學多種角色和多重社會責任,大學相應地擴大規模、增加科學研究和社會服務活動以滿足社會需要。在此過程中,大學的運行和辦學成本增大,對資源的需求更加迫切。大學不得不努力地迎合政府、企業和學生等利益相關者的需求,以從中獲得辦學經費。而各利益相關者也就是資源占有者所能提供的資源或優質資源數量是有限的。資源擁有者為提升資源利用效率打破平均和按需分配的原則,根據競爭者的實力強弱和滿足自身需要的程度予以資源配置,競爭和壓力隨之產生。而在這種富有市場色彩和重視績效的資源分配和管理方式出現之前,大學可能存在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等角色方面的壓力,但是大學之間的競爭壓力幾乎不存在。如我國在改革開放以前,教育資源按需分配,高校無需為獲得更多資源而彼此進行較量;在西歐大多數國家(英國除外),在“卓越計劃”等世界一流大學建設項目實施以前,高等教育也被政府和公眾視為是同等優秀的,大學間的競爭并不顯著。
高等教育資源分配和管理方式向市場化轉變是競爭和壓力的重要來源。而排名作為治理工具是隨著上述轉變而產生的高等教育市場化的產物[12],同時排名在高等教育資源分配和管理中的運用,將原有的壓力生成鏈由“需求/資源-競爭-壓力”演變為“需求/資源-排名-競爭-壓力”,進一步加劇了競爭和壓力。競爭和壓力在排名出現以前就有,但從未如此激烈,可以說當前我們所面臨的包括爭奪世界一流大學等在內的競爭壓力大都是由排名引起的。
以排名的方式衡量和比較大學質量、聲望并不鮮見,早在20世紀60年代,科學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和社會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等文獻計量數據就被用于排名和評估學術工作。2003年上海交通大學為比較中國與世界大學之間的差距研究并公布了第一份全球排名——“世界大學學術排名”(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隨后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Times Higher Education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QS世界大學排名(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等世界大學排名系統陸續涌現,國家內部排名更是不勝枚舉[13]。不同于高等教育問責制下的大學績效評估,大學排名往往并不注重質量改進,而只是以向公眾呈現大學質量狀況為目的;有別于高校評估,大學排名通常不是由教育管理部門或高校自行實施,而是多由第三方機構研究和公布,新聞媒體和報刊成為發布大學排行榜的主力軍[14]。排名能夠反映大學辦學質量和發展狀況,進而告訴資源擁有者哪些學校是有價值的、值得投入的[15],為政府資源配置、企業校友贊助和學生入學等決策提供依據。排名在資源擁有者和大學之間建立起緊密的聯系,名次即意味著大學獲取資源的多寡,大學圍繞排名展開資源競爭。競爭的結果通常是一方實體得到了稀有資源,其他競爭者沒有得到[16]。究竟誰有資格獲得資源,要看社會比較和擇優選擇[17]的結果。
在排名未出現以前,大學承受的競爭壓力相對較小。其一沒有排名前,資源擁有者主要根據各個學校官方網站信息或者是社會口碑來界定和評價大學,其中大部分信息來源于競爭者和資源擁有者之間的模糊的直接傳播。而排名增加了第三方評價環節,將競爭者與資源擁有者之間的直接溝通演變為以第三方排名者為中介的間接交流:排名者根據資源占有者需求設置指標評價競爭者,然后再將排名結果反饋給資源占有者,資源占有者依據排名結果進行資源分配。在這個過程中,排名者將資源擁有者需求以及大學質量“透明化”,資源擁有者依據排名清楚地掌握了各大學質量和價值狀況并進行資源配置,大學通過排名更加明確了資源擁有者需求和自身發展目標——提升排名。當大學將發展目標和精力都聚焦于排名指標上并且對照排行榜搞建設時,面對不斷變化的排名結果,大學的緊張感便明顯增強了。其二,沒有排名前,高校A、高校B乃至高校N對于彼此之間的情況也是相對模糊的,甚至不知道彼此之間誰是競爭對手。在這種情況下,各方的壓力相對較小。而排名將各競爭對手的“家底”暴露給對方,將模糊的競爭顯性化,加劇了競爭對手間的比較和“算計”。此外,中央教育部門會依據排名對地方一級教育部門進行考核評價,地方教育部門也會采取同樣方式對大學加壓,即排名所造成的壓力會通過“中央教育部門-地方教育部門-大學-師生”進行縱向傳導。排名不僅成為通過市場化方式激勵大學產出以滿足利益相關者需求的治理手段,更因排名應用引入了新的競爭機制,建立起大學與利益相關者之間更加緊密的依附關系。面臨獲取資源、防范對手、完成上級管理部門的目標任務等多重挑戰,大學時刻處在壓力環境之中。
(二)排名的數字化、可視化及周期性發布? ?帶來持續競爭
排名被廣泛使用作為資源分配的依據并能夠引起競爭,還要歸因于排名的可計量性和周期性發布等自身特征。杰萊娜·布蘭科維奇(Jelena Brankovic)等人將排名概念化為類別界定、量化、可視化和周期性公開出版四個子操作,通過排名的概念化闡釋“排名為何能夠帶來持續競爭”[18](P270-288)(見圖1)。
排名的第一個子操作是類化比較,即確定評價指標。排名是一個分類、聚類和排序的過程,它之所以被廣泛運用在于其能夠使多樣化的實體經過分類、規范化和標準化處理變得具有可比性[19]。排名的第一步便是依照評價的目的、服務對象和被評價實體特征確立具有可比性的評價指標。對大學質量排名而言,首先要確定可納入到“大學”范疇的組織,再逐級制定衡量大學質量的指標,比如一級指標是研究質量、教學質量、國際化水平等,其中反映研究質量的二級指標則可能有引文、出版物、諾貝爾獎獲得者等。
排名的第二個子操作是量化。量化是對第一步的評價指標賦值的過程,是評價指標的數字化表達。量化能夠彌補定性的敘述性描述所存在的證據和說服力不足的缺陷。比如,倘若用定性的方式描述“牛津大學是最好的大學”,則會有人站出來說“耶魯大學比牛津大學好”,并列出具體依據如文化傳統、特定部門質量以及辯論文化等;而支持“牛津大學是最好的大學”的人會同樣列出優勢條目進行反駁,結果是雙方都難以給出令對方信服的證據。而排名數字化的呈現方式,則予人一種客觀、公正和確定性的感受,加之排名結果由權威機構發布,使排名具有很強的說服力和可信度[20]。比如,要比較牛津、耶魯誰更具國際化,可以將國際學生人數作為國際化的評價指標,假使計算結果顯示牛津大學國際學生占35%,耶魯大學國際學生僅有27%,那么毫無爭議,牛津比耶魯大學更具國際化[18](P270-288)。
排名的第三個子操作是可視化。以清晰和簡單的視覺效果將排名結果按順序呈現在公眾面前,是排名能夠被目標群體認可的另一原因。可視化為受眾和競爭者提供了易識別和理解的信息。為增強可視性,排名通常用表格呈現比較對象、比較指標及名次。表格不僅能夠呈現總體排名,還能顯示各具體指標的排名情況。例如上海交通大學“世界大學學術排名”網站上,以表格的形式明晰地呈現了排名年份、排名情況、排名方法、排名統計等指標。讀者可根據需求方便地選擇查看不同年份、不同國家和地區以及校友獲獎、教師獲獎、高被引學者、N&S論文、國際論文、師均表現等排名情況。
排名的第四個子操作是周期性公開出版。排名發揮效用的前提是建立起其與競爭對手及公眾之間的鏈接。如果說可視化是針對排名呈現方式的易于接受和理解程度而言的,那么,公開發表則涉及排名所波及和影響到的公眾范圍。可視化和公開出版兩個子操作是排名的執行層面。為保障排名的有效性和準確性,排名通常會周期性發布;周期性連續發布是排名制度化的一個關鍵因素[21]。排名的周期性發布,為公眾提供了大學橫向與其他競爭者以及縱向與過去的自己雙重比較的結果。
排名以自身特質詮釋了其能夠激化競爭帶來壓力。通過指標化、數字性、可視化、周期性發布等操作,排名為所有競爭對手確立了等級順序和質量標準,導致競爭者紛紛以第一名為標桿向既定的標準看齊。因此,大學過于激烈的競爭很大程度上的確是由排名引起的。
三、排名、競爭與壓力籠罩的大學:基于世界大學排名的分析
世界大學排名將全球所有大學放入同一框架中進行比較,拓寬了大學競爭的范圍。其數字化和周期性發布等特征,放大了大學之間的差距,增加了大學競爭的力度和強度,使大學時刻處于緊張的競爭和巨大的壓力之中。
(一)排名的全球性擴寬了競爭廣度,給全世界高等教育蒙上了一層“壓力網”
世界大學排名將大學競爭推向了更廣闊的國際范圍[22]。置身國際比較之中的大學承受了更多的壓力:一方面,參與國際競爭的大學所面臨的競爭對手增多,競爭更為激烈。另一方面,大學必須在國家層面的競爭中脫穎而出,才有機會在國際競爭中勝出,也就是說國際層面的競爭也刺激了國家內部大學之間的較量。相較于其他類型的大學,研究型大學承載了更多的壓力,世界大學排名所引起的競爭更多的是研究型大學的競爭。由于研究型大學居于高等教育“金字塔”的塔尖,是高等教育質量的象征和標志,因此,世界大學排名都是以研究型大學為樣版確立聲譽、文獻、師資與教學、國際化、科研收入等排名指標[23]的,這些指標幾乎適應于世界上所有的研究型大學。
大學為了在競爭中取勝,會在學校內部同樣采用排名的方法動員教師、學生、管理人員,由此形成由個人到團體、機構、國家再到國際多個層次自上而下依次鋪展的競爭序列。國際間競爭作為最上層目標,構筑了下一層級間進行較量的“筋骨”,指引著其競爭目的和內容;而低層次的競爭又成為了上層競爭的“血肉”,豐腴著上一層級競爭的體量。在此背景下,整個高等教育系統都彌漫著競爭的意味,遍布著由競爭而來的緊張壓力。
(二)排名的數字化加強了競爭力度,為競爭者提供了放大差距的“顯微鏡”
世界大學排名是信息技術發展的產物,具有量化和數字化的特征。互聯網的運用及數據獲取的便捷性使得依靠數字化評判成為可能,科學網(Web of Science)、斯高帕斯(Scopus)和谷歌學術(Google Scholar)、百度學術等引擎都有關于學者和機構的發文、引文等數據信息的統計和公布。排名的數字化,改變了原有依靠偏主觀的“互動中判斷”的方式,對大學的評價不再僅僅依據評估對象個體、相關部門機構的陳述,人際網絡關系及評價者對評價對象的主觀印象,而是越來越依靠客觀數據。其數字化的呈現方式改變了此前大學評價的模糊判斷和結論,放大了競爭者之間的差距,會導致競爭者“斤斤計較”于分數和排名,從而加大大學間的競爭力度。事實上,幾分之差并不能說明大學之間存在實質性的優劣差異,以至于有學者反對大學排名,指出“排名正在使得高等教育被數字所控制”[24],認為數字化的排名在許多情況下“基本上是毫無意義的噪音”[25]。數字化排名背景下,用力過猛的競爭和競爭者對身份地位的瘋狂追逐,確實不僅導致整個高等教育系統面臨著巨大的壓力,而且還蒙蔽和妨礙了競爭者對競爭和排名的本質思考。
(三)排名的周期性增大了競爭強度,階段性的持續刺激使競爭者時刻處在壓力之中
《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的出現徹底改變了學術質量排名[26]。一方面,因為它是由一本廣為流傳的新聞雜志創辦和發布的,傳播范圍廣,受眾多。而早期的排名大都由教授和高等教育管理者實施,排名結果只在大學內部小范圍傳播,影響力較小。另一方面,它是第一個定期發布的排名,每年或每兩年發布一次[18](P270-288)。隨后頒布的上海交通大學世界學術排名、QS世界大學排名等也都實行周期性發布。世界大學排名的周期性發布使競爭主體在與競爭對手的橫向和與自己過去的縱向比較中預見假想的“敵人”,由此引發強烈的危機意識和緊張感。世界大學排名發布是全球“卓越競賽”年度周期中的關鍵事件,所有大學公共部門都會持續關注排名動態,而有些競爭者為了美化數據甚至不惜學術造假。為了排名發布的這一刻,國家、大學、教師、學生、管理者時刻處在不容懈怠的準備之中。世界大學排名的周期性發布,促成了競爭的連續性,增大了大學競爭的強度。
除發布排行榜外,排名機構為營造競爭態勢,擴大自身影響力還會組織其他宣傳活動。每年排行榜發布之際,泰晤士高等教育排名機構會組織“世界學術峰會”以及一系列與專業排名相關的其他活動(例如卓越研究峰會、創新與影響力峰會、亞洲大學峰會,等等),讓大學相互分享成功的實踐和創新經驗。業界類似的此起彼伏的宣傳和交流活動,也為高校增添了一層緊張氣氛。
簡而言之,大學壓力的根源不是競爭,而是來自其走出“象牙塔”在迎合不斷變化著的眾多需求時所確立的多種角色、多重社會責任。排名是促使大學滿足外部需求而采取的具有市場色彩的重要治理手段的組成部分,是催動高等教育競爭的核心機制,堪稱大學“增壓泵”。它不僅改變了高等教育的競爭結構,打開了競爭的“黑匣子”,將大學的底細暴露在公眾視野中,還確立了大學與資源的緊密聯系,排名靠前意味著能夠獲取更多資源。正是在追尋資源、提防對手和完成上級管理部門的目標中,大學壓力倍增。而排名能夠促進競爭,還歸因于排名自身具有的數字化、可視化和周期性發布等特征。在世界大學排名的影響下,整個世界高等教育系統被連成了層級網絡,從個人到團體再到大學、國家、國際,所有系統內部要素都被激活;排名的數據化和量化放大了大學間細微的差別,使各競爭者時刻處于“提心吊膽”之中;排名的周期性發布,不斷地刺激著競爭者,使競爭壓力源源不斷地涌現。排名已經將隱性的、零散的、局部的競爭演化為顯性的、全球性的、系統的較量,并將高等教育系統內部競爭制度化為“事實”[18](P270-288)。總體而言,排名在推動高等教育治理變革,調動大學發展動力、活力、行動力、創造力,提高組織機構辦事效率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由“需求/資源-競爭-壓力”到“需求/資源-排名-競爭-壓力”,事實上排名成為大學壓力的重要來源。盡管當下大學及整個高等教育都面臨沉重的競爭壓力,但并不必然得出“大學的壓力來自競爭而非排名”的結論。“程文”將大學的壓力之源歸結為“競爭”,不僅顛倒“競爭”與“排名”的邏輯關系,同時還忽略了排名在激化競爭和壓力中的作用,實為不妥。
參考文獻
[1] 程瑩.大學的壓力之源是競爭而非排名[J].大學教育科學,2019(02):19-20+122.
[2] 陳德云.教師壓力:來源分析與應對策略[D].上海:華東師范大學,2004:4-6.
[3] 劉淑娟.社會心理學[M].延吉:延邊大學出版社,2017:54.
[4] Siegall M,Cummings L L.Stress and Organizational Role Conflict[J].Genetic,Social,and General Psychology Monographs,1995(01):65-95.
[5] Goode W J.A Theory of Role Strain[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60(04):483-496.
[6] Biddle B J.Recent Developments in Role Theory[J].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1986(01):67-92.
[7] Burridge T D.What Happened in Education:An Introduction to Western Intellectual History[M].Boston:Allyn & Bacon,1970:50.
[8] 吳根洲.德國研究型大學成功經驗探析[J].寧波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06(01):25-28.
[9] 全守杰.德國大學模式新論——論德國研究型大學模式與工科大學模式[J].中國高教研究,2011(08):66-68.
[10] Scott J C.The Mission of the University:Medieval to Postmodern Transformations[J].The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2006(01):1-39.
[11] 陳貴梧.美國大學社會服務使命及其實現路徑[J].高等教育研究,2012(09):101-106.
[12] 張應強.綜合治理大學評估排名市場,營造“雙一流”建設良好環境[J].高等理科教育,2020(01):5-7.
[13] Huang M H.Opening the Black Box of 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J].Research Evaluation,2012(01):71-78.
[14] 劉珵,蔣凱.全球大學排名:高等教育作為一個市場[J].大學教育科學,2012(06):107-112.
[15] McClung G W,Werner M W.A Market/Value Based Approach to Satisfy Stakeholders of Higher Education[J].Journal of Marketing for Higher Education,2008(01):102-123.
[16] Smith K G,Ferrier W J,Ndofor H.Competitive Dynamics Research:Critique and Future Directions[EB/OL].(2020-04-25)[2020-04-25].https://www.researchgate.net/profile/Ken_Smith10/publication/255620865_Competitive_Dynamics_Research_Critique_and_Future_Directions/links/0a85e53bbe82d558eb000000/Competitive-Dynamics-Research-Critique-and-Future-Directions.pdf.
[17] Festinger L.A Theory of Social Comparison Processes[J].Human Relations,1954(02):117-140.
[18] Brankovic J,Ringel L,Werron T.How Rankings Produce Competition:The Case of Global University Rankings[J].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2018(04).
[19] Hammarfelt B,De Rijcke S,Wouters P.From Eminent Men to Excellent Universities:University Rankings as Calculative Devices[J].Minerva,2017(04):391-411.
[20] Porter T M.Trust in Numbers:The Pursuit of Objectivity in Science and Public Life[M].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6:9-11.
[21] Sauder M.Third Parties and Status Position:How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atus Systems Matter[J].Theory and Society,2006(03):299-321.
[22] 劉信陽,萇光錘.一流大學建設背景下高等教育競爭的新樣態及其反思[J].大學教育科學,2020(01):22-28.
[23] 張勇,張強,杜啟振.世界大學排名指標體系對比及其對中國“雙一流”建設的啟示[J].中國石油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02):93-97.
[24] Lynch K.Control by Numbers:New Managerialism and Ranking in Higher Education[J].Critical Studies in Education,2015(02):190-207.
[25] Dichev I.News or Noise?[J].Research in Higher Education,2001(03):237-266.
[26] Bowman N A,Bastedo M N.Getting on the Front Page:Organizational Reputation,Status Signals,and the Impact of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on Student Decisions[J].Research in Higher Education,2009(05):415-4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