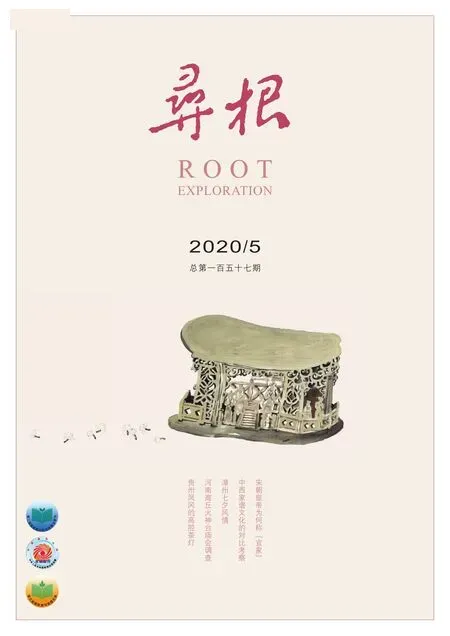宋代的開封府
□任崇岳
趙匡胤禪代后周,建國號為宋,都城仍舊設在東京。但在立國之初,有人主張設在洛陽,趙匡胤也猶豫不決。朝廷之間曾展開過一番爭論,爭論的結果是主張定都東京者占了上風。原因很簡單,誰擁有了開封,誰就掌控了隋唐大運河,也就有了交通和漕運優勢。一個叫李懷忠的官員獻言說:
東京有汴梁之漕,歲致江、淮米數百萬斛,都下兵數十萬人,咸仰給焉,陛下居此,將安取之?且府庫重兵,皆在大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動搖。若遽遷都,臣實未見其便。
宋代東京人口眾多,在百萬左右。宋太宗說“東京養甲兵數十萬,居人百萬”。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說“人煙浩穰,添十數萬眾不加多,減之不覺少”。如此龐大的人口,養活幾十萬軍隊,糧秣供應是一個棘手問題,倘不是江淮之米漕運至京城,北宋政權便無法運轉,在當時具備漕運優勢的城市只有東京開封,因此北宋定都開封,乃是歷史的必然。
京城是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是首善之區,地位自然重于其他城市,曾權知開封府,后又任過參知政事的張方平說:“臣聞王都者,天下之根本,九州之樞會,譬一人之身,則京畿為之腹心,而四方乃其支末。腹心宜泰,支末處勞,養身之道也。先安京畿,后康四方,理國之體也。”
既然京城如此重要,遴選京城的長官當然也非常嚴格,既要求對朝廷忠貞不貳,又要求較高的文化素養和敏捷干練的辦事能力。但是,要求歸要求,知開封府者并非人人都能達到這一境界。鞠躬盡瘁、為民請命者固然不少,如包拯、范仲淹、寇準、歐陽修、蔡襄、張方平等人,但茸無能、隨波逐流者也大有人在,真可謂是良莠并存,賢愚互見。
開封府長官的官稱
同是開封府長官,但官銜并不完全相同。如宋太宗趙光義在即位前封晉王,因他是趙匡胤胞弟,身份自與別人不同,建隆二年(961年)以泰寧節度使兼殿前都虞侯再兼開封尹、同平章事。同平章事或稱同平章軍國事,位在宰相之上,不常設。趙匡胤、趙光義之異母弟廷美以永興軍節度使兼侍中,又任開封尹兼中書令,封齊王,中書令,侍中品階極高,不常授,只是榮譽銜。太宗次子元僖封陳王,為開封府尹兼侍中。宋真宗為皇太子時封壽王,判開封府。宋欽宗以皇太子為開封牧。宋代制度,凡以親王為開封尹者為“判南衙”。所謂“判”是指二品以上的京官或帶有中書省、樞密院的職銜擔任官職較低的知州、知府者。以上幾人均官居一品,他們兼職開封府尹,故稱“判”。因為他們是親王,出行時威風凜凜,侍從甚眾,填滿街衢。《清異錄》中說,每當他們出行,“羽儀散從,燦如圖畫,京師人嘆曰:好一條軟繡天街”。除親王之外,宋初只有昝居潤、吳廷祚、沈倫3人判過開封府,他們都是以宰相身份管理開封府的,時間是在宋朝初年。太宗以后,便沒有人判開封府了。還有親王為開封府尹時皆在南衙視事,真宗大中祥符年間權知開封府事周起上奏說,陛下即位前常在南衙辦公,為臣不敢居此,于是南衙不再成為府尹辦公之地。
除了判開封府,還有知開封府、權知開封府、權發遣開封府等名稱。所謂“知”是主持之意,知開封府就是主持開封府的事務。宋代的政治制度是權力高度集中于中央,地方官大多是由中央派人以朝內官的名義擔任,故稱“知某府事”“知某縣事”。也有一些地方官不是派朝廷內官擔任,而是由其他渠道擔任者,叫府尹、縣令。所謂“權”是指暫代職務而非正式官職,經正式任命后,再根據寄祿官的官品確定是行、守、試。擔任比本職級別低的職務叫行,級別低而官職高者叫守,試是指官員試用期為1年,合格后轉為正式官員。又因為宋太宗趙光義、宋真宗趙恒在即位前任過開封府尹,后世主政開封府者均不再稱開封府尹,而稱權知開封府了。所謂“權發遣”也是宋太祖趙匡胤定的名目,把資序低、隔兩級而委以重任的官員叫權發遣。明乎此,可知同是主持開封府政務,稱呼卻不相同,《宋史》中歐陽修、李穆、呂夷簡、錢若水、呂嘉問、蔡襄、王存等人是“知開封府”,包拯、寇準、范仲淹、陳堯咨等大多數人是“權知開封府”,傅求等幾個人則是“權發遣開封府”。
調動頻繁的開封府長官
開封市博物館庋藏一通《開封府題名記》石刻,上起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二月,下迄宋徽宗崇寧四年(1105年)閏二月八日,主政開封府的共有183人次,可見人事更迭之頻繁。各人的任職情況也不盡相同。大部分人是正常調動,也有因受排擠而任職開封府的。最典型的例子是范仲淹。他從貶謫之地回到朝廷,職務是天章閣待制、吏部員外郎。天章閣是收藏宋真宗御制文集、御書之地,長官稱待制,員外郎是吏部下屬機構司一級的副長官,長官稱郎中。范仲淹遇事敢言,每論國事,便慷慨陳詞,不吐不快。宰相呂夷簡恐怕他說出對自己不利的話,派人對他說,你的官職是待制,議論國家大事,不是你的職責所在,請勿多管閑事。范仲淹說,待制雖然不是糾察邪惡的官員,但關乎國家大事,不能閉口不言。呂夷簡見沒法阻止他,便調他權知開封府,那里事務繁忙,范便不暇他顧了,一旦辦事有疏漏,便可將其免職,逐出京城。范仲淹于是走馬上任開封府。不過開封府的任命也有隨意性。宋仁宗時唐介知諫院,諍諫不避權貴,因與右丞相不合,請求去地方任職,被任命為知荊州。但敕命經過門下省時,被掌管銀臺司的何郯退回,他認為唐介并未失職,不應貶出京城。但他諫官的職務已免,于是朝廷便命他“留權開封府”,即留在京城權知開封府。還有毛遂自薦者。真宗朝畢士安知開封府時因事請求辭職,翰林學士宋白躍躍欲試,真宗便讓他權知開封府。還有因吏治清明而擢升為知開封府者,如宋真宗時薛田,原為知天雄軍(今河北大名),“未幾,擢知開封府”。天雄軍所在地的大名府是宋代的北京,地位雖然重要,但不如東京開封顯赫,由地方官員調任京城行政長官,當然是升官了。

◇開封府題名記碑
走馬燈似的官員更迭,不利于京城的長治久安。任職長者有1年多的,也有幾個月的,甚至十幾天的,要想在任上大有作為,真是戛戛其難。唐介剛剛權知開封府,“旋因論罪陳升之,亦出知洪州(今江西南昌)”;范仲淹在開封府任上,處之彌月,京師肅然稱治;韓絳知開封府,“浹日又遷詳省”,浹日者,10天也;宋白知開封府,“自倦于聽斷,不半歲亦罷去”,他嫌斷案麻煩,任職不到半年,便掛冠而去。還有雖獲任命卻稱病不到職者,如宋真宗時盛度“遷右諫議大夫,權知開封府,以疾不拜,改會靈觀判官”;還有剛獲任命又遭罷職者,如宋神宗時李師中“權知開封府,既而以師中不允人望,罷之”。所謂“不允人望”,是說他在眾人眼中,不具備知開封府的才干,因而剛上任又被免職。官員任職時間短暫,不可能有效治理京師。除此之外,任職官員中有兩度權知開封府者,宋仁宗時的王素、宋神宗時的吳居厚;有3次執掌開封府,如英宗時的傅求;有父子先后任職的,如真宗時的李若谷、李淑父子,呂夷簡及其子呂公綽、呂公弼、呂公孺、曾孫呂嘉問均曾任職開封府。徽宗時權知開封府梁子美上奏說,臣曾祖梁顥、祖父梁適曾領開封府事,臣今又任此職,恐怕德薄能鮮,不堪負此重任。徽宗夸獎他說:“卿三世尹京,縉紳盛事也。”
名士治理開封府
執掌開封府的官員賢愚不一,良莠不齊,政績自然不能同日而語,后世的評價也就大異其趣。宋人周密的《癸辛雜識》一書記載:
開封府有府尹題名,起建隆元年昝居潤,而晉王、荊王以下皆在焉,獨包孝肅公姓名為人所指,指痕甚深。
凡是來開封游覽的人,都來摩挲刻有任職官員姓名的《開封府題名記碑》,包拯的名字被人摩挲的次數最多,石頭凹陷了,因此指痕甚深,這表明人們對清官的敬重與仰慕。包拯也確實是享譽千秋、婦孺皆知的人物,他剛正不阿,恪守官箴,戚畹貴族不敢以私事相求。他辦事穩重,不茍言笑,讓他開懷暢笑一次,比讓黃河渾濁的河水變清還難。但他又待人謙和,兒童婦女皆知其名,稱呼他為“包待制”。這是因為他曾任過天章閣待制。因他清正無私,不接受請托,京城里有諺語說:“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按照慣例,凡有訴訟之事,不能直接來到包拯問案的堂前,得先到大堂門口登記,有人收了訟牒再轉給開封府尹,這樣一來,收訟牒的人就可上下其手,收受賄賂。包拯到任之后,下令告狀人可徑直走到堂前陳述曲直,那些想從告狀人手中漁利的官吏也不敢為非作歹了。京城中的權貴之家在惠民河旁建筑園林臺榭,侵占了河道,以致河道淤塞不通,一旦下雨,京城中一片汪洋,成了水鄉澤國。包拯下令悉數拆除那些侵占河道的園林臺榭,權貴們為之斂手,誰也不敢找包拯求情。還有權貴偽造地券,想繼續侵占河堤上的土地,包拯審驗清楚,戳穿他們的騙局,并一一彈劾,使他們受到了懲處。
開封府尹中兩袖清風、為民請命者甚多,只是沒有包拯的聲名顯赫而已。范仲淹上任后,京城的達官顯貴、皇親國戚倚仗權勢,依舊恣行不法。范仲淹鐵面無私,依法行事,一些蠅營狗茍之徒想乘范仲淹剛剛上任之際興風作浪,都被繩之以法,其他人受到震懾,不敢再以身試法了。范仲淹上任只一個月,偌大的京城便“肅然稱治”,秩序井然了。京城中有諺語說:“朝廷無憂有范君,京城無事有希文。”一時范仲淹聲名鵲起,譽滿京城。歐陽修繼包拯之后,掌管開封府,治理辦法與包拯不同,一切都循規蹈矩,按規章行事。有人建議他應效法包拯,歐陽修說人的才能性格各有短長,不能讓人舍所長取所短,歐陽修治理京城同樣得到了人們的稱贊。李穆在太宗時知開封府,他“剖判精敏,奸猾無所假貸,由是豪右屏跡,權貴無敢干以私。”他死后,太宗嘆息說:“穆國之良臣,朕方倚用,遽茲淪沒,非斯人之不幸,乃朕之不幸也。”
神宗元豐年間,王安禮(王安石弟)知開封府,判案果斷,雷厲風行。在他之前開封府案件堆積如山,久滯不決,已經拘系下獄而未結案者有幾萬人。王安禮不憚辛勞,對案卷爬梳剔抉,處理得當,不到三個月,牽連幾萬人的案子全部結案,無一錯案,“三獄院及畿、赤十九邑,囚系皆空”。一些棘手案件,他都一一剖析停當,不冤枉一人,京師之人稱他為“神明”。神宗皇帝有幾個兒子接連夭殤,掌天文歷法的太史上奏說,庶民百姓家的墳墓離京城太近,因而不利于皇嗣,神宗馬上下詔,讓百姓改遷墳墓,這牽涉到數十萬家的墳墓,百姓怨懟不已。王安禮進諫說,周文王當政,把掩埋百姓家的死者當作大事,以此來維系人心,沒有聽說過遷別人家之墳以利自己子孫者。神宗聽了,連忙取消了這道詔令。
有一次,巡邏探事的人收到了匿名信,信上控告京城有一百多家圖謀不軌,打算造反。神宗把此事交給王安禮處理,要他從嚴懲治。王安禮查驗謀反事由,情節基本相同,最后一封控告信上加了3個人,其中有個姓薛的。王安禮把那人找來問,你得罪過什么人嗎?姓薛的說,前天有人來拋售毛筆,被我拒絕了,那人怏怏而去,面露怨恨之色,匿名信可能是此人所寫。王安禮把那人拘捕審訊,果然是他所為,當即梟首于市。京城人物都嘖嘖稱贊。有個叫趙令的皇室成員,花了數十萬買來一個小妾,此人是個紈绔子弟,花花公子,把小妾玩膩了,便把她攆回了娘家,又訴諸開封府,索要當初買人的錢。這分明是恃勢訛詐,那婦人只是掩面啼哭,一言不發。王安禮看那婦人,臉上傷痕斑斑,花憔柳悴,甚為婦人不平。他當即上奏神宗說,婦人之所以售價數十萬者,是因有花容月貌,如今她臉已破相,不會再有人娶為小妾,這與炮烙之刑何異?該女子不應償還其值,趙令應受到處理。神宗見王安禮說得有理,下詔停止給趙令發放俸祿,以示懲罰。京城百姓莫不拍手稱快。
后宮從商家購得覆蓋雜物的油箔,雙方商定,如果在三年內油箔損壞,商家必須照價賠償。結果不到一年,油箔便有損壞者,后宮派人拿著油箔來到開封府要求賠償,宮人仗著自己來自宮廷,說話時聲色俱厲。王安禮不為所動,對宮人說,油箔應放在干燥通風之處,宮中的油箔是否放在陰暗潮濕之地,被風雨淋壞所致?如果真的如此,商家便無利可圖,賠償的約定便不具備法律效力了。王安禮不再受理此案,宮人只得空手而還。從此以后,京城中的皇室國戚都對王安禮忌憚三分。
仁宗天圣年間,程琳權知開封府。上任不久,蜀中大姓真宗劉皇后的姻親王蒙正之子王齊雄在京城居官,他打死了家中仆人,卻威脅死者妻子以病故上報給開封府。程琳仔細察看報案者的臉色,見她悲悲切切,痛不欲生,知道她有難言之隱,便命人重新勘驗死者尸首,得知是捶楚致死,人命關天,便上報給了朝廷。劉皇后自然袒護王齊雄,對程琳說,王齊雄非殺人者,殺人者是王齊雄家的另一仆人。程琳說,奴才無獨斷自專之理,他必然是得到主人的授權,才敢行兇殺人的。王齊雄雖不親手殺人,但下令殺人應與殺人者同罪。劉皇后無言以對,指使仁宗把王齊雄調往他處繼續為官。御史中丞蔡齊挺身而出上奏說,王齊雄殺人一案,程琳已審理清楚,只因他是皇太后姻親,犯了殺人之罪,未受懲治,只是改調官職,這是以恩廢法,臣期期以為不可。仁宗說,降他一級官職,可以嗎?蔡齊說,如此一來,朝廷之法如同兒戲,朝廷還會有威信嗎?仁宗默然不語,只得依法治王齊雄的罪。
同樣在仁宗時期,王臻知開封府時,奸邪之人偽裝成皇城司的探聽消息的人,編造謊言,恐嚇百姓,敲詐錢財,京城庶民苦不堪言。王臻經過縝密調查,打聽清楚了這些人的姓名,先是拘捕,然后在臉上刺字,流放遠方30余人,京城恢復了正常秩序。針對京城諸衙門辦事拖沓的弊端,王臻又上奏說,三司(鹽鐵、度支、戶部合稱三司,統籌國家財政)和開封府諸曹參軍(各州縣長官的僚屬,如南朝文學家鮑照就當過參軍,人稱鮑參軍)、赤縣(宋代把縣分為赤、畿、望、緊、上、中、下七等,赤縣是京城所管的縣)的縣丞、縣尉都是戚畹貴族子弟,驕惰成性,不懂得如何辦理政事,請求更換成孤寒之家出身,熟悉政事且品德端正之人擔任。仁宗答應了他的請求。王素也是在仁宗至和年間執掌開封府的,有一年淫雨連綿,蔡河決堤,濁水灌入城中,仁宗慌忙下詔堵塞朱雀門,把水堵在城外。王素上奏說,城外居民廬舍甚多,倘若堵塞河道,水流不暢,豈不淹沒更多百姓?不待仁宗批準,便下令不再封堵朱雀門,河水也未造成危害。
像包拯、范仲淹、程琳、王臻、王素這樣的官員還有不少。如仁宗朝蔡襄知開封府,他“精吏事,談笑剖決,破奸發隱,吏不能欺”;英宗朝呂溱知開封府,他“精識過人,辨訟立斷,豪惡斂跡”;吳奎在仁宗朝知開封府,他“達于從政,應事敏捷,吏不敢欺”。富人孫氏經商贏利,凡欠他錢的人,孫氏都巧取豪奪,低價弄走其財物,甚至搶掠婦女作抵押。吳奎得知后,把孫氏兄弟貶往淮、閩服勞役,其他豪猾之人再也不敢敲詐百姓了。3個月之后,京城肅然稱治。沈遘在英宗朝執掌開封府,他“敏于政事,號稱嚴明”。在他之前任職開封府的官員,早晨剖決政務,到黃昏時還未辦完,甚者連飯都顧不上吃。沈遘在任時,上午處理政務,到日中(中午)時便已處理完畢,下午“出謝賓客,從容談燕”,京城翕然稱治,士大夫交口稱譽,贊他為才能卓越之人。
治理開封多風險
東京開封作為京城,是皇親國戚、高官勛貴、豪紳富商聚集之地,執掌開封府要做到公正公平,使權貴們滿意,委實不易。徽宗時李倫掌管開封府,剛正無私,人稱“李鐵面”。一次,朝廷中一位官員犯法,應當追究責任,但那位官員有權貴撐腰,竟不肯到案,李倫甚為憤怒,略施小計,把那人騙到了開封府。那人到案后,又大放厥詞,不肯認罪,李倫大怒,依律懲治。幾天之后,李倫忽然接到通知,說是奉圣旨推勘幾起案件,其中一案牽連到開封府,須李倫前去御史臺作證。當時御史臺大門朝北,開封府大門朝南,兩個衙門只有一路之隔,只消片刻便可到達。但有人引著李倫繞道而走,曲曲彎彎,竟由巳時走到酉時,到達御史臺時,已是暮色蒼茫的黃昏時分了。李倫看到了那里審訊犯人的駭人場面,又被領到另一處聽獄卒拷打犯人的號哭之聲。李倫驚魂未定之際,又有官吏問他審判朝廷官員是根據祖宗的哪條法規。折騰一夜,至次日凌晨方才放出,李倫已是疲憊不堪,步履蹣跚了。隔了數日,李倫不明不白,又被罷了官。宋代官場的黑暗,由此可見一斑!
開封府尹中也有人品差池、能力不逮之人。呂夷簡曾孫呂嘉問知開封府時,把祖父呂公弼議論王安石新法不當的奏疏稿子拿給王安石看,導致呂公弼被貶謫出朝,呂氏族人稱呂嘉問為“家賊”,不讓他入族譜。
程琳初知開封府時有膽有識,審判劉皇后姻親王齊雄殺死奴仆一案,贏得了許多人稱贊。但后來因心生雜念鑄成大錯,被降職貶出京城。原來已故的樞密副使張遜有宅第在武成坊,他的曾孫張偕年方7歲,乃趙宋皇帝宗室之女所生。此時張家已淪落貧窶,無米可炊,他家的乳母拿出房契打算賣房,程琳見宅第寬敞,又在城市中心,打算購為己有,便心生一計,派人曉諭乳母,說張偕年幼,須得宮廷同意,才可賣房。張偕的乳母便去宮中求見太后,太后給她蓋上了御寶。程琳見手續完備,知道萬無一失,這才買下了房子。又讓手下人買來木材裝修房屋,又買來婢女伺候。不巧的是,那個替程琳買木材、買婢女的手下因貪贓被捕,御史臺審理案件時查出了程琳設計買房的內幕,被降職,貶知潁州(今安徽阜陽)去了。
還有一個叫傅求的人,英宗朝執掌開封府,他性格平恕,胸無城府,操守純正,判案公正,所至之處,均有可稱道之處。但是到了老年,精力不濟,判事往往出紕漏。開封府內有一個叫錢吉的官員,因與妹妹發生口角,一時失手,竟將妹妹打死,被鄰居告發。這本是一樁明明白白的殺人案,昏聵的傅求卻斷不清楚,反將告發者責打一頓,京城人驚詫不已。另有幾件案子,也斷得不公。御史臺的官員彈劾他不能勝任知開封府之職,于是被貶往外地任職。還有自己清白而被兒子輩攪壞者。真宗朝咸平年間慎從吉權知開封府,受命之日,真宗告誡他說,京城人口眾多,情況復雜,凡辦事要三思而后行。辦事太速則容易誤判,辦事太緩問題便會遲遲得不到解決,須仔細斟酌,尋找適中可行之策。還有一條,不要接受別人的請托,這樣你辦事才能鑒空衡平。慎從吉叩頭唯唯聽命。上任幾個月后,咸平縣(今河南通許縣)民張斌妻子盧氏,控告侄子張質醉酒罵人,從而引起糾紛。張姓是咸平縣豪族,張質是張家養子,他自知理虧,忙向縣中官吏行賄。慎從吉之子任大理寺丞的慎銳正督運石塘河,經常往來咸平,因大理寺是審判決獄的機構,他也留意這個案件,與咸平縣令商議之后,判張質恢復原姓,改名劉質,仍與養母盧氏生活在一起。張質與盧氏均不服這一判決。因咸平是開封府的屬縣,縣令無法決斷,便把此案上報給了開封府,慎從吉命戶曹參軍呂楷到咸平縣推問。盧氏的本家叔父盧昭一賄賂呂楷白金(銀子)300兩,希望判盧氏勝訴,呂楷猶豫不決。盧氏的哥哥盧文質又賄賂慎從吉長子、大理寺丞慎鈞70萬緡,慎鈞把此事告知父親慎從吉,求他偏袒盧氏,但隱瞞了自己受賄之事。盧氏仗著本家叔父和兄長均已行過賄,官司勝券在握,便到開封府催促盡快結案。盧昭一的兄長盧澄曾給慎從吉的妻兄錢惟演寫信,讓他轉告從吉,此案牽連到從吉的兩個兒子慎鈞、慎銳,處理此案要緩一緩。那錢惟演是吳越王錢之子,隨父歸宋后頗受重用,曾官拜樞密使,是朝中炙手可熱的人物,因此盧澄才給錢惟演寫信。慎從吉見事情發展成一團剪不斷、理還亂的麻團,便將此案上報給了御史臺。御史臺很快查清了此案的來龍去脈,慎從吉被削職勒停,錢惟演罷翰林學士,從吉之子慎鈞與戶曹參軍呂楷免官刺配郢州(今湖北江陵縣)、衡州(今湖南衡陽),慎從吉另一子慎銳與盧氏之兄盧文質降一級,盧氏本家叔父盧昭一與盧氏之兄文質被決杖發配遠方服勞役。《宋史·慎從吉傳》稱他“臨事敏速,勤心公家,所至務察。多請對陳事,上謂其無隱”。這樣一位能干的官員,卻被兒子、親戚害得丟了官。
東京作為都城,政務繁劇,遠遠超過其他州郡,不少人不勝其擾,要求去職。真宗咸平年間,知開封府溫仲舒“以京府務劇求罷,遂以本官兼御史中丞”。真宗朝畢士安知開封府時,一官員恃勢強娶民家女子為小妾,畢士安判民家女返還其父母。那位官員是皇親,天天在天子面前哭訴,畢士安“因求解府事,上許之,復入翰林為學士”。英宗朝知開封府馮京請求辭職,英宗問大臣韓琦,馮京因何要求辭職?韓琦回答說:“京領府事頗久,必以繁劇故求去爾。”又問京為人何?琦曰:“京在開封府歲余,處事無過,求之高科中,有足嘉者。”英宗問馮京人品如何,韓琦說,他知開封府一年有余,處事公平,沒有過錯,在朝廷高官中值得嘉獎。韓琦并未言過其實,馮京的確是位清官。
北宋時期東京開封是國際性的大都市,也是北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這與知開封府諸多人的經營擘畫密不可分,開封城的繁盛也浸潤著他們的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