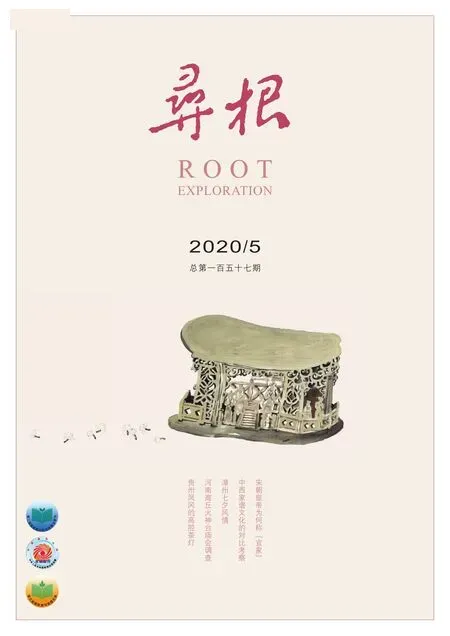一代通儒鄭玄
□ 孫永娟
兩漢時期的經學界,無論是今經文學家,還是古經文學家,都嚴守“師法”和“家法”。嚴守經師之說毫不走樣,叫師法;同一經師的不同學生又各自為家,故師法之下又講家法,在遵從師法的前提下才能成一家之言。東漢后期,在北海高密(今山東高密)出了一位對中國學術影響深遠的通儒大師——鄭玄。他以淵博的知識,沖破了師法、家法的界限,站在“通學”的立場上遍注群經,“整”而“齊”之。注經以古文為主,兼采今文,“括囊大典,網羅眾家,刪裁繁誣,刊改漏失”(《后漢書》卷三五),使古文經學、今文經學通而為一,“鄭學”之說遂成。從他一生的行跡中,我們可見鄭玄的志向——思整百家之不齊。
一
鄭玄一生經歷東漢六個皇帝:順、沖、質、桓、靈、獻,正值東漢衰落時期。鄭玄的八世祖鄭崇,哀帝時為尚書仆射,家世顯赫,但到鄭玄祖父輩時已經衰落。他的祖父、父親都在鄉間務農,生活比較貧困。

◇ 鄭玄像
鄭玄自幼聰慧,志趣超俗。少年時期就卓爾不群,十一二歲時,有一次隨母親到外祖父家做客,在座的十多位與其年齡相仿的客人都衣著華麗,舉止優容,言談宏遠,唯獨鄭玄默默地坐在一旁,一言不發,他的母親覺得臉上無光,便催促他顯露才華,鄭玄不以為然,回答母親說:“此非我志,不在所愿。”(《后漢書》卷三五注引《鄭玄別傳》)在這有力的回答中,可以看出鄭玄堅持自己、不流于俗的品質。
十六歲時,他就精通儒家經典,對古代典制詳熟,而且通曉讖緯方術之學,在家鄉聲名遠播,號為“神童”。有一年,老百姓獻瑞,縣里要討好上級,要將這事寫成公文,贊頌政治清明,無奈縣吏腹中空空,請鄭玄來寫。鄭玄很快就寫好了公文,又寫了兩篇頌辭,縣吏贊賞不已。
據《鄭玄別傳》記載,鄭玄十七歲時,有一天,在家讀書,沒來由地忽然刮起了大風,他就用方術來推算,預測到某地將于某日某時發生火災。于是,他立即到縣衙去報告,到了預測推斷的日期,某地果然發生了火災,但由于及時通知官府,早有準備,并沒釀成大害(洪頤煊撰集,孫彤校訂《鄭玄別傳》,《經典集林》卷十七)。這件事不脛而走,鄭玄又被當地視為“異人”。這些事的真實性已經無從考證,但從一個側面說明鄭玄少年時就很有名。
十八歲為“鄉嗇夫,復為鄉佐”(鄭珍:《鄭康成年譜》)。然而鄭玄好學不愿為官,每逢休假返家,“常詣學官,不樂為吏,父數怒之,不能禁”(《后漢書》卷三五)。鄭玄記憶力極好,“每經歷山川,及接顏一見,皆終身不忘”,二十一歲就“博極群書,精歷數圖緯之言,兼精算術”(《鄭玄別傳》,劉義慶《世說新語·文學》劉孝標注引)。
當時有一位名士杜密,任北海相,到高密縣巡視時見到鄭玄,對鄭玄非常賞識,“即召署郡職,遂遣就學”(《后漢書》卷六七)。鄭玄“遂造太學受業”(《鄭玄別傳》,劉義慶《世說新語·文學》劉孝標注引)。從此,鄭玄就開始了在外漫漫求學之路,為“鄭學”奠定了基礎。
二
至三十八歲,都是鄭玄未入關前的求學時期(鄭珍:《鄭康成年譜》)。鄭玄從太學諸師所學:“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除此之外,又出游各地拜師求學,“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兗、豫之域,獲覲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受焉”(《后漢書》卷三五)。
鄭玄在三十八歲時,離開故鄉,千里迢迢西入關中,通過友人盧植的介紹,拜馬融為師。馬融是扶風茂陵(今陜西興平)人,是當時最著名的經學大師,他遍注儒家經典,把古文經學發揚光大。他的門徒上千,長年追隨身邊的就有四百余人,其中優秀者亦達五十人以上。他“素嬌貴”(《后漢書》卷三五),只親自面授少數優秀的學生,其余學生則由優秀的學生轉相授業。鄭玄投學其門下,三年都沒見到馬融,只能聽其高足弟子們的講授。鄭玄日夜誦習,毫無怠倦。
有一次,馬融和他的一些高足弟子在一起演算渾天,遇到了疑難不能解決。有人說,鄭玄精于數學,于是就把他召去相見。鄭玄當場就解答了問題,馬融與在場的弟子們都驚服不已。鄭玄在馬融門下學習了七年,因父母老邁需要歸養,就向馬融告辭回山東故里。馬融此時已經感到鄭玄是個了不起的人才,甚至會超過自己,他深有感慨地對弟子們說:“鄭生今去,吾道東矣!”意思是說,由他承傳的儒家學術思想,一定會由于鄭玄的傳播而在關東發揚光大。
三
鄭玄學成回鄉后就發生了第一次黨錮之禍,但并未禍及鄭玄。鄭玄當時在東萊,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以耕地為生。學徒相隨,過著傳道授業解惑的平靜生活。
《世說新語·文學第四》有則小故事。有一次,鄭玄使喚某奴婢做事,不稱鄭玄的意,準備打她的手心,奴婢覺得有點委屈,就想為自己辯護,不料,鄭玄正在氣頭上,不容她申訴,反而叫人將她拽到院中的泥濘里。過了一會兒,一婢女看見,覺得好奇,問:“胡為乎泥中?”被罰的婢女委屈地說:“薄言往訴,逢彼之怒。”這似乎是一出小鬧劇,但從某個角度也告訴我們鄭玄的學識澤潤周圍的人。
與第一次黨錮之爭僅僅時隔一年,第二次黨禍又起。據《后漢書·黨錮列傳》載,李膺、杜密、范滂等一百余人,皆捕系而死獄中,受牽連而死、徙、廢、禁者有六七百人。這次鄭玄并未幸免,黨錮之爭一開始,他就與同鄉孫嵩等四十余人被禁錮,這一禁錮就是十四年。這十四年中,鄭玄“隱修經業,杜門不出”,完成《周禮》《儀禮》《禮記》的注釋工作。按鄭珍的說法,鄭玄的著書次序是先注緯書后注經書。
這一時期,還發生了經學史上一次今古文之爭。何休喜歡《公羊傳》,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梁廢疾》,鄭玄為駁斥何休乃發《墨守》,針《膏肓》,起《廢疾》。何休感嘆說:“康成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可見,鄭玄對何休的論說剖析準確,直指要害,才贏得對手如此的稱贊,從此以后,就再也沒有類似的論爭了。史稱:“中興之后,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后馬融答北地太守劉環及(鄭)玄答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后漢書》卷三五)所謂“義據通深”,說明了鄭玄是從“通學”的立場上對《春秋》三傳作綜合研究,而且見解不流于俗,獨到精深,才最終解決了問題,消除了門戶之見,結束了兩百余年的今古文爭辯。黨錮解禁之后,鄭玄又注經《古文尚書》《論語》。至其卒之年,仍在元城注《周易》。鄭玄一生著述豐厚,遠不止上述諸種。
四
鄭玄不樂仕進,拒不為官,這在其一生的經行中可見。
靈帝時執掌朝廷權柄的外戚大將軍何進為了籠絡人心,首先征辟聲名顯著的鄭玄入朝為官。州郡官吏害怕受到牽連,威脅強迫鄭玄入朝做官,鄭玄不得已,只好入朝去見何進。何進為表示禮賢下士,設幾、杖之禮以待之,對鄭玄禮敬有加。鄭玄為保其名士節操,拒不穿朝服,只穿普通儒者的便服與何進相見。僅隔了一夜,未等授予官職,鄭玄就逃走了。
靈帝中平四年(187年),三司府曾先后兩次征辟鄭玄,但他均借故婉言謝絕。靈帝中平五年,鄭玄、申屠蟠及韓融、陳紀等十四人被征為博士,這些人拒不應征。不久,后將軍袁隗又舉薦鄭玄為侍中,鄭玄“以父喪不行”。
同年十月,青州、徐州黃巾軍復起,攻破北海郡,鄭玄就與門人崔琰、公孫方等人到不其山避難,生活舉步維艱。鄭玄帶領弟子們在困厄之中朗誦不絕,正如孔子厄于陳蔡之間。后來鄭玄罷謝學生。
靈帝中平六年(189年),鄭玄六十三歲,這年朝廷又征鄭玄為官,鄭玄不至。靈帝死后,少帝劉辯繼位,不久董卓廢少帝而立獻帝,遷都于長安。這時,公卿們又舉薦鄭玄為趙王劉乾之相,鄭玄仍未受召。
當時,袁紹自稱為將軍,兼督冀、青、幽、并四州,為北方最大的割據勢力。鄭玄七十一歲時,有一次,袁紹宴請賓客,鄭玄應邀出席。在席上,鄭玄對一些所謂“豪俊”的提問一一答對,當時應劭也歸順袁紹,自我夸贊說:“從前的泰山太守應中遠,做您的學生怎么樣?”鄭玄笑著說:“仲尼之門考察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回、賜等人不自稱官職。”應劭臉上帶有慚愧之色。鄭玄語驚四座,使賓客無不折服。袁紹遂舉薦鄭玄為茂才,并表請鄭玄為左中郎將,但鄭玄毫不為之所動,一一婉拒。
建安三年(198年),獻帝征鄭玄為大司農,這是位列九卿的高官,賜給安車一乘,所過郡縣長吏送迎。鄭玄在家拜受后,便乘安車至許昌,但馬上又借口有病,請求告老還鄉。他雖然并未到任就職,但已經拜受此命,故世人稱他為“鄭司農”。
鄭玄解禁后被征辟、舉賢良方正、茂才等共有十四次,皆拒不受官。公車征左中郎、博士、趙相、侍中、大司農,也都沒有就職。
鄭玄屢拒征辟,其間除避亂于徐州外,大都是在家鄉隱居,聚徒講學,專心經術,著書立說。鄭玄在《戒子益恩書》中寫道:“但念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這是他一生的志向,這高潔的品行吸引了眾多的弟子,有人從遠方慕名而投至門下,趙商、崔琰、公孫方、王基、國淵、郗慮等即為其間著名者。他的學生遍于天下,常常超過千人,為一時之盛。
鄭玄不樂仕進,但并不意味著他不關心世事。他六十六歲時,董卓已被殺,而李、郭汜作亂,陶謙欲聯合諸郡,推舉當時名臣朱為元帥討伐汜,鄭玄與陶謙等奏議,支持朱為帥。鄭玄在這關鍵時刻旗幟鮮明地表明自己的態度,心向高潔,可見其胸懷天下、國家安危。鄭玄始終對外戚、宦官集團采取不合作的態度,保持自身正直清明,體現出不屈不撓的漢儒風節。
五
鄭玄的高潔品行也得到了世人的敬仰。
六十四歲時,孔融為北海相,對鄭玄的學識、人格十分敬仰,命令高密縣“為玄特立一鄉”,命名為“鄭公鄉”,廣開街衢,可容高車通過,號為“通德門”,這是對鄭玄名德的表彰(《后漢書》卷三五)。
六十八歲時,劉備以尊師之禮待鄭玄,鄭玄“告備以治道,無所不悉,因薦同郡人孫乾,備辟為從事”(鄭珍《鄭康成年譜》)。
六十九歲時,在徐州,當時孔融想請鄭玄返回郡鄉,敦請懇惻,派人接踵而至,孔融對眾人說:“鄭公久游南夏,今艱難稍平,儻有歸來之思,無寓人于室,毀傷其樊垣林木,必繕治墻宇以俟還。”(《太平廣記》卷一六四)孔融對鄭玄的敬重之意深厚至極。
鄭玄應孔融邀請回鄉,在途中遭遇黃巾起義軍,眾人驚恐不已,但黃巾軍“見玄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鄭玄一行人回到故里,孔融告誡屬下說:“昔周人尊師,謂之尚父,今可咸曰鄭君。”(《太平廣記》卷一六四)
建安五年(200年),鄭玄七十四時,春天,鄭玄夢見孔子告訴自己說:“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在巳。”醒來后,以讖合之,知道自己命將終結,沒過多久便臥病在床。當時袁紹與曹操戰于官渡,袁紹派人逼迫鄭玄隨軍,不得已,鄭玄帶病上車,到元成縣時,病重不能前行。六月,鄭玄病逝。正處于戰亂之時,葬禮從簡,但自郡守以下官員和受業弟子一千多人披麻戴孝送葬。
鄭玄最初葬于劇東(今山東益都境內),后又歸葬于高密縣西北50里劉宗山下的厲阜。現在山東高密市雙羊鎮鄭公后店村存有唐代墓碑和鄭玄祠,距此不遠,就是當年的“鄭公鄉”。
鄭玄的學生們十分景仰這位老師,為了紀念恩師的教誨,他們像孔門弟子為紀念孔子而編輯《論語》一樣,也把鄭玄平時和弟子們問答五經的言論編輯為《鄭志》,共有8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