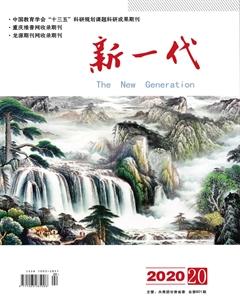書寫·涂抹·記憶
賴起鳳
摘 要:原中央蘇區的紅色標語是以識字運動為中心的中央蘇區文化教育成果的有效檢驗與充分展示。在近一個世紀的時間里,紅色標語歷經自然的、人為的多重涂抹。幸存下來的紅色標語實物,成為“歷史記憶”的載體,成為今天我們追溯那段特殊時期的重要線索。本文圍繞書寫、涂抹、記憶三個問題,大致勾勒出中央蘇區紅色標語的歷史變遷的基本輪廓。
關鍵詞:紅色標語;書寫;涂抹;記憶;歷史變遷
中央蘇區紅色標語作為黨與紅軍早創時期用于自我密集宣傳、群眾動員、威懾敵人的武器,在對敵斗爭中充分發揮了積極的效用。經過兩次國內革命戰爭、社會主義改造與社會主義建設、改革開放、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滄桑巨變,大量蘇區紅色標語仍然有幸保留下來。實用書寫、人為的或自然的涂抹、后世的歷史記憶三者,共同構筑了蘇區紅色標語的歷史變遷之流。
一、中央蘇區的紅色標語書寫
以識字教育、掃盲教育為中心工作的中央蘇區文化教育,短時高效地培養出一大批可以勝任書寫標語的文字宣傳員。中央蘇區教育直接指向包括識字掃盲在內的群眾覺醒。紅色標語是檢驗蘇區以識字運動為中心的文化教育成果的有效形式。
紅色標語的書寫者,以蘇區識字教育背景下培養出來的能識字能書寫的紅軍指戰員和普通戰士為主體。早年接受過良好書寫教育的舊知識分子,具有一定書法功底的個別紅軍干部(如舒同),以及黨和紅軍的部分領導同志(如毛澤東、朱德、陳毅等),都參與了紅色標語的書寫。紅軍宣傳兵制度的設立,強化了紅色標語書寫的規范性、穩定性、普泛性特點。中央蘇區有針對性的、高效的識字掃盲教育,直接培養了大批紅色標語書寫者,并且決定了紅色標語總體的書寫水準與書寫狀態。黨和紅軍多次就標語書寫的字體、行款、大小、位置、宣傳對象以及書寫態度等方面作出過技術性規定。紅軍標語由起初單調的紙質載體的文字書寫,逐漸走向多樣化、大眾化、立體化的形式。
戰時條件下的主客觀條件,決定了蘇區紅色標語書寫品質良莠不齊。文字宣傳員因陋就簡、就地取材,使用易得的破布、掃帚、棕刷、筍殼等書寫工具,石灰砂漿、紅土石粉、作坊染料等液體材料和紙、布、木、竹、墻等書寫載體。標語字體以工整的正楷為主,也通行隸書、行書。黑體字、宋體字也較常見。清末以來盛行的顏真卿楷書、行楷風格大行其道。字跡有紅、黑、紫、白諸色。書寫者文化水平不高,現學現用,邊學邊用,使紅色標語書寫存在許多不盡如人意之處:增減筆畫、錯訛、繁簡字糅雜使用,上下或左右字距排布不勻,漏字補插和涂改等等。
蘇區紅色標語的書寫,其目的是實用的而非藝術的,方式是革命的而非抒情的,形式是直接的而非婉約的。但是我們又不能完全排除其書寫中藝術裝飾的成分。紅色標語中最為常見的“工”、“人”,“工”字中間有意稍作扭動,“人”字捺上加三點的書寫處理即屬于此類型。它反映了書寫者美化文字書寫的樸素追求。毛澤東從文化水平相對低下的工農受眾的角度出發,對該書寫方式提出過批評和指導意見。古代有所謂“秦書八體”,其中之“摹印”,是篆書字體在印章中的運用。書篆時為填充印章方形空間的需要,文字部分點畫通常作折疊處理,以致于屈曲縝密。紅色標語書寫者運用到此類處理手法,顯示出不自覺的復古動機。這大概是舊社會長期被剝奪了受教育權的底層民眾對漢語言文字的敬畏、對知識的渴望、對文化的推崇的一種曲折反映。在識字教育教學過程中,蘇區各類型教育形式中的教員率先垂范,學員便踵隨風從,文字書寫修飾形成一種典型現象,以至引起了毛澤東的關注。
縱觀當代有關蘇區紅色標語的研究,關注點主要集中在紅色標語的背景和類型、性質和特點、功能和作用、保護和利用等方面的闡釋,對紅色標語的書寫行為本身及其現象的討論較少。從事語言文字研究的學者,則熱心于紅色標語的文字使用問題。由于學科之間壁壘森嚴,多數紅色標語的研究者疏離于書寫實踐,缺乏書法習練的經歷,論及書寫問題只能淺嘗輒止,難以真正觸及書寫的核心。尷尬的是,具有專業書寫水準的書家,因為標語的實用性質、書寫者的底層身份、書寫水平的粗率,似乎又無意將精力傾注于此。實際上,關于紅色標語書寫,仍然還有許多可思考的空間,還有將研究引向深入的可能。
紅色標語發揮了宣傳、組織、武裝群眾的威力,其密集性與高效的底層動員力,是對蘇區文化教育成果的重大演練與肯定。我們聚焦紅色標語的書寫,把它放在中央蘇區教育的視野下進行考察,并對其書寫的現場性、歷時性進行揣度,則能夠更加深刻地理解關于紅色標語的書寫行為及其相關現象。
二、關于中央蘇區紅色標語的涂抹
蘇區紅色標語的涂抹現象有人為、自然之分,有主觀、客觀之分。綜觀其歷史的變遷,無非如下幾種:標語書寫中的自然涂乙;紅軍陳舊標語的自我洗滌和更新,或者國共兩黨政權力量較量中因雙方在宣傳陣地上的爭奪而產生的翻覆與涂改;久經歲月的風雨剝蝕以及社會歷史進程中的社會改造造成的紅色標語資源的流失。
紅軍標語宣傳的基本要求是書寫端正、清楚醒目、美觀大方。然而,紅色標語的書寫者主體,是粗通文墨的文字宣傳員,甚至是每一個紅軍戰士。他們短時間內難以完全消化和熟練運用識字教育中習得的漢字及有限的書寫技巧。書寫者的書寫水平、書寫態度存在個體差異,書寫失誤也就在所難免,一旦有誤便順手涂改。盡管上級在宣傳方面有過技術性規定,也下達過指導性意見,然而實際操作中,書寫涂乙現象仍時常發生,即使有現成的標語在手也難以避免。
隨著時局變化,紅軍會對那些陳舊的、失去時效性的標語進行更換洗滌,換寫新的標語。這是一種主動的涂抹,以切合新的赤色革命需要。紅色標語是蘇維埃政權下黨和紅軍宣傳自己,反映廣大工農群眾利益呼聲的唇舌。國民黨軍對紅軍的紅色標語既怕又恨,經常組織人馬進行涂抹篡改,污損、鏟除墻頭標語,鑿毀石刻標語。有些標語經過多次篡改,變得語義不通。最為典型的是湖南炎陵縣城南橋組孫豐新家照墻上的“不分姓氏只分貧富”標語,經過了紅軍、白軍的多次改動[1]。有一種情形也值得關注,即有些地方豪紳會根據戰爭形勢的變化而左右逢源,對紅色標語進行相應的改頭換面,以適應戰爭環境的復雜性,趨利避害。井岡山市行洲村至今保存了井岡山革命斗爭時期的一條標語,書寫內容是“紅軍是為勞苦工農謀利益的先鋒隊(!)” [2]。這條標語明顯有屢次改動的痕跡。行洲戰略位置重要,因而成為紅軍、白軍拉鋸式爭奪的目標。墻壁上書寫了紅色標語的房屋主人李煥湘為防止房子被毀壞,政治立場搖擺,紅、白通吃,通過涂改、篡寫標語部分內容的方式來保全自身。雙方宣傳陣地的爭奪與翻覆,是國共力量的消長在視覺與語言上的直接反映。
紙質標語被風吹雨淋易遭毀損,農村土墻也易倒塌,依附于這些載體上的紅色標語隨之消逝。蘇區紅色標語在漫長歲月中,遭遇人為的、自然的磨損。一部分有幸留存下來,成為今天追溯那段特殊歷史的重要線索。
三、關于中央蘇區紅色標語的記憶
中央蘇區的紅色標語是中國革命史上獨特的文化景觀,是不可再生資源的歷史文化遺產。經過鮮血與歲月的不斷磨洗,紅色標語實物資源正在減少。書寫之后,它必然要被“涂抹”、“記憶”。
法國社會學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ibwachs)將記憶分為個人記憶、集體記憶、傳統。個人記憶與個人的生活經歷相關。集體記憶,則由一些經歷過同樣事件的人們的共同記憶和相關的事件留下的客觀痕跡(與事件有關的空間、留下的制度、與此相關的文字和口頭檔案材料等)構成的。而傳統,在相關事件的當事人消失以后才出現。從那段血與火的歷史中走過來的紅軍將士和根據地民眾,對紅色標語絲毫不陌生。他們在回憶錄、訪談中經常談起當年滿墻赤色標語的盛況。他們一起經歷過的戰爭歲月構成彼此都無可回避的共同記憶。近一個世紀過去了,許多戰爭痕跡隱沒殆盡,而紅色標語至今尚有留存。仰仗這些客觀痕跡,他們構建他們的集體記憶。隨時間推移,漸漸地,紅色標語形成紅色文化的一個獨特傳統。
集體記憶的一個重要功能就是重構過去,滿足當今的精神需要。集體記憶總是和當今現實聯系在一起的。我們從文字學、文獻學、教育學、美術學、歷史學、社會學、傳播學、美學等多學科角度研究紅色標語書寫,是通過回顧過去,挖掘其歷史文化價值,讓紅色文化基因為新時代服務。記憶總是具體的、主觀的、帶有感情色彩的。人們研究紅色標語的記憶“亮點”,傳達對它的態度、情感以及價值取向。
保護、利用和闡釋,即是后人對蘇區紅色標語進行歷史記憶的重要方式。建國以后,當地各級政府特別是文物保護部門和文化管理部門,加緊收集整理蘇區紅色標語資源,根據實物毀損程度、現有資金技術條件,采取加固、修復、揭取、槌拓、轉移、攝影攝像等方式予以保護。原中央蘇區所在地多處標語群舊址被列為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湖南炎陵、福建永安、江西樂安等地開工建設紅色標語專題博物館,并積極建立紅色標語數據庫。條件適宜的老區部分農村,開啟紅色標語保護與傳統村落保護并行疊加的開發利用模式,將紅色標語保護與主題教育結合起來,紅色標語利用與鄉村旅游開發結合起來,實現紅色標語的活態呈現和活化利用。
紅軍標語文獻、標語實物,是蘇區紅色文化“歷史記憶”的重要載體。從事紅色文化研究的學者通過編輯整理標語實物圖像及其文獻并付梓出版的方式,喚起民眾的紅色記憶。迄今為止,《紅色印跡——贛南蘇區標語漫畫選》[3]、《歲月留痕——井岡山紅色標語選》[4]、《蘇區紅色標語》[5]、《紅色守望——炎陵縣紅軍標語選輯》[6]等一系列關于中央蘇區紅色標語的書籍先后出版面世。
人們的記憶并非一成不變,它會隨記憶對象在時間距離上的不斷推移而發生變形——凸顯或者隱沒。人們有意強化某些部分的記憶,也刻意淡化某些記憶。目前我國紅色旅游方興未艾,蘇區紅色標語作為紅色文化旅游的獨特資源被陸續開發利用。當代學者對紅色標語進行價值評估。他們選擇性地記錄,同時選擇性地對這些記錄作出一定的解釋。蘇區紅色標語及其遺產地的精神傳承、思想政治教育、史料研究借鑒等方面的社會效應,深深嵌在對它持續不斷的歷史記憶里。
紅色標語記憶實現了過去與現在的交融,而且這種交融和互動被視為歷史現實的一部分。
實用書寫、人為的或自然的涂抹、后世的記憶構成中央蘇區紅色標語流動的歷史進程。將紅色標語的書寫置于中央蘇區教育的歷史視野下進行考察,我們可以從源頭上找到紅色標語所呈現出來的獨特書寫狀貌的根本原因。蘇區的文化教育和紅色標語書寫兩者存在著一種因果共生的關系。紅色標語的重大歷史價值,還在于促使我們當代對原中央蘇區教育的制度模式、得失經驗進行深度思考和適度借鑒。
把紅色標語置于特定歷史時空下,遠距離冷靜地觀察與其相關的種種涂抹、隱沒、修復等變遷歷史,可以為后人提供一種客觀看待紅色文化資源的方式,對于形成系統保護、合理利用各種紅色資源的方法與途徑具有現實指導意義。
參考文獻:
[1]中國井岡山干部學院.蘇區紅色標語[M].北京:黨建讀物出版社,2015:345-346.
[2]中國井岡山干部學院.蘇區紅色標語[M].北京:黨建讀物出版社,2015:290-291.
[3]贛州市文化局、贛州市文物管理局.紅色印跡——贛南蘇區標語漫畫選[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4]曾文憲、謝敬霞.歲月留痕——井岡山紅色標語選[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
[5]中國井岡山干部學院.蘇區紅色標語[M].北京:黨建讀物出版社,2015.
[6]周新發.紅色守望——炎陵縣紅軍標語選輯[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