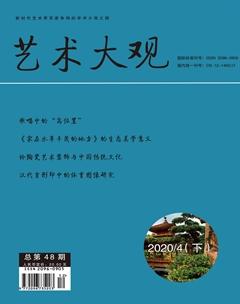《家在水草豐茂的地方》的生態美學意義
吉洛打則
摘 要:《家在水草豐茂的地方》拍攝出了一個少數民族的空間歷史記憶和時代宿命印記、精神心靈狀態和社會生存狀況。本文主要以生態批評的視角對影片進行草原文化生態“空骨化”、自然生態“荒漠化”和社會生態“離散化”等多維生態美學解讀,揭示影片在環保意識傳播上特殊的人文藝術價值,為和諧構建“一帶一路”領域生態文明建設與文化旅游開發提供電影人的思想視野。
關鍵詞:李睿珺;《家在水草豐茂的地方》;民族志電影;生態批評
中圖分類號:J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6-0905(2020)12-00-02
當前,生態問題的核心與關鍵是人與自然的關系,但生態危機并不僅僅限于狹義的自然生態危機,還有文化生態危機和社會生態危機。所以說,生態批評也不單只是關注自然生態這一層面,文化生態和社會生態同樣是生態批評著重關注的對象。作為一名具有環保意識的“80后”新銳導演,李睿珺在獨立電影制作探索路上的付出與收獲可謂有苦有樂。《家在水草豐茂的地方》是他繼《老驢頭》和《告訴他們,我承白鶴去了》之后,又一部關于人與自然、土地、親情的生態倫理題材電影。因此,這三部電影也被稱為“土地三部曲”。
《家在水草豐茂的地方》講述了裕固族兩兄弟巴特爾和阿迪克爾在爺爺去世后,為尋找爺爺遺言里父母所在的那個水草豐茂的地方,而在一路上經歷了兄弟情感從隔閡到和解、草原生態從豐美到荒蕪、家庭環境從合歡到流離的落寞過程。影片真實還原式地記錄了兩兄弟沿途所見所聞以及變化的心路歷程,他們只憑一句“如果放牧迷路順著河流走,家在水草豐茂的地方”,就抱著爺爺遺像騎著駱駝去尋找自己草原上的樣子,只想回到夢中的草原之家卻連草原在何處都找不到的故事。本文擬以生態批評理論為審美視角,通過文化生態、自然生態和社會生態等多維來解讀影片中所映射出的草原文化、自然以及社會與游牧民族之間的破裂的生態關系,試圖喚起人類對生態環境的思考以及對人類自身發展問題的審視。[1]
一、草原文化生態的“空骨化”
《家在水草豐茂的地方》的故事背后有著濃厚的現實基礎,影片拍攝手法也充滿了現實主義風格,對地域歷史的深度挖掘,對生態文明的深情關懷,特別是面對深受漢化西化雙重壓力影響的少數民族的命運,從人文主題到人性內容,多方位、多角度、多層面折射出現代化進程中失語失落失魂的邊緣族群不可名狀無奈深切的焦慮迷茫。電影講述的是裕固族的故事,也帶出了中國西域的少數民族古老悠久的歷史記憶。在這個意義上,影片無意中與“一帶一路”的國家戰略視野下的文化觀和歷史感形成了深度呼應關系。電影片頭字幕是在斑駁的壁畫中逐漸回顧中剝落的歷史信息,宛如一個族群的文明時代在我們眼前逐漸地消失:回鶻與黨項、契丹、吐蕃等同為中亞地區的游牧民族,9世紀晚期,甘州回鶻的勢力得到了發展,并在絲綢之路咽喉部位的河西走廊地區建立了甘州回鶻王國。11世紀初,甘州回鶻王國亡于西夏,此后甘州回鶻飽經戰亂,流散于河西走廊地區。裕固族是甘州回鶻后裔,目前人口大約一萬四千人。1953年以“裕固”為族名,意為“富裕、鞏固”。[2]
裕固族所處的草原文化生態的“空骨化”主要體現在母語的遠去和歷史意義的淡化。特別是母語的消逝情況在影片里有濃墨重彩生動傷感的表達:裕固族歷史上使用的文字叫回鶻文,而如今,這個民族90%的人以及不會說自己的母語,本民族文字已面臨失傳瀕危狀態。沒有母語的傳承,就沒有民族的未來。電影并沒有正面表現裕固族的興衰史,只是用兄弟二人在路途中的怪石林里發現的古老壁畫,來折射這一民族悠久的歷史。兄弟倆騎著駱駝尋找回家的路。一路走來,草原的毀壞,民房的破敗,水源的短缺在他們眼前晃過。草原文明遭遇了工業文明的蹂躪,家在哪?那個水草豐茂的地方又在何處?他們的爺爺離世前告訴他們,家就在水草豐美的地方,于是他們循著水源一直往前尋找,到最后終于找到了河流,可是家,不見了。當一族人面臨著文化、自然和社會等多重生態危機之后,當一地方喪失著輪廓、根骨和希望等多向歷史質感之后,當一時代遺忘著詩意、歌聲和母語等多層精神境界之后,我們不得不捫心拷問:“家”在哪里?或者,何處是“家”? [3]
二、草原自然生態的“沙漠化”
1970年代以來,沙漠化在全球迅速發展,對許多國家的經濟和人民生活造成嚴重威脅,沙漠化問題日益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關注。我國沙漠廣袤千里,既是世界上沙漠面積最大的國家之一,也是世界上沙漠化發展最為迅速、受沙漠化危害最嚴重的國家之一。電影用了大量鏡頭描繪反映我國北方環境遭工業污染、草場退化后形成的沙漠和戈壁,當中的環保主題意識是顯而易見的。片中采用了大量的細節來表現環境的惡化,特別是對草原自然生態極度“沙漠化”的展現。跟隨影片中兩兄弟一路緩慢飄忽經過的視角鏡頭,我們如臨其境般看到了草原上的土是“沙土”,草原上的草是“荒草”,草原上的井是“空井”,草原上的河是“枯河”,草原上的房是“空房”,草原上的村是“棄村”……正如隨著爺爺在離世前騎馬望著草原最后的背影響起的母語歌曲唱道:“綠色的草原啊,正在消失;奔流的河水啊,早已干枯。”同時,通過影片中的一些人物對白臺詞,我們也會直擊心靈般感受到草原自然生態的惡化:
“離鎮子越近的地方,草原沙化、退化越嚴重。”(劇中父親語)
“現在好多年輕人,他們賣掉牛羊,搬到農場種地。到處都開墾耕地,到處都打機井,井里的水抽干了,海子也都干了。還有的去淘金,有的去城里打工再也不回來了……”(劇中爺爺語)
“如今像母親一樣的河流干枯了,像父親一樣的草原枯萎了。”(劇中老者語)
從這些影片中主要人物的臺詞表達中,不難感受到電影敏銳指向過度開墾對牧場的破壞的生活背景,以及日漸嚴重的環境問題導致的草原沙化。影片的開始,以打井開始,一口井下打30多米依然沒有水源,可見地下水位下降已經非常嚴重。牧民原本的生活方式在現代化進程中發生變化。最后倆兄弟尋找了一路的“在水草豐茂地方”的家也變成了隆隆作響金屬冶煉廠,看不見成群的羊群,只看見原本拿著長鞭的父親現在卻站在河邊做起了開采工人。
三、草原社會生態的“離散化”
我們知道,家庭是社會最基本的單位。電影深入聚焦一個裕固族家庭不能繼續傳統游牧生活后,為了生存,父母只好把大兒子交給爺爺代養,父母去淘金,這樣導致家庭分離,兄弟矛盾加深。隨著城市(鎮)化進程從緩慢到加快,特別是近30多年來的飛速進展,城市舊區的改造開發和村鎮的撤并集聚,使大多數城鄉地區原有的自然和社會生態系統瓦解或改換,以地域風土建筑(民俗)為代表的傳統文化特征正以極快的速度消失。無疑,這種走向現代化的工業文明進程,削弱了草原社會生態結構的傳統紐帶,伴隨著這些結構變遷出現的各種文化影響,侵擾了草原特有的精神信仰和民俗。由此,草原社會變遷最主要是從個人或家庭之間地緣整合的原生紐帶,向族群離散的衍生紐帶轉變。[4]
總體而言,這部電影實質上是在表達一個民族在所謂的全球化經濟大發展的社會背景下逐漸消亡的時代寓言。在整部片子中,草原的消失、文化的斷脈、心靈的沙化三者交織交融。現代化、城市化的發展以及環境的破壞已經給裕固族的傳統生活、生產方式造成了很大的破壞和威脅,游牧放羊的方式已經被嚴重的沙漠化逼到越來越深的遠方。為什么在當下這個時代,生態成為一個問題?就是因為隨著現代化的急速推進,人變成一種悖論性的存在。人在成為自然主人的同時,人也失去了自然的家園。現代人突然發現自己無家可歸,成了“精神游牧者”。也就是說,原來可以提供給我們心靈關懷、精神庇護和詩意棲居的“家”沒有了。這種自然的失去和生態的災難日益加劇,使得藝術家們特別是有環保意識的創作者開始以自己的創作去反思人和自然之間關系的衰敗,進而反觀人和人之間的情感關系、人和社會之間的文化關系以及人和歷史之間的存在關系等等。
《家在水草豐茂的地方》不僅成為導演第一部在國內公開上映的影片,而且獲得了鹿特丹國際電影節HBF劇本獎、中國電影華表獎優秀少兒影片獎等獎項。影片在講述兩兄弟找尋父母和“水草豐茂”家園而行走草原的過程中,讓觀眾也通過熒幕目睹經歷了令人心碎的環境、生態及歷史文化,草原沙化、河流干涸、牧民遷徙等,對西部邊緣少數民族裕固即將消逝的生存環境及民族文化的深刻憂思,探討了特殊人群與周圍物質環境的關系,包括土地、自然、動物以及文化、社會關系等。總之,電影對生態問題及人與文化、自然和社會的關系進行了深刻的反思,提示人們重建和諧生態觀,從而實現人類價值觀主導的和諧社會。從文化生態學或生態批評的視角觀照當下中國的主流影片,無疑可以獲得一種更為普泛的價值取向和較有成效的言說方式。
參考文獻:
[1]王諾.生態批評與生態思想[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2]黃軼.中國當代小說的生態批判[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
[3]嚴平編.全球化與文學[M].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9.
[4]楊城.告訴他們,好電影在初心澄明的地方[J].電影,2015(0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