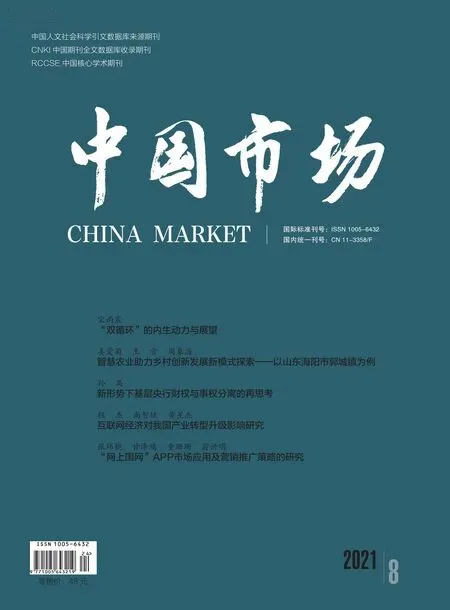地區社會信任水平與企業避稅行為
李思汕
[摘 要]文章運用中國2012—2017年A股上市公司數據,探討社會信任水平與企業避稅的關系。研究發現,公司所處地區的社會信任水平越高,其避稅水平越低。這說明企業高管行為可能受到社會信任形成的社會規范所帶來的外在壓力,以及由這種社會規范內化而成的個人道德規范的影響。稅收征管力度、法制環境水平、企業外部監管力度,以及產權性質的異質性均對這一關系有顯著影響,具體表現為:在稅收征管力度較小、法制環境水平較弱和企業外部監管力度較低的地區,社會信任對企業避稅行為的抑制作用才會顯著存在;同時,相比于非國有企業,社會信任對避稅影響在國有企業里才會顯著存在。文章豐富了公司避稅影響因素及社會信任經濟后果等方面研究。
[關鍵詞]社會信任;企業避稅;社會規范
[DOI]10.13939/j.cnki.zgsc.2020.24.103
1 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社會信任主要包含兩個層面的意思,即愿意相信他人的同時也值得被他人信任。信任是經濟交易的基礎,因為經濟交易是否會發生不僅取決于契約合同的可執行性,還取決于交易雙方對彼此的信任程度。并且,信任水平越高,能夠促進經濟交易的進行效率。由于交易契約的不完備性、買賣雙方之間信息不對稱性等,那么信息優勢方為了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可能會損害信息劣勢方的利益,而社會信任能夠產生一種承諾機制,即對于那些信任他人同時也值得被信任的人而言,他們能夠承諾自身行為與契約精神的一致性,即使這些行為無法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從而促進經濟交易的進行。
企業避稅行為能夠很好地體現社會信任的重要作用。可以把企業稅法看成是一種隱形的社會契約,在這一契約中,企業納稅人向公共支出、社會福利納稅。由于稅收準則的復雜性與高度技術性,企業稅法不可能明確規定企業納稅人在每一納稅環節的具體行為,因此,存在利用稅收制度的模糊性與規則漏洞進行避稅的可能性,稅法的這種不完備性給企業納稅人營造了避稅空間。
社會信任對企業避稅行為的影響具體表現如下:從社會規范角度分析,信任作為一種社會規范,可能會給總部位于該地區的企業高管的行為決策帶來一種外在壓力。Neighbors等將社會規范定義為社會成員所理解的指導和約束社會行為的一系列規則和標準,主要有兩種類型:描述性規范和禁令性規范。描述性規范指的是某一特定行為的流行程度(即在某一特定人群中,信任他人同時值得他人信任的人數),而禁令性規范指的是對某一特定行為的實際或感知認可程度。描述性規范和禁令性規范應該是高度相關的,因為一種流行的行為意味著許多人贊同這種行為。因此,在社會信任水平較高地區,社會上遍及信任他人并且值得被信任的人,從而形成信任這種社會規范。根據社會規范理論,社會規范之所以會影響個人行為,是因為個人更傾向于去遵循他們所在的社會群體,以規避因拒不遵從被人們普遍認同接受的準則、價值觀或信仰帶來的懲罰或成本。而社會規范的傳播和加強,在一定程度上是通過“社會啟發式證明”來實現的。“社會啟發式證明”認為,當個體感知到某一特定行為受到強大社會力量支持時,他們就會模仿這種行為。因此,在社會信任水平較高的地區,信任形成了一種社會規范,企業高管會更傾向于去從事大部分人所認同的誠信行為,減少避稅這種不誠信行為,來避免違背人們普遍認同的行為準則和價值觀而給自己帶來聲譽受損、失去他人尊重等成本。同時,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個人從事一種社會規范(社會信任)認為不合適或錯誤的行為(企業避稅),社區成員將會把經濟成本強加于行為不當的個體,如個人的聲譽、經濟前途可能受到損害。
因此,在信任氛圍較為濃厚的地區,高管會因受到社會規范帶來的外在壓力而減少企業避稅行為決策。
假設1:在信任氛圍較為濃厚的地區,高管企業避稅行為決策會受到抑制。
2 研究設計
2.1 樣本選取
文章將在控制公司特征變量的基礎上分析地區信任對公司避稅行為的影響。考慮到文章選取的信任調查數據在2013年,信任度在調查期間的幾年當中將會保持穩定,故文章選取2012—2017年A股上市公司作為初始研究樣本,并按照如下規則對初始樣本進行了剔除:①剔除金融行業上市公司。②剔除財務數據不全和注冊地缺失的公司。③剔除樣本期內計算公司實際稅率公式分母為負的公司,為避免異常值的影響,剔除實際稅率大于1或小于0的公司,還剔除了所得稅費用為負的觀測值以及名義稅率缺失的觀測值。對連續變量進行了上下1%的縮尾處理,最后得到4701個公司年度觀測值。
2.2 實證模型
為了檢驗文章的研究假說,構建了如下實證模型:
2.3 變量說明
文章借鑒陳冬、孔墨奇等對于避稅程度的衡量,采用名義稅率與實際稅率的差額進行衡量,其中,實際稅率=所得稅費用/息稅前利潤。上市公司適用的名義稅率與實際稅率的差額表示為 Diffetr1,即是文章使用的公司避稅程度變量。對于社會信任的衡量指標,采用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2013年的問卷中的問題“總的來說,您同不同意在這個社會上,絕大多數人都是可以信任的?”被調查者可以選擇“非常不同意”“比較不同意”“說不上同意不同意”“比較同意”和“非常同意”這5項中的一項。分別給這5個選項賦予值1、2、3、4和5,然后對每個省市的所有居民計算平均值作為這個省市的社會信任指標值。由于制度具有內在的穩定性,其變遷發生得十分緩慢,因而在實證研究中,可以使用地區某年的社會信任水平替代某段時間該地區的信任水平。這種處理方法已被廣為接受,而且也是合理的,因為已有研究發現社會信任在很長時間內可以保持穩定。
借鑒現有文獻的做法,在模型中加入了如下一些控制變量:①企業規模(size),它等于企業總資產的自然對數。一方面,大企業更容易受到關注,從而帶來更高的監督成本,實際稅率較高;另一方面大企業可能存在更多關系資源從而獲得的稅收優惠更高,因此無法預計該變量的符號。②盈利能力(roa),它等于稅前利潤除以總資產。盈利能力對實際稅率的影響可能正相關也可能負相關,因此也無法預計其符號。③企業的資產特性影響企業實際稅率,ppe(固定資產凈值/總資產)和chta(存貨/總資產)分別表示資本密集度和存貨密集度,以及intang(無形資產凈值/總資產)表示無形資產密集度。④企業成長性(growh),它等于企業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成長性對實際稅率的影響方向不確定,因此也無法預計其符號。⑤投資收益(roi),它等于年末投資收益除以總資產。⑥財務杠桿(lev),它等于總負債除以總資產。⑦公司前3位大股東持股比例之和(shrcr2)。考慮到公司治理因素會影響公司避稅行為,大股東的權力越大,越能制衡管理者的避稅行為。
3 實證結果
3.1 描述性統計分析
在稅收避稅指標中,differ1的平均值和中位數分別為0.0308和0.0244,最小值為-0.3,最大值為0.234,可見中國上市公司的避稅程度存在較大差異,這與吳聯生(2009)的研究結果相近;2013年的各個省份信任得分的最小值為3.271,中位數為3.283,最大值為3.294,方差為0.0044,表明各省份間的社會信任水平差異較大;growh均值為0.506,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別為-0.592和9.778,說明不同企業的成長性差距較大。其他控制變量均在合理范圍之內,在此不再贅述。
3.2 相關性系數分析
社會信任與資本密集度、無形資產密集度呈顯著正相關,同時社會信任與存貨密集度、企業成長性、投資收益呈顯著負相關,綜合來看,這些結果強調了在分析中控制以上這些企業特征的重要性。
3.3 基本回歸:信任與企業避稅
國稅總局對于稅法執行的力度在不同年份存在差異,宏觀經濟沖擊也會影響企業的實際稅負,這些都會導致企業避稅決策因時間而變化,為了剔除這種影響,在第二列回歸中加入了反映時間趨勢的虛擬變量,此時社會信任的系數依然顯著為負且變化不大。為了進一步保證回歸結果的穩定性,在第三列回歸中還控制了省份效應,可以看到,此時結果仍然穩定。上述逐步回歸的過程基本證實了文章的主要觀點,即在社會信任水平越高的地區,企業避稅行為越少。
此外,其他控制變量的估計結果都比較穩健,與現有文獻的結論也基本一致。其中,企業規模越大,企業的避稅程度也越高,即規模越大的企業,其經營活動也越復雜,因而能夠用于逃避稅的手段和機會也越多,相關的稅收籌劃也更容易成功實施。盈利能力越高的企業避稅程度較低,這可能源于盈利能力較強的上市公司,其受到稅收征管部門的關注度也越高,越容易成為“重點稅源企業”,大大壓縮了其逃避稅的空間。資本密集度越高的企業可以通過資本的加速折舊來進行更多的逃避稅,結果也證實了這一點,資本密集度越高的企業避稅越多,而存貨密集度越高的企業避稅則相應較少。
4 進一步分析:正式制度、信任與企業避稅
以上檢驗了社會信任對企業避稅行為的作用,而信任的這種作用在法制環境水平不同的地區是否存在差異呢?因為社會信任和法律是市場經濟交易秩序的兩個基本機制,正式契約的交易行為主要通過法律來規范和約束,許多無法通過法律機制執行的非正式契約交易則由信任機制來保證完成。特別是在法制環境水平較弱的地區,交易的達成更多地依賴交易雙方的信任與合作,此時,包括信任在內的社會資本所起到的作用會更加明顯。現有研究也證實了信任等社會資本對金融發展水平的影響在法律保護不完善的地區更為顯著;特別是在我國,盡管具有同樣的法定權力,但不同地區的法律環境依然存在較大的差異,此時社會信任等社會資本是法律保護的一種重要替代機制。因此可以認為在抑制企業避稅行為方面,社會信任在法制環境水平較差的地區就更為重要。
文章分別按以下三個指標來衡量一個地區的法制環境水平:①稅務稽查人員密度=稅務稽查人員總數/檢查戶數;②稅務稽查機構密度=稅務稽查機構數/檢查戶數;③稅收案件發生率=稅收案件數/總檢察戶數。如果稅務稽查人員密度、稅務稽查機構密度越大,說明該地區法制環境水平越高,而一個地區的稅收案件發生率越低,則該地區法制環境水平越高。通過手工翻閱相應年份的《中國稅務稽查年鑒》的方式獲取此方面的數據。將各省份2012—2017年的各指標值取其平均值,作為該省份的指標值,分別按上述三個指標的均值為標準,定義稅務稽查人員密度、稅務稽查機構密度高(低)于其指標均值的、稅收案件發生率低(高)于其指標均值的,為法制環境水平較高(低)組,將所有地區分為法制環境水平高低兩組,分組進行重新回歸。在稅務稽查人員密度、稅務稽查機構密度較低組,以及稅收案件發生率水平較高組,社會信任更有效抑制了企業避稅行為,并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通過了統計檢驗。
綜合以上發現,在法制環境水平較低組,社會信任影響系數更大,可能的原因是,在外部法制環境水平較低的地區,企業高管進行避稅操作的空間更大,社會信任對高管行為的約束作用更為凸顯,從而對企業避稅行為的抑制作用影響更顯著。
5 穩健性檢驗
5.1 內生性問題
以上結果充分表明社會信任會對企業避稅行為產生重要而又顯著的影響,但這一結果可能會受到內生性的影響。在內生性的三種形式中,即測量誤差、遺漏變量及反向因果關系,由于信任在一段時間內較為穩定,因而較少受到反向因果問題的困擾,但是用調查數據來測度的信任,可能會存在測量誤差及遺漏變量問題,這兩方面的內生性會影響結論的穩健性。根據張維迎和柯榮住的研究結果,交通情況、公民受教育程度等因素都與信任度具有顯著正向關系。為此,用高等教育普及程度、交通設施情況作為社會信任的工具變量。首先將社會信任作為因變量,以各地區的交通設施狀況(包括內河航道里程、鐵路、公路里程之和)、高等教育普及程度(在校高等學生占總人口比例)為工具變量進行回歸,以上數據取自歷年《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年鑒》《中國人口與就業統計年鑒》,再提取剔除以上因素之后的模型殘差,重新將其作為自變量對企業避稅回歸,如果結果依然保持顯著,那么就表明前文的結論是穩健的。這種方法不僅能夠緩解社會信任的測量誤差,而且能夠弱化遺漏變量可能導致的偽回歸問題。
第一階段回歸結果顯示,社會信任作為因變量時,在1%的水平下以上兩個工具變量都顯著為正,這意味著交通越發達以及受教育人數比例越高的地區,其信用環境也會越好,這與張維迎等的研究結論一致,并且第一階段回歸中F值為83,大于10,說明所選工具變量不存在弱工具變量問題,即所選工具變量是有效的。Durbin-Wu-Hausman檢驗結果顯示,可以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拒絕“所有變量均為外生”的原假設,即認為社會信任為內生變量。在第二階段,從結果來看,關注的主要解釋變量社會信任的結果依然顯著為負,表明文章的主要結論在考慮內生性的情況下依然穩健。
5.2 更換被解釋變量
替換企業避稅衡量方式。借鑒葉康濤與劉行的研究,采用會計—稅收差異(BTD)來刻畫企業的稅收規避程度。具體而言,BTD等于(稅前會計利潤—應納稅所得額)/期末總資產。應納稅所得額=當期所得稅費用/名義所得稅率。BTD越大,意味著會計利潤與應納稅所得額的差異越大,從而企業越有可能從事避稅活動。
替換社會信任衡量方式。文章借鑒武恒光與鄭方松的研究,采用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2015年的數據。采用的社會信任指標xinren2(Trust),是針對問題“在不直接涉及金錢利益的一般社會交往/接觸中,您覺得下列人士(陌生人)中可以信任的人多不多呢?”被調查者可以選擇“絕大多數不可信”“多數不可信”“可信者與不可信者各半”“多數可信”和“絕大多數可信”這5項中的一項,分別給這5個選項賦予值1、2、3、4和5,然后對每個省市的所有居民計算平均值作為這個省市的社會信任指標值。
綜上可見,上述穩健性檢驗結果未發生實質性變化,說明文章的研究結論具有較高的可信度。
6 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社會信任可以通過社會規范給予高管更多的外在壓力,以及內化為個人道德信仰給予高管內在動力,從而降低企業避稅行為。文章以2012—2017年中國上市公司作為研究樣本,運用OLS和分組回歸的方法檢驗了社會信任對企業避稅的影響。研究結論如下:①地區社會信任水平越高,企業避稅行為越少,即社會信任可以有效抑制高管避稅行為決策;②地區稅收環境(稅收征管力度、法制環境水平)會影響社會信任對企業避稅的抑制作用,且兩者為替代關系,即,在稅收征管力度較強、法制環境水平較高的地區,社會信任對避稅行為的影響會被弱化,只有在地區稅收環境較差的地區,社會信任對避稅行為才有顯著影響;③雖然企業外部監管與社會信任都會對避稅行為產生抑制作用,但兩者是替代關系,即,在企業外部監管水平較低時,社會信任對避稅的抑制作用才能凸顯出來;④相比于非國有公司,社會信任僅對國有公司的避稅行為有顯著的抑制作用。在改變主要變量度量方法的穩健性測試后,文章結論依然成立。上述經驗證據表明,社會信任是公司避稅行為的重要影響因素,文章豐富了公司避稅的影響因素以及社會信任的經濟后果文獻。
文章提出以下政策建議:①社會信任水平越高,對企業避稅行為的抑制作用越強,因此,想要減少企業避稅,政府可以從加強社會信任制度建設入手,通過打造公平正義的制度環境構建社會信任體系,積極引導社會的價值取向,營造人人相互信任的良好經濟社會發展環境。②由于稅收征管力度、地區法制環境水平、公司外部監管力度與社會信任都是替代關系,所以在社會信任水平較弱的地區,建議相關執法部門加大稅收征管力度、提高法制環境水平,建議所在地區的企業加強外部監管,以增加避稅機會成本,減少企業避稅行為的實施。
參考文獻:
[1]田彬彬, 范子英. 稅收分成、稅收努力與企業逃稅——來自所得稅分享改革的證據[J].管理世界, 2016(12):36-46.
[2]陳德球, 陳運森, 董志勇. 政策不確定性、稅收征管強度與企業稅收規避[J].管理世界, 2016(5):151-163.
[3]NEIGHBORS C, LOSTUTTER W, WHITESIDE U, et al. Injunctive norms and problem gambling among college students[J].Journal of gambling studies, 2007,23(3):259-273.
[4]SHERMAN J. The psychology of moral development. vol. 2: the nature and validity of moral stages. lawrence kohlberg[J].The journal of religion, 1986,66(3):354-355.
[5]朱國泓, 張璐芳. 宗教的公司治理作用機制和影響效應研究述評與未來展望[J].外國經濟與管理, 2013,35(7):23-34.
[6]R C. Influence: the psychology of persuasion[M].New York: Quill, 1993.
[7]陳冬, 孔墨奇, 王紅建. 投我以桃,報之以李:經濟周期與國企避稅[J].管理世界, 2016(5):46-63.
[8]吳聯生. 國有股權、稅收優惠與公司稅負[J].經濟研究, 2009,44(10):109-120.
[9]劉鳳委, 李琳, 薛云奎. 信任、交易成本與商業信用模式[J].經濟研究, 2009,44(8):60-72.
[10]WU L, WANG Y, LIN B, et al. Local tax rebates, corporate tax burdens, and firm migr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J].Journal of accounting & public policy, 2007,26(5):583.
[11]張維迎,柯榮住. 信任及其解釋:來自中國的跨省調查分析[J].經濟研究, 2002(10):59-70.
[12]潘越, 吳超鵬, 史曉康. 社會資本、法律保護與IPO盈余管理[J].會計研究, 2010(5):62-67.
[13]GUISO L, SAPIENZA P, ZINGALES L. The role of social capital in financial development[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4(94).
[14]ANG J, CHENG M, WU P. Social Capital,Cultural Biases,and Foreign Investment in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J].Mendeley,2009.
[15]葉康濤, 劉行. 公司避稅活動與內部代理成本[J].金融研究, 2014(9):158-176.
[16]武恒光, 鄭方松. 審計質量、社會信任和并購支付方式[J].審計研究, 2017(3):82-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