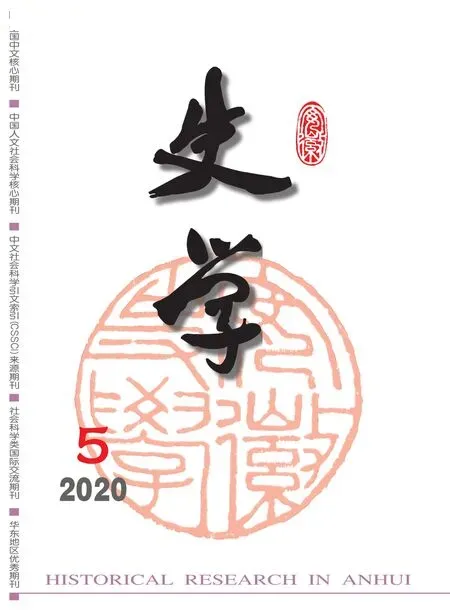北洋政府時期米禁政策研究
——以蘇米弛禁案為中心(1918—1920年)
(長沙學院 馬克思主義學院,湖南 長沙 410081)
米禁是我國平準物價、保護民食的重要糧政。時至近代,隨著商貿的興盛,這一政策因有違自由主義通商規則而飽受抨擊,政府卻將之納入條約制度,不斷強化。1858年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條約》及1902年《中英續議通商行船條約》對禁米出口與出洋皆有明確規定,1905年清政府又頒布《運米出省章程》和《稽查私運米石章程》,聲明除特別允許外,不得運米出省。
江蘇素有“魚米之鄉”的美譽。北洋時期,該省承襲清代的米禁制度,先后頒布《江蘇運米出省章程》和《江蘇限制運米出省章程》。這項有著種種弊端的糧政為何盛行于世?既有研究主要從承襲清制和食米緊缺兩方面解釋,對外力介入及走私出洋的問題探討有限。本文之所以選擇1918—1920年的蘇米弛禁案為研究對象,以其既關涉英日外交,又牽及中央與地方、政府與社會等多層面,充分暴露出列強干預我國糧政、走私販米出洋的行徑,頗具典型意義。目前研究多著眼于該案所呈現的中日關系和政商互動(1)有關蘇米弛禁案的專題研究,主要有[日]馬場明《日中関係と外政機構の研究(大正·昭和期)》第二章“中國米輸入問題”(東京原書房1983年版,第38—66頁),張莉《利益與秩序:1919年蘇米弛禁風波研究》(《華中師范大學研究生學報》2015年第4期),紀浩鵬的《內政與外交的二重變奏:日本“米騷動”與中國江蘇米糧弛禁之爭(1918—1919)》(《海洋文明研究》2019年第4輯),分別從政府外交、政商互動、以及“米騷動”對華影響等視角,不同程度地梳理了日本運弛江蘇米禁的交涉過程。,對近代蘇米何以遽難弛禁這一核心問題尚缺乏深入分析。本文利用中、英、日外交檔案,通過爬梳國家之間、中央與地方之間、地方軍政商農之間的復雜糾葛及動態變化,說明在外力干預、內政失序的北洋時期,米禁是地方政府保護糧食安全、維護社會安定的必要途徑。
一、違約與恤鄰:蘇米弛禁之外來壓力
1918年初,北洋政府加入巴黎糧食同盟以接濟協約國。江蘇作為農業發達地區,須清查米麥牛羊茶糖的常年產額、輸出數目及時價,為出口做準備。是時,蘇省米禁厲行多年,投機者早已蠢蠢欲動。消息傳出,滬寧等地即有弛禁謠言,奸商囤積居奇,米價驟然騰貴。后經中央澄清,地方當局重申禁令,并有外地米及時輸入,米價才暫得平復。而因前番爭買,上海各碾米廠米谷積壓嚴重,米商為免虧折,先是搜羅火車,從浦口運米北上,致使津浦路走私成風。遭官廳緝查后,其又勾結英國輪船公司,企圖航運糧米,結果被海關扣留。聞知英商運米受阻,駐寧英領翟比南介入此案,蘇米弛禁遂上升為外交糾紛。
《中英續訂通商行船條約》第14款規定:“惟米谷禁期之內,應于示內聲明漕米、軍米不在禁列;如運出口者,須先載明數目若干。但此項米谷雖在不禁之列,而應于海關冊簿逐日登記進出若干。除此之外,其余他項米谷一概不準轉運出口。……倘于既禁之后,如準無論何項米谷載運出口,則應視該禁業已廢弛。”(2)王鐵崖編:《中外舊約章匯編》第2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社1982年版,第109頁。可見,米禁期的江蘇只準出運持有護照的軍米和漕米。然則翟比南調查后獲悉:津浦路運載北上的米谷每日至少在300至500噸,大都來自蘇常無錫等地,其中僅有二成領有軍用護照,余八成皆為無照販運。即便領有護照者,至天津后亦在市面銷售。如此亂象,翟比南認為已違約章,且根據中英商約,禁運前提是有饑荒之虞,而浦口、無錫等多地米谷卻有壅滯腐壞之患。(3)《江蘇省咨一件》(1918年8月5日),北洋政府外交部檔案,臺灣“中央研究院”近史所檔案館館藏(下文簡稱“北洋政府外交檔”,不再注明藏地),館藏號:03-18-069-01-004-29。是而他以應視米禁業已廢弛為由,催促江蘇省署準許各英輪公司出運米谷。外交部得知后,亦令江蘇省長齊耀琳嚴密查禁,“以免外人指為違約,而于蘇省米禁致生障礙。”(4)《咨江蘇省長》(1918年7月26日),北洋政府外交檔,館藏號:03-18-069-01-003-23。
面對英領質詢,齊耀琳斷然否認米禁開弛。實際上,地方當局對津浦路走私并非毫無覺察,苦于屢禁不止。而英方指該路為國有鐵路,“非經該處官員知情許可,則不能有此巨數米石出口之事。”(5)《英朱使照會一件》(1918年10月7日),北洋政府外交檔,館藏號:03-18-069-01-023-117。所影射的官商勾結問題亦未必空穴來風。然因米禁與條約牽涉頗深,一旦弛禁,復禁須以42日為限。如禁期之前米谷不及裝完,仍有7日寬限,如此數十日間米谷輸出將不可勝計。且蘇省頻年歉收,本地產米供給省內尚有不敷。故齊耀琳堅持從未放行無照之米,并咨請交通部強化對津浦路的稽查。英方卻頗不以為然,雙方各執一詞,僵持不下。正值此時,日本又有告糴之請。江蘇米禁政策面臨著嚴重危機。
1918年6月,日本因大量收購軍糧,又有商人囤積居奇,以致糧價飛漲,社會不安。為緩解糧食不足,日政府將目光投向中國。8月,無錫商會聲稱有存米200余萬石,要求開弛米禁。然則江蘇內部米谷流通不暢,一地存米雖多,并不意味整個省份皆無乏食之憂,而這一消息卻給日本以口實。參贊船津辰一郎照會外交部和農商部,意欲指定商人采買蘇米輸送日本。 20日,日領清野長太郎拜訪齊耀琳,船津亦面會財政總長曹汝霖。日本運弛米禁遂從中央和地方同時展開。
齊耀琳對米禁的態度,從與英使的交涉中可見一斑,他卻向清野表示:省署并無阻撓之意,只是省議會在討論本案時曾有以20票對90票的多數否決。(6)《在南京清野領事館事務代理ヨリ後藤外務大臣宛》(1918年8月20日),日本外務省:《日本外交文書》(1918年),第2冊上卷,第546頁。齊耀琳此舉究竟是虛與委蛇,還是真情實意呢?實際上,他早已向中央說明蘇省連年荒歉的情況,言及不能弛禁之理由:首先,根據條約規定,非禁期內米谷亦不準出洋。一旦開此先例,勢必無法阻止各國援引。其二,依照《江蘇限制運米出省章程》第2款“凡產米或聚米素多之地,上等米……如已過8元,即由該縣知事禁止出境”(7)《本省法令》,《江蘇省公報》第87期,1912年12月28日,第5頁。,而上海米價每石已在8元以上,內地各處糧價亦有所漲,理應維持米禁。其三,無錫作為存米地區,不足以代表蘇省。由是他以米禁事關地方要政,駁斥日使所謂“江蘇省長已有允意”一說。(8)《外交部收農商部咨一件》(1918年9月6日),北洋政府外交檔,館藏號:03-18-069-01-019-94。可見齊耀琳堅執米禁,并未有絲毫動搖。然而,北京政府的態度卻與其截然不同。
是時,執掌北京政府的皖系軍閥主親日外交,1918年5月與日本簽訂有《共同防敵軍事協定》,加之其早有運糧出洋的意向,回應日本告糴甚是積極。曹汝霖向船津表示:公然標榜禁米出洋必然引發各方反對,不如以軍米為名,由政府秘密購買100萬乃至150萬石(9)《在中國林公使ヨリ後藤外務大臣宛》(1918年8月20日),《日本外交文書》(1918年),第2冊上卷,第546、547頁。,再向日本輸出。軍米是條約允許禁期出境的米谷之一,也是津浦路上私運泛濫、英使迭次抗議的焦點。且據《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第7款規定:“關于共同防敵所需之兵器及軍需品并其原料,兩國應互相供給。”(10)王鐵崖編:《中外舊約章匯編》第2冊,第1366頁。中國可以軍需品名義將軍米接濟日本。作為交換條件,北京政府意在謀取暴利,“若政府輸出百萬石,每石征收5弗的特許費,合計將得500萬弗之收益。”(11)《在中國林公使ヨリ後藤外務大臣宛》(1918年8月20日),《日本外交文書》(1918年),第2冊上卷,第546、547頁。船津一度認為要價過高,不以為然。而隨著“米騷動”形勢惡化,日本國內需求急迫,雙方遂各有讓步。國務總理段祺瑞提出:“征收每石2弗左右的護照授予費、限制輸出數量和時間。”(12)《在中國林公使ヨリ後藤外務大臣宛》(1918年8月25日),《日本外交文書》(1918年),第2冊上卷,第549頁。總統馮國璋也肯定輸出米谷有救濟鄰邦、維護本國農商之益。至此中央態度趨于一致。考慮到米禁依然是運米出洋的嚴重阻礙,北京政府與日本遂在地方展開活動。同時,社會關于米禁的爭論也喧囂塵上,偷漏私運愈發嚴重,英使抗議日益激烈。來自英國、日本、中央政府乃至輿論的壓力,對江蘇當局形成了嚴峻考驗。
二、各執一詞:中央與地方政府之博弈
北京政府既決定弛禁濟日,便迭電省長齊耀琳和督軍李純,以救恤鄰邦之義、業已許諾日本為由(13)《在中國林公使ヨリ後藤外務大臣宛》(1918年9月3日),《日本外交文書》(1918年),第2冊上卷,第550頁。,訓令江蘇裝運米谷100萬石,上海派20萬石,無錫、常熟等59縣酌量出數、再定限額。實際上這一所謂承諾,連日本政府都不甚明了,可見是中央脅迫地方就范的手段。齊耀琳只得分行各屬官員自行研究利害,由是引發輿論嘩然。
偷漏私販之于蘇省已是心腹巨患。日本乞糴消息傳出后,投機商戶早已囤積米谷,且有流言紛紛,或指北京政府可能輸送米谷赴日,或稱日商購米若干萬石、正待船裝運。更有前財政總長王克敏私設大有公司,專門販米運日,其他運米機關也有繼起之勢,激起民眾強烈不滿,米商聯合抵制,省署也致電國務院要求沿省各關卡嚴查過境蘇米。
大批米谷既被轉運出洋,江蘇米價遂漲至8元左右。省議會、多地社會團體及士紳紛紛呼吁省署和中央取消弛禁、嚴拒日本。旅滬津幫米商則要求查辦大有公司。日文報紙《上海日日新聞》也指出,若因輸出華米而誘發內亂,將使日本對華商務大受損害。一時間,申禁吁求占據輿論主流。不過,也有少數弛禁的聲音。虞洽卿的三北公司曾向日商購買仁陽丸輪船,因日政府不允過籍,不得已而與華僑改組申陽公司。在聞知日本亟需接濟民食的消息后,虞洽卿為維持華商航業起見,請中央以購買和租用日船為交換條件,由上海公共機關有限制地購運米谷,“已商通滬商領袖及米業董事,專候政府采擇。”(14)《收上海虞和德電》(1918年9月5日),北洋政府外交檔,館藏號:03-18-069-01-018-91。基于其上海總商會要人的身份,9月11日《北京國民公報》以“滬商會請弛米禁”揭露此事,該商會遭致商界人士質問,被迫公開表示與各團體同一宗旨。
鑒于輿論爭議及可能引發的社會問題,齊耀琳維持米禁的立場愈發堅定。中央意識到此事難以迅速解決,逐漸傾向以軍米輸出的方式。但曹汝霖因不滿于日方過低的收購價格,遂利用虞洽卿的影響力,由商會發起請愿,再度試圖運弛米禁。然而10月10日江蘇省議會第二屆第一年常會通過的重申米禁案,則證明了這一嘗試的失敗。咨文中,省議會痛陳江蘇近年災荒不斷、所產米谷僅能勉強自給的現狀,批判奸商只知牟利、不顧民生,以致米價昂貴,進而請求省署堅守條約定規,嚴杜私運。是可知米禁政策雖有缺陷,但走私問題的存在,卻使地方官民不得不未雨綢繆,引以為限。照此意見,齊耀琳一面函知商會勸告各米商顧全大局,不可違背禁令;(15)《江蘇實業廳訓令第2128號》,《江蘇省公報》第1766期,1918年11月7日,第5頁。一面駁復英、日兩國:“今復考察地方輿情,證以省會議案,萬難開弛米禁。”(16)《外交部收國務院秘書廳抄交齊耀琳電一件》(1918年11月6日),北洋政府外交檔,館藏號:03-18-069-01-027-135。
英國與日本接連遇挫,卻并未罷休。就日本而言,時至12月中旬,日商在江北地方收購、輸出米糧的數額已經達到三四十數萬石。對于接下來的行動,清野指出:一,考慮到北京政府購米不會驚動地方,可委托中國財政部和農商部辦理。二,針對省議會的阻礙,可從當地選出相關利益者,予以援助。三,鑒于商務總會在省議會中有相當的勢力,可令該會相關人士設立臨時米輸出公司等組織。督軍署顧問溫世珍也建議日方活動二、三個商務總會,“在言明可能輸出數額的基礎上,謀求省議會的再次考慮。”(17)《在南京清野領事館事務代理ヨリ內田外務大臣宛》(1918年12月13日),《日本外交文書》(1918年),第2冊上卷,第556頁。在設法采購蘇米的同時,日使還向外交部請準運日蕪湖米100萬石,雖得安徽督軍倪嗣沖積極響應,然蕪湖米并不適合日本人食用,在承辦者武內金平看來,實際上是借中國米輸入之聲勢以緩和本邦米價。(18)《在中國芳沢臨時代理公使ヨリ內田外務大臣宛》(1918年12月20日),《日本外交文書》(1918年),第2冊上卷,第557頁。日陸軍當局也有依據《中日軍事協定》來華購米的意向。而英國方面,鑒于津浦鐵路每周運米已達5000包以上,半數以上仍無任何執照(19)《英朱使照會一件》(1918年12月31日),北洋政府外交檔,館藏號:03-18-069-02-002-19。,公使朱爾典依舊強烈要求取消蘇省米禁。值此之際,經顧問施愚、溫世珍等人的活動,督軍李純的態度也有所動搖。是以各方勢力紛紛介入,事態愈加錯綜復雜。作為利益分配者與最終決策者,地方當局陷入了左右為難的窘境。
三、里應外合:蘇省米禁之危機
重申米禁后,江蘇米價漸有平復。1918年11月,時逢秋收,省署統計各縣所存米谷實數,獲悉無錫存米糧共300萬石,上海43家機器米廠約存糙白各米50萬余石。(20)《調查上海存米之函復》,《申報》1918年12月8日,第10版。而在松江、青浦等產米之區,新谷更異常涌旺。市場旋即出現存貨過多、積而不化的情狀,有國稅難征、谷賤妨農的隱患。省署在準予出運軍米50萬石的同時,對禁米出洋的態度也出現了松動。
在此期間,日方對省署和議會要人的活動甚力。省議會方面,日商代表藤田諭一拜訪議長錢崇固,角田他十郎擬就請愿書與意見分致各議員。江蘇當局方面,三井洋行于12月31日向李純遞交了購運蘇米100萬石的申請。隨后李純在與清野的會面中,流露出用米谷換取軍備之意。督軍態度何以發生轉變?除購買軍器的原因外,彼時南北和平會議即將在南京召開,李純負責籌備工作,故清野推測其有借機取得會議機密費的打算。為從速辦理以免橫生枝節,1月11日清野提請特批三井洋行購運蘇米。對此,李純欲直接授予該日商購運蘇米的特別許可,而齊耀琳卻堅持征求省議會意見。因案屬民政,無省長批準難以成事,李純縱有助日之心,暫也無可奈何。根本而言,蘇省的存米狀況是米禁申廢的基礎。適逢上海有新設組織糧食研究會,借調查米糧實數而要求開弛米禁,李純得知后頗為支持。省長方面則由王克敏、施愚等人繼續活動,以求達到既定目的。
加緊消除地方障礙的同時,日本并未放松與北京政府的聯系。獲知英國也有弛禁要求后,新任日使小幡酉吉建議聯合英國對華施壓,徹底廢除米禁。而借助延長《中日軍事協定》有效期的交涉,駐京日本陸軍中將齋藤季治郎也秘密搜購軍米,他一方面命三井等日商在江蘇運作采買,另一方面收集情報,意欲從天津、江西與安徽等地著手購米。時逢年末,北京政府14000余萬政費尚無著落,對日態度更見積極。不久后船津獲悉,財政部擬與日本政府締結《采運米石合同》,將長江一帶產米450萬擔分3年輸出日本。由于米價騰貴與社會非議皆有導致失敗的可能,這一交涉由兩國極秘密地開展。
《中日采運米石合同》共分8款,詳細規定了分批采運數額、采運地點、計量標準、運米執照等內容。為規避商約,其第8款特載:“本合同系屬特定,不受各約章規定之限制,一俟運額完竣,本合同即行作廢。”(21)《在中國小幡公使ヨリ內田外務大臣宛》(1919年1月27日),《日本外交文書》(1919年),第2冊上卷,第560、558頁。實際上這一聲明究竟有否約束力,尚待商榷。為了緩解財政危機,北京政府甚至要求日本將照費先行交付或分期預繳。至于售價,賦稅司長袁永廉建議執照手續費定為1弗40仙,其中40仙分配給地方政府,再加上輸出稅、厘金等雜費約計50仙,這樣執照費便限于在2弗以內。(22)《在中國小幡公使ヨリ內田外務大臣宛》(1919年1月27日),《日本外交文書》(1919年),第2冊上卷,第560、558頁。日方卻有顧慮:一方面從預付形式來看,政府能否壓制地方以履行其義務,尚未可知。若出現無法購買的情況,預付的照費如何處理?所以日方提出特許輸出至少250萬擔(23)《道家農商務省臨時米穀管理部長ヨリ田中通商局長宛》(1919年1月29日),《日本外交文書》(1919年),第2冊上卷,第570頁。、預繳金額再行議定等修改意見。另一方面就費用而言,由于中央與地方間存在著利益爭奪,任何一方需求得不到滿足都有礙輸出,日本還要給予地方一擔米約50仙左右的秘密活動費,如此每擔米便合計須2弗50仙。(24)《在中國小幡公使ヨリ內田外務大臣宛》(1919年1月28日),《日本外交文書》(1919年),第2冊上卷,第561頁。據此,日方認為中央提出的價格過高,希望將執照手續費降至每擔銀1弗以下。是時,三井和大倉在蘇皖的購米活動已見成效。日本若與地方當局協商成功,則大部分手續費有被地方剝奪之虞,中央或有非難之舉。而如果購米合同成立,則地方反會被中央奪去多數利益,致有不喜契約成立之事。結合李純購置武器的意圖,不難推測中央與江蘇間的利益之爭,一定程度上也是皖系與直系間維護統治、擴大實力的斗爭。為保證購米的順利進行,日政府指示三井和大倉將其大部分利益給予地方,暫作權宜之計。
經多方疏通,齊耀琳雖不明確反對弛禁,但仍堅持提交省議會審議。是時,日使敦促國務總理、財政部與外交部,齋藤中將指導三井活動靳云鵬、徐樹錚等陸軍要員,中央與地方就蘇米輸出已基本達成一致,惟省議會可能成為阻礙。財政部在訓令齊李二人時指出,召集臨時省議會徒延時日,況且日本公使的催促也極為迫切(25)《在中國小幡公使ヨリ內田外務大臣宛》(1919年2月7日),《日本外交文書》(1919年),第2冊上卷,第576頁。,意圖繞過省議會行事,以免再生事端。
盡管中央和省署皆視蘇米運日為絕對機密,然日人種種活動早已見諸報端,流言不斷,米價隨之見漲。又有馬相伯、熊希齡、孫寶琦等士紳名流組織上海糧食研究會,要求疏通存米以解民困,并派代表分赴京省請愿,招致申禁者大為反感。社會輿論漸分成申廢兩派,議論紛岐。因傳聞中央施壓,地方官廳不能自主,南京總商會、地方公會、農會、教育會、地方自治公所等機關拍電北京府院,痛斥糧食研究會計遠利而忘近害,請求切勿弛禁。(26)《收南京地方公會總商會電》(1919年2月3日),北洋政府外交檔,館藏號:03-18-069-02-009-44。南京寧垣等地則組織民食維持會,與糧食研究會相抗衡。省議員亦多有通電中央和地方官廳者,或請堅持禁令,或求速開議會。
不難發現,處于輿論旋渦中的上海糧食研究會無論是成立的時間與地點,還是所持意見,均有耐人尋味之處。它雖表達出地方士紳疏通存米、活潑市場的愿望,然行事卻頗為可疑:其號稱調查米糧實數以定出口限制,卻沒有出示任何結果,坊間亦傳言該組織者系受外人及米販委托,代謀疏通。此種說法是否屬實?據小幡酉吉所言,該會實際上是“當地三井洋行利用有勢力的中國人組織發起。”(27)《在中國小幡公使ヨリ內田外務大臣宛》(1919年1月22日),《日本外交文書》(1919年),第2冊上卷,第554頁。財政部也曾援引糧食研究會來電為弛禁借口。可見該組織背景非同尋常,被輿論抨擊也是情理中事。值得注意的是,時至1919年2月中旬,糧食研究會態度卻驟然一變,轉而主張禁米出洋,原因何在?這實際上與中日關系的變動有著密切聯系。2月2日,小幡無理干預中國代表在巴黎和會上的發言,并以聽任東三省獨立、停止交付參戰借款、永遠占領膠州等詞威脅北京政府。消息傳出,北京政府畏首畏尾的處理方式立即遭到國內外的批判和質疑,糧食研究會主要成員張謇、熊希齡等皆極為憤慨。張謇原本贊成運米輸日,曾向齊耀琳、李純建議實施有限制的弛禁辦法。然在干涉事件發生后,他當即致電總統徐世昌,指責政府軟弱(28)《致徐世昌電》(1919年2月2日),《張謇全集》第2冊《函電 上》,上海辭書出版社2012年版,第703頁。,并聲明因情勢變遷,米石出洋為自害政策,絕不可行。熊希齡電告李純,認為日本既無親善誠意,我方也不必顧念救災恤鄰,亟應停止軍米護照,嚴禁蘇米出口,“無論中央政府如何允許,尊處可以反對扣留。”(29)《請嚴禁米糧出口日本致南京李督軍電》(1919年2月6日),《熊希齡集》第7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5頁。同期,蘇滬民眾也掀起了聲勢浩大的反日浪潮。受此影響,李純亦有與日延期協議之意。江蘇官民態度復趨一致,即重申米禁。
鑒于民意沸騰,上海米價又見增長,小民和工界已有“食粒維艱之嘆”(30)《蘇省米禁問題之文件》,《大公報》1919年2月25日,第3版。,齊耀琳預定于2月28日召開省議會,擬將《中日購米合同》及三井請購米谷100萬石這兩種辦法交付討論。14日,徐樹錚將省長承諾輸出100萬石的消息轉告齋藤。(31)《在北京斎藤陸軍中將ヨリ福田參謀次長宛》(1919年2月14日),《日本外交文書》(1919年),第2冊上卷,第580頁。而齋藤仍不放心,又命三井在上海秘購蘇米20萬石,一旦省議會否決議案,即作為中國陸軍用米向北方輸送,此乃與徐樹錚的私下協議。(32)《在北京斎藤陸軍中將ヨリ福田參謀次長宛》(1919年2月16日),《日本外交文書》(1919年),第2冊上卷,第583頁。極力滿足日方要求的同時,因關涉條約,北京政府與地方官廳也不得不重新審視英方要求。在中日秘密交涉的兩月間,英領數度抗議皆被省長駁回。購米合同公布后,翟比南又迭次催請弛禁。外交部認為,如果省議會同意開弛米禁,則可一律照允英領要求,倘若不然,則照舊按約施行。(33)《外交部復財政部》(1919年3月7日),北洋政府外交檔,館藏號:03-18-069-02-014-64。英領所請雖在運米出口,但禁令一旦廢除,外人亦可援引日本先例而販運米谷出洋。數十年來米谷出洋為條約絕對禁止,可知輿情擔憂未必無因。同期,又有廣東向蘇省乞糴,經中央核準20萬石。一時間,江蘇承受著來自外國、中央及他省糧米需求的巨大壓力。省議會出于多方考慮,最終在3月4日徹底否決輸出契約案。喧囂一時的蘇米弛禁案,在形式上以民意的勝利而告終。
四、家賊難防:蘇米朦運出洋之惡果
1919年3月4日,江蘇臨時省議會舉行第一次大會,議事日程中共17案,其中9案關涉米禁。截止2月28日開幕前,各議員通過正式提案、意見書、電報、信函等方式紛紛發表觀點,情況如表1。
由表1可見,議員中反對出洋、請申米禁者十之有九。在致省長的咨文中,議長錢崇固具陳萬難弛禁理由者五。(34)《收江蘇省議會咨》(1919年3月24日),北洋政府外交檔,館藏號:03-18-069-02-020-100~101。除存米供不應求、無詞以拒英領這兩項外,還包括:一,昔時日本“米騷動”劇烈未聞救恤,現時過境遷,卻又需轉運米谷450萬石,且延及三年,于理不合。二,國家理財應利害兼權。弛禁后,一旦糧價上漲誘發騷亂,危害將遠超政府所獲的數百萬利潤。斥責政府目光短淺,舍大益而逐小利。三,根據蘇省農情駁斥“谷賤傷農”的說法,指出弛禁若致米價暴增,則農未受利而民先受害。據此,省議會要求政府堅拒日使,謝絕粵省所請,重申米禁。李純雖有不甘,終不能公開違拗決議,加之民眾排日情緒激烈,只得由施愚向清野領事私下解釋。之后,軍民兩署公布了嚴厲禁運米糧出境的通令。
省議會的第二次米禁決議,是否能夠斷絕英日之念呢?事實證明,在中外官商勾結的情況下,重頒禁令無非是使運米出洋轉為私下進行。3月8日,朱爾典宣稱津浦路所輸出的米谷,大都已用作非軍用銷售,指江蘇政界有任便出售軍用執照的行為。(35)《英公使照會一件》(1919年3月8日),北洋政府外交檔,館藏號:03-18-069-02-015-72。齊耀琳堅決否認,雙方爭執又起,直至1920年7月為止。英方何以如此執著于廢弛米禁?從國際局勢觀之,時逢協約國出兵西伯利亞,干涉蘇俄革命,中國既已加入巴黎糧食同盟,有接濟盟軍之義,而作為產米大省的江蘇卻實施米禁,自然多有妨礙。英國派至遠東的軍隊人數雖少,糧食頗依賴中國。一旦蘇米弛禁,英商和英軍皆有利可圖,加之蘇省違約私運確是授人以柄,無怪乎英方有此舉動。盡管齊耀琳的態度使英國未能達成目的,但其也并非一無所獲。1919年1月底,北京政府曾與英使接觸,表示可暫時撤廢米禁,出口大米與其他糧食以濟英軍,但不是通過條約規定下征收關稅的形式,而是采取所謂的執照費制度。朱爾典以該費用實

表1 蘇省議員意見統計表
際上是“由總稅務司以外的部門所收取的異常高額的出口稅”(36)“Note from J.N.Jordan to Wai Chiao Pu”,January 29th ,1919,Chinese tax regulations,British National Archives,FO671/449/569.,認為中國政府有意利用參戰來擺脫條約,故而表示反對。北京政府被迫讓步,退回了從英方征收的執照費用。(37)Note from Wai Chiao Pu to His Majesty’s Minister,February 20th ,1919,FO671/449/570.此案所涉數額在日領致齊耀琳的函中曾被提及:“為救濟英國糧食缺乏起見,貴省有面粉50萬袋輸運該國,最近已邀特準免稅。”(38)《蘇米弛禁問題》,《申報》1919年1月26日,第7版。
盡管齊耀琳對英交涉可謂義正辭嚴,但軍米護照成為走私的保護傘,早已是各級官廳心照不宣的事實。重申禁令僅半月,官廳便查獲運日米谷6萬石。大有公司經津浦鐵路轉運米谷至青島、大連等地,更達數十萬至百萬石之巨,且半數均持陸軍部護照。針對偷漏行為,省署特在浦口設立查驗處,對軍米及本省流通的蘇米嚴密稽查。隨后齊耀琳、李純又請中央飭令路捐各局相互配合,杜絕朦運之弊。出于對權奸米蠹的憤恨,江蘇省議員亦紛紛致電府院,要求嚴懲大有公司組織者、中央代表王克敏和吳鼎昌等人,并質疑其軍米護照的來源。對此,陸軍部聲稱發放購米護照極為慎重,敷衍答以“王克敏等勾結運米,當無赴部冒領護照情事”。(39)《陸軍部咨呈》(1919年4月2日),北洋政府國務院檔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館藏號:1002-775-77。軍米護照的頒發與使用向來有嚴格的規定,現輕易被挪為他用,發照機關卻作如此解釋,實難令人信服。然而違約販米還遠不限于此。
先前齋藤令三井洋行采購20萬石蘇米,已在3月8日完成。因以中國人的名義秘密進行(40)《查復私販米糧之令知》,《申報》1919年7月25日,第10版。(后報載系滬南萬豐米行行主楊和清所為),一時未被人發覺。如何將此項米谷輸運日本,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在與徐樹錚磋商的同時,日方從上海岑春煊之子處以每石2弗的價格購買2萬石份額的運米護照。(41)《在北京斎藤陸軍中將ヨリ福田參謀次長宛》(1919年3月10日),《日本外交文書》(1919年),第2冊上卷,第589—590頁。但該照只能用作由上海至天津的省外移出證明,具體出洋仍需財政部、參戰督辦處等中央部門協辦。由于軍用米和普通軍需品在購運程序上有所不同:軍需品經參戰督辦處發給護照后,稅務司和稅關便允許其輸出入,而軍用米運輸卻須先報部核給護照,按照所載數目報關完稅(42)《飭遵限制軍米之辦法》,《申報》1914年10月30日,第10版。,故日本販米僅憑參戰督辦署下達的護照發給通知尚且不夠,還須陸軍部出面通告海關監督。是時,徐樹錚正在丁憂不能出面,陸軍總長靳云鵬因恐擔責而暫未應承。遲至4月17日,經日本多方活動,靳云鵬和稅務總署辦孫寶琦方有允諾,惟陸軍部究竟是重新發放護照,還是單發通告、依舊使用督辦處的護照,尚待研究,“兩三日內,離解決終不遠矣。”(43)《東在中國日本公使館附陸軍武官ヨリ福田參謀次長宛》(1919年4月18日),《日本外交文書》(1919年),第2冊上卷,第593頁。
經過北京軍官們的周旋,三井所購米谷還是從徐樹錚一派處購置了相當數量的護照,但因李純的反對,運送出現困難(44)《昨年ニ於ケル支那米運送ノ経過》,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檔號:B-3-5-2-98_1之06-404。,后由負責輸運的日商高田商會與王郅隆簽訂委托契約,規定相關費用,這批米谷遂經王郅隆之手,從天津運送大連,繼而輸往日本。王郅隆乃皖系重要人物,時任安福國會參議院議員,有“安福財神”“安福財閥”之稱,其如此行徑足可印證坊間對他借段祺瑞政府參戰處開辦榮慶米行,“陽託采辦軍米,陰濟東洋”的流言并非空穴來風。(45)《安福中之王郅隆》,鴻隱生:《安福秘史》,宏文圖書館1920年版,第99頁。由是在皖系政府與日本的里應外合之下,“米禁雖嚴,而安福部所販之米,仍得暢行無阻焉。”(46)瀨江濁物輯:《直皖戰爭始末記》,《近代史資料》1962年第2期,第22頁。
軍米朦運的猖獗,逐漸引發各方的不滿和強烈抗議,陸軍部不得不修正購運軍米條款,將限制辦法從3條增訂為6條,詳細規定了應需米數、采購地點、護照填發要點、驗放過程、押運人員等內容。(47)《陸軍部修正購運軍米條款及擬定限制辦法并有關文書》(1919年5月14日),北洋總統府軍事處檔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館藏號:1003-615-5—7。即便如此,走私依然不絕。北京政府又電令蘇省把軍米和漕米合糴160萬石。此時蘇省存米無多,又逢雨水成災,米價騰貴,人心惶惶。盡管該電令因地方反對而作罷,然江蘇所攤20萬石漕米的定額卻未取消,十數萬石軍米亦被采購出省。8月上旬,鑒于米價連日飛漲,省署將漕米和軍米一概禁運,只驗放已發護照的軍米。徐樹錚又以西北邊籌使名義,陸續從蘇輸出數萬石軍米,齊耀琳迭次勸止,始終無效。直至秋谷登場,米價猶有漲無跌,最終在1920年釀成嚴重米荒。
于江蘇運弛米禁受挫后,日本通過勾結北京政府及各路軍閥,又輾轉在安徽、江西、湖南、東三省等地購得大量米谷,經上海直航大連,然后移送日本。為此,1919年11月,日方陸軍代表特意拜訪財政次長李思浩,感謝其在輸出中國米方面所表現的厚意。李思浩甚至表示未來將盡可能地尋求解除米禁的方法,并為日本爭取份額巨大的護照(48)《東在中國日本公使館附陸軍武官ヨリ上原參謀総長宛》(1919年11月22日),《日本外交文書》(1919年),第2冊上卷,第605頁。,由是該年出口至日本的中國米突增1,000,000余擔。(49)巫寶三:《中國糧食對外貿易——其地位趨勢及變遷之原因(1912—1931)》,參謀本部國防設計委員會1934年版,第22頁。各地民眾強烈抗議的同時,和地方當局的矛盾也日漸激化。江西數千學生為反對弛禁而掀起罷課風潮。湘人則以督軍張敬堯擅開米禁、勒加米捐為契機,發起如火如荼的“驅張運動”。江蘇雖為產米大省,然迭遭官商私運,僅無錫一地,1918年已有上海鈴木洋行、三井洋行購米15.8萬石(1185萬公斤)運日,從1919年7 月14日至9月6日,輸出日、英等地的大米又達37.4萬余石(5160萬公斤)。(50)談汗人主編:《無錫縣志》卷12,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521頁。巨額輸出致使江蘇存米稀少,米源不足,加之省內各縣互不流通,鄰省又逢秋收荒歉。1920年5月,滬上米價每石已近10元,荒象已顯。省署在辦理平糴之余,從嚴取締米糧私運,并向贛湘等省求援,然各省食米皆已被徐樹錚借軍米為名采購運日。(51)《西報紀中國米荒之原因》,《申報》1920年6月13日,第10版。如此,江蘇欲求接濟卻不能得,6月米價增至16元左右,存米堪敷數日之用,竊米案及搶米風潮時有發生。上海各路總聯合會致函工部局,一方面請其即日起禁止食米出口、嚴查偷漏出洋,另一方面設法運米入境,以資接濟。(52)《上海各路商界總聯合會致工部局函》(1920年6月15日),上海檔案館藏,檔案號:U1-3-727-23。值此社會動蕩之際,蘇省政局又現亂象:省長齊耀琳被指私運蘇米、供給安福黨費,遭到省議會彈劾。觀蘇米弛禁案前后脈絡,省長盡管有緝私不力之嫌,勾結安福黨一說卻并無根據,齊耀琳亦有自辯,只因與省議會的沖突日益激烈,終究被迫辭職。就彈劾案提出的時間而言,無論省議會出發點為何,米糧問題應是促使兩方矛盾爆發的導火索之一。
江蘇重申米禁后,以徐樹錚為代表的安福黨人販米猖獗,致蘇滬等地遭逢大難。那么其向日本偷運數量究竟有多少呢?隨著皖系的失敗,徐樹錚、曾毓雋、王郅隆等安福政客被通緝。1920年8月7日,《北華捷報》轉引上海《新聞報》的一則專電,稱徐樹錚販米凈利潤高達325萬美元,相關文件已從王郅隆的家宅中搜獲。根據他與日本軍官間的數份合同來看,僅從江蘇與安徽輸送至日本的米糧總數就有130萬石,“出口的每石需交付1美元照費與1.5美元的特許費。”(53)“Views From The Chinese Pess: Sale of Rice to Japan-Little Hsu’s Millions”,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August.7,1920;p348.徐樹錚所從事之非法交易,有證據者尚有如此,漁利之巨可以想見。無怪乎字林報有評論云:“唯一負責者則北京政府也,茍不早圖悔將無及,屆時雖欲歸罪于日本之購米,然不為世人所恕。何則?賣米者中國,故負責者中國而非日本也。”(54)《西報紀中國米荒之原因》,《申報》1920年6月13日,第10版。
余 論
糧食乃民生之本。時至近代,糧食安全受到來自國內外的嚴重威脅,米禁之所以被一再重申,個中緣由可從本案窺得一斑。溯及晚清,條約早已規定禁米出洋,卻依然有私販米谷的情況,特別是甲午戰爭期間奸人賣米濟日,震動清廷,出口與出洋之米遂被一概禁運。不過,這一階段的米禁并非常年實施,隨時可根據米價調整,以便疏通。是時,中央權威尤存,政令上傳下達,地方間互相配合,緝私行動較有成效,奸商尚有忌憚。但到了北洋時期,從外部來看,糧食長期受列強覬覦,英法美日俄等國商人均有干預米麥出口之舉。內政方面,中央統治力下降,地方軍閥割據,吏治腐敗,為奸商違禁走私提供了溫床。軍米朦運在歐戰初期即已成風,不獨皖系,各路軍閥皆有為之,即便是本案核心籌劃者徐樹錚,亦指“販米而托名軍米者”為鐵路運輸的一大弊病。(55)徐樹錚:《建國詮真》,1923年版,第67頁。所以,江蘇等地惟有頒布米禁,運用行政手段穩定糧食市場,借助條約保護糧食安全。本案中,津浦路走私貫穿始終,政府要人大肆出賣民食。條約與米禁俱存尚能如此,遑論弛禁之后果,也就不難理解米禁盛行于近代的原因。
本案同時暴露出近代中國內外政治的復雜性和聯動性。因有英國和日本的介入,江蘇米禁的存廢不僅影響糧食安全和恤鄰之義,還牽涉外交、財政等諸多層面。對此,相關各方態度不一:中央為緩解財政危機、履行糧食同盟的道義起見,贊成弛禁。地方當局固應配合中央決策,更須考慮民生,不得不尊重省議會及主流輿論的意見,審慎抉擇。社會方面,農工商等階層為己謀利而各執一詞,士紳名流則主張兼顧外交和民食。隨著中日外交局勢急轉,民族主義勃興,申禁又成為了反制日本的外交工具。期間北京政府與江蘇省署的博弈,不僅是中央和地方的財政之爭,也折射出皖系和直系間的暗流涌動。而相較同期皖系之倪嗣沖、張敬堯等督軍的肆意妄為,直系李純對民政的有限干預也反映了地方政治中的軍政制衡,一定程度上說明了蘇滬地區士紳力量的強大。
毋庸諱言,在保護糧食安全的同時,江蘇對米谷貿易的常年封禁確實存在著很多問題,較之清末更加僵化與保守,有因噎廢食之嫌。自1919年起米禁被再度強化,其結果只能是市面衰頹,金融枯涸,加劇奸商囤貨居奇、走私偷漏的情況,造成惡性循環。而省內各區域間的流通不暢,也是米價居高不下的誘因之一。該政策不獨傷及本省,亦遏制了荒政作用的發揮,有礙恤災救鄰,加深了各省區之間的嫌隙。
由是觀之,米禁實為一把雙刃劍。不過,在外敵環伺,內部政治腐敗、經濟失序、社會混亂的北洋時期,這一政策是地方政府維護糧食安全所采取的必要舉措,在保證亂世中的米谷供應、恢復秩序、安定民心等方面產生了重要的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