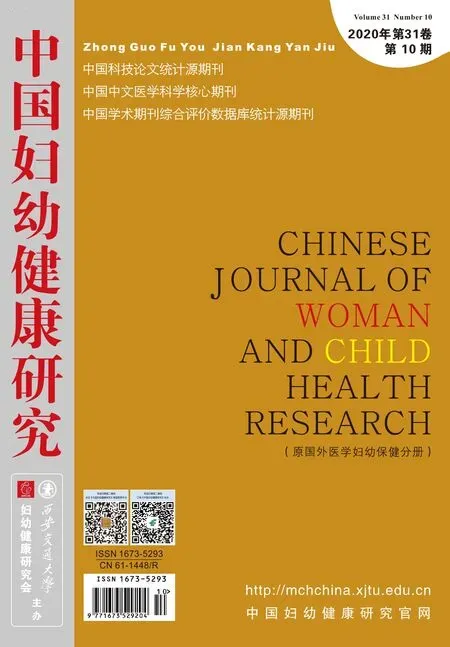兒童1型糖尿病血管并發癥血清學預測指標的研究
韓 敬,陶月紅
(1.大連醫科大學,遼寧 大連 116044;2.揚州大學臨床醫學院 江蘇省蘇北人民醫院,江蘇 揚州 225001)
全球1型糖尿病(type 1 diabetes mellitus,T1DM)的患病率正逐漸升高,且呈低齡化趨勢[1-2]。T1DM患者帶糖生活時間長、急慢性并發癥發生風險高,給患者、家庭及社會帶來了沉重的負擔。隨著胰島素的臨床應用,急性并發癥的病死率明顯降低,但慢性并發癥如糖尿病微血管病變、大血管病變、神經病變等,成為威脅患者生命的主要原因。在對糖尿病并發癥發生發展機制的不斷探索和研究的過程中,發現晚期糖基化終產物(advanced glycation end products,AGEs)、誘導型一氧化氮合酶(inducible nitric oxide synthase,iNOS)可能是重要影響因素[3-4]。關于AGEs和iNOS及血糖控制情況、糖尿病并發癥的相關研究,多見于動物實驗及2型糖尿病患者中,而在T1DM患者,尤其是在兒童T1DM的研究中較為少見。
眾所周知,糖化血紅蛋白(glycohemoglobin A1c,HbA1c)是臨床評價長期血糖控制的“黃金標準”。但血糖波動程度也是評估血糖控制不可或缺的部分。由自我血糖監測計算得到的血糖標準差(standard deviation of blood glucose,SDBG)可用來評估血糖波動情況[5]。目前公認,尿白蛋白肌酐比(urinary albumin/creatinine ratio,UACR)是糖尿病患者早期腎臟病變的篩查指標[6],血流介導的血管擴張功能(flow-mediated dilatation,FMD)是評價血管內皮功能的指標[7]。本文旨在研究血清AGEs水平和iNOS活性與血糖控制情況、病程,以及UACR、FMD的關系,探討AGEs和iNOS作為T1DM患兒早期微血管及大血管并發癥預測指標的可行性。
1研究對象與方法
1.1研究對象
選取2018年1月至2019年12月在江蘇省蘇北人民醫院兒科就診的T1DM患兒,參照納入及排除標準篩查后,T1DM組的研究對象共有33例,其男童10例,女童23例;年齡為4~16歲;病程為0.1~84.0個月。選擇健康對照組15例,其中男童5例,女童10例。所有研究對象的監護人均知情同意。
納入標準符合2018年國際兒童青少年糖尿病協會提出的T1DM的診斷標準[8]。①實驗室檢測指標:血漿血糖≥200mg/dL(11.1mmol/L),或空腹全血血糖(FPG)≥126mg/dL(7.0mmol/L);或口服糖耐量試驗葡萄糖負荷后2h靜脈血葡萄糖≥200mg/dL(11.1mmol/L);或HbA1c≥6.5%;或糖尿病相關自身抗體的酪氨酸磷酸酶樣胰島素瘤抗原2、谷氨酸脫羧酶抗體、胰島素自身抗體、β細胞特異性鋅轉運蛋白8自身抗體中一項為陽性。②臨床表現:起病年齡小,20歲以前起病;起病急,有糖尿病典型“三多一少”癥狀(煩渴多飲、多尿、多食、不明原因的體重下降),部分直接表現為脫水、循環衰竭或昏迷等酮癥酸中毒的癥狀;治療上依賴胰島素治療。
排除標準:①2型糖尿病,其他類型糖尿病,如新生兒糖尿病、年輕的成年發病型糖尿病(maturity onset diabetes of the young,MODY)、胰腺外分泌疾病等;②甲狀腺功能亢進,腎上腺皮質功能減退等其他內分泌疾病;③酮癥酸中毒;④先天性心血管疾病。
1.2研究方法
收集研究對象的一般資料:年齡(歲)、身高(cm)、體重(kg)、糖尿病病程(月);血糖資料:自我指尖血糖檢測值(mmol/L)、HbA1c(%);血管功能指標:UACR(mg/g)、FMD(%)。
收集研究對象的早晨空腹血清樣本,于-80℃冷凍儲存。采用酶聯免疫法測定血清AGEs水平及iNOS活性,按試劑盒說明書進行操作,試劑盒均購自上海信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血糖波動程度通過SDBG體現:由研究對象提供的自我指尖血糖監測值計算得到其標準差[5]。
身體質量指數(BMI)=體重(kg)/[身高(m)]2。
1.3統計學方法
2結果
2.1 T1DM組與健康對照組各指標的比較
對T1DM組與健康對照組的各指標進行比較,符合正態分布資料的比較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非正態分布資料的比較應用非參數檢驗。T1DM組與健康對照組的年齡、BMI、FMD間均無顯著性差異(均P>0.05),T1DM組的HbA1c、AGEs、iNOS、UACR均高于健康對照組,兩組間均存在顯著性差異(均P<0.05),見表1。因受倫理學限制,健康對照組未進行每日多次的血糖監測,故缺乏SDBG數值。

表1 T1DM組與健康對照組各指標的比較結果
2.2 T1DM血清預測指標與其他指標的關系
對T1DM患兒血清預測指標與其他指標進行相關性分析。AGEs與HbA1c、SDBG、UACR均呈正相關(均P<0.05),與FMD呈負相關(P<0.05);iNOS與HbA1c、SDBG、UACR均呈正相關(均P<0.05),與FMD呈負相關(P<0.05);AGEs和iNOS與病程、年齡、BMI均無相關性(均P>0.05),見表2。

表2 T1DM血清預測指標與其他指標的相關性結果
3討論
3.1血清AGEs水平與血糖控制指標及病程關系的分析
本研究結果顯示T1DM患兒血清AGEs水平高于健康兒童,且與HbA1c、SDBG均呈正相關,但與病程無相關性,即T1DM患兒血糖控制越差,血清AGEs水平越高。分析其機制:AGEs是還原糖與蛋白質、脂蛋白、核酸發生非酶促共價結合,然后再進行一系列折疊、重排形成的不可逆化合物[9]。糖尿病患者高血清葡萄糖為AGEs的產生提供了原料;而長期高血糖和血糖波動觸發機體的氧化應激加速了AGEs的形成,同時機體產生過多的AGEs又反過來加強氧化應激,由此形成一個惡性循環[10-11]。Jaisson等[12]的研究顯示,T1DM患者血清AGEs水平與HbA1c呈正相關,與病程無相關性。這與本研究結果一致。本研究表明,在平均病程不足2年的情況下,T1DM患兒血清AGEs水平仍與血糖控制指標存在正相關,更加說明了早期強化血糖控制及保持血糖相對穩定的重要性。
3.2 AGEs作為T1DM早期微血管及大血管并發癥預測指標的可行性
本研究結果顯示,T1DM患兒血清AGEs水平與FMD呈負相關,而與UACR呈正相關,即T1DM患兒血清AGEs水平越高,內皮功能和腎功能越差。這驗證了AGEs在T1DM早期大血管和微血管病變中的損傷作用。分析其機制:AGEs通過抑制內皮iNOS的表達來減少內皮細胞源性一氧化氮(NO)的產生,導致內皮功能受損[13];而且AGEs與AGEs受體結合誘導氧化應激炎癥反應,導致血管內皮功能受損[14]。有研究表明,糖尿病患者內皮功能障礙與血清AGEs水平有關,存在嚴重內皮功能障礙時,血清AGEs水平更高[15]。這都表明AGEs在糖尿病大血管疾病發生發展中起重要作用。血清AGEs水平可作為T1DM患兒早期大血管并發癥的預測指標。
腎臟中AGEs的沉積和AGEs-AGEs受體軸的激活導致腎小球基底膜增厚、系膜擴張、腎小球系膜細胞和腎小管細胞損傷、腎小球硬化[3,16],這些都是糖尿病腎病的病理學改變,臨床上將會表現為尿蛋白排泄增加和腎功能進行性惡化。有研究表明,足細胞損傷是蛋白尿形成的重要組成部分,而AGEs參與糖尿病患者足細胞的損傷[17]。可見血清AGEs水平相較于UACR可能反應更早的糖尿病腎臟損害。血清AGEs水平可以作為T1DM患兒早期微血管并發癥的預測指標。
3.3血清iNOS活性與血糖控制指標及病程關系的分析
本研究結果顯示,T1DM患兒血清iNOS活性明顯高于健康兒童,并且與血糖控制指標呈正相關,血糖控制越差,iNOS活性越高。高血糖導致iNOS活性表達增加的機制為:iNOS幾乎只在炎癥、氧化應激等病理條件下才表達、激活。糖尿病患者長期處于高血糖病理狀態,刺激單核細胞激活多種炎癥細胞釋放炎癥因子[18],且不正常的短期血糖波動可活化核因子(nuclear factor-kappa b,NF-kB)等核因子,調節炎癥基因的表達,加重機體氧化應激炎癥反應[19],這些都會導致糖尿病患者體內iNOS活性表達增加。本研究中未發現血清iNOS活性與病程的關系。這可能與本研究中病例數偏少、病程短有關。
3.4 iNOS作為T1DM早期微血管及大血管并發癥預測指標的可行性
本研究結果顯示,T1DM患兒血清iNOS活性與UACR呈正相關,iNOS活性越高,UACR越高,這驗證了iNOS對糖尿病患者早期腎功能的損害作用。分析其機制:高血糖使機體iNOS活性表達增加,然后催化產生大劑量NO參與糖尿病腎病的發生和進展[20]。Hofni等[21]的動物實驗表明,由鏈脲佐菌素誘導的糖尿病大鼠模型,其UACR水平、iNOS活性表達較健康對照組顯著增加,經過螺內酯與坎地沙坦聯合治療后,iNOS活性表達顯著降低,從而改善了UACR。這支持本研究結果。FMD是評價大血管功能較可靠的檢測指標,但目前尚未見可靠的iNOS與FMD臨床關系的研究。Li等[4]的研究發現,通過抑制NF-kB途徑減少iNOS的表達激活可減輕糖尿病大血管病變。本研究結果顯示,T1DM患兒血清iNOS活性與FMD呈負相關,即血清iNOS活性越高,FMD越低,血清iNOS活性可能成為預測T1DM早期大血管病變的預測指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