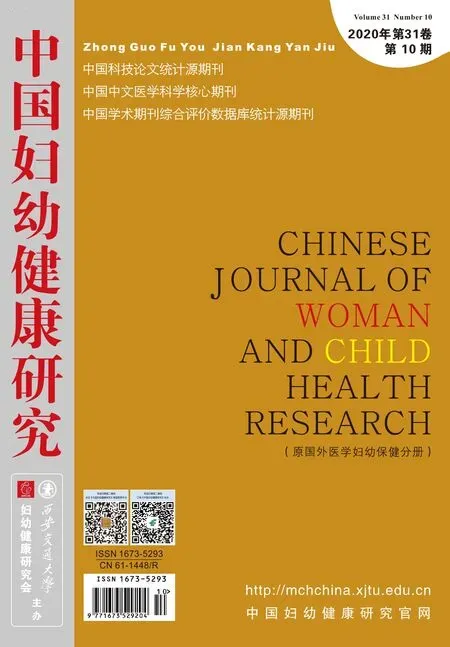妊娠期糖尿病合并子癇前期患者臨床特點分析
劉素新,羅夢夢,胡小月,霍 琰
(1.河北省人民醫院產科,河北 石家莊 050051;2.金華市中心醫院產科,浙江 金華 321000)
據世界衛生組織(WHO)最新研究發現妊娠期肥胖發生率高達25.3%[1],其可導致妊娠期糖尿病(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GDM)、妊娠期高血壓、子癇前期(preeclampsia,PE)、早產、巨大兒、產后出血等不良妊娠結局[2]。GDM及PE均是妊娠期常見并發癥,可增加孕婦及新生兒遠期代謝綜合征風險[3-4]。孕前肥胖、妊娠期超重均可增加GDM、PE等不良妊娠結局的發生[5],但GDM患者中僅部分同時并發PE。本研究通過回顧性分析GDM合并PE婦女的臨床特點、妊娠結局及其與孕前體質量的關系,探討GDM合并PE的高危因素,以便早期識別,改善母兒結局。
1資料與方法
1.1資料來源
收集2016年9月至2018年10月在河北省人民醫院定期進行產前檢查并分娩的單胎妊娠孕婦共3 264例,其中單純GDM患者480例,同時合并PE者70例。所有孕婦既往無肝腎功能不全、胃腸道疾病、肺部疾病、感染性疾病或甲狀腺疾病、糖尿病等內分泌及代謝性疾病史,均未服用影響血脂、血糖代謝的藥物,自愿加入調查并簽署知情同意書。
1.2方法
采取回顧性研究,記錄孕婦的年齡、孕前身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BMI)、分娩次數及方式、孕期是否患有并發癥或合并癥(如羊水過多、羊水過少、胎膜早破、產后出血、甲狀腺疾病等);記錄新生兒出生體質量、新生兒并發癥(如新生兒呼吸窘迫綜合征、新生兒高膽紅素血癥、新生兒咽下綜合征等)。
GDM和PE疾病均參照《婦產科學》[6]進行診斷,孕前BMI分類參照中國成人分類標準[7]。本研究將甘油三酯(TG)、總膽固醇(TC)、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LDL-C)、極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VLDL-C)水平高于同孕期健康孕婦第95百分位數(P95)及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HDL-C)水平低于同孕期健康孕婦第5百分位數(P5)定義為妊娠期脂代謝異常(dyslipidemia,DLP)[8]。本組臨床資料TG>4.73mmol/L,TC>7.91mmol/L,HDL-C<1.33mmol/L,LDL-C>4.74mmol/L,VLDL-C>1.08mmol/L,超過各值即診斷為DLP。
1.3統計學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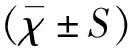
2結果
2.1兩組臨床資料和生化指標的比較
GDM+PE組的孕前BMI、孕早期FPG、TG和VLDL-C水平均高于GDM組,而OGTT 2h血糖、HDL-C值則均低于GDM組,且GDM+PE組初產婦比率高于GDM組,兩組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均P<0.05);經Spearman相關性分析結果表明,孕早期FPG水平與OGTT 0h(r=0.310)、OGTT 2h(r=0.277)血糖值呈正相關(均P<0.05),而與OGTT 1h無相關性(r=0.130,P>0.05),見表1、表2。

表1 兩組臨床資料的比較結果

表2 兩組生化指標的比較結果
2.2 GDM+PE相關因素的分析
2.2.1單因素分析情況
以是否發生GDM+PE疾病為因變量,以孕前BMI、孕早期FPG、TG、HDL-C、VLDL-C水平及產次為自變量,行單因素分析,結果顯示孕前BMI≥24kg/m2及初產婦與GDM+PE疾病發生有關,見表3。

表3 影響GDM+PE疾病的單因素分析結果
2.2.2多因素分析情況
進一步行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Logistic回歸模型PGDM+PE=1/{1+exp[-(-3.177+1.496×孕前BMI≥24kg/m2+0.629×初產婦)]};結果顯示孕前BMI≥24kg/m2發生GDM+PE疾病的風險是BMI<24kg/m2的4.463倍;初產婦發生GDM+PE疾病的風險是經產婦的1.876倍,可見孕前BMI≥24kg/m2及初產婦是發生GDM+PE疾病的高危因素,見表4。

表4 GDM+PE疾病危險因素的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
2.3兩組妊娠結局的比較
GDM+PE組發生羊水過多、早產兒、轉NICU、低出生體質量兒及產后出血的發生率均明顯高于GDM組,兩組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均P<0.05),見表5。

表5 兩組妊娠結局的比較結果[n(%)]
3討論
3.1孕前超重與肥胖是GDM并發PE的高危因素
GDM和PE是導致妊娠期母嬰不良結局的主要原因,GDM合并PE的發生率較低[9],尚無充足證據明確兩者間的具體機制。Vieira等[10]發現GDM和PE發病機制不同,且早孕期的胰島素抵抗和炎癥與PE發病無關[11]。陳鵬等[12]研究顯示,孕前超重和肥胖的孕婦使妊娠期高血壓疾病的風險明顯增加,而GDM并非是PE的相關危險因素,其他相關因素在影響PE疾病的同時也對GDM產生了一定的影響。近來有研究發現兩者發病機制相似,GDM是PE發病的獨立危險因素,而孕前BMI的增加是兩者發病最重要的預測指標[9]。GDM可繼發血流動力學改變致動脈硬化和血壓升高[13-14]。GDM患者良好的血糖控制可顯著降低遠期心血管疾病的風險[15]。
本研究將GDM組與GDM+PE組孕婦進行比較發現,GDM+PE的孕前BMI、孕早期FPG、TG、VLDL-C水平及初孕婦比率均高于GDM組,而HDL-C則低于GDM組(均P<0.05)。經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發現,僅孕前BMI≥24kg/m2及初產婦是GDM+PE的危險因素(均P<0.05),表明超重及肥胖是GDM合并PE的高危因素,這與以往研究結果[5,9,16]一致。分析原因可能是由于肥胖可致脂質水平異常,氧化血脂可直接或間接損傷內皮;另外,肥胖可誘發炎癥因子的過度表達[17],多種炎性細胞因子分泌水平異常,如白介素-6(IL-6)、腫瘤壞死因子-α(TNF-α)及c-反應蛋白(CRP)等進一步介導了炎癥和胰島素抵抗,從而影響妊娠期代謝過程,造成GDM和PE等不良妊娠結局[18-20]。Montoro等[21]研究顯示,GDM發生PE組的初產婦率高于GDM組未發生PE組,GDM是PE發生的高危因素。胰島素抵抗和細胞缺損是GDM的特征,很難排除其在妊娠期高血壓疾病發病中的作用。GDM與妊娠期高血壓疾病之間還可通過交感神經、CRP、TNF-α及內皮細胞之間相互作用,因此影響GDM發生的相關因素有可能直接或間接進一步促使并發妊娠期高血壓疾病的發生[18]。同時,初產婦更容易精神緊張、焦慮,促進了病情的進展。本研究發現,GDM合并PE組中初產婦比率明顯增高,初產婦也是GDM合并PE疾病的高危因素,與Montoro等[21]研究結果相似。
本研究中影響GDM發生的年齡、孕早期FPG、TG水平等均不是GDM合并PE疾病的危險因素,分析原因可能為:①與本研究中患有GDM合并PE疾病的孕婦孕期規范產前檢查、孕期干預(調整飲食,控制血糖及血脂、血壓等)、及時住院治療有關;②兩組樣本量均較少,尤其是GDM合并PE疾病的患者病例數僅70例,故還需增加樣本量進一步研究。
3.2 GDM合并PE增加不良妊娠結局的發生
與GDM組相比,GDM合并PE組的產后出血、羊水過多、早產兒、低出生體質量兒及轉NICU發生率均明顯增高(均P<0.05)。有研究顯示,孕前超重及肥胖是產后出血的危險因素,考慮可能與肥胖孕婦脂肪堆積,腹肌、肛提肌乏力,出現原發性子宮收縮乏力、導致第二產程產力延長等產力因素有關[22-23]。肥胖可通過多條途徑參與子宮收縮力的調節[24-25]。一項納入了24 634名妊娠婦女的研究表明,肥胖與巨大兒、多胎妊娠等因素共同增加了產后出血發生率,結果證實肥胖并非產后出血的重要危險因素[26]。Butwick等[27]發現GDM、PE等可直接導致產后出血的發生,與GDM和PE發病有關的脂肪細胞因子,如瘦素、內脂素、生長素等細胞因子參與了子宮收縮的調節[28]。因此考慮GDM合并PE疾病發生產后出血的可能與兩者發病的病理機制有關。有研究發現初產婦可能因子宮自身張力高、精神心理等因素易增加PE、GDM的發生,也增加胎膜早破和胎兒窘迫的發生,可能直接或間接地增加了早產、低出生體質量兒、轉NICU的風險[29]。有研究顯示,GDM、PE是導致早產的主要原因,因GDM孕婦易發生羊水過多,增加了胎膜早破、自發性早產的發生,若同時并發PE疾病,可影響胎盤血管結構及功能變化導致胎兒低體質量,胎兒長期缺血缺氧可致胎兒窘迫,往往需提早結束妊娠,使早產兒、低出生體質量兒及轉NICU的風險均有所增加[30-31]。
總之,本研究表明GDM合并PE妊娠婦女孕前BMI、孕早期FPG、TG、VLDL-C水平及初孕婦比率均高于GDM婦女,孕前BMI≥24kg/m2、初產婦是GDM合并PE疾病發生的高危因素。GDM合并PE疾病的患者羊水過多、早產兒、低出生體質量兒、轉NICU及產后出血等母兒并發癥明顯增多。因此,應做好孕前宣教,超重及肥胖婦女應控制體質量后再妊娠,孕期通過宣教、飲食調節及適量運動等方法控制體質量增長,減少GDM、PE疾病的發生,改善母兒預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