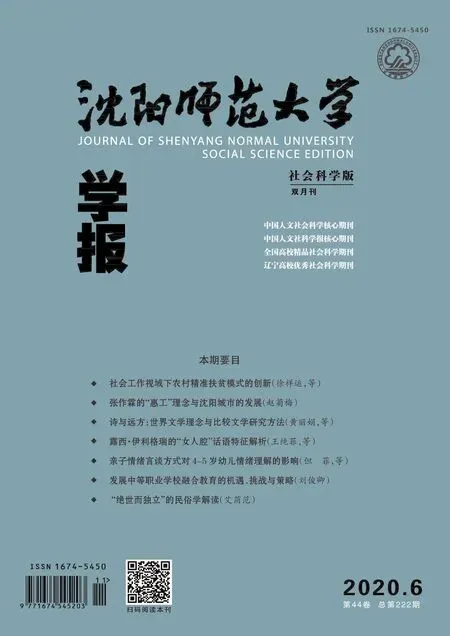遼寧革命遺址資源的基本特征及其文化解讀
何 軍,劉麗華
(沈陽師范大學 旅游管理學院,遼寧 沈陽110034)
一、問題提出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是“熔鑄于黨領導人民在革命、建設、改革中創造的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植根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1]。紅色文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在長期的革命和建設中形成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精神文化,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2010 年,中央印發了《關于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史工作的意見》,明確要求加強黨史遺址保護,組織開展黨史遺址考查,調查黨史方面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等工作。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高度重視紅色文化的重要作用,他多次強調要把紅色資源利用好、把紅色傳統發揚好、把紅色基因傳承好[2]。為此,2018 年7 月,中共中央印發了《關于實施革命文物保護利用工程(2018—2022 年)的意見》,以加強新時代革命文物工作,充分發揮革命文物在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中的重要作用[3]。在此背景下,各地區對本地區的紅色文化進行提煉,形成了一系列的紅色文化財富,如“紅船精神”“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沂蒙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
革命遺址是紅色文化的重要物質載體,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艱苦斗爭的見證,是社會公眾了解紅色歷史的重要場所和途徑。革命遺址不僅是寶貴的革命歷史文化遺產,還是中華民族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是人類文明史上獨特的文化遺存[4]。
通過對中國知網以“革命遺址”和“紅色文化”為檢索詞的檢索結果進行可視化分析,可以發現(如圖1 所示),首先,從文獻數量發展趨勢看,二者的趨勢基本一致,呈上升趨勢,這反映了國內關于紅色文化的研究逐漸成為熱點;其次,與紅色文化研究中的熱潮相比,以革命遺址為研究對象的研究在紅色文化的研究中所占比重小;最后,目前絕大多數的研究集中于革命遺址“保護和利用”及其政治功能的實現,其他方面的研究相對較少。從整體看,當前對于革命遺址領域的研究需要加強和擴展。
對遼寧革命遺址研究的文獻則更為稀少。從2008 年到2019 年,關于革命遺址研究的文獻為316 篇,而從2008 年至2019 年以遼寧革命遺址為一般性研究對象的文獻卻僅為3 篇,此外還有一些是對于特定遺址的研究,如關于沈陽“九一八歷史博物館”,不但數量較少,且基本不是從紅色文化角度進行研究。
根據我國2011 年關于革命遺址的普查數據,遼寧共有各類型革命遺址782 處,時間范圍從中國共產黨建立初期一直到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這些革命遺址記錄了中國共產黨領導遼寧人民進行艱苦奮斗的光輝歷史。深入挖掘遼寧革命遺址資源的文化內涵有利于豐富紅色文化的內涵,展現遼寧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奮斗歷程,增強遼寧人民的文化自信。
從目前看,對于遼寧革命遺址的研究處于起步階段,現有的文獻基本都集中在對個別革命遺址的保護與利用方面,不僅數量相對較少,且在創新性、合理性方面還待進一步商榷(見圖1)。遼寧的革命遺址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過程中形成的。其除了具有紅色文化資源的一般特征外,還與遼寧地區特殊的歷史和社會經濟環境相關聯,具有反映遼寧地域和歷史發展特點的文化內涵。而關于遼寧革命遺址的整體性分析,特別在文化和歷史方面的分析則基本處于空白狀態。這種情況不利于準確認識遼寧在我國革命歷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不利于對遼寧革命遺址的保護和充分利用。

圖1 2008—2019 年以“紅色文化”和“革命遺址”為直接研究對象的文獻發表年度趨勢
二、遼寧革命遺址資源概況
根據2011 年遼寧對于省內革命遺址的普查,目前遼寧共有革命遺址782 處,分布于省內13 個市。其中沈陽、大連、撫順、本溪境內的革命遺址中共有435 處,占總數的56%。遼寧省內的革命遺址共包括5 個類型,分別是重要機構舊址、歷史事件和革命活動紀念地、重要人物故(舊)居、革命烈士墓、革命紀念設施[5]。具體分布及類型信息見表1。

表1 遼寧革命遺址總體情況 單位:處
在這些遺址中,有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6 處,占遼寧革命遺址總數的0.77%;遼寧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 處,占遼寧革命遺址總數的3%(見表2);市縣級文物保護單位87 處,占遼寧革命遺址總數的11%。此外,還有10 處革命遺址被列入其他各類保護名錄中。列入各級文物保護單位及其他類型保護名錄的革命遺址僅占總數的16%。革命遺址保護的覆蓋面偏小,不利于革命遺址的整體保護。

表2 遼寧革命遺址中省級以上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一覽表
目前,遼寧革命遺址列入國家級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的革命遺址共有6 處,而目前全國被列入國家級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的革命遺址或紀念館共有281 處,遼寧僅占全國的2%。總體看,遼寧革命遺址被列入高級別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的數量偏少,其不可避免地會影響革命遺址的利用。
在革命遺址保護工作方面,除了被列入各級保護目錄的遺址以外,還有很多普通革命遺址沒有得到充分的保護,特別在我國城市化及經濟發展進程中,很多遺址,特別是普通地下工作者工作和生活的遺址,由于基本都處于民居中,都被拆除或正面臨被拆除。雖然這些普通革命遺址不需要進行“博物館”式的保護,但應該為其建立完整的檔案,這樣才能夠相對完整地反映我黨在革命時期的活動。
在開發利用方面,遼寧革命遺址存在重實物展示,輕內涵挖掘;重史實傳遞,輕價值提升的情況,整體效果不及預期。
三、遼寧革命遺址資源的基本特征
遼寧地區的革命遺址數量較多,分布廣泛,記錄了中國共產黨領導遼寧人民反壓迫、反侵略的斗爭歷程,反映了遼寧地區復雜的社會歷史背景,具有鮮明的特征(見表3)。
(一)從時間維度看,解放戰爭時期的革命遺址所占比重最大
從總體上看,本研究所涉及的時間分為三個階段,即中國共產黨在遼寧開始革命活動到九一八事變爆發,這一階段包括奉系軍閥統治時期及南北統一后的民國時期,時間跨度從1923 年到1931 年;抗日戰爭時期,時間跨度從1931 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到1945 年日本投降;解放戰爭時期,時間跨度為1945 年日本投降到1949 年建國。總時間跨度為26 年。其中奉系軍閥統治時期及九一八事變前的民國時期的革命遺址數量為50 個,約占總數的6.39%;抗日戰爭時期的革命遺址為178 個,約占總數的22.77%;解放戰爭時期的革命遺址為554個,約占總數的70.84%。可見,解放戰爭時期的革命遺址數量要遠遠多于前兩者。但從具體的區域看,沈陽九一八事變前的革命遺址數量僅僅比解放戰爭時期少13 處,而撫順和本溪抗戰時期的遺址的數量也接近解放戰爭時期的革命遺址,其中撫順在抗日戰爭時期留下的革命遺址數量還要多于解放戰爭時期的革命遺址的數量。

表3 遼寧革命遺址涉及的時間和區域分布表 單位:處
(二)從空間維度看,革命遺址的分布相對不平衡
1.從不同區域分布看,沈陽、大連、撫順、本溪的革命遺址分布較多。沈陽、大連、本溪、撫順共有革命遺址435 處,占遼寧省革命遺址總數的55.6%。丹東和遼陽革命遺址分布的數量也相對較多。
2.從不同時期的革命遺址分布看,九一八事變前的革命遺址和抗戰時期的革命遺址分布集中度高。九一八事變前的革命遺址主要分布在沈陽,其次是大連,二者所占的比重分別為62%和24%。兩個城市合計達到86%;抗戰時期的革命遺址則主要分布于撫順、本溪,二者所占的比重分別為39%和23%,兩個城市合計為62%。丹東、大連和沈陽三個城市合計共有革命遺址46 處,所占的比重為26%。這五個城市抗戰時期革命遺址所占的比重達到88%。
3.從不同類型的革命遺址分布看,機構舊址和名人故(舊)居分布相對集中,紀念設施分布相對均衡。機構舊址中,沈陽有31 處,約占該類遺址總數25%。大連共有40 處,約占總數的32%,二者約占該類遺址總數的57%;名人故(舊)居類,沈陽和大連各有3 處,兩者數量約占總數的46%;歷史事件和革命活動紀念地遺址以撫順和本溪分布最廣,二者共有138處,約占該類遺址總數的46%。其次是沈陽和大連,二者共有78 處,約占該類遺址總數26%;各種紀念設施類遺址則分布相對較為均衡。
(三)從革命遺址內部結構維度看,名人故(舊)居類遺址和重要機構舊址類遺址偏少
遼寧革命遺址可以分為五個類型,分別為重要機構舊址、歷史事件及革命活動紀念地、重要人物故(舊)居、革命烈士墓及革命紀念設施。其中,重要機構舊址共有125 處,約占總數的16%;重要人物故(舊)居共有13 處,約占總數的2%;歷史事件及革命活動紀念地遺址301 處,約占總數的38%;具有紀念性質的革命烈士墓和革命紀念設施343 處,約占總數的44%。從總體看,名人故(舊)居類遺址和重要機構舊址類遺址偏少。
(四)從歷史影響維度看,與遼寧革命遺址相聯系多為普通黨員群眾和一般性歷史事件
在遼寧782 處革命遺址中,與重大歷史事件或重要歷史人物及活動相聯系革命遺址較少,如遼寧重要人物故(舊)居的革命遺址,僅有13 處,而且與之有關的有全國性影響的重要歷史人物僅有劉少奇和徐海東兩位同志。其他人雖然也有一定影響,但從影響范圍和歷史地位看則影響有限;在重要機構舊址和重要歷史事件紀念地的革命遺址方面,與之相聯系的比較有影響力歷史事件主要是滿洲省委的設立及遼沈戰役。與許多省份相比,其無論在數量還是在影響力方面都不是很突出。
總之,遼寧革命遺址在歷史影響維度方面,與有全國性影響的事件和人物相聯系的革命遺址相對較少。當然,遼寧革命遺址是對特定的歷史時期和遼寧特殊的社會文化和地理環境的反映,本身具有特定的文化價值,歷史影響方面相對較弱并不影響遼寧革命遺址的文化價值。
四、遼寧革命遺址資源的文化解讀
遼寧革命遺址資源是我國紅色文化資源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們是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和遼寧特殊的社會文化和地理環境中產生的,其既具有紅色文化的普遍性價值,也具有自身的文化價值。
(一)蘊含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和自身解放的革命精神
1921 年7 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成立。1923年初,唐山的黨組織派人到京奉鐵路遼寧段發展黨的組織。1923 年下半年,溝幫子鐵路黨小組建立,并開辦夜校宣傳革命思想。1924 年上半年,在溝幫子鐵路黨小組的基礎上建立了中共溝幫子鐵路支部。這是遼寧境內第一個地方黨組織[6]。此后,遼寧各地紛紛建立黨支部組織,并領導群眾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進行斗爭。遼寧在北方屬于最早建立黨組織的地區之一。
九一八事變后,中國共產黨逐漸將斗爭轉向爭取民族獨立。九一八事變當晚,當時在沈陽工作的中共滿洲省委常委、宣傳部長趙毅敏起草了《滿洲省委為日本帝國主義武裝占領滿洲宣言》,公開申明了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1931 年12 月,中共奉天特委成立,領導遼寧的抗日斗爭。斗爭是艱苦而殘酷的,奉天特委屢遭破壞,但又頑強重建。僅從1931 年到1935年,奉天特委先后在四個地點輾轉辦公[7]。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事力量也開始同日本侵略者展開艱苦斗爭[8],僅在撫順和本溪便留下了110 處戰斗遺址或遺跡。
遼寧在解放戰爭中留下的革命遺址有554處,僅革命烈士墓和革命紀念設施超過330處。其代表的是遼寧人民對解放事業的巨大付出[9]。
這些遺址蘊含著中國共產黨和遼寧人民為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而艱苦奮斗、不屈不撓、一往無前、敢于犧牲的革命精神[10]。
(二)從微觀還原歷史,映現了人民群眾在歷史進程中的價值
遼寧的革命遺址中,與有全國性影響的事件和人物相聯系的革命遺址數量相對較少。如前所述,遼寧重要人物故(舊)居的革命遺址,僅有13 處,而且與之有關的有全國性影響的重要歷史人物僅有劉少奇和徐海東兩位同志,其他人雖然也有一定影響,但從影響范圍和歷史地位看則影響有限;在重要機構舊址和重要歷史事件紀念地的革命遺址方面,與之相聯系的比較有影響力的歷史事件主要是滿洲省委的設立及遼沈戰役。
從另一個角度看,雖然遼寧的革命遺址大部分都是普通黨員和普通群眾革命活動的記憶,但其更客觀地展現了普通黨員和群眾日常的工作和生活場景,體現了唯物史觀中關于“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的原理,展示了人民群眾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也拉近了社會大眾同紅色文化的距離。
(三)體現了遼寧人民的民族抗爭精神
由于日本從19 世紀末就開始對東北地區進行滲透,其中遼寧地區是最主要的滲透地區。因此,九一八事變后,日本對于遼寧地區的控制力最強[11]。此外,從地理角度看,遼寧同國內大部分地區距離較遠,很難得到國內支援。在這種情況下,開展反侵略斗爭的艱難程度是超乎想象的。東北特別是遼寧地區的抗戰環境在全國范圍看是最艱苦和殘酷的,在這種情況下,堅持斗爭的困難程度可想而知[12]。
遼寧的革命遺址中,抗戰時期的遺址有178 處,其中日本統治力量最強的沈陽和大連分布有13 處和14 處;而自然環境極為惡劣的撫順、本溪、丹東三者合計129 處,且幾乎全部為武裝斗爭遺址。說明即使在這樣艱苦的環境下,遼寧人民也沒有放棄民族解放斗爭,充分體現了遼寧人民的民族抗爭精神。
(四)展現了遼寧人民的逐漸覺醒及覺醒后所迸發出的革命熱情與獻身精神
由于地理環境相對封閉和歷史上主要是少數民族的居住地,遼寧與中國大部分地區的聯系相對較少,在文化方面相對獨立。此外,由于東北地區人口稀少,可耕種土地面積大且土地肥沃、資源豐富,因此社會矛盾沒有當時中國大部分地區的社會矛盾尖銳。在這種特殊的地理、歷史和社會環境中,人民對于革命思想的接受相對緩慢。從革命遺址可以看出這樣一點。遼寧的782 處革命遺址中,奉系軍閥時期及九一八事變前民國時期的革命遺址僅有50 處,而這一時期涵蓋的時間則有八年多,可見在遼寧地區開展革命斗爭的困難程度。當然,這是遼寧人們對特定的歷史時期和特殊的社會文化和地理環境的反映,是正常的。
經過抗日戰爭,中國共產黨的思想逐漸被遼寧人民所認可和接受,遼寧人民逐漸覺醒。覺醒后的遼寧人民立刻迸發出前所未有的革命熱情與獻身精神[13]。在遼寧的782 處革命遺址中,屬于解放戰爭時期留下的就有554 處,占總數的71%。遼寧人民的努力支持對于東北地區的解放發揮了重要作用。當然,遼寧人民也付出了巨大犧牲,在554 處革命遺址中,僅革命烈士墓和革命紀念設施就超過330 處。
五、結語
對革命遺址保護和利用的前提就是要建立對革命遺址基本特征的全面認識,形成對革命遺址的文化內涵、文化類型的科學識別。在此基礎上,對革命遺址價值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進行評估,區分不同地區革命遺址的獨特性,只有這樣才能為革命遺址的保護和利用提供切實可行的路徑[14]。
遼寧地區的革命遺址,反映了遼寧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爭取民族獨立和自身解放的歷程。深入研究遼寧革命遺址資源,對于完善遼寧革命遺址資源的開發利用與保護,激活遼寧革命遺址資源所蘊含的精神力量,弘揚和傳播遼寧紅色文化具有重要意義。本文通過對遼寧革命遺產相關資料的收集和分析得出以下結論:(一)遼寧革命遺址有鮮明的基本特征和文化內涵,這是研究遼寧革命遺址的地方文化價值和普遍價值的前提和基礎;(二)研究遼寧革命遺址的基本特征和文化內涵,要與遼寧地區獨特的地理自然條件和復雜的社會歷史背景相聯系,這是探討遼寧革命遺址保護和利用路徑的關鍵和依據;(三)未來對遼寧地區革命遺址保護利用的研究,既要借鑒國內外文化遺產保護利用的成功經驗,也要根據自身獨特的文化內涵和蘊含的普遍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