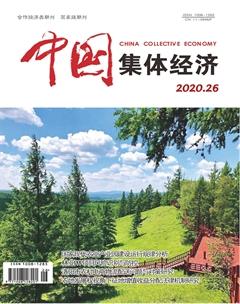農地發展權視角下征地增值收益分配法律機制研究

摘要:隨著城鎮化建設的加快,大量農地轉為非農建設用地,農地價值產生了巨大的增值。現行農地征收補償法律制度逐漸完善,但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不合理問題依然存在,其根本原因在于缺乏農地發展權制度安排。因此,文章以農地發展權為切入點,運用其理論,以湖南省征地補償為例進行研究,完善征地增值收益分配法律機制,保護相關利益主體的合法權益。
關鍵詞:農地發展權;征地;土地增值;分配
一、對農地發展權及價值構成的闡釋
(一)對農地發展權的概念闡釋
在我國,廣義的農地發展權包括:在堅持農地所有權性質不變的前提下, 權利主體為了追求農業生產的高效益而進行農業結構調整的權利或權利主體將農用地改變為農村集體建設用地的權利,或者改變農地所有權性質,農地被征收為國家建設用地的權利。狹義的農地發展權是指對土地進行再開發的權利,即土地所有權人或土地使用權人通過改變農地現有用途而獲取的額外收益的權利。它是從農地所有權派生出來并可單獨處分的權利,既可被土地所有者擁有,也可被非土地所有者使用。在我國,將農村集體所有的土地征收轉為國家所有的建設用地,其征地增值收益的理論依據為狹義的農地發展權。因此,征地增值收益分配主要涉及承包農戶、農村集體、農地經營者、地方政府、用地單位等利益主體。
(二)對農地發展權價值構成闡釋
農地價值是一個具有社會、生態、經濟及商業等多方面價值的綜合系統。其中,農地社會價值主要包括社會保障和糧食安全保障等并為國家所擁有,以前我國部分地區人民政府的農地征收補償已納入了社會保障價值,現在已被立法認可,如2019年新《土地管理法》四十八條規定:“征收土地應當……并安排被征地農民的社會保障費用”。農地經濟價值表現為農地收益和成本之差,并為國家、農村集體及承包農戶共同擁有。目前,農地征收補償主要體現為農地經濟價值部分,較少考慮農地其他價值部分。農地商業價值主要體現為農地發展權價值,在我國也主要為國家、農村集體及承包農戶等共同擁有。出于保障糧食安全,國家實施農地用途管制,不允許農民從低收益土地用途轉變為高收益土地用途。其實,這限制了農地發展權,導致農地價值不能完全實現。雖然我國目前無農地發展權的立法規定,但它是客觀存在的并被大部分學者認可。理論上,關于其價值構成,孫弘學者認為“土地發展權物質要素的價值形態就是土地發展權價值構成。具體包括:用途變更所產生的價值變化;開發密度變更所產生的價值變化;體現在用途與開發密度價值中的區位價值差。”
二、湖南省被征地農村集體和農民的征地增值收益分配現狀及原因分析
(一)被征地農村集體和農民的征地增值收益分配現狀
本文選取2012年和2018年省會長沙市、湘南郴州市和湘北常德市三個代表地區,比較其不同年份和不同區域的征地補償標準。
首先,通過比較表1和表2省會長沙市地區市區和長沙縣兩區域的被征地農村集體和農民的征地補償標準,可以發現:2012年長沙市市區Ⅰ區76000元/畝、Ⅱ區70000元/畝、Ⅲ區65000元/畝;長沙縣Ⅰ區54700元/畝、Ⅱ區52600元/畝。2018年長沙市市區Ⅰ區99000元/畝、Ⅱ區84000元/畝、Ⅲ區78000元/畝;長沙縣Ⅰ區71100元/畝、Ⅱ區68400元/畝。同一年份征地補償標準,長沙市市區標準高于長沙縣區域標準;同一區域的征地補償標準,2018年標準高于2012年標準。通過比較表1和表2的湘南郴州市地區市區和桂陽縣兩區域的征地補償標準,可以發現,2012年郴州市市區Ⅰ區55000元/畝、Ⅱ區48000元/畝、Ⅲ區40000元/畝;桂陽縣Ⅰ區42000元/畝、Ⅱ區36400元/畝。2018年郴州市市區Ⅰ區715000元/畝、Ⅱ區62400元/畝;桂陽縣Ⅰ區54600元/畝、Ⅱ區44800元/畝。同一年份征地補償標準,郴州市市區標準高于桂陽縣區域標準;同一區域的征地補償標準,2018年標準高于2012年標準。通過比較表一和表二的湘北常德市地區市區和安鄉縣兩區域的征地補償標準,可以發現:2012年常德市市區Ⅰ區60500元/畝、Ⅱ區52900元/畝;安鄉縣Ⅰ區44400元/畝、Ⅱ區39400元/畝。2018年常德市市區Ⅰ區76800元/畝、Ⅱ區67100元/畝;安鄉縣Ⅰ區57700元/畝、Ⅱ區51200元/畝。同一年份征地補償標準,常德市市區標準高于安鄉縣區域標準;同一區域的征地補償標準,2018年標準高于2012年標準。
然后,通過比較2012年和2018年省會長沙市、湘南郴州市和湘北常德市三個地區的被征地農村集體和農民的征地補償標準,可以發現:湖南省不同地區的不同區域存在不同補償標準且2018年標準比2012年標準均有一定提高,但是湖南省2018年征地補償標準仍然偏低,即享有土地所有權的農村集體和擁有集體土地使用權的農民取得的征地增值收益偏低。由此可以得出:湖南省被征地農村集體和農民的征地增值收益分配現狀與其他學者的相關研究結果基本一致。我國目前的土地征收補償范圍太小,農民得到的補償是一次性的經濟補償,如鮑海君、吳次芳研究指出,如果以成本價為 100%,則擁有集體土地使用權的農民只得5%,擁有集體土地所有權的農村集體為25%~30%,而60%~70%為政府及各級主管部門所得。
(二)被征地農村集體和農民征地增值收益分配不公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農地發展權
《憲法》第十條規定“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土地實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給予補償”《物權法》第四十二條規定“征收集體所有的土地,應當依法足額支付土地補償費、安置補助費、地上附著物和青苗的補償費等費用,安排被征地農民的社會保障費用。”舊《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條規定:“征收耕地的補償費包括土地補償費、安置補助費以及地上附著物和青苗的補償費。”可見,三部法律都沒有土地發展權及其補償的規定。舊《土地管理法》規定的農地征收補償為被征地農業用途的農地價值補償,即農地的經濟價值補償。《物權法》新增了農地社會價值的規定,但也沒有規定農地發展權價值。2019年新《土地管理法》提高了被征地農民征地補償,似乎包含了部分農地發展權價值,如第四十八條:“征收土地應當給予公平、合理的補償,保障被征地農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長遠生計有保障。”“征收土地應當……并安排被征地農民的社會保障費用”但由于農地發展權的立法缺失,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不公平不合理問題依然存在。一般來說,將農村集體所有土地征收轉變為國家所有的建設用地,必然引發土地價值巨大增加,但依據湖南省征地補償標準來看, 農村集體和農民的土地被征收后,他們所獲得土地補償內容并未完全包含農地發展權的收益部分。由于農地發展權是農地所有權的組成部分,作為農地所有權主體的農民集體理應取得較大的征地增值收益。因此,被征地集體組織和農民征地增值收益分配不公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農地發展權。
三、完善農地發展權視角下征地增值收益分配法律機制
(一)政府參與征地增值收益分配
中央政府是國家公共利益的最大提供者和守護者,在土地征收過程中承擔全國土地管理和監督職能,且站在國家整體發展目標的戰略高度,制定并完善土地相關法律法規,保護耕地面積,確保國家糧食安全和生態安全,引導土地資源合理利用,維護全社會多方利益。地方政府作為國家法律政策執行者,既要保證當地經濟發展,又要執行保護耕地的法律政策。因此,作為國家代表的人民政府理應參與征地增值收益分配,這既是權利主體享有農地糧食安全價值和農地生態安全價值的體現,也是政府取得間接投資增值的表現。政府主要是通過土地稅費及土地出讓金的分成等來實現增值收益分配。2019年新《土地管理法》第五十五條第二款:“新增建設用地的土地有償使用費,30%上繳中央財政,70%留給有關地方人民政府。”可見,政府分享征地增值收益分配是農地發展權在立法上一定程度的體現。
(二)被征地農村集體參與征地增值收益分配
農村集體是農地所有權的主體,其參與征地增值收益分配的理由主要有:第一,農村集體土地作為土地的自然增值載體,農地征收使其喪失了土地所有權,相應的,地方政府則取得了土地所有權,如果按照農地用途經濟價值和社會價值補償,就會嚴重損害農村集體的利益;如果集體有權參與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就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漲價歸農民集體經濟組織”的農地發展權理論。第二,從農地發展權的來源來看, 農地所有權是農地發展權的權源,作為農地所有權主體的集體理應取得較大的增值收益。農村集體依據其享有的土地所有權,可依法對其占有、使用、收益和有限的處分。而農地發展權是行使其土地處分權與收益權的具體表現。第三,從土地增值來源來看,征地前農村集體為建設農村水利交通等設施而進行了投資,如農田水利基礎設施的改善等,即實現土地直接投資增值或人工增值。
(三)被征地承包農戶或經營者參與征地增值收益分配
被征地承包農戶或經營者參與征地增值收益分配的理由主要有:第一,從農地使用權和農地發展權關系看,農村集體土地使用權派生于土地所有權,并獨立存在。農地承包經營權是承包農戶對農地進行占有、使用、收益和有限處分的權利,當對某塊土地行使農地發展權時,該土地將失去作為農業用途土地使用的功能,所以,從這個角度看,農地發展權對集體土地使用權具有“注銷”功能。2019年新《農村土地承包法》規定“耕地的承包期為三十年……” 對被征地承包農戶而言,農地征收使得承包農戶失去了剩余承包期限的土地承包經營權,相應的,經營者喪失了經營權。因此,土地發展權的行使關系到土地使用權人的利益。同時,被征地承包農戶或經營者作為土地直接投資主體,為提高地力而對土地進行投資進而產生了土地增值。所以,被征地承包農戶或經營者理應分享部分土地增值收益。第二,從法律屬性來看,土地承包經營權既可對抗地方政府在農地征收過程中對承包經營者的侵害,還可排除農村集體組織在土地補償費分配上的不法損害,要求農村集體合理分配補償費用。第三,從農村土地的社會保障屬性看,“失去了土地,農民集體成員就會失去從事農業生產的基本生產資料,也就失去了土地的社會保障,”農地非農化過程意味著被征地承包農戶以其擁有的農地社會保障價值交換了農地發展權價值,因此,被征地承包農戶應獲得相當于農地發展權價格的補償。《物權法》雖然將土地承包經營權納入征地補償的內容,且增加了體現農地社會價值的社會保障費,但卻未具體規定。
(四)未被征地承包農戶或經營者參與征地增值收益分配
對在同一農村集體組織內農地未被征收的承包經營者而言,也應給予其適當比例的征地增值收益分配。“中國征地補償制度存在的一個問題是,那些偏遠農村大田農民的土地發展權一直被忽略。在理論上,全國的每一塊土地都天然地擁有土地發展權。”“大田農民的土地缺乏被征收的機會,他們不會、也不懂得爭取發展增益,是 ‘沉默的大多數”因為未被征地的承包經營農戶以土地失去農地發展權的機會為代價承擔著為國家和社會保障農地數量、生態安全和糧食安全的責任。農地的生態價值和糧食安全價值是因公共利益而存在的,且為國家所擁有,政府理應給他們分配征地增值收益。因此,應該從農地發展權的增值收益中,進行再次分配,使得這部分農地未被征收的承包農戶或經營者,也能參與分享本村集體農地發展權的增值收益。此外,有學者提出:“為防止近郊農民獨享土地增值,形成‘土地食利者階層,應該通過土地發展權轉讓制度讓遠郊保護區農民參與到城鎮化進程中,進而分享其帶來的收益,以調節管制地租在遠郊保護區農民和近郊失地農民之間分配。”這主要針對被征地農村集體之外的農地未被征收的承包農戶或經營者也能適當分享征地增值收益。
參考文獻:
[1]周建國.論農村土地征收中農地發展權的法律保護[J].貴州農業科學,2010,38(04):223-227.
[2]孫弘.中國土地發展權研究:土地開發與資源保護的新視角[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87.
[3]謝付杰.農村土地征收中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機制研究[J].農業經濟,2016 (08):111-112.
[4]臧俊梅等.農地發展權在土地權利體系中的地位及其相互關系研究[J].國土資源科技管理,2009(05):100-104.
[5]吳興國.征地補償費受償主體及農地發展權歸屬探究[J].中國發展,2008(03):63-67.
[6]韓松.農民集體土地所有權的權能[J].法學研究,2014(06):63-79.
[7]陳柏峰.土地發展權的理論基礎與制度前景[J].法學研究,2012(04):99-114.
[8]李懷,董志勇.關于農地“非農化”增值收益的合理分配[J].理論探索,2019(05):107-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