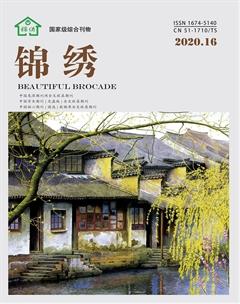秦腔須生表演藝術之我見
肖文敏
中國戲曲藝術是一種來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藝術表演體系,分生、旦、凈、丑等行當,這是中國戲曲特有的角色表演體制,秦腔更是如此,這些有深刻美學內涵的表演程式,要求通過演員的“唱、念、做、打”和“手、眼、口、身、法、步”等表演形式來表現戲中人物的喜、怒、哀、樂、愁等情緒。
演員入科學習六年甚至十年,就是在日積月累的繁復訓練中傳承、創新戲曲程式,讓自身和戲曲程式融合,化于表演中,演員須運用行當程式去塑造角色形象,與此同時,要想成功塑造好角色,演員還須在理解人物、體現人物、挖掘人物性格方面下功夫。舞臺表演具有“生天生地生鬼生神,極人物之萬途,攢古今之千變”的特點及功能。這是基于中國戲曲藝術特點的本質認識,既是以以唱念做打的舞臺表演表現人物,又是以演員對人物的理解來展示演員的戲曲功底,既是人演藝,又是藝托人,作為演員的表演主體與作為角色表演的客體二者互相成全,相得益彰。
戲曲的舞臺表演具有無限的價值,將生活的真實通過藝術加工變為藝術的真實,達到塑造人物形象,表演故事,傳遞情感的目的,戲曲產生于“情”,回歸于“情”,唱念做打的程式化表演即是對這種生活與歷史真實之“情”造化為藝術逼真、傳神之“情”的過程,這個藝術創作的過程始于對角色人物時代背景的了解以及人物性格的準確分析,終于準確傳神的程式化舞臺表現。
戲曲的表演,盡管遠離生活,但首先要遵循的是“本色當行”的要求,這是戲曲藝術千年流傳的根本基因,是戲曲最重要的美學訴求。形式表現內容,內容豐富形式。角色的唱念做打等表演形式必須忠于生活中的人物形象,又要符合人們理想藝術形象的本來面目。演戲就是表演人物,應根據人物的身份、性格、處境有選擇的運用程式。 如我在學演《逃國》、《拆書》時,因伍員這個人物在表演中屬于做工較多,不斷跑圓場,雙手揮動馬鞭。此外該劇對演員腿功的要求也甚高,劈叉,提腿,又有左右腿交替動作。在學演時,基于對伍員性格及遭遇的理解,我覺得要緊緊貼合人物心理,呈現出其復雜、為難的整體情感特點。由于秦腔中須生行當的特點是注重唱,唱腔需慷慨激昂、酣暢淋漓方可達標,這樣的話演員就需將口腔完全打開,大段的唱腔需要通過聲音完成人物塑造。同時,結合手、眼、身、發、步等技巧表演,以及精簡、抒情的道白,共同助力于人物情感的表現。秦腔名家王保易老師曾說“表現情緒的程式,是表現特定情境下人物的心理狀態,它利用剖析的表現手段把人物內心的秘密淋漓盡致地藝術地展示給觀眾,以達到高度意境的創作境界。”秦腔的程式把人物的內心世界通過夸張、變形的手法表現出來,運用程式化的動作、技巧,使之成為刻畫人物性格的手段,能夠增強表現的力度、深度。如捋髯、提袍、甩袖、亮靴底等傳統式須生的做功,這些在戲曲表演中,是必須的、必不可少的。但是,我們的表演不要被傳統的表演程式所捆綁,要按照人物的劇情的需要,靈活地運用程式,切忌僵化、呆板,或炫耀技巧等。這就要求演員要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根據具體人物有選擇的利用程式。
“劇戲之道,出之貴實,而用之貴虛”,中國傳統戲曲最重要的特點之一就是虛擬性,這里的虛擬指的是演員表演動作技巧之虛,虛只是形式,回歸到本位還是實,即情緒之實,審美之實。須生角色由于其行當特點規范所限,人物性格沉穩,情感充沛,在表演中需要極其注意情感表達的收與放,情感的“放”,是汪洋恣肆、信馬由韁的夸張化表演,是塑造人物的主要手段和重要特點,而“收”則體現的是細節,在大部頭的動作與技巧的表達之外,注重其細節,注重人物情緒情感的變化的多重情節點,如能準確拿捏這粗細之間的度,達到收放自如、節節累積的狀態,才能更好的表達出人物性格發展的動態過程,為人物的舉動增添其合理性,使其合理合情。秦腔傳統折子戲《打鎮臺》中“王震做官太懦弱”的中心唱段表現了縣令王震不畏權勢、剛正不阿、秉公執法的性格,這段唱腔節奏由快轉慢,再由慢到快,演員的演唱既要噴口有力,又要在情緒轉入較為舒緩的對前朝故事的回憶當中,唱得一板一眼,把人物對包公的敬仰、對秦香蓮母子的同情以及對陳世美的憎惡準確地傳達給觀眾。最后幾句,人物情感達到高潮,要讓觀眾真切感受到人物情緒上的劇烈轉化和波動,表現出人物秉公執法、伸張正義的性格,唱腔要如長空鶴鳴,奇峰突出,以產生劇烈的震撼人心的力量。演員在表演和演唱中吐字清晰是最基本的要求也是最關鍵的。一定要將唱詞準確地送到觀眾的耳中卜前輩京尉大師譚鑫培就曾這樣比喻戲曲演員的咬字:要象嘴里咬著一條“活魚”,不能咬得過緊,過緊就會咬死(使字音生硬僵死);也不能口松,因為“魚”是“活”的,稍一口松,“魚”就跑掉了(即嘴上無力不能響堂打遠)。所以咬字實在是演員的一項基本功。既要使“魚”在嘴里生動活躍,無論唱念,都要抑揚頓挫,流暢悅耳;又要把“魚”緊緊地叼在嘴里,使得字眼兒清楚,噴口有力,節奏鮮明,響堂打遠。在多年的藝術實踐中我深刻體會到要想同時達到這樣兩個要求,我們必須下苦功反復練習才行。須生演員除了唱腔之外還要通過剛健細膩的表演來渲染劇情、感動觀眾。如今的秦腔藝術不再講究聲嘶力竭、粗暴生猛的“吼”字了,而是更多的講究音色的美感,發音的科學性。秦腔藝術逐漸融合了多種藝術元素,日臻完善文明,更具審美價值。“吼”起來的秦腔逐漸遠去,但“吼起來”的精神卻留下深刻的烙印。
秦腔藝術是誕生于農耕文化成熟時期的大眾性、通俗性舞臺藝術,它的題材、內容、藝術形式代表三秦文化和西北地區廣大人民群眾生產生活、價值觀念以及黃土高原粗獷、荒蠻、樸實、善良、正直、驃悍民風民俗。它的表現題材內容廣泛,唱腔特別是須生唱腔高亢激越、蒼涼質樸,清人焦循稱它“其音慷慨,血氣為之動蕩。”表演上大氣細膩,真實動人。這些都對演員形成較高的要求,須生演員的演唱應努力做到脆中見亮,厚中藏韻,高峻挺拔,蒼勁酣暢,吐字清晰。秦腔有六大板式,演員要運用這些較定型的曲調來表現不同的劇情刻畫不同的人物,體現不同的思想感情,這就不能不根據人物性格和具體內容在行腔的表現方法上有所處理。若演員的行腔以真實的情感,細膩深刻地表現出劇中人物的思想動態,就能使觀眾為之動容。
秦腔藝術源遠流長,博大精深,作為青年演員,在練功排戲演出之余,要以歷史和前輩為師,砥礪繼承和發揚傳統劇目中的精華,勤勉思考,刻苦練功。同時,一定要以生活為師,做個有心人,體察人性的復雜和真善美。只有如此才能成為一個優秀的戲曲演員,為我們中華民族文化復興多做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