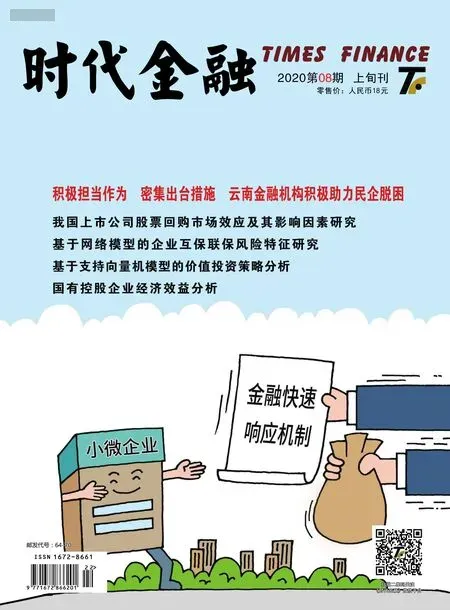基于網絡模型的企業互保聯保風險特征研究
楊洋



摘要:本文對企業互保聯保貸款的發展脈絡、風險演化過程進行了梳理,在靜態、動態分析框架下構建企業互保聯保風險特征指標集,借助網絡模型模擬風險傳染路徑測度擔保圈風險,結合敏感性分析總結擔保圈風險特征及其與企業規模、杠桿、不相稱不對等擔保等屬性的關系,并從重建授信準入標準、加強擔保圈風險的量化管理、優化地方政府風險處置舉措等角度提出建議。
關鍵詞:企業互保聯保關系網 擔保圈 風險特征 網絡模型
企業互保聯保貸款是在我國信用擔保體制不健全背景下,融資擔保機構等商業性、政策性外部擔保供給不足的替代性、過渡性創新產物。依靠企業互保聯保關系網內的橫向監督約束機制和損失吸收機制,互保聯保貸款在一定程度上對降低銀企信息不對稱、拓寬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融資渠道發揮了重要作用,在民營經濟活躍的東南沿海地區得到推廣。但企業互保聯保貸款本質上屬于關系網內部的信用擔保,風險分散程度有限,隨著企業互保聯保關系網的日益復雜化,擔保關系向圈、鏈方向發展,不相稱、不對等等問題擔保不斷增多,在經濟上行及平穩運行期間這些擔保虛化積累的風險尚能被掩蓋,但在經濟下行期間便會快速暴露、大量釋放,普惠金融的創新模式隨即演化為火燒連營的風險鏈條,進而演變為區域性金融不穩定因素,對地方經濟金融運行、地方金融生態建設造成了較為不利的影響。如何管理企業互保聯保風險引發了金融從業人員、金融監管部門、地方政府和學界等的廣泛思考。有效管理企業互保聯保風險,首先應提高量化監測的水平。因此,構建企業互保聯保風險特征指標,集量化擔保圈(鏈)風險、模擬預測風險傳染路徑、研判影響效果,對商業銀行提高互保聯保風險管理的精細化程度、金融監管部門及時準確開展風險監測預警,以及地方政府參與風險處置協調、修復區域金融生態環境均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文獻綜述
西方國家大多已建立起完備的社會信用體系、健全的法律約束機制和較為通暢的融資渠道,西方學者對復雜擔保關系所形成的互保聯保、擔保圈(鏈)風險研究較少,對融資擔保問題的研究主要基于交易成本理論(Coase R H.,1937[1])、信息經濟學理論(George A.Akerlof,1970[2];J.E.Stiglitz,Andrew Weiss,1981[4])、代理成本理論(Michael C.Jensen,William H.Meckling,1976[3])和監督機制理論(Banerjee A.V,Besley T.W.,1994[5])等。Allen、Gale(2000)[6]基于風險共享視角,得出經濟體的信用聯結程度與系統性風險呈負相關關系的結論,認為互保聯保所形成的信用聯結關系可有效降低系統性風險。M.Richiardi et al(2011)[7]反駁了上述觀點,指出信用聯結程度與系統性風險的負相關關系存在邊界,突破邊界的信用聯結反而會加大系統性風險。
我國學者結合現實案例,對企業互保聯保風險演化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張樂才(2011)[8]以紹興華聯三鑫為案例,通過信用網絡模型對擔保圈的風險傳染機制進行了研究,認為企業資金擔保鏈具有風險消釋和風險傳染的雙重功效,當經濟環境有利時風險共享是有益的,經濟環境不利時會降低風險共享的能力,導致企業全部陷入困境。陳少華、陳菡(2013)[9]從博弈論視角研究了我國中小企業擔保圈從形成、擴張到破裂的演化過程中銀企之間的利益博弈關系,分析了銀行抽貸行為對擔保圈危機的作用。葛志強(2014)[10]對威海鋼貿貸款互保聯保風險進行了案例研究,指出聯保融資模式存在以行業下行信號為標志的有效邊界,銀行追求短期利益的行為是導致風險形成的直接原因。中國人民銀行濟南分行課題組(2015)[11]基于對山東省擔保圈現狀的考察,采用金融網絡分析法,以擔保圈內的違約家數測度擔保圈風險,認為應辯證地看待企業互保聯保問題,提出互保聯保貸款存在合理邊界,肯定了其在促進企業融資、緩釋風險方面的積極作用,但指出也要防止擔保圈無限放大導致的風險失控。徐子慧(2018)[12]以上市公司為例,就擔保網與企業風險承擔水平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研究,認為融資能力較差的企業通過擔保網絡獲取融資所承擔的風險水平更高,在復雜的擔保網絡中,這種正相關關系更加顯著。白旭東(2018)[13]基于洛陽、紹興、杭州等地擔保圈典型案例,對家庭式互保、金字塔型擔保圈、復合型擔保圈的風險傳染路徑分別進行了定性剖析。通過上述文獻梳理,我們發現,國內文獻主要著眼于單個微觀主體或擔保圈聯合體,分析多為定性判斷或命題證明,未能將微觀主體屬性與整個擔保圈(鏈)風險特征相結合對互保聯保風險進行量化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二、企業互保聯保貸款的基本情況及風險演化
互保聯保貸款作為保證貸款的一種形式,是在我國信用擔保體系不健全、外部擔保供給不足背景下的替代性、過渡性創新,其實質是通過企業間信用擔保關系緩解信息不對稱、彌補抵質押物匱乏等劣勢的手段,是中小企業提高融資可得性的重要渠道。在互保聯保貸款快速發展的同時,風險相伴而生。隨著宏觀經濟增長放緩,企業前期盲目投資帶來的產能過剩矛盾開始顯現,單個企業貸款違約引發的多米諾骨牌效應沿擔保圈(鏈)傳染蔓延,逐步危及正常經營的擔保企業。隨著代償風險的快速傳染,東南沿海地區以中小企業為參與主體的互保聯保風險相繼爆發。以X省為例,2014年至2015年,互保聯保風險在個別縣域暴露。這些擔保圈(鏈)企業具有較強的地域屬性,未現跨地區擔保;行業集中度較高,行業附加值低,多為同行業或產業鏈內的上下游傳統制造業企業;企業規模小,擔保關系復雜。互保聯保貸款這一制度創新逐漸演化為火燒連營的風險鏈條,成為當時區域性金融不穩定因素。
經過幾年積極的風險化解處置,上述縣域互保聯保風險已得到控制。但受此影響,銀行信貸風險偏好逐步走弱,尋找優質資產、瞄準大型企業成為涉貸銀行共同的選擇,與大型企業多元化擴張對資金的渴求一拍即合。在嘗試過不動產抵押貸款、股權質押貸款、表外融資等多重融資手段后,大型企業間互保聯保貸款成為一種新的擔保方式產生,擔保圈(鏈)開始出現大型企業的身影。大型企業互保聯保主要表現為集團內子公司互保、母公司為子公司擔保、集團間互保等。2016年開始,大型企業保證貸款余額快速增長,截至2017年6月末,各類型企業保證貸款總額已超過抵質押貸款總額,成為企業第一大貸款方式。互保聯保貸款主體的規模雖有所增加,但風險傳染機理未發生變化,且大型企業融資渠道較中小企業更寬,杠桿總量高、杠桿結構復雜、風險傳染源多,自2018年大型企業互保聯保風險在個別地區開始顯現,處置協調面臨一定的困難。
三、企業互保聯保風險的量化分析——基于網絡模型的研究
為直觀反映代償風險傳染對企業互保聯保關系網的沖擊,本文通過構建網絡模型,在靜態、動態和敏感性分析框架下開展案例研究,量化企業互保聯保風險特征,為區域性金融風險的監測預警提供參考。案例采用X省內典型擔保圈數據,涉及樣本企業106家、地區6個,企業所屬行業包括紡織業、化工業、建筑業、金屬制品及加工業、電氣業等,企業規模包含大、中、小型企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一)企業互保聯保關系網的靜態分析
假設擔保圈內共有N家企業,將其構成的互保聯保關系設計為方陣X:
其中,Xji表示企業i為企業j提供擔保的金額,因企業無法為自己提供擔保,故方陣對角線上的金額均為0。列向量之和表示擔保圈內企業i的對外擔保總額。
提取企業間擔保關系,使用gephi軟件繪制企業互保聯保關系網,對其進行靜態分析。定義以下靜態指標,反映擔保圈的基本屬性。
1.度(degree)。體現企業互保聯保關系網中企業的地位,擔保關系越復雜,度越高。包括出度和入度兩個概念:出度(out degree)體現被擔保關系,出度越高表明為其擔保的企業家數越多,當其發生違約時,各擔保方需履行無限連帶義務為其代償;入度(in degree)體現對外擔保關系,入度越高表明對外擔保的企業家數越多,需對違約的擔保對象進行代償,承受代償風險。
2.相稱、對等互保。體現企業互保聯保關系網的穩定性。“相稱”指互保雙方凈資產規模較為相當;“對等”互保指各自為對方的擔保金額較為相當。
3.潛在杠桿率(Potential Leverage,PL)。體現互保聯保關系網中企業的最高杠桿水平。隨著代償的發生,企業或有負債向表內債務轉化,當企業i的對外擔保全部成為現實的代償時,企業i的杠桿水平達到最高,即為潛在杠桿率。
其中,Gji為企業i為企業j的擔保金額,為企業i的對外擔保總額,Di、Ei分別為企業i的負債總額、凈資產余額。
以擔保圈2為例,形成如下關系(如圖1)。該互保聯保關系網中共有7家企業,圓圈的尺寸代表企業凈資產大小,如擔保圈2內企業1、2、5、6均為凈資產余額較大的企業,3、4、7為凈資產余額較小的企業;圓圈的顏色深淺代表企業杠桿水平的高低,如顏色最淺的企業3在擔保圈2中擁有最低潛在杠桿率(0.57),而顏色最深的企業4潛在杠桿率最高(4.32);線的多少代表度的高低,如企業2和5擁有較高的度(均為8),與擔保圈內其他企業的關系較為緊密,企業3的度最低(僅為2),在擔保圈中地位重要性較低;線的粗細代表擔保金額的高低,如企業4和6的互保金額遠高于企業3和5。左圖中,箭頭表示風險傳染方向,如企業2為企業6提供擔保,則代償風險由企業6向企業2傳導;右圖中,以曲線更清晰地展示了擔保圈2中樣本企業的互保關系及擔保金額的大小。
可以看出,該擔保圈以互保為主,不相稱、不對等互保使該擔保圈潛藏風險隱患。一方面,相稱不對等互保關系易引發道德風險。如擔保圈2中,企業2和6凈資產規模較為相稱,但企業2為企業6擔保金額是其反擔保金額的2.5倍。由于互保關系不對等,當企業6違約時,企業2代償意愿較弱,甚至可能發生企業2惡意違約要求執行反擔保的道德風險事件。另一方面,對等不相稱互保關系降低擔保圈的穩定性。如擔保圈2中,企業4和6互保金額較為對等,但企業6凈資產規模是企業4的2.65倍,若企業4違約,銀行會依據擔保方的無限連帶責任向其全額追償,借貸雙方的“蹭大戶”心理促使代償風險加速傳染;反之,若企業6違約,企業4的償債能力較弱,無法履行擔保責任,這樣的擔保形同虛設,企業間的橫向監督約束機制極易被破壞。
通過設定臨界值對不相稱不對等互保的判斷進行量化處理。本文中,若互保雙方凈資產比值大于1.5倍,我們視為不相稱互保;若互保雙方為對方提供的擔保金額比值大于1.5,我們視為不對等互保關系。據此,統計各擔保圈中不相稱、不對等互保關系,得出如下結果(如表1)。
靜態分析可知,擔保圈1內的企業互保聯保關系較為復雜;擔保圈2、4不相稱互保對數占比、不對等互保關系占比較高,發生道德風險的可能性較高,擔保圈潛藏不穩定性因素;擔保圈1、2、4擁有較高的潛在杠桿率,企業自身負債和對外擔保相對于凈資產而言較多。
(二)企業互保聯保關系網的動態分析
為準確判定擔保圈內企業的系統重要性及擔保關系穩健性,需進一步考慮企業代償額、杠桿率等指標,對擔保圈中的企業開展風險傳染的網絡模擬。
定義企業i為企業j的擔保金額、代償金額分別為Gji、Cji,違約率、代償率分別為DR、CR,因代償導致企業i的杠桿率為Lji,企業i的負債總額、凈資產余額分別為Di、Ei。故有:
Cji= Gji·DR·CR;
Lji=×100%
擔保圈的風險傳染路徑即為對擔保圈內每一家被擔保企業實施壓力測試的過程:假設被擔保方逐個違約,在無限連帶擔保責任的法律關系下,引發擔保方為其全額代償,CR均為100%,擔保方按違約率為企業j代償Cji;由于發生代償,企業i或有負債向表內債務轉移,此時企業i面臨的杠桿上升至Lji,當Lji超過某個臨界值時,表明由于為企業j代償超出自身承受能力,企業i破產,企業i破產引發的違約進一步通過其擔保關系向企業i的擔保方傳導。若未超過臨界值,則表明企業i可抵御代償風險,傳染終止。傳染過程直到擔保圈內所有企業均經過上述風險沖擊不再發生新增違約企業為止(如圖2)。
定義以下動態指標量化互保聯保風險:
1.傳染性指數(Contagion index,CI)。一家企業倒閉會引起整個擔保圈內其他企業資本損失的比例,體現擔保圈內被擔保方風險外溢力度的大小。高出度的企業風險外溢的路徑較多,擁有較強的傳染性。被擔保方企業j的傳染性指數計算公式為:
CIjr=×100
CIj=
其中:Cjir為第r輪中擔保圈內企業i為企業j代償的金額,n為傳染終止的輪數,k為擔保圈內企業總數。
2.傳染波及的違約數(induced default,ID)。直至傳染終止,一家企業違約所牽連的企業家數(包括直接傳染和間接傳染)。傳染波及的違約占比(induced default rate,IDR)體現傳染的覆蓋范圍。
3.脆弱性指數(Vulnerability index,VI)。擔保圈內企業逐一違約對本企業資本沖擊的平均力度,體現擔保圈內擔保方承受代償沖擊的韌性。高入度的企業發生代償的可能性較高,存在較多的風險沖擊來源,在同等凈資產條件下,脆弱性較強。擔保方企業i的脆弱性指數計算公式為:
4.代償導致的違約次數(hazard,Hz)。當擔保圈內其他每一家企業違約時,某企業因代償發生違約的次數(包括直接沖擊和間接沖擊)。代償導致的違約次數占比(hazard rate,HR)體現擔保方遭受沖擊后的死亡率。
5.傳染輪數(rounds,RD)。按照所設計的傳染路徑,從初始違約到傳染終止經歷的輪數。
通過matlab模擬上述傳染路徑,計算體現互保聯保風險特征的動態指標。取杠桿率臨界值為1,違約率為0.5時,仍以擔保圈2為例,得出圈內7家企業各風險特征指標。結合靜態指標,對擔保圈2進行結構分析(如圖3)。
結果表明,擔保圈風險傳染路徑具有較高的復雜性,需將靜態、動態方法結合起來分析擔保圈風險特征。以擔保圈2中的樣本企業3為例,度僅為2,在整個擔保圈2中地位較不重要,但與其存在唯一互保關系的企業5(如圖1)的度高達8,企業3違約引發的傳染持續4輪導致其他6家企業違約(如圖3),產生較強的傳染性。企業3凈資產余額較小,其對外擔保總額和自身負債總額也較低,在擔保圈2中擁有最低潛在杠桿率,因此擔保圈內其他6家企業輪番違約對其進行沖擊,企業3均不會破產,沖擊后存活率為100%,擁有較低的脆弱性。
為體現擔保圈風險全貌,各擔保圈如法炮制,以擔保圈為單位計算風險特征指標均值(如表2)。CI、VI是金額占比指標,體現了擔保圈內單位凈資產的損失吸收能力和抵御代償沖擊的能力,分別用以衡量風險外溢性和抗沖擊韌性;IDR、HR是企業家數占比的指標,反映了擔保圈風險的覆蓋面,用以衡量風險外溢范圍;RD反映了風險傳染延續的時間,用以衡量風險影響深遠程度的指標。上述動態分析指標分別從風險傳染的強度、廣度、深度三方面度量了擔保圈的穩定性。
將企業互保聯保關系網的靜態、動態分析相結合(表1、表2),分析其內在關聯性,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結論1:傳染性指數(CI)、脆弱性指數(VI)與擔保圈復雜程度非正相關關系,與企業規模非負相關關系,與不對稱不對等互保關系、杠桿水平等屬性具有一致性。以度、擔保圈內企業家數等指標衡量擔保圈的復雜程度,可發現,復雜程度相當的擔保圈2和3(企業家數分別為7家、8家,度分別為21、20)CI和VI差異較大,并非預想的正相關關系。中小企業擔保圈5的CI和VI明顯小于大型企業擔保圈1和6,說明大企業擔保圈風險不一定低于中小企業。結合靜態分析結果,我們發現擔保關系、杠桿水平等基本屬性是影響擔保圈穩定性的重要因素。減少不相稱、不對等擔保,能從一定程度上降低道德風險發生的概率,控制杠桿水平,可保持企業具備一定的償債能力,從而維持互保聯保關系網中企業間的橫向監督約束機制,保持擔保圈的穩定。如擔保圈1和6同為大型企業擔保圈,但擔保圈1擁有較高的潛在杠桿率及不相稱擔保關系,穩定性弱于擔保圈6。擔保圈5由于不存在不相稱、不對等互保關系,杠桿較低,雖為中小企業構成的擔保關系,但具有較強的穩定性。
結論2:企業互保聯保關系網的靜態分析更多地體現擔保圈內企業的抗沖擊韌性。從靜態分析結果看,具有較高潛在杠桿率的擔保圈,表明相對于負債總額和或有負債,企業凈資產較低,償債能力較弱,抵御代償風險沖擊的韌性不強。從動態分析結果看,在企業互保聯保關系網復雜程度相當的情況下(如擔保圈2和3),潛在杠桿率與脆弱性指數(VI)呈正相關性。
結論3:從擔保圈視角看,傳染波及的違約占比(IDR)和代償導致的違約占比(HR)均體現傳染的波及范圍。從擔保圈視角看,IDR和HR分別從風險源頭和沖擊對象計算違約次數,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因此對于同一擔保圈而言,各家企業傳染波及的違約數之和等于各家企業受代償沖擊導致的違約次數之和,ID和Hz、IDR和HR相等,均衡量了擔保圈風險波及的范圍。案例中,風險強度較高的擔保圈2和4同時也擁有較廣的影響面。
結論4:傳染輪數(RD)與杠桿激進程度、風險強度、傳染波及范圍等多個指標相關,與企業規模無明顯關系。擔保圈1和6均為大型企業,擔保圈1杠桿倍數高、擔保較為激進,風險強度和風險波及范圍相對較大,傳染輪數顯著超過擔保圈6,風險出清的速度較慢,對地方金融生態的影響較為深遠。擔保圈2和4均為中小企業,擔保圈2的杠桿激進程度、風險強度和風險波及范圍均超過擔保圈4,風險爆發后將在較長時間內發酵蔓延。擔保圈5(中小企業)和6(大企業)均具有較低的杠桿倍數,由于擔保圈5風險觸發后將在稍大的范圍內傳染蔓延,故傳染輪數略多。
根據靜態、動態分析框架下企業互保聯保風險特征指標集,我們可通過可視化方式呈現擔保圈的穩定性。如圖4,橫軸為IDR、HR,體現擔保圈風險波及范圍;縱軸為傳染輪數(RD),體現傳染持續時間;氣泡大小為CI和VI之和,體現風險強度;氣泡顏色深淺為不對稱不對等擔保關系占比之和,體現擔保圈靜態風險屬性。據此,我們可以多維度描述各擔保圈風險特征。位置越靠近右上角、氣泡越大、顏色越深的擔保圈,風險越高。如擔保圈2,在樣本擔保圈中穩定性最差,不對稱、不對等擔保關系最多,風險強度最高,一旦觸發風險,將波及擔保圈內大部分企業且風險蔓延持續時間較長,需重點關注。
(三)企業互保聯保關系網的敏感性分析
為進一步分析動態指標的影響因素,我們以違約率、杠桿率臨界值作為可變因子,對擔保圈案例進行敏感性分析。設步長為0.1,違約率、杠桿率臨界值取值范圍分別為[0,1]和[1,3],使用matlab繪制企業互保聯保風險特征動態指標的三維曲面圖。
以擔保圈2為例進行雙因子敏感性分析,其他擔保圈的風險特征動態指標整體走勢較為相似(如圖5)。可得出如下結論:
結論1:企業互保聯保風險特征的動態指標與違約率、杠桿率臨界值整體呈正相關關系,相對于杠桿率臨界值擁有更高的敏感度。由于擔保方承擔無限連帶責任,發生風險時代償率即為100%,故違約率反映了每一輪傳染中風險沖擊的大小,在杠桿率臨界值不變的前提下與擔保圈風險強度(即CI、VI)基本呈線性關系;而杠桿率臨界值與擔保圈風險強度的關系為邏輯判斷,直接決定了一輪風險傳染中擔保方的生死,進一步影響到傳染的輪數和波及范圍。隨著杠桿率臨界值的下降,觸發破產的企業增多,體現波及范圍的ID、Hz,及體現傳染輪數的RD等指標呈階梯式跳升。面對代償風險向表內負債的轉化,擔保圈內企業損失吸收作用被破壞,互保聯保關系網的穩定性趨弱,CI、VI的三維曲面圖也呈現出階梯式坡面,較違約率具有更高的敏感度。
結論2:CI、VI相對于杠桿率臨界值具有非單邊性,呈有偏分布。一方面,CI、VI具有非單邊性,存在區域極值。在經濟環境較差時,企業違約風險頻發,抗沖擊能力較弱的企業在前幾輪傳染中悉數暴露,風險快速釋放出清,擔保圈的CI、VI較低。隨著經濟回暖,企業杠桿率臨界值上升,在前幾輪傳染中部分企業未達觸發違約的杠桿臨界值,代償能力逐步消耗,風險不斷積聚,需要經過多輪傳染才能出清,此時互保聯保風險的傳染性、脆弱性均達到極值。隨著經濟持續回暖,融資環境趨于寬松,企業依靠循環融資維持流動性,市場風險偏好走強推高杠桿率臨界值,擔保圈風險被掩蓋,CI、VI下降。另一方面,CI、VI相對于杠桿率臨界值呈有偏分布,具有非對稱性。在經濟周期中,擔保圈風險將經歷一個緩慢積累到快速積聚、并在較短的時間內釋放的過程。在經濟上行或平穩運行時期,風險積聚不宜被察覺,一旦市場風險偏好轉變,風險爆發將會產生很強的破壞性。在風險出清的過程中,雖有部分企業破產退出企業互保聯保關系網,擔保圈風險的強度有所降低,但由于存活企業均面臨較為緊張的信用環境,擔保圈風險強度仍無法降低至從前(如圖6)。
結論3:CI、VI的極值點與企業規模無直接關系。由于CI、VI與違約率呈正相關關系,在各杠桿率臨界值下,當違約率達到100%時,代償產生的沖擊力度最大,故違約率極值點對于各擔保圈而言均為1,與企業規模無關。CI、VI達到極大值時各擔保圈所取得的杠桿率臨界值是傳染機制作用的結果,與企業規模無直接關系。如表4,擔保圈5(中小企業)和擔保圈6(大企業)CI、VI的極值點均為1.3,擔保圈1(大企業)和擔保圈4(中小企業)CI、VI的極值點均為1.6。
結論4:傳染輪數存在立體“金字塔”效應。在杠桿率臨界值極低時,多家企業觸及臨界值破產,在較少的輪數中即可終止傳染;隨著經濟緩慢復蘇,杠桿率臨界值略有上升,僅部分企業觸及破產警戒線,通過其互保聯保關系網逐輪傳染蔓延,此時傳染輪數出現極值;待經濟完全回暖,市場風險偏好趨強,所能容忍的杠桿率臨界值不斷放大,觸發的破產企業家數減少,傳染輪數相應減少。同理,某特定的違約率既能觸發違約和傳染,又能以較低的代償金額保持擔保圈內擔保方的適度存活率,此時傳染輪數達到極值。因此,傳染輪數相對于杠桿率臨界值、違約率均存在區域極值。同時可觀察到,雙因子的極值疊加共振,在三維曲面圖上呈現出立體“金字塔”效應。
四、幾點啟示和政策建議
借助對企業互保聯保風險特征的量化分析,我們應趨利避害,肯定互保聯保融資模式降低信息不對稱的優勢,借助其拓寬企業融資渠道,同時,結合靜態、動態、敏感性分析結論的啟示,積極管理擔保圈風險,避免誘發區域不穩定因素。
第一,企業規模并非決定互保聯保風險大小的主要因素,破除“大到不能倒”迷信,將借款人償債能力作為授信的首要考慮因素。大企業為滿足多元化發展的資金需要,往往動用各類抵質押資產獲取融資,互保聯保貸款成為其加杠桿的“最后一招”。從擔保方式看,大企業互保聯保貸款與中小企業同屬企業信用,同樣缺乏硬擔保,貸款質量劣化后處置手段有限;從風險分散效果看,大企業多為集團內互保,同質化、同源性導致風險集中度甚至高于中小企業互保聯保貸款;從借款人償債能力看,大企業存在更嚴重的過度融資問題,盲目放大杠桿開展多元化經營,資金鏈更加脆弱;從信息對稱性和再融資能力看,大企業融資渠道較廣,境內外資本市場直接融資披露的信息更多,一旦發生償付困難,市場關注度高,負面輿情擴散更快,再融資難度更大。因此,大企業互保聯保貸款作為純信用擔保融資,與中小企業相比并不存在規模優勢,大企業擔保虛化問題在經濟上行或平穩運行時期所積累的風險甚至可能遠超過中小企業。從擔保圈案例分析可知,擔保關系得當、企業融資適度,即使中小企業群體也可以構建較為穩定的互保聯保關系網。商業銀行應破除“大到不能倒”迷信,重塑市場約束和授信準入原則,回歸第一還款人的償債能力的風險管理思路,給予中小企業更加平等的融資機會。
第二,加強擔保圈風險量化管理,多視角跟蹤監測、模擬預測互保聯保風險。一是建立完備的企業信息庫是開展互保聯保風險量化管理的基礎。將企業互保聯保貸款風險監測指標體系引入實踐,需以建立完備的企業信息庫為基礎,而這正是夯實“貸款三查”制度、增強與借款企業之間信息透明度的重要手段。某些中小銀行“貸款三查”流于形式,特別是貸后檢查頻度較低,現場檢查方式較少,企業財務數據時滯較長,無法及時掌握互保聯保關系網中各家企業的經營狀況,導致擔保圈風險管理較為被動,授信客戶信息管理體系亟待完善。二是綜合運用靜態、動態分析方法,建立傳染強度、波及廣度、影響深度等多維度風險監測框架。如通過靜態分析,理清企業間擔保關系,摒除“背靠大樹好乘涼”的思維慣性,審慎對待不相稱、不對等擔保關系,從源頭上規避道德風險;再如通過動態模擬,對擔保圈實施壓力測試,多維度篩查企業風險,跟蹤監測擔保圈風險指標異動,重點關注傳染強度高、持續時間長、波及范圍廣的互保聯保授信企業及其所屬的擔保圈。三是積極開展企業互保聯保風險敏感性分析,加強企業杠桿管控。通過上述分析可知,應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優先把握杠桿率臨界值這一高敏感性影響因子進行互保聯保風險管理。經濟下行期間,擔保方執行代償的過程,即為其表外擔保向表內負債轉化、杠桿水平由當前的負債比率(Debt-to-Equity ratio)上升至潛在杠桿率的過程,而杠桿率臨界值的變動則是伴隨著金融機構風險偏好收緊逐步下降的過程。若此時市場風險偏好所決定的臨界值位于極值點附近,一旦擔保方杠桿率上升至突破臨界值極值點,擔保圈風險將以極大強度暴露,對當地企業、金融生態都將造成極為不利的影響。為避免這一情形發生,授信銀行應對企業進行風險提示,督促其有效控制杠桿水平。此外,控制杠桿水平還應注意杠桿率臨界值與違約率對于傳染輪數的疊加共振作用,避免立體“金字塔”效應作用下擔保圈風險持續傳染。
第三,擔保圈風險在經濟周期中的有偏非對稱分布加大了處置難度,遵循市場規律,及時出清問題企業,有助于增強擔保圈的穩定性。擔保圈風險在整個經濟周期中呈有偏非對稱分布,風險從緩慢積累到加速積聚,后又在相對較短時間內釋放,破壞性大,且在經濟復蘇之前風險強度無法完全消退,給擔保圈風險處置帶來了較大困難。出于維護地方金融生態和市場平穩運行的考慮,地方政府往往采用貸款平移、協調平臺代償、貸款展期等重組方式進行“保守治療”,緩釋風險。加入新的借貸主體替代不相稱擔保,通過貸款平移剪斷不對等擔保關系,雖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風險爆發過程中伴生的道德風險,但卻無法修復企業間的橫向監督約束機制,甚至可能產生借政府信用置換企業信用的尋租空間。由于地方政府介入時擔保圈風險往往已經爆發,協調可能釋放錯誤的經濟周期信號,使擔保圈風險積累的勢能無法自然釋放,一些已觸及杠桿率臨界值的問題企業無法及時出清,CI、VI逆向攀升,將加劇擔保圈的不穩定性。地方政府可借助上述指標集分析擔保圈風險特征,合理預判風險大小,因圈施策,提高風險處置的科學性。對于一些風險強度高、波及面小、傳染輪數少的擔保圈,應遵重市場規律,及時出清問題企業,以市場化手段剪除虛化的擔保關系,持續關注存活企業經營風險,盡快修復地方金融生態環境。
注釋:
①案例中6個地區的企業互保聯保關系網為擔保圈形狀,一地一圈,故此處及后文均直接稱其為擔保圈。
②該臨界值由涉貸銀行的風險偏好共同決定,具有順周期性。當市場環境較好時,企業對融資成本的上升不敏感,由于融資較為便利,即使利率較高也可以通過借新還舊方式維持資金周轉,故涉貸銀行風險偏好共同決定的杠桿率臨界值較高,企業違約概率相對較低。當市場環境較差時,涉貸銀行認為提高貸款利率無法覆蓋其所承擔的風險,抽貸、斷貸等導致企業資金難以接續,此時杠桿率臨界值較低,企業較易觸及。
參考文獻:
[1]Coase R H.The nature of the Firm[J].economica,1937,4(16):386-405.
[2]George A.Akerlof .The Market for“Lemons”: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70,84(3):488-500.
[3]Michael C.Jensen,William H.Meckling,Theory of the Firm:Managerial Behavior,Agency cost and Ownership Structure[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October,1976,V.3,No.4,305-360.
[4]J.E.Stiglitz,Andrew Weiss.Credit Rationing in Markets with Imperfect Information[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1,71(3):393-410.
[5]Banerjee A.V,Besley T.W.The Neighbors Keeper:The Design of a Credit Cooperative with Theory and a Test[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es,1994,109(2):491-515.
[6]F.Allen,D.Gale.Financial Contagion[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0,108(1).
[7]M.Richiardi,et al.The Asymmetric Effect of Diffusion Processes:Risk Sharing and Contagion[EB/OL].Http://www.laboratoriorevelli.it/pdf/wp71.pdf,2011-06-2.
[8]張樂才.企業資金擔保鏈:風險消釋、風險傳染與風險共享——基于浙江的案例研究[J].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11(10):57-65.
[9]陳少華,陳菡.我國中小企業擔保圈風險演化過程分析——基于博弈論研究視角[J].開發研究,2013(2):114-119.
[10]葛志強.聯保融資的有效邊界:威海鋼貿企業集體違約案例[J].金融發展研究,2014(5):59-62.
[11]中國人民銀行濟南分行課題組,基于合理邊界控制的擔保圈風險化解策略研究[J].金融發展研究,2015(2):54-59.
[12]徐子慧.擔保網絡與企業行為——影響機制及經濟后果研究[D].暨南大學,2018.
[13]白旭東.基于典型案例分析的擔保圈融資業務風險防范研究[D].河南科技大學,2018.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銀行南京分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