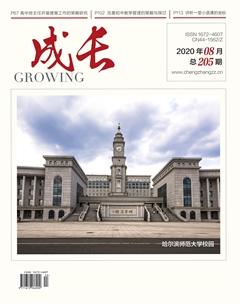未琢之美
李吳悠
唐朝末年,人們依舊贊賞著辭藻華麗的詩句,因而有些評論者談論杜甫的詩時,不免因他粗樸的詩句而輕蔑之,但我不敢茍同,我認為杜甫的詩是未經雕琢的璞玉。
誠然,杜甫的詩不同于盛唐時的細膩豐富,有的甚至十分簡單,不加修飾,但它們卻有著“無食無兒一婦人”一樣的悲憫,刻畫“三月三日天氣新”一樣的真實,又有“生女猶得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的哀婉,加上口語化的詞句,說是粗樸,也不為過。
但是粗樸并不代表著詩的好壞,嬌嫩的花朵有時是經不起風吹雨打的,它們綻放時僅僅繁華一時,凋零后就化為塵土了。有些華麗的詩詞,似牡丹,陽春四月里“花開時節動京城”,人們贊嘆它的國色天香,而到了隆冬時節,牡丹的美就如過眼云煙般消失,蒼茫大地,只有梅花還在散發著幽香。杜甫的詩正是梅花它絕不是華美艷麗的,可它雖然粗樸素凈但氣力十足,一字一詞間流露著無限的意境,再加上飽含深情的雅言,沉郁頓挫,令人心馳神往。環顧整個盛唐,又有多少詩人能用最原始、最純正的語言描繪出波瀾壯闊,深刻繾綣?
同樣是因為粗樸的語言更易深入人心,杜甫的詩千口傳誦,和藹可親的詩句無時無刻不牽動著所有人的心,拋開枷鎖與鐵鏈,用真誠的話語流露純粹的思緒。除了杜甫,誰又能做到將家鄉的語言編成千古的名言?
法國現實主義畫家米勒曾說“給藝術真正力量的,是融會于偉大情感之中的平凡”,我想現實主義詩人杜甫也是如此。杜甫同情百姓,于是,他便以百姓的名義,訴說黎民的心聲,宣泄他們的痛苦,控訴上天的不公,發出“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的悲嘆,面對蒼生的疾苦,杜甫的淚,流進詩中,化為粗樸卻有力的悲鳴。
杜甫的這份粗樸,不僅僅體現在對百姓的深情,更有對國家的深愛。
“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正在異鄉避難而十分落魄的杜甫,聽聞喜訊立馬精神抖擻、提筆賦詩,毫不吝嗇地表達了他對國家最真誠的愛,濤翻浪涌,不能平息。然這滿腔熱血的杜甫又怎能忍受得了“國破山河在”的悲痛,一生的抱負和理想石沉大海,他雖不甘心,卻依舊愛著祖國,盼望著盛世再來。于是,他對國家沉甸甸的愛,刻在了詩間,吟誦到今天。
真的,詩如玉,也如人,不要因未經雕琢而鄙棄它,不要因它與大流格格不入而嫌棄它,因為它是自然誠摯的精華。它有純潔的精神,獨特的內核,用光去照射它,會散發出別具一格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