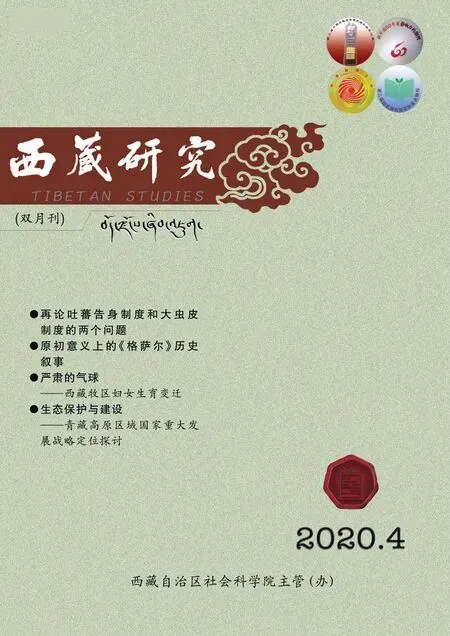清代康藏民俗的珍稀史料《漁通問俗》簡介
焦虎三
(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院(四川文化藝術學院)羌文化保護與發展研究中心,四川 綿陽 621000)
“清代藏學漢文文獻是有清一代漢藏民族交往過程中產生的有關西藏的文獻,包括史料、檔案、方志、方略、典章制度、筆記、詩歌等。其內容涉及西藏歷史、政治、宗教、民俗、語言等各個方面,具有多方面的研究價值。”[1]
有清一季,四川涉藏州縣撰史修志年代滯后,數量本又稀少,故現學界認為“從目前已知的資料來看,乾隆《打箭爐志略》是康定成書時間最早的地方志,也是四川藏區成書較早的地方志之一。”[2]至光緒時期,劉廷恕署打箭爐同知時,又纂有《打箭廳志》。這兩部志書,成為目前所見清季關于打箭爐最為重要的方志史料。但相關的其他歷史文獻,也陸續有所發現。《漁通問俗》便是清季記載打箭爐風土的珍稀文獻。該書清末由王錫祺收入《小方壺齋輿地叢鈔補編第三帙》,以后吳豐培先生又將書目收錄于《藏族史料書目舉要(漢文二)》中[3]。但學界對該書至今并無專文介紹,故筆者就其著作年代和內容試作簡析,并附錄該書點校全本于文后。
一、《漁通問俗》的著述年代等初考
《漁通問俗》共1卷。關于其作者,王錫祺編錄時標注“闕名”,此書凡2133字,僅從這些短小的文字來推測作者,幾無可能。書中言“自我〇朝歸化后,〇〇皇上深仁厚澤,恩普四裔,柔遠之道,無后不至。特設駐藏大臣幫辦大臣,督同番王、土官綏輯治各臺站”,作者的道里行程為省城至臨邛、雅州,再經爐城至后藏,該書行旅雜記的性質明顯,尤打箭爐記載最詳。過“遮多”(折多山)經日地、巴塘、章谷、里塘、木坪、倬司甲、哈爾巴、瞻對、察木眵(察木多)各臺站至后藏各程站,記述簡略,故推測作者應為駐藏幫辦大臣的隨員,書為隨駐藏幫辦大臣入藏時沿途偶記,但確切的作者,在無更多史料發掘與印證前,確難辨定。
《漁通問俗》的著述年代,書中也無明識。只是記“瀘定橋”一節,并無實錄“御制瀘定橋碑”一事,該書又云瀘定橋“長百丈余,懸空高數百丈”,而《御制瀘定橋碑記》(以下稱《碑記》)明顯有載“橋東西長三十一丈一尺,寬九尺”[4],清季諸多游歷之著,至瀘定橋時,或記“御制瀘定橋碑”一事;或引《碑記》相關數據。如《藏程紀略》記“瀘定橋橋高十余丈,長數百步,兩岸建亭閣,用大鐵繩九條”[5];《衛藏通志》記“瀘定橋……以鐵索,行橋上。橋長三十一丈一尺,寬九尺,施索九條,覆板于其上”[6];《西征日記》云“下輿過鐵索橋。橋建于康熙四十年辛已,以巨鐵索九條,長三十一丈余”[7],這是文中采用了《碑記》中數據的例證。又如《定藏紀程》、乾隆《雅州府志》與乾隆《打箭爐志略》,均明文記有“河邊立有御制碑文”[8]或“奉旨建橋”[9],這是文中實錄了“御制瀘定橋碑”的史事。而《漁通問俗》兩者皆無,可見作者過橋時,“御制瀘定橋碑”并未有建。瀘定橋于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四月投入使用,《碑記》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二月初十由四川巡撫能泰、提督岳升龍所立。故《漁通問俗》的著述年代一種可能是在康熙四十五年四月至康熙四十八年年初之間。
另一種年代推測在于對文中“(我朝)特設駐藏大臣幫辦大臣”的解讀。眾所周知,“欽差駐藏辦事大臣”與其副職“幫辦大臣”于雍正五年(1727年)始置。文中專言“我朝特設”,語含初設之意,故其著述年代應在1727年后不久。
第三種年代推測,其一源于文中所記駐爐官員設有“茶課委員一”,爐城在清代素為漢藏“茶馬互市”的中心城鎮,也為漢藏貿易的總匯之處,依《打箭廳志·茶政》所記,“光緒七年(1881年)總督部堂丁奏明改設茶關委員征收”,故打箭爐“茶課委員”的設置,應于光緒七年始;其二,書中記有“爐城四十八家鍋莊”,考清季康定鍋莊的發展歷史以及相關記錄,康定鍋莊明顯存在一個由少至多的發展過程,“康定鍋莊發端于明末清初,成型與完善于雍乾時期,清末至民國初年進入其壯大、繁榮期。”[10]清早、中期多記為“十三家”左右,至清末方有“四十八家”的史載。如:《西藏紀述》載“明正……轄正副安撫司、土千百戶五十五戶,十三鍋莊頭目一十三名”[11],《康輶紀行》云“宣撫司奢札察巴已故,乏嗣,其妻工喀承襲。后遂傳其外孫甲勒參達爾結,所轄十三莊蕃民”[12],《大清一統志》卷360《雅州府志》有記明正土司“管轄十五鍋莊番民并新附各土司及五十六土千戶”[13],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劉廷恕署打箭爐同知,其編纂《打箭廳志》時仍記“今之明正土司地,管轄爐之十三鍋莊番民,約束新附土司及土、千百戶”,至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有泰在《駐藏日記》中才言“鍋莊有四十八處”[14](見表1)。故據此推測,《漁通問俗》成書年代不早于1903年。

表1:清季文獻所載康定鍋莊數目及年代對照表
客觀而言,這三種年代中,筆者現傾向于第三種,認為《漁通問俗》成書年代不早于光緒二十九年,年代上應晚于《打箭廳志》,但有清一代,因系統而完整記錄爐城風土俗為的歷史文獻較少,而《漁通問俗》專事記錄爐城的風俗,故仍為清季打箭爐珍稀的藏學漢文歷史文獻之一。
二、《漁通問俗》的內容簡介
《漁通問俗》實為行旅雜記,其所記均為作者親歷親見,因其實錄,故傳統志書中的山川、形勢、關隘、城池、衙署、茶政、風俗、兵制、土司、程站等均或多或少有所涉及,特別是社會經濟與民俗文化,記載尤詳,故其史料價值也彌足珍貴,為研究清季打箭爐與康藏社會經濟、政治軍事、文化風俗、歷史地理提供了一手的資料。
《漁通問俗》主線為由蜀進藏路程。所記由成都南關始,涉及地點依次為:臨邛、雅州、金雞關、佛鴉嶺、滎經縣、小關山、大相嶺、清溪縣、瀘定橋、瓦司溝、漁通、爐城、遮多山、日地、巴塘、章谷、里塘、木坪、倬司甲、哈爾巴、瞻對各臺站,終于駐藏幫辦大臣駐地察木多。全書可分為省南關至爐城、爐城見聞、爐城至察木多3部分。其中大半篇幅為打箭爐見聞,計1549字,占全書篇幅73%。
(一)關于自然地理和歷史地理的情況
該書記由川入藏,沿途主要程站的山川地貌均有記錄,如記“南路邊茶”滎經縣至大相嶺間“山川精景物豁然一新,矚目闊即見萬峰環拱,千瀾奔流,濕云對樹。旭日晦光間,路則山腰峻絕,一線羊腸”;記折多山“山下堅冰四時不解,頗礙行旅。山為積雪凝結而成,年復一年,倍增高大”。記錄爐城地貌與氣候“有寒無暑,年如二八月,四季均有雪至。已午便起罡風,搖山撼屋,四圍皆山,林木最少,高下禿然”。歷史地理方面,記瀘水為“昔武鄉侯所渡者也”等。
(二)關于政治與軍事的情況
該書對清季治藏方略、打箭爐衙署與土司有所反映,如記“皇上深仁厚澤,恩普四裔,柔遠之道,無后不至。特設駐藏大臣幫辦大臣,督同番王、土官綏輯治各臺站,要隘設同知一員,與土司分理民事。更設防營、丁勇,核其地里之繁簡,駐札武弁,協同巡守,三年一更換。”打箭爐衙署為“駐爐官員協鎮一,部司一,城守二,撫民同知一,照磨一,茶課委員一”;記土司為“蠻官明正土司一,紅頂花翎,朝靴蟒服,衙署壯麗,近與漢官抗禮,治下有頭人二,即渠耳目之官。例無生殺之權。小罪罰牛數頭;大罪青杖數百;極惡不赦,即以權杖斃之。”
(三)關于康藏經濟財政的情況
該書對康藏經濟的記載較多,如記漁通(魚通)的淘金業,瓦司溝(瓦斯溝)“為漁通口徑。山皆產金礦,芽長茁者為飛瀑沖斷,或如瓜子;或如莞豆,流入溪澗石畔。漁通娃拾之亦知貨售,故吳、楚金客旅于此處,專收細金。約有數十字號長年業此,獲利頗厚。”書中對于打箭爐經濟,著墨最多,主要有以下幾點:
1.記錄打箭爐經濟總況。如“蠻、漢交易界以爐城為止。近時人煙稠密,漸習繁華者,實因互市之故也。”在商幫方面,“城以內所駐商賈惟秦、晉兩幫最夥,其久歷族處,能操番語者亦眾。”
2.記錄了打箭爐的財政(茶政、稅課)等要情。如“城以內,另設百貨厘卡,歸地方官督收,為數亦鉅。”厘稅方面,“每貨抵爐,先向厘關,照章納稅。”
3.記錄打箭爐的“茶馬互市”。“每燉酥油,非用中國所產之茶不可。故雅州六屬之茶專銷西藏。數有額引,六屬別無土產,亦專藉茶務以養民生……按:茶務一宗,照引收稅,每年納有千余萬金之多。向以此金撥充臺站餉需。”
4.詳盡記錄了打箭爐“茶馬互市”“鍋莊”交易的情景。其所記年代雖較晚,但比早期的一批文獻,如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成書的《隴蜀余聞》、雍正十一年(1733年)刊刻的《四川通志》、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成書的《西藏紀游》等,所述內容更詳,也更加客觀,是目前所見“康定四十八家鍋莊”較早的確切記錄。“女子能操漢音握籌,日出與商賈交易,穎繳過于男子所居之舍,名曰‘鍋莊’。(止惟在樓上,其樓下則多荒敝,用以飼牛、犬,堆粗貨而已)。爐城四十八家均如中華之客棧,出藏蠻子均以牦牛駝其土產寶貨至爐,即藉各鍋莊而居停,獨鍋莊主人經紀互市。藏貨售貲,大半購茶,主人按例抽用,頗類牙行。”
5.記錄了打箭爐的物價情況。“一切服、食、器用皆仰給于內地,非藉長途夫背負肩掮,爬山越嶺不能運至。米珠薪桂,不言可知矣。”
6.記錄了康藏用于易茶的商品。“(打箭爐)此處土產最富實,寶貨亦多。上則珊瑚、瑪瑙、鹿茸、麝香、蟲草、貝母、琥珀、牛黃、沉香、阿魏、桑寄生、老鸛草;次則狐羊皮、猞猁猻、藏片綢段、氈毯等類。”
7.記錄了打箭爐的物產。如“沿山均產金、銀”與“附近山麓多產硃砂、雄黃、蟲草、貝母等藥”。
(四)關于康藏民俗文化的記錄
《漁通問俗》以“問俗”命名其書,故以訪問并記錄風俗為該書重心。其對于康藏民俗文化的記錄最為鮮活,其內容廣涉服飾、飲食、居住、信仰、藝術諸方面。
1.服飾文化方面,詳記了打箭爐藏族男、女的服飾。“男蠻身驅高大,官竅昂藏,左耳墜金環,如斗大,下絡珊瑚珠一,重約二兩。有奇發辮盤頭以五色寶玉,琢成大珠球,鏨眼于中,實十余枚于辮根,項際掛頂大珊瑚一串,披無面老羊裘,四圍巾底用虎豹皮纏之,足登紅色皮靴;蠻女則身材窈窕,多妍少媸,語音如驚燕,媚態可人,不椎髻,不裹足,發分雙辮札以彩繩。披衩衫,腰支纖細,足下靴堆云蝴蝶等。花衣料均駝羊籌毛織成,不拘男女,喇嘛俱不著袴。”
2.飲食文化方面,概記了酥油茶與糌粑的制作過程。“飲食以牛、羊乳煎提精華,燉成酥油。傍山自種短穗、胡麥,和面為劑,命名曰‘糌粑’。勿論貴賤僧俗,悉以此二物為養身之需。余惟嗜酒,喜鼻煙。”
3.居住文化方面,其涉地甚廣。如記魚通一帶四種番夷錯居,“率皆穴處”;由折多山而進,“蠻皆洞居,旅無傳舍,入藏官民必攜牛皮帳棚,按站野宿。凡值日地、巴塘、章谷、里塘、木坪、倬司甲、哈爾巴、瞻對、察木眵各臺站,始有城垣,官府板屋。”
4.信仰文化方面,以打箭爐考察為中心。如記打箭爐民眾“其性好佛,無論男女長幼,行止坐臥,其口中‘咕咕嚕嚕’,不少休息,是為唪經”;記其地的寺廟“城內有大、小喇嘛寺各一。大者容三四千僧;小者一千余僧。寺建殿宇四五重,高大壯觀,鑄大小銅佛各千百列龕供奉。每重建層樓,排斗室如蜂房。一室容一僧,與今之火輪船艙差等。經梵皆番字,無卷帙,以黃紗布刊印,疊單張高數寸,夾以檀木板,捆成軸。經架滿殿宇,佈藏數目不可核計,‘恒河沙’借喻也。”
5.文化藝術方面,該書詳記了打箭爐佛誕會期“開寺跳神”的經過,是清季關于藏族“羌姆”與“酥油花”較早的漢文文獻史料。書中所記“羌姆”活動時間從晝至夜,有情有景,有對“羌姆”法器、面具的記錄;有對舞蹈、音樂的形象描繪,鮮活生動,極具文學的感染力。
其他如交通、民族、程站等情況,是書也有涉獵。
三、余論
由于書中歷史局限性,《漁通問俗》作者對少數民族有所偏見,言詞也頗有隅曲甚至歪曲之處,但因所記均為作者親歷之事,對于我們今天研究清代康藏的社會歷史與文化風俗,仍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是書特別對于打箭爐經濟與民俗,記載尤詳,對于我們今天考證“南路邊茶”的諸多史實,也提供了一批可資信賴的史料。
筆者撰此薄文,也希望學界借此更加重視諸如《漁通問俗》等游記類、雜記類藏學漢文文獻的搜集與研究,以期推進康藏地區歷史文化研究的深入與發展。
附錄:
漁通問俗(1)本文錄自《小方壺齋輿地叢鈔補編第三帙》,焦虎三點校,文中〇〇為原書避諱,[]為點校者勘誤,□為無法辨析而缺字。
闕名
漁通者,古國名地。距離蜀省會主西南千里。附近有城,曰“打箭爐”,即今西藏出入咽喉。
計由蜀晉[進]藏應經道路,出省南關兩站至臨邛,又兩站至雅州。州為建南觀察駐節之所。沿途小山排關,不礙行程。再前度金雞關,越佛鴉嶺,下嶺至滎經縣界,而山川精景物豁然一新,矚目闊即見萬峰環拱,千瀾奔流,濕云對樹。旭日晦光間,路則山腰峻絕,一線羊腸。乖輿則轅首高瞻,雙牽馬勒度小關山,越大相嶺。過絕頂,宜蕭靜,或稍喧嗓即有黑云一片旋轉而來,如卵冰雹當頭墜打。嶺下忽開平陽,地形似龜就而砌城,即清溪縣也。
由山麓分道,左則穿城達建昌鎮,歸寧遠府屬;右從牛市坡進西藏六站。至瀘定橋,以鐵索為之,上鋪薄板,長百丈余,懸空高數百丈。下即瀘水,昔武鄉侯所渡者也。建昌接壤邊陲,四種番夷錯居:曰“苗”;曰“猺”;曰“猓”;曰“狢”,率皆穴處。漁通則統一為“蠻僧”、為“喇嘛”。建南所屬橫直千余里,惟建昌產稻谷,其他則只產苞谷,即芉麥也。
過瀘定橋一站,名“瓦司溝”,為漁通口徑。山皆產金礦,芽長茁者為飛瀑沖斷,或如瓜子;或如莞豆,流入溪澗石畔。漁通娃拾之亦知貨售,故吳、楚金客旅于此處,專收細金。約有數十字號長年業此,獲利頗厚。
再一站始抵爐城。距后藏尚有八十余站。內止一徑可通滇省,城內居民大半蠻子,然喇嘛之數倍于俗人。天氣有寒無暑,年如二八月,四季均有雪至。已午便起罡風,搖山撼屋,四圍皆山,林木最少,高下禿然。蓋爐城本為蠻煙瘴雨之鄉,自我〇朝歸化后,〇〇皇上深仁厚澤,恩普四裔,柔遠之道,無后不至。特設駐藏大臣幫辦大臣,督同番王、土官綏輯治各臺站,要隘設同知一員,與土司分理民事。更設防營、丁勇,核其地里之繁簡,駐札武弁,協同巡守,三年一更換。臺站人員因公往來,絡繹不絕。昔時偏僻之地,今日遂為沖要之區矣。
此處土產最富實,寶貨亦多。上則珊瑚、瑪瑙、鹿茸、麝香、蟲草、貝母、琥珀、牛黃、沉香、阿魏、桑寄生、老鸛草;次則狐羊皮、猞猁猻、藏片綢段[緞]、氈毯等類。沿山均產金、銀,蠻王向禁開礦。自設漢官化導而后,風俗漸改,應接多禮。所在土官職皆世襲,按所轄萬、千、百戶以分,大小僉由中國〇〇大皇帝諭旨冊封。
民間貧富以畜牛多寡論。飲食以牛、羊乳煎提精華,燉成酥油。傍山自種短穗、胡麥,和面為劑,命名曰“糌粑”。勿論貴賤僧俗,悉以此二物為養身之需。余惟嗜酒,喜鼻煙。每燉酥油,非用中國所產之茶不可。故雅州六屬之茶專銷西藏。數有額引,六屬別無土產,亦專藉茶務以養民生。然蠻、漢交易界以爐城為止。近時人煙稠密,漸習繁華者,實因互市之故也。按:茶務一宗,照引收稅,每年納有千余萬金之多。向以此金撥充臺站餉需。城以內,另設百貨厘卡,歸地方官督收,為數亦鉅。
駐爐官員協鎮一,部司一,城守二,撫民同知一,照磨一,茶課委員一。蠻官明正土司一,紅頂花翎,朝靴蟒服,衙署壯麗,近與漢官抗禮,治下有頭人二,即渠耳目之官。例無生殺之權。小罪罰牛數頭;大罪青杖數百;極惡不赦,即以權杖斃之。
男蠻身驅高大,官竅昂藏,左耳墜金環,如斗大,下絡珊瑚珠一,重約二兩。有奇發辮盤頭以五色寶玉,琢成大珠球,鏨眼于中,實十余枚于辮根,項際掛頂大珊瑚一串,披無面老羊裘,四圍巾底用虎豹皮纏之,足登紅色皮靴;蠻女則身材窈窕,多妍少媸,語音如驚燕,媚態可人,不椎髻,不裹足,發分雙辮札以彩繩。披衩衫,腰支纖細,足下靴堆云蝴蝶等。花衣料均駝羊籌毛織成,不拘男女,喇嘛俱不著袴。風俗貴女賤男,男子司撫嬰、守戶、理炊各事,女子能操漢音握籌,日出與商賈交易,穎繳過于男子所居之舍,名曰“鍋莊”。□止惟在樓上,其樓下則多荒敝,用以飼牛、犬,堆粗貨而已。爐城四十八家均如中華之客棧,出藏蠻子均以牦牛駝其土產、寶貨至爐,即藉各鍋莊而居停,獨鍋莊主人經紀互市。藏貨售貲,大半購茶,主人按例抽用,頗類牙行。然每貨抵爐,先向厘關,照章納稅。使用銅錢最稀,尚男女圖花邊銀洋,大者□三錢二分;次一錢六、一錢二至八分、四分為□;余則散銀。城以內所駐商賈惟秦、晉兩幫最夥,其久歷族處,能操番語者亦眾。一切服、食、器用皆仰給于內地,非藉長途夫背負肩掮,爬山越嶺不能運至。米珠薪桂,不言可知矣。
爐城三門,向無北關。穿城一澗,南北涌流,水聲洶洶,晝夜聒耳。附近山麓多產硃砂、雄黃、蟲草、貝母等藥,數處溫泉。但逢月夜,蠻家不分男女,往浴其中,名曰“泡水”。并挈所歡。漢人同浴不禁。有“笑貧不笑淫”俗習。今雖粗學漢人婚嫁之禮,而野合宵奔者仍復不少。
其性好佛,無論男女長幼,行止坐臥,其口中“咕咕嚕嚕”,不少休息,是為“唪經”。城內有大、小喇嘛寺各一。大者容三四千僧;小者一千余僧。寺建殿宇四五重,高大壯觀,鑄大小銅佛各千百列龕供奉。每重建層樓,排斗室如蜂房。一室容一僧,與今之火輪船艙差等。經梵皆番字,無卷帙,以黃紗布刊印,疊單張高數寸,夾以檀木板,捆成軸。經架滿殿宇,佈藏數目不可核計,“恒河沙”借喻也。值佛誕會期,開寺跳神,山門外平地寬逾百畝園地,有坐樓中豎幡竿掛龍、鳳幢巾荒,縛佛脾[牌]于上。萬千僧眾均用各禽獸假面具、籠首服。云帳□裳,鳳帶飄飖。按部伍立,手執塵尾,中設筐,大扁鼓數百面。以乙安錘擊扣雜銅鼓數面,肩抬丈長銅笳一對,以大力僧吹之,聲如鶴唳,鼓聲相應,皆能中節,毫不紊亂。僧聽鼓動,群舞如一盤旋。膜拜口宣佛號,其音難辨何辭。小喇嘛百余,盡裝虎、豹、麋、鹿等形,兩手貼地代運。徵逐場面,肖像如生。至夜燃酥油燈數千盞,輝煌燦目。以糌粑面掐各種佛像,絡金花架代龕供,坐樓一周。先期即請合城官員安座,樓中布素筵享客。命婦夫人另設專座,垂簾而觀。誠勝會也!會竣,報以金錢,主僧則怒形于色;賞以茶包,則喜謝不遑。
習俗民間生子數多者,例以一子承禋祀;以一子赴土司衙門當差;其余盡驅入寺剃度披緇矣。所謂“僧倍于俗”,蓋由此也。
按道里行程,由爐起馬四十里外,地敝風勁,迎面高峰,粉妝玉琢,名曰“遮多”[折多]。山下堅冰四時不解,頗礙行旅。山為積雪凝結而成,年復一年,倍增高大。雖距爐城一站,宛然屏障焉。由漸而進,蠻皆洞居,旅無傳舍,入藏官民必攜牛皮帳棚,按站野宿。凡值日地、巴塘、章谷、里塘、木坪、倬司甲、哈爾巴、瞻對、察木眵[多]各臺站,始有城垣,官府板屋,直至后藏活佛所居之地。駐藏大臣駐節于此,則風景大異,土產亦饒,百谷、百果咸備,起居、飲食,亦均安善,不似沿途瘠苦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