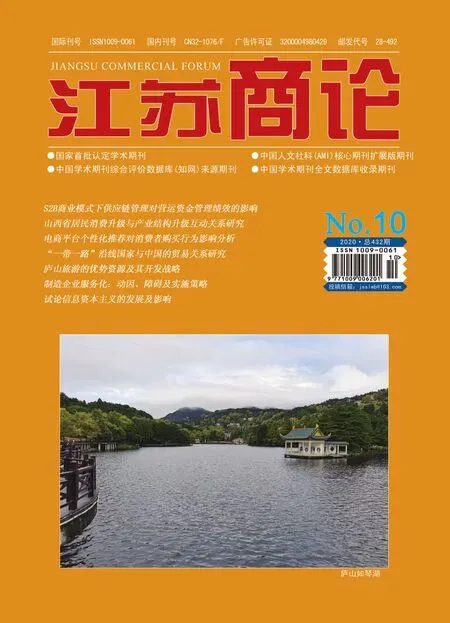境外資本“迂回投資”并購我國科創企業的財稅法律問題研究
——以海外N 公司并購為例
鄔展霞,鄭丹娜
(上海對外經貿大學,上海201620;上海海展廣告工程有限公司,上海201702)
公司國際化發展戰略是驅動公司進行跨國并購的根本原因(嚴鐘,2013)。 相比于綠地投資1綠地投資又名創建投資,指海外投資主體在東道國境內依法申請設立的企業。,跨境并購通過控制被兼并企業資源, 能快速擴大國際生產和國際市場,實現組織產業鏈的延伸,已成為當前跨國公司全球化戰略的重要內容。 我國健康有序的社會氛圍、 日益發展的科技水平、 高度自由的投資環境, 正在不斷地吸引海外資本以并購方式進入國內市場, 目前已有諸多本土知名企業和品牌被外資收購。 不可忽視的是,外資并購可以為我國企業提供資金支持、技術支持并帶來先進的管理經驗,但也會帶來自主品牌消亡的威脅。 在海外,螞蟻金服(Ant Financial)收購速匯金、中國私募公司(Canyon Bridge)收購Lattice 半導體相繼被美國否決已經釋放出強烈的信號,對外開放和國家安全之間需要某種平衡。 政府對外資并購的干預變得格外重要(李宇立,2019),而財稅法律制度對此亦需要做出正確的呼應。
一、外資并購與“迂回投資”
企業并購已成為我國資本市場中重要的經濟活動。 據普華永道《2019 中國地區并購回顧與2020展望》統計,2019 年外資入境并購創歷史紀錄,工業領域的并購脫穎而出,特別活躍。 在人民幣企穩、跨境合作大趨勢不可逆轉的背景下外資并購正在迅猛增長2數據來源:普華永道發布的《2019 中國地區并購回顧與2020 展望》報告。。
“并購” 一詞在我國不存在統一的定義。 我國《公司法》僅規定了“公司合并、分立、增資、減資”;《國有資產評估管理辦法施行細則》定義了“企業兼并”;2008 年中國證監會發布的《上市公司企業并購重組財務顧問業務管理辦法》用列舉法說明了并購的內涵。 學術界普遍認為,企業并購是一家企業通過一定的合法方式和手段獲得另一家企業的全部或部分股份、資產以達到控制目標企業的行為。 具體而言有兩種類型:(1)兼并。 指兩家及兩家以上的企業,合并后只有一家企業成立,其他參與企業均注銷;原參與企業的權利和義務均由合并后的企業承繼。 此類合并又可以根據原企業是否存續劃分為新設合并和吸收合并。(2)收購。指某一家企業以持有另一家企業的股權或資產為目的,用現金等資產購買目標企業的資產或股權的行為,此模式下收購后雙方企業均存在。
根據我國商務部《外國投資者并購境內企業的規定》第2 條,外資并購是指外國投資者協議購買境內非外商投資企業的股權或認購境內公司的增資(即“股權并購3《外國投資者并購境內企業暫行規定》第1 條。”);或外國投資者(或通過設立外商投資企業),協議購買境內企業資產且運營該資產; 或外國投資者協議購買境內企業資產并以此設立外商投資企業(即“資產并購”)。本文研究采用了股權并購與資產并購這一分類。
與所有的并購相同,外資并購的實質是控制目標企業的資源以便快速進入中國市場。 離岸金融市場在外資并購中發揮著重要的樞紐作用,一些企業為利用稅收優惠措施會選擇在開曼群島、英屬維京群島等離岸金融中心注冊公司,然后在國內進行并購,形成境外資本的“迂回投資”購并模式(計啟迪等,2020)。
二、外資并購的稅法規定
Alfons J. Weichenrieder(2006)的研究顯示,企業在進行并購決策時會基于稅收影響的基礎之上,合理合法地進行稅收籌劃。 研究稅收法規對于并購模式的選擇至關重要。
(一)股權并購模式下的稅收規定
股權并購模式具體可分為“存量轉讓”和“增資并購”兩大類。
1.存量轉讓型。這是指外國投資企業或個人(下稱外國投資者)直接購買境內企業股東原有的股權或者股份,此交易僅涉及持有人之間的轉讓,目標公司的股份總額不發生變化。 股權出讓方獲得的股權出售收益 (即外國投資者所支付的并購對價)為應稅所得,屬于所得稅的征稅對象。 根據我國稅法的有關規定, 出讓方因所屬不同類別承擔不同稅率:(1)當該出讓方為法人時,上述收益適用出讓方的企業所得稅稅率,一般企業為25%;高新技術或先進技術服務業為15%。 (2)當出讓方為境內外個人時,上述財產轉讓所得繳納20%的個人所得稅4我國沒有資本利得稅,但有證券投資收益稅,即對從事證券投資所獲得的利息、股息、紅利收入的征稅。。(3)當出讓方為外國企業而未在我國境內設立常設機構時,則適用10%的預提稅稅率5預提所得稅,簡稱預提稅,是指預先扣繳的所得稅。它不是一個稅種,而是對這種源泉扣繳的所得稅的習慣叫法。我國稅法第三條和實施條例第九十一條規定,外國企業在中國境內未設立機構、場所,而有取得的來源于中國境內的利潤(股息、紅利)、利息、租金、特許權使用費和其他所得,或者雖設立機構、場所,但上述所得與其機構、場所沒有實際聯系的,都應當繳納10%所得稅。。 另外,出讓方與受讓方還需要各自承擔0.05%的印花稅。此時,外國投資者作為受讓方需交納0.05%的印花稅。 表1是“存量轉讓”模式所涉及的稅目及稅率。 目標公司由內資公司轉變為外商投資企業時,可以享受相應的稅收優惠。

表1 存量轉讓模式下適用稅制
2.增資并購型。這是指外國投資者出資認購目標公司增資或者增發的股份, 此交易不會對原始股東股份產生影響。 這一模式下的增資行為尚不涉及境內稅法的投資所得,對外國投資方無任何稅務影響。
(二)資產并購模式下的稅法規定
資產并購模式下,目標公司為出讓方,其所獲得的資產出售收益(即外國投資者所支付的并購對價)為應稅所得。 與存量轉讓型一樣,因出讓方所屬不同類別承擔不同稅率,資產轉讓方同時需要按照視同銷售繳納增值稅,印花稅同存量轉讓型。 出讓方涉及房地產的,則需繳納增值稅、土地增值稅。 外國投資者作為受讓方,主要應考慮交易稅中的契稅和印花稅。 企業有尚處于監管期的進口設備時需要補交關稅和進口環節增值稅。 表2 是“資產并購”模式所涉及的稅目及稅率。 資產并購模式稅收規定的復雜性遠遠超過股權并購模式。 因此,外資并購大多通過股權并購完成。
(三)企業所得稅關于企業重組的特別規定
根據我國稅法規則,一般情形下,企業重組時需以公允價值為計稅基礎確定被合并企業的資產負債。 公允價值與原賬面價值的增值,為被并購企業的資產轉讓所得計算交納正常的企業所得稅。 但在特殊情形下,被收購、合并或分立部分的資產或股權比例符合規定的比例,如股權收購比例不低于50%, 則可以按照賬面價值確定被合并企業的資產負債,此時被并企業的資產轉讓所得為零,不需要交納企業所得稅。
(四)內資企業轉變為外商投資企業時的稅收待遇界定問題

表2 資產并購模式下適用稅制 (單位:%)
外資并購在法律后果上是將內資企業變更為外商投資企業,此種方式必然產生對諸多“歷史遺留問題”的爭議。 國家稅務總局關于外資并購出臺了系列規定:由于發生外資并購而由內資企業變更為外商投資企業的,若外資比例超過25%,則該變更后的公司可以視作外商投資公司,適用相關財稅法規。 變更設立前企業累計發生的尚未彌補的經營虧損,可在稅法規定的5 年虧損彌補年限的剩余年限內,由變更設立的外商投資企業延續彌補6國家稅務總局于2003 年5 月發布的《關于外國投資者并購境內企業股權有關稅收問題的通知》(國稅發2003(60)號)。。
三、外資并購的會計準則規定
與其他法律的規定不同, 從會計準則的角度,形成一項合并業務的實質是“形成控制”,并對“形成控制”給出了嚴格的判斷條件:基于股份、基于表決權、人事任免權等。 未“形成控制”的業務,則只是屬于正常交易的投資業務,如長期股權投資或資產購買。
并購方會計處理的基本方法分為購買法(Purchase Method)、權益結合法(Equity Method)。由于權益集合法容易通過并購行為直接增加合并方的利潤從而引致財務舞弊行為,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已經不允許采用權益結合法,只能選擇購買法。 在歐洲市場上,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IASC)在2004 年發布的企業合并準則中明確規定禁止適用權益結合法。 購買法是目前歐美并購市場上唯一適用的會計方法。 我國關于企業合并的會計準則(CAS20)中仍然保留這兩種方法,并明確規定同一控制下的企業合并適用權益結合法進行會計核算;非同一控制下的企業合并采用購買法進行會計核算7《會計準則第20 號——企業合并》中指出,參與合并的企業在合并前后均受同一方或相同的多方最終控制且該控制并非暫時性的,為同一控制下的企業合并;參與合并的各方在合并前后不受同一方或相同的多方最終控制的,為非同一控制下的企業合并。。 不滿足同一控制的情形,需要采用購買法。 但這一規定僅影響合并方的賬務處理。
對于合并后存續的目標企業,財務上表現為接受一項常規投資,因此會有資產和所有者權益(數值上等于凈資產) 的同時增加。國內外很多研究認為,外資并購會對被并購企業產生正面效應,如Bae(2002)等發現來自股市短期的財富效應,其會計上的主要原因就是因為每股凈資產的上升帶來每股市價的上升所致。
四、境外N 公司“迂回投資”并購境內M 科技公司案例分析
(一)并購交易背景
N 是境外全球最大的高端重型裝備企業,M 科技有限公司(簡稱“M”)是中國國內主要的裝備科技企業,適用稅率為15%。 N 公司擬收購M 除廠房和土地以外的全部資產8廠房和土地問題在中國法律制度下比較復雜,一般并購不會觸及。,包括人員、設備、知識產權(包括商標、專利等)。 M 的歷史遺留問題較多,在資產收購模式下面臨較多稅負,特別是房地產增值帶來的稅負。 N 公司只能通過股權模式,實現對M 生產能力的收購。 雙方經過協商,將M 公司的估值確定為4 億元人民幣,并以現金支付合并對價。
(二)財稅法律約束下的交易架構設計選擇
前述分析,合并會計準則主要影響合并方的會計處理,基本不存在制度障礙;故稅法規定是交易模式選取的主要考慮因素。
1.M 分立新公司的雙股權交易模式:首先,原M存續并分立成為老M 和新M, 原M 廠房和土地之外的所有資產全部納入新M。 其次由M 的大股東S在稅源地設立SPV1 和SPV2,分別從原股東手中受讓新M 的40%和60%股權。最后N 受讓SPV2 持有的新M60%股權(圖1)。
此交易架構的涉稅法規包括:(1)M 分立新M 的過程中符合企業所得稅關于資產重組的規定,原M 需要確認資產轉讓所得繳納企業所得稅(稅率為15%)、印花稅(稅率為3‰或按件5 元)。 (2)新M 的股東向SPV1 轉讓股份,需繳納個人所得稅9個人轉讓金融產品不屬于增值稅增稅范圍。。 (3)SPV2 向N轉讓60%股權時應按照企業重組的規定支付企業所得稅10轉讓非上市公司股權不屬于增值稅征稅范圍。。 此交易下無須繳納契稅、增值稅。

圖1 分立并購交易架構

圖2 新設并購模式交易架構
2.原M 以資產投資,共同設立新M 模式(圖2)。如圖2, 原M 直接以部分非不動產投資設立新M,其余操作同上。 原M 和新M 都應屬于增值稅納稅人。 原M 將企業的存貨、固定資產轉讓給受讓方新M,正常情況下應視同銷售貨物的行為,計算繳納增值稅(稅率為2%或13%);根據稅法11《關于納稅人資產重組有關增值稅問題的公告》(國家稅務總局公告2011 年第13 號)規定,納稅人在資產重組過程中,通過合并、分立、出售、置換等方式,將全部或部分實物資產以及相關聯的債權、債務和勞動力一并轉讓給其他單位和個人,不屬于增值稅的征稅范圍,其中涉及的貨物轉讓,不征收增值稅。,如果資產并購中目標公司(轉讓方)轉讓的資產不僅包括實物資產, 還包括與實物資產相關聯的專利、 技術、債權、債務和勞動力,此時目標公司出售的是業務組合,不是資產組合,不屬于增值稅的征稅范圍。 交易過程另需繳納印花稅(稅率為3‰)、企業所得稅(稅率為15%,符合條件可減免)等。
3.新M 收購原M 部分資產模式。M 原大股S 設立特殊目的實體,并以此投資設立新M 公司;新M與原M 交易取得其除廠房、土地之外的資產,最后由新M 與N 公司進行外資并購交易, 現金收購60%的股份。 此種情況下,原M 需要就資產轉讓所得繳納企業所得稅(稅率為15%, 符合條件可減免)、印花稅 (稅率為3‰或按件5 元);無須繳納契稅、增值稅(圖3)。
上述三種交易模式下稅負對比見表3。 表3 表明,第二、三種架構模式下稅負最低;同時,第三種模式下只需要設立一家SPV 即可達到目的,既簡化了并購流程也節省了并購費用,因此第三種由新公司收購M 資產的模式并購成本最低。

圖3 收購模式交易架構
五、結論和建議
(一)結論
根據上述境外資本“迂回投資”收購境內科創企業的交易構架設計案例推演,可得到如下結論:
1.境外資本“迂回投資”的交易模式旨在回避稅收監管。 很多研究認為,跨國并購中對目標企業的股權選擇是并購整合的關鍵決策 (趙毅和喬朋華,2018;劉煜和王疆,2019 等),合理的股權設計可以提高整合效率(Contractor et al,2014)。 然而上述監管案例可以看出,在中國,外資并購模式的選擇、股權的設計與稅收制度緊密相關。2008 年稅制改革以來,為吸引外資,鼓勵外資并購,我國已經出臺多項稅收優惠。 如關于增值稅在資產與負債、勞動力整體轉移并購中的免稅優惠,企業所得稅關于股權收購達到規定份額的免稅規定,極大地減少了企業合并中的稅負。

表3 三種模式下外資收購的稅負對比12 稅率均參考增值稅最新規定,即2019 年4 月1 日的下調規定。
案例中第三種模式下,通過“迂回投資”的股權交易設計,既享受了“非上市公司股權交易免稅”的增值稅稅收優惠,又通過特殊目的實體100%持股的新M 收購原M 的50%以上資產滿足了企業所得稅關于企業重組稅收優惠所要求的資產持有要求13參見《企業所得稅法》關于企業重組的免稅要求。。 可以說,本案例的交易模式選擇完全是當前企業并購稅收制度下的產物。 雖然近年來為響應BEPS 行動計劃,我國在防止稅基侵蝕和濫用稅收協定中對跨境并購活動嚴格了監管措施, 但通過境外注冊SPV 進行“迂回投資”的交易模式,完全可以回避上述監管。
2.“迂回投資” 的外資并購會帶來市場秩序失衡風險。 本案例的交易金額為4 億元人民幣,模式三下最后稅收優惠的結果僅雙方繳納0.3%的印花稅,相對于其他標的交易額,這一稅負明顯偏低。同時,S 的注冊地和外資企業的注冊地如果均選在境外低稅率地區, 其在境內的各項所得納稅均需按照預提所得稅10%繳納。相比正常企業25%的稅率,會帶來額外的市場秩序失衡風險, 最終會使大量我國高科技企業為他國所有或控制,帶來潛在的國家安全風險。
3.外資并購可以或可造成企業無形資產和關鍵技術的流失。 上述案例的三個模式中,由于稅收優惠政策規定, 企業可以通過交易構建享受增值稅、企業所得稅的整體性關鍵優惠,而無須在并購中體現和確認企業知識產權的市場價值。 在企業合并的會計準則要求中,雖然購買法的會計處理要求合并方按照被并方可辨認資產的公允價值記錄入賬,但由于外資企業注冊地在境外,其賬務系統的處理并不在我國監管之內。 因此,通過并購,企業知識產權的市場價值難以體現,原本歸屬于中國企業的知識產權和關鍵技術可能因無法得到持續確認而流失。事實上,美國學者的研究很早就發現,外資并購中股權比重較大時,能夠更好地吸收對方的“隱性”無形資產(Chari and Chang,2009;Das and Deng,2000);反之,則意味著被并方無形資產和關鍵技術等柔性競爭力的流失。
(二)建議
1.我國需要及時調整吸引外資的著力點。 在我國經濟邁入高質量發展階段, 吸引外資更應重視內涵式資源整合, 鼓勵外商進行綠地投資和原企業增資; 原外商僅僅通過大規模股權收購享受的稅收優惠應該逐漸取消, 并通過配套的財稅政策調整予以指引。 研究表明,在外資并購領域,政府的宏觀層面干預主要體現在通過法律法規引導外資企業的投資流向(何云,2017)。 建立高水平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促進外商投資與國家安全之間必須相互平衡。
2.統一我國財稅法律中企業并購的概念范圍。 伴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的戰略布局,高水平投資自由化局面即將形成,我國應該盡快統一關于外資并購的各項概念范圍,以便及時維護我國市場穩定和我國企業利益。例如我國對于企業并購一直沒有統一的定義;“外資并購”一詞,雖然在《關于外國投資者并購境內企業的規定》中有所解釋,但對行為主體“外國投資者”卻一直沒有范圍界定14“外國投資者”的概念在《外國投資法(草案)》中出現過,但在正式版《外商投資法》中被去除。,在2019 年《外商投資法》中僅列明“外商投資”的概念,導致實務屆對稅收優惠的政策解釋口徑不一,給投資者帶來投資風險。
3.對外資并購行業和技術領域進行明確規定。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正在加緊對制造業高精尖技術行業并購的管控,如2018 年美國推出的《外國投資風險審查現代化法案》(Foreign Investment Risk Review Modernization Act of 2018, 以下簡稱“FIRRMA”), 旨在防止外國公司通過并購獲得美國關鍵技術(董靜然)。 我國業已建立若干安全審查制度,比較重要的是2011 年的 《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建立外國投資者并購境內企業安全審查制度的通知》《商務部實施外國投資者并購境內企業安全審查制度的規定》《國務院自由貿易試驗區外商投資國家安全審查試行辦法(2015)》等,其中關于安全審查的范圍,包含軍工、農業,經濟范圍廣泛,但都只是用“重要”“關鍵”來形容,缺乏可操作性強的規定,同時也沒有考慮新經濟的構成要素, 如網絡安全、技術安全、人工智能等(鄭聿舒,2019)。
4.加強知識產權保護。 在WTO 推進的《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TRIPS)下,各國正在抓緊制定知識產權保護條例, 越來越注重無形資產的收益,來自知識產權、無形資產的影響力已經成為合并方股權設計的重要考慮(Khoury and Peng,2011)。目前我國政府關于外資并購的知識產權尚缺乏單獨立法。我國政府規范外資并購的主要規定為2009年的《外國投資者并購境內企業規定》,還缺乏對外資并購中知識產權保護的專門規定,同時建議在外資并購的稅收優惠中建立與自主知識產權保護相關的條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