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小板膜標志物表達水平與頸動脈粥樣硬化病人支架內再狹窄的關系
王濤 張梅 余傳慶 薛敏 武慶彬 康殿貴
頸動脈粥樣硬化(carotid atherosclerosis,CAS)是指頸動脈因長期受血流沖擊導致血管內膜機械性損傷,進而引起內膜下脂質沉積,血小板黏附聚集,造成血管腔狹窄[1]。隨著血管內介入技術的不斷發展,頸動脈支架成形術已成為CAS性狹窄的重要治療手段之一,由于安全、有效、微創的優點,已得到廣泛應用[2],然而研究報道術后3年支架內再狹窄(ISR)發生率為3.4%,病人術后腦卒中及死亡的發生率明顯增加[3]。因此分析頸動脈支架成形術后ISR的危險因素,可為制定治療決策帶來重要參考。有研究發現血小板活化與ISR密切相關,是ISR的獨立危險因素[4],而α顆粒膜糖蛋白(CD62p)及溶酶體膜蛋白(CD63)是血小板活化的重要膜敏感性標志物[5],為此,本研究分析了影響CAS狹窄病人支架成形術后ISR的相關危險因素,探討了血小板膜標志物CD62p及CD63的表達水平與ISR的關系,旨在為預防CAS病人支架成形術后ISR提供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2015年10月至2017年6月于我院確診為CAS且行頸動脈支架成形術的病人共124例病人,最終將臨床資料完整且完成隨訪106例納入分析,其中男76例,女30例,年齡60~78歲,平均年齡(69.28±3.17)歲,106例病人共放置支架119枚,其中13例因首次支架放置不佳而進行2次支架置入。病人按是否發生ISR分為ISR組和非ISR組(NISR組)所有病人均知情同意本研究并自愿簽署知情同意書,本研究經我院倫理委員會審核通過。
1.2 納入與排除標準 納入標準:2組病人均經超聲及數字減影血管造影(DSA)診斷為CAS[6];符合頸動脈支架成形術的手術指征,即有臨床癥狀的病人狹窄程度≥50%或無臨床癥狀的病人狹窄程度≥70%;所有病人均自愿接受抽血、彩超及DSA檢查;認知功能正常,可配合研究過程。排除標準:對碘造影劑過敏者;合并心、肝、腎等重要臟器損傷者;非CAS引起的血管病者;合并惡性腫瘤者;合并血液系統疾病者;合并精神障礙者。
1.3 頸動脈支架成形術治療過程 術前2 h開始經靜脈泵持續泵注尼莫地平注射液,手術選擇經股動脈入路,在局麻條件下進行,穿刺股動脈并放置股動脈鞘,頸動脈給予70 IU/kg劑量的肝素,而后每小時追加1/2的初始劑量,先行全腦血管造影確定狹窄部位及程度,使用導引管將導絲送至狹窄處,經導絲放置頸動脈支架。在術后開始給予阿司匹林及氯吡格雷,而后減量,維持終身服用。手術均由經驗豐富的介入醫師操作完成。治療期間根據病人實際情況給予降壓、降糖、調脂、戒煙、戒酒等對癥處理。
1.4 觀察指標 收集2組病人性別、年齡、吸煙史、酗酒史、卒中史、高血壓、DM、CHD、高血脂、使用支架數量、術后抗血小板藥物應用依從性等一般資料;采用DSA檢查確認2組病人術前狹窄程度及術后有無殘余狹窄。
血小板膜標志物CD62p、CD63的測定:分別于術前及術后1個月抽取所有病人全血10μL,分為2份,各5μL,分別將其加入20μL CD62p單克隆抗體、20μL CD63單克隆抗體(均由美國R&D Systems公司提供)中,在室溫環境下避光反應20 min后將其加入4 mL磷酸緩沖鹽溶液(PBS)中,混合均勻后再加入1 mL 1%多聚甲醛(2~8 ℃),低溫環境下避光固定30 min,而后上機檢測。選擇488 nm波長的氬離子激光門,通過側向及前向散射光設定血小板門,區分血小板群和其他細胞及顆粒,共檢測5000個血小板,測定出熒光標記陽性的血小板數量,并計算百分率,熒光標記陽性的血小板百分率即為CD62p、CD63的表達率。
1.5 術后隨訪 所有病人均于術后1個月、3個月、6個月及之后每半年復查頸部血管彩色多普勒超聲及DSA檢查判定是否存在ISR,隨訪時間截至2018年6月,以ISR或病人死亡為隨訪終點。ISR判定標準為:經DSA檢查證實支架部位血管管腔狹窄程度≥50%,排除支架斷裂及支架內血栓(ISR的范圍包括支架近、遠兩端5 mm以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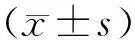
2 結果
2.1 隨訪結果 106例頸動脈支架成形術均成功。在圍手術期,4例并發短暫性腦缺血發作,2例并發非致殘性腦卒中,未出現圍手術期死亡病例。復查DSA的結果顯示,在ISR病人中,中度再狹窄(狹窄程度為50%~69%)ISR 9例,重度再狹窄(狹窄程度≥70%)7例;5例重度再狹窄病人并發腦卒中,另外11例無明顯臨床癥狀;5例重度再狹窄病人實施了球囊擴張血管成形術;2例重度再狹窄病人分別于術后6個月、8個月因大面積腦梗死而死亡。
2.2 影響頸動脈支架成形術后ISR的單因素分析 2組在吸煙史、高血壓、DM、支架數量、術后殘余狹窄、術后抗凝藥物應用依從性、術后1個月CD62p及CD63的表達率方面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表1 影響頸動脈支架成形術后ISR的單因素分析(n)
2.3 影響頸動脈支架成形術后ISR的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 將單因素分析差異有統計學意義的項目進行Logistic逐步回歸分析,結果顯示,支架數量、術后殘余狹窄、術后1個月CD62p及CD63的表達率是頸動脈支架成形術后ISR的獨立危險因素,見表2。

表2 影響頸動脈支架成形術后ISR的多因素分析
2.4 術后1個月CD62p及CD63表達率預測ISR的ROC分析 以是否發生ISR為結局,分別以術后1個月CD62p及CD63的表達率繪制ROC曲線。結果顯示,術后1個月CD62p的表達率>5.43%是預測ISR的最佳切點,靈敏度為88.42%,特異度為76.27%;術后1個月CD63的表達率>8.13%是預測ISR的最佳切點,靈敏度為77.34%,特異度為90.68%。見表3,圖1。

表3 術后1個月CD62p及CD63表達率預測ISR的ROC分析

圖1 術后1個月CD62p及CD63表達率預測ISR的ROC分析
3 討論
據統計大約51.1%的短暫性腦缺血發作病人存在不同程度的CAS,其發病率隨年齡增加而增高[7]。目前頸動脈支架成形術是臨床上治療CAS狹窄的重要方式之一。然而,老年人在術后易出現ISR等問題,嚴重影響了手術的遠期療效。近年研究發現血小板活化可促進血小板聚集及血栓形成而導致支架內再狹窄的發生發展[8],而CD62p及CD63是血小板活化的重要標志物。本研究在分析CAS狹窄病人支架成形術后ISR相關危險因素基礎上,同時評估血小板膜標志物CD62p及CD63作為ISR標志物的潛在價值。
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顯示支架數量、術后殘余狹窄、術后1個月CD62p的表達率、術后1個月CD63的表達率是頸動脈支架成形術后ISR的獨立危險因素。段春苗等[9]指出頸動脈支架成形術術中使用支架數量及術后殘余狹窄是頸動脈ISR的危險因素,本研究進一步證實了該結論。當支架數量增多時,血管腔內阻力增大,極易對血管內皮細胞造成損傷,導致血小板黏附及聚集,促進血栓形成,進而導致支架內再狹窄[10]。支架植入血管后可導致附壁血栓的形成,造成ISR,盡管目前所使用支架均為自膨式支架,有一定的自膨趨勢,但如術后殘余狹窄較重,支架的膨脹無法充分抵消附壁血栓所致的再狹窄趨勢[11],可導致ISR。
CD62p也稱P-選擇素,在正常機體CD62p表達較少,當血小板活化時,CD62p可大量表達,促使血栓的發生與發展,是目前反映血小板活化的金標準[12]。CD63是溶酶體膜蛋白的一種,正常機體血小板表面CD63表達率極低,當血小板活化時,其可迅速在血小板表面表達,參與血栓的形成,反映血小板活化的敏感性及特異性較高[13]。楊鐵驪等[14]指出術后1個月血小板活化標志物CD62p及CD63的表達率是冠狀動脈介入治療術后ISR的獨立危險因素,與本研究結果相似。基于此,本研究將術后1個月CD62p及CD63的表達率繪制ROC,術后1個月CD62p的表達率>5.43%、CD63的表達率>8.13%是預測ISR的最佳切點,具有較高的預測價值,可用于CAS狹窄病人支架成形術后ISR的早期預測。CAS狹窄病人支架成形術后可導致血管內膜損傷,內皮下膠原暴露,血小板活化,促進血小板活化標志物CD62p及CD63的表達,激活血小板形成白色血栓,引起ISR;同時引發炎癥反應,促使細胞因子、生長因子等大量釋放,促進中層平滑肌增殖并向血管腔移行,進一步加重ISR[15]。
綜上所述,術后1個月血小板膜標志物CD62p、CD63的表達水平與ISR密切相關,其和支架數量及術后殘余狹窄均為術后ISR的獨立危險因素,可作為預測行頸動脈支架成形術后ISR的指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