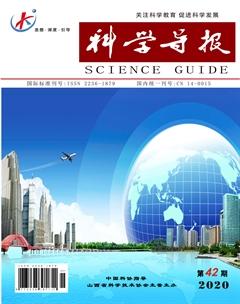洪荒之力
于豐寧
《Ng?u H?ng》這首純音樂,我第一次聽是在姐姐車上。
當時便覺得這旋律獨特,歌里定是藏了些什么。于是便瞥了一眼行車顯示屏,知道了它的名字。這才罷休。
心里暗暗竊喜,又有一首值得回味的音樂了。只是,之后的日子,這首歌,我卻并沒有常聽。
但有時,事情就是這樣奇妙。就像你永遠不知道也許月亮最初是地球的一部分,一只蝴蝶也能掀起颶風狂浪,就像你不知道跋涉千里突然有一座小亭會飄搖在山河間,有些人不是特意的安排,便永遠不會再見。
這首歌,于我,也是如此。
去年的四月天,我在醫院待了一周后,才對這音樂有了更別樣的感受。
處在醫院中的無奈真是數不勝數。
沒辦法出去散步,沒辦法自由活動,怎么辦呢?我害怕寂寞與無聊的狂潮把我淹沒。可怎么辦呢?有了,聽首歌吧。
在信號微弱的環境中,我擺弄著媽媽的舊手機,歷盡“艱辛”,排除萬難,終于下載了一支歌曲。而這首歌曲便是《Ng?u H?ng》。
第一天的晚上特別難熬。
由于身上的儀器,我曾試圖安穩地入睡。可不能翻身,只能以一種姿勢“抗爭”到天明。這樣煎熬,我怎能受住。索性不睡了,一個人緩緩走到窗戶旁邊,坐了下來。
晚上十一二點的時候,病房里的人都睡了。只有我還醒著。媽媽睡得也不踏實,她總是瞇了一會兒便朝我看來,以喑啞的聲音同我說,“快來睡吧。都幾點了啊。”而我卻總是擺擺手,示意讓她先行睡下,不必管我。之后便又自顧自地望向窗外。
病房里的燈徹夜開著,隔壁房間的電視還響著,我靜靜地拿出手機,以最小的音量放起了音樂。
旋律響起,我看著窗外霓虹燈邊和漆黑一片。心,隨著音樂漸漸起伏。有時眼前空蕩蕩的,就好像不在這個世界一樣。
后來朋友問我,那是因為難受嗎?
不,我想,遠不是這樣的。
黑夜中,一個人,靜寂的房間只有空調吹出的氣流聲,一葉窗外,車水馬龍,聽不到任何鳴笛聲,聽不到任何談笑聲,唯有孤寂,唯有忍受。而那一切,也都是在這無垠的黑暗中。
我想,這是比難受更纏人的一種感受。那樣的環境使人難堪,因為你想超脫,卻又明知做不了什么,一切的行為也只能淪落為掙扎的丑態了。
歌曲一直循環著,旋律的高潮次次回蕩。
這時,會瞬間明白人生的某些意義,價值,或許就是平時埋在枯葉下的那些東西。
就這樣,一直這樣,大概到了凌晨。我回到床上躺了下來。我不知道我有沒有睡著,但早晨五點便就醒來。略帶疲憊的媽媽出門去買早飯,而我又在窗邊坐了下來。
白天,我便來到樓層間的等候區靜坐,目光依然是窗外,手機依然循環著那首音樂。時不時的便有人從對面的電梯里走出,手里提著各樣果盒,不用說,一定是去看望慰問他們的親人或朋友。
他們臉上的表情很多。
偶爾也會有人朝我看來,眼中閃著詫異的光。我知道他們想的是什么。
對了,偶爾還會有要做手術的病人,躺在車架上,被醫生推入電梯。醫生在一旁嚴肅地囑咐,“注意......”親屬靠在病人耳邊輕輕耳語,“沒事的,沒事的。”
是不是真如周夢蝶先生說的那樣,所有美好過后,至少人們還有虛無留存?所有美好過后,至少人們已經懂得什么是什么了?是不是人遠天涯遠,若欲相見,便真的即得相見呢?
真的,是這樣嗎?
…………
回家后,我翻看著這首歌的評論。
有一則說,這首歌是越南DJ在挪威的一個街道邊看到一個作為流浪藝人的老頭彈奏的(這樣的人在挪威很多),然后根據那旋律改編的。
后來我仔細地查了查信息。發現這顯然是胡編的,而之后我也找不到那條評論了。
但是,久久,久久,我是愿意相信這件事的。我愿意相信是那個老頭彈奏的。
腦海里時常浮現那個畫面。坐在街道邊,衣衫襤褸,滿臉胡須的一個老頭,對著挪威的繁華和人們的風情,手里捧著貝斯彈奏著這樣的樂曲。
我不知道他的故事是什么,他的一生又經歷了什么。
真是讓人費神,又讓人神往啊。
藝術有時毀人,有時救人。
而也就是這樣,當你再次傾聽這首歌曲的時候,你才會發現原來你之前所想的那些都是對的,你才會發覺這首曲中有著怎樣復雜的情感以及多么震撼人心的“生的力量”,正如它的中文名《洪荒之力》一樣。
指導教師:任鳳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