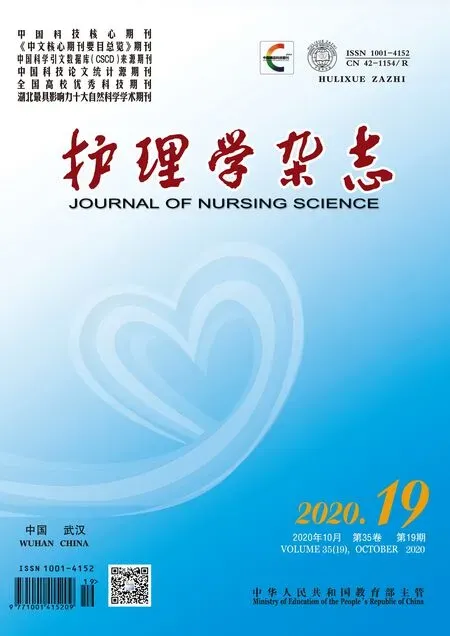橈動脈壓迫器首次減壓開始時間對冠狀動脈造影術后并發癥影響的系統評價
任靜,呂順,劉鳳,徐芬,黃永麗,黃棋,李彥伶,唐文豪,孫鴻燕
經皮橈動脈(Transradial Intervention,TRI)途徑的冠狀動脈介入診療技術(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PCI)具有效率高、創傷小、并發癥少、恢復快等優點[1],目前已成為診斷及治療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臟病(CAD)的主要手段[2]。隨著TRI術的廣泛開展,術后橈動脈壓迫止血器的使用也越來越多[3],目前針對橈動脈壓迫止血器術后首次減壓時間沒有明確的規定。本研究運用Cochrane系統評價方法,選取國內外公開發表的有關橈動脈壓迫止血器術后首次減壓開始時間(術后1 h與術后2 h),對術后并發癥影響的相關文獻進行Meta分析,探究術后首次最佳減壓時間,為橈動脈壓迫器的規范使用和正確護理提供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文獻納入與排除標準 納入標準:①研究對象為TRI;②研究類型為隨機對照試驗(RCT),研究主題為比較術后首次減壓開始時間(術后1 h與術后2 h)對術后并發癥的影響;③研究對象均接受常規護理,并且在年齡、性別、病情、壓迫部位、壓迫器種類等方面均具有一致性;④結局指標包括出血、疼痛、迷走神經反射、橈動脈閉塞、腫脹、麻木、淤斑、水皰、血腫等止血器壓迫后并發癥;⑤文獻為中文或英文文獻。排除標準:①文獻信息不足,數據不完整,無法納入統計分析;②未評價本研究中的結局指標;③重復發表的文獻;④研究對象分組不合理;⑤方法學質量為C級文獻。
1.2文獻檢索策略 檢索PubMed、EMbase、Cochrane Library、Web of Science、中國知網、萬方數據、維普網和中國生物醫學文獻服務系統等國內外數據庫。檢索時限為建庫至2020年5月1日。以“橈動脈”“橈動脈穿刺”“經橈動脈介入”“橈動脈壓迫止血器”“橈動脈壓迫時間”“止血器減壓時間”等為中文檢索詞,以“radial artery/radial artery puncture/radial artery access/compression device/decompress/compression hemostasis device/radial artery compressor”等為英文檢索詞。采用布爾邏輯運算符連接檢索詞進行檢索,人工檢索納入文獻的參考文獻作為補充。
1.3文獻篩選與資料提取 由2名經過培訓的研究人員根據文獻納入與排除標準獨立篩選文獻、提取數據,并進行核對。當提取結果不一致時,由第3名研究人員參與商討后決定。
1.4文獻質量評價 由2名經過培訓的研究人員按照Cochrane5.1.0系統評價手冊推薦的關于RCT質量評價方法對納入的文獻進行質量評價,其評價內容包括隨機分配、分配隱藏、盲法、結果數據的完整性、選擇性報告研究結果和其他偏倚來源。若納入研究完全符合上述標準,提示發生偏倚的風險低,其質量等級為A級;納入研究部分滿足上述標準,提示發生偏倚的風險為中度,其質量等級為B級;納入研究完全不滿足上述標準,提示發生偏倚的風險高,其質量等級為C級[4]。
1.5統計學方法 采用RevMan5.3軟件進行Meta分析。計數資料采用比值比(OR)為效應指標,各效應量均給出其點估計值和95%置信區間(95%CI)。若各研究間異質性較小(P≥0.1,I2≤50%),則采用固定效應模型進行Meta分析;若各研究間存在異質性(P<0.1,I2>50%),采用敏感性分析盡可能找出異質性的來源,若仍然無法消除異質性,則采用隨機效應模型進行Meta分析[4]。
2 結果
2.1文獻檢索結果 符合檢索要求的文獻共736篇,其中英文262篇,中文474篇,通過逐層篩選,最終納入8篇文獻[5-12]。其中,中文文獻7篇[5-11],英文文獻1篇[12]。共納入2 399例研究對象,其中1 h組1 176例,2 h組1 223例。文獻的基本特征見表1。

表1 納入文獻的基本特征
2.2文獻質量評價 所有文獻采用Cochrane5.1.0系統評價手冊評價,隨機分配:4篇文獻[9-12]為低風險,3篇文獻[5-7]為高風險,1篇文獻[8]不清楚;分配方案隱藏均不清楚;盲法:均不清楚;結果數據完整;選擇性報告為低風險;文獻質量評價均為B級。
2.3結果分析
2.3.1出血率 4篇文獻[5-6,8,12]評價了術后首次1 h與2 h后開始減壓導致出血的比較,研究對象共1 231例,其中對照組601例,實驗組630例。研究間異質性小(P=0.13,I2=47%),采用固定效應模型。結果顯示:OR=1.31,95%CI(0.87~1.98),Z=1.29,P=0.20,差異無統計學意義。
2.3.2迷走神經反射發生率 3篇文獻[5,10-11]評價了術后首次1 h與2 h后開始減壓導致迷走神經反射發生的比較,研究對象共774例。研究間異質性小(P=0.21,I2=37%),采用固定效應模型。結果見圖1。

圖1 兩組迷走神經反射發生率的Meta分析
2.3.3疼痛率 4篇文獻[5,7-8,10]評價了術后首次1 h與2 h后開始減壓導致肢體疼痛發生的比較,研究對象共1 522例。研究間異質性小(P=0.27,I2=23%),采用固定效應模型。結果見圖2。

圖2 兩組肢體疼痛率的Meta分析
2.3.4橈動脈閉塞發生率 5篇文獻[5-6,8,10-11]評價了術后首次1 h與2 h后開始減壓導致橈動脈閉塞的比較,研究對象共1 474例。研究間異質性小(P=0.19,I2=38%),采用固定效應模型。結果顯示統計學差異處于臨界值,見圖3。

圖3 兩組橈動脈閉塞發生率的Meta分析
2.3.5肢體腫脹、麻木、淤斑、水皰、血腫情況 ①肢體腫脹。4篇文獻[6,8-10]評價了術后首次1 h與2 h開始減壓致肢體腫脹的比較,研究對象共1 296例,其中對照組687例,實驗組609例。研究間異質性較大(P=0.04,I2=65%),采用隨機效應模型。結果顯示差異無統計學意義[OR=0.76,95%CI(0.34~1.68),Z=0.68,P=0.50]。②肢體麻木。3篇文獻[6-8]評價了術后首次1 h與2 h開始減壓致肢體麻木的比較。研究對象共1 060例,其中對照組530例,實驗組530例。研究間異質性較大(P=0.02,I2=73%),采用隨機效應模型。結果顯示差異無統計學意義[OR=0.91,95%CI(0.40~2.07),Z=0.23,P=0.82]。③淤斑。2篇文獻[6,8]評價了術后首次1 h與2 h后開始減壓致淤斑的比較。研究對象共700例,其中對照組350例,實驗組350例。研究間異質性較大(P=0.09,I2=66%),采用隨機效應模型。結果顯示差異無統計學意義[OR=2.30,95%CI(0.20~26.51),Z=0.67,P=0.51]。④水皰。3篇文獻[6,9,11]評價了術后首次1 h與2 h開始減壓致水皰的比較。研究對象共646例,其中對照組322例,實驗組324例。研究間異質性較大(P=0.005,I2=81%),采用隨機效應模型。結果顯示差異無統計學意義[OR=0.30,95%CI(0.01~13.55),Z=0.62,P=0.54]。⑤血腫。3篇文獻[8-9,12]評價了術后首次1 h與2 h減壓致血腫的比較。研究對象共1 165例,其中對照組566例,實驗組599例。研究間無明顯異質性(P=0.65,I2=0%),采用固定效應模型。結果顯示差異無統計學意義[OR=1.06,95%CI(0.62~1.81),Z=0.21,P=0.83]。
3 討論
3.1術后首次開始減壓時間對穿刺部位出血的影響 TRI已成為PCI首選入路,出血、血腫是橈動脈穿刺介入術后的常見并發癥,嚴重者可以造成骨筋膜室綜合征[13]。本次分析結果顯示,首次1 h減壓與首次2 h減壓在止血效果方面差異無統計學意義,這與大部分研究結果[5-6,8]一致。橈動脈管徑較小且位置表淺,出血易于控制。有研究顯示,年齡、性別、糖尿病、吸煙、房顫、高血壓、術前術后用藥、介入治療的性質[14-16]等是出血主要影響因素。出血的發生主要與壓迫點的定位不當有關,壓迫點偏下時容易引起前臂血腫,而偏上則容易發生滲血[17]。研究中未考慮嚴重肝臟病變、凝血功能障礙等高危因素,首次1 h減壓是否可滿足止血需求有待進一步研究。
3.2對術后肢體疼痛、迷走神經反射的影響 患者術后常有疼痛感,可能與橈動脈管徑細小,前臂近掌側皮膚對疼痛較敏感,術中動脈鞘管、導管、導絲對血管壁的擴張和刺激,以及止血器壓力過大、時間過長等有關,均可引起前臂或穿刺點疼痛不適[3]。本次系統評價中,有4篇RCT[5,7-8,10],探究了術后首次減壓時間對穿刺處疼痛的影響,研究顯示首次1 h開始減壓能顯著降低患者術后疼痛感,可能與壓力減小、時間縮短有關。
經橈動脈穿刺術后并發癥特別是迷走神經反射較為兇險[18],目前認為是血管迷走性抑制性暈厥,主要發生機制是各種刺激因素(如創傷、疼痛、恐懼等)作用于皮層中樞和下丘腦,通過使膽堿能植物神經的張力突然增加,引起內臟、肌肉、小血管強烈反射性擴張,從而產生降壓效應,重者可出現神志模糊、意識喪失危及患者生命。本研究提示術后首次1 h開始減壓能明顯降低迷走神經反射的發生率,可能主要與壓力減輕后疼痛感較低有關。
3.3對術后腫脹、麻木、淤斑、水皰及血腫的影響 有研究表明,一般血管在局部壓迫2 h后即開始出現腫脹、麻木等循環障礙表現,因而適當提前減壓,能有效減少血管并發癥的發生[19]。多數研究者主要針對術后1 h及2 h開始首次減壓展開研究,但研究結論并不一致。陳蓓蓓等[11]、任冬梅等[20]研究發現,術后1 h開始減壓對減輕患者手部腫脹、麻木,預防水皰發生等并發癥方面有明顯優勢。而李福秀等[7]研究則表明,術后壓迫止血2 h后開始逐漸減壓,出現皮膚并發癥較術后1 h減壓少。本次Meta分析結果顯示,術后首次1 h開始減壓與術后首次2 h開始減壓患者在術后腫脹、麻木、淤斑、水皰及血腫等方面差異無統計學意義。究其原因,可能與手術操作方法、橈動脈止血器類型、術后解壓方法及患者個體差異等有關。
3.4對術后橈動脈閉塞的影響 橈動脈閉塞是經橈動脈穿刺術后常見的并發癥,橈動脈閉塞的直接原因是橈動脈內血栓形成[21],雖然臨床癥狀輕,但一旦出現橈動脈閉塞,則會影響該路徑未來的應用[22]。橈動脈閉塞的發生主要與經橈動脈穿刺術中動脈鞘管的長度、尺寸、數量、肝素使用劑量、止血方式以及與患者年齡、性別等有關,降低橈動脈閉塞最有效方法是較高劑量的肝素[23-24]。本研究納入的5篇RCT探究了術后首次減壓時間對橈動脈閉塞發生的影響,Meta分析結果顯示,術后首次1 h與2 h開始減壓對患者術后橈動脈閉塞發生率統計學差異處于臨界狀態(P=0.05),再看其實際發生率:術后首次2 h開始減壓組發生率為1.80%(14/777),相對高于術后首次1 h開始減壓組的0.43%(3/697);根據臨床觀察,術后首次1 h開始減壓有利減少橈動脈閉塞的發生,但得出經得起驗證的結論還需更大樣本量的比較來證實。
4 小結
本研究顯示,橈動脈壓迫器首次1 h開始減壓與首次2 h開始減壓均能夠有效達到止血目的,腫脹、麻木、淤斑、水皰及血腫發生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橈動脈閉塞發生率統計學差異處于臨界狀態,但首次1 h開始減壓能顯著降低患者的疼痛感及迷走神經反射發生率,患者更容易耐受,增加了患者舒適度。然而,本研究僅檢索了公開發表的中英文文獻,不能排除潛在的發表偏倚;受納入研究數量的限制,未能按照止血器類型、解壓操作方法、疼痛程度等進行亞組分析;部分結局指標納入的研究數量較少,Meta分析的結果有待進一步驗證。鑒于本研究的局限性,今后尚需開展更多高質量、多中心、大樣本RCT,就橈動脈壓迫器首次減壓時間對經橈動脈穿刺術后并發癥的影響進一步探討,進而提高循證依據的強度和效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