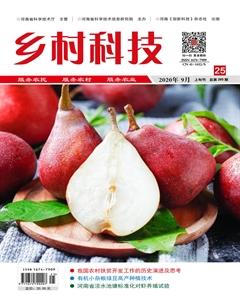我國鄉村治理脈絡演進與未來應關注方向
李三輝
[摘 要] 鄉村治理是基層社會治理的重點,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加強和改進新時代鄉村治理,需結合鄉村治理的五大發展脈絡來厘清歷程,總結鄉村治理研究經驗,從而在立足我國鄉村社會發展現實的基礎上,更好地把握社會轉型躍進的內在規律,分析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鄉村治理的重大方向性問題,探索不同發展階段、不同類型、不同地區鄉村的社會治理途徑和治理目標,展望未來鄉村治理發展前景。
[關鍵詞] 鄉村治理;發展脈絡;鄉村振興
[中圖分類號] F320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4-7909(2020)25-12-3
治理有效是鄉村振興展開和推進的社會基礎,加強和改進鄉村治理是當前面臨的時代任務。推進新時代鄉村治理,需要系統梳理鄉村社會治理發展變遷,充分了解和把握鄉村治理的動態趨勢。
1 我國鄉村治理的五大發展脈絡
受歷史傳統和社會發展進程的影響,我國的社會治理研究始于村落,并形成了以鄉村為核心的基層社會治理體系。隨著社會變遷日益深刻和社會治理問題日益復雜化,鄉村社會治理研究與時代同頻共振,逐步深入并聚焦以下5個方面。
1.1 探尋鄉村治理模式
鄉村治理模式和鄉村治理結構的時代變遷,大致經歷了“政權不下縣,縣下惟宗族”“鄉紳自治”“政權下鄉”“人民公社”“鄉政村治”“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等基本模式。我國傳統鄉村大致相似于滕尼斯所言的社區,或涂爾干指稱的機械團結社會,具有較高的同質性,國家管理農村和維護鄉村秩序遵循“皇權不下縣”的原則,依賴“紳治”和傳統道德體系,正如費孝通所言“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會”。民國時期(1912—1949年),保甲制度在鄉村普遍推行,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以“鄉族”為村政單位的傳統格局,而以晏陽初、梁漱溟等人為代表的社會學家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廣泛開展了以改造鄉村社會為直接目標的鄉村運動。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極具時代特色的公社化運動織就了一張自上而下的經濟、行政控制網絡,國家政權對鄉村社會的滲入和控制力度達到了空前狀態。20世紀80年代以來,以“村民自治”為基本方式的“鄉政村治”模式全面鋪開,對鄉村生產生活影響巨大。然而,一段時期以來,這種治理模式的弊端逐漸凸顯,普遍存在治理主體單一、治理水平低下、鄉村公共物品供給不足、治理機制不夠完善以及村兩委矛盾突出等問題,因此需要思考如何在新問題、新要求下尋求更有效、更適合我國鄉村現狀的治理方式。黨的十九大和鄉村振興戰略為今后的鄉村治理樹立了風向標,構建了適應新時代鄉村社會發展的嶄新框架。
1.2 關注多元治理主體
不斷切換的鄉村治理模式已經表明,多元化治理主體才符合鄉村實際,其大致包括三重力量,一類是國家政權組織或者準國家政權組織如鄉鎮黨委政府、“村兩委”等正式力量,一類是村民為主體的自治力量,一類是各種形式的民間社會組織力量。有些學者結合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變過程來考究我國農村治理主體結構,其經歷了由“有社會、無國家”到“有國家、無社會”再到“有國家、有社會”的3個發展階段,農村治理的權力主體也呈現了“地方權紳—工農群眾—參議員—人民代表”的路徑調整。還有許多學者認為,鄉村基層治理主體已從“士紳”模式演進為“地方精英”模式[1],特別是在一些經濟社會發展程度較高的農村地區,經濟強人在村莊公共權力結構中越來越占主導地位,“能人治村”演化成了一種群眾自治下的精英主導形式。
1.3 聚焦鄉村治理問題
自改革開放后城鄉建設的推進,鄉村社會的開放性、流動性不斷加大,鄉村社會結構的新舊矛盾不斷交織,而對標黨的十九大提出的新要求,當代鄉村社會治理面臨一系列新情況、新問題。改革開放以來的我國城鎮化經歷了低起點、高速度的發展,雖然城鄉融合逐漸加快,但是新舊問題不斷交織。一方面,城鄉一體化進程帶來了農民思維方式、行為規則、農村社會結構和規則的巨大變化,給鄉村社會發展注入了市場活力和全方位變革思緒;另一方面,其解構了傳統鄉村社會治理模式(以宗族為代表的社會治理力量,以鄉規民約為主要治理規則),直接暴露了城鄉融合與二元結構矛盾、現代城市文明與鄉土傳統的矛盾、鄉村“空心化”、公共服務及社會保障滯后問題、發展內生動力不足問題,表現在經濟基礎與秩序上是貨幣化壓力加劇與就業危機,在社會秩序上是宗法禮俗消解與現代規則待建,在村治秩序上是權力分化與自治困境,這些都給當前的鄉村治理帶來了很大挑戰[2]。不難發現,現在的農村處于一個變革的階段,新時代鄉村治理和鄉村秩序的基礎面臨新的挑戰,如基層黨組織能力薄弱、鄉村治理方法單一、鄉村治理目標不明確或與治理需求及環境不吻合、群眾鄉村治理參與度低等。
1.4 總結鄉村社會形態
著眼于鄉村治理結構、鄉村社會問題、鄉村社會結構、鄉村治理主體等基礎性因素的變動,許多學者都適時對所處的鄉村社會形態轉換進行了考察研究。具體來看,20世紀40年代之前的中國鄉村是傳統的鄉土社會,到改革開放之前是鄉土斷裂期,改革開放之后則進入了轉型加速期和深度裂變期,而“鄉土中國”“半熟人社會”“無主體熟人社會”“斷裂社會”“弱熟人社會”“后鄉土中國”“并未發生質變的熟悉社會”則是不同時期的學者對我國鄉村社會尤其是深度社會轉型下鄉村社會裂變的概念解釋。步入新時代,直面我國鄉村發展階段、社會治理境況、鄉村演化態勢,習近平提出的鄉村振興戰略的逐步實施成為當下和今后一個時期鄉村社會形態轉換的主推力。
1.5 重視三治融合
隨著黨的十九大勝利召開和鄉村振興戰略的正式實施,“三治融合”鄉村治理體系研究步入了一個新階段。古今中外,自治、法治、德治及三者的結合問題始終受到政府與社會各界的關注,各地自覺和不自覺地進行著實踐。浙江省桐鄉市最早推出“法治為要、德治為基、自治為本”的“三治”建設,隨后浙江省全面推行“健全法治德治自治相結合的基層治理機制”,這些為黨的十九大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做出了前期探尋。實際上,除了政府會議、官方文件對“三治”的推廣,“三治融合”的深化與學界的持續跟蹤研究密不可分,而這又大致分為2個研究高潮期。第1個階段是浙江省“三治”實踐之初。聚焦黨的十八大強調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管理體制,有學者認為“三治”是社會建設層面的地方治理創新,“三治一體”模式對接了“自上而下”的政府引導與“自下而上”的民眾參與,形成了系統化、協同化和一體化的治理機制,契合善治理論。第2個階段則以黨的十九大為時間節點。“三治”不僅被正式表述為“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而且鄉村振興戰略規劃文件進一步明確了自治為基、法治為本、德治為先的原則。許多學者都贊同,“三治結合”實現了政府服務、公民自治、道德共建的有機融合,有助于解決鄉村治理權威弱化、農村空心化、主體缺位、法治意識淡薄和鄉土文化流失等鄉村振興困境,是實現新時代鄉村治理體系重構創新、通往善治的基本路向[3]。
2 我國鄉村治理未來可關注的方向
回顧我國鄉村社會治理實踐歷程和研究成效,一方面,可以發現我國一直有重視鄉村治理研究的傳統傾向和操作實踐,不同學者在鄉村治理問題、鄉村治理主體、鄉村文化建設、鄉村社會秩序等方面展開了較為充分的論述,這對于大家認識和理解新時代條件下鄉村社會治理問題的形成基礎、結構演變及發展態勢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和實踐支撐;另一方面,必須看到鄉村社會治理研究有“散化”趨勢,一個路徑是偏向于強調基層組織、制度建設等政治或政策性的分析,另一個路徑是傾向于遵照歷史傳統、注重文化建設和傳統價值引領,顯現出研究缺乏一定的統合性,并未從整體上謀劃鄉村治理的進路和宏觀性趨向。根植于我國農村發展階段、社會治理境況、鄉村演化態勢,黨的十九大提出了鄉村振興戰略這一個農村社會發展總規劃,治理有效作為鄉村振興基礎自當貫穿其中,并從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力量、現代規則完善和文化價值維系等層面來整體推進鄉村社會治理,完善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
鑒于此,要立足科學分析我國鄉村社會發展現實、借鑒學習國外鄉村治理發展經驗,更好地把握社會轉型躍進的內在規律,回答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鄉村社會治理的重大方向性問題,探索不同發展階段、不同類型、不同地區鄉村的社會治理途徑和治理目標,對未來30年鄉村社會治理發展做出具有中國獨特性和世界眼光性的展望和預測,從中國特色中提煉出一般規律,貢獻鄉村發展的中國經驗。結合新時代條件下我國鄉村社會治理問題,需要考慮如下4個重要因素:一是當前正處在一個新時代,鄉村社會治理的基礎、社會結構、社會秩序等都已急劇動遷,新時代農村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社會基本矛盾等都發生了重大變化;二是我國的一個發展目標是在保持鄉村獨立性和差異化的基礎上實現城鄉融合,以此消解發展的不平衡性和不充分性,新時代我國農村社會是一個由多元主體合作治理的社會;三是鄉村振興戰略為未來一個時期農村發展和鄉村治理謀劃了中長期前景,新時代設想規劃與現實發展差距需要大家來填補,新征程中的新問題和新狀況需要大家來解決,未來發展路徑和具體模式道路需要大家來探索;四是農村治理模式創新必須關注我國農村區域間明顯存在的非均質特征——橫向的異質性與縱向的發展不平衡性,不同農村在區位、交通、資源、功能定位等方面存在差異,其發展路徑和進度必然無法同步,各地應根據條件選擇適宜的治理組合、治理體系和善治類型。
明晰了下一步深化研究所應注意的時代基礎和視角問題,認為未來鄉村社會治理研究可以聚焦以下層面并尋求可突破實現的幾個目標。其一,探尋未來30年鄉村治理的重大方向。著眼于新時代鄉村社會治理面臨的重大變化與中央的新要求,沿循鄉村振興的戰略愿景,科學分析我國鄉村發展現實、借鑒學習國外鄉村治理經驗,回答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鄉村治理的重大方向性問題。其二,把握社會轉型躍進的內在規律。結合我國鄉村治理的歷史梳理和全球農村發展的世界性對比,總結歷史經驗中社會變革的發生規律,挖掘促成社會治理深刻變遷的基礎性因素。其三,分類推進“實體治理”。由于我國農村社會存在廣泛的區域差異性,鄉村治理不存在統一的、理想化模式,要區分平原、山區、丘陵等不同地域,區別城市化地區、農產品主產區和重點生態功能區等不同主體功能類型的農村區域發展,運用治理適用性和實效性的“實體治理”策略,避免實施機械式治理,探索不同類型、不同發展階段、不同地區農村的社會治理途徑和治理目標。其四,構建鄉村治理現代化指標體系。對未來30年我國鄉村治理分3個階段(2022、2035、2050年),探討社會治理現代化的基本要件和發展要件。其五,展望鄉村發展模式。面向鄉村振興戰略所謀劃的未來30年鄉村發展,分3個時間節點、分類別提出鄉村社會治理模式,構想未來不同時期農村發展趨向、特征、模式等社會圖景,并提出相應的構建路徑。
參考文獻
[1]狄金華,鐘漲寶.從主體到規則的轉向:中國傳統農村的基層治理研究[J].社會學研究,2014(5):73-97.
[2]冷向明,范田超.流動中的鄉村:社會基礎變遷與有效治理實現[J].求實,2016(1):90-96.
[3]鄧大才.走向善治之路:自治、法治與德治的選擇與組合——以鄉村治理體系為研究對象[J].社會科學研究,2018(4):32-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