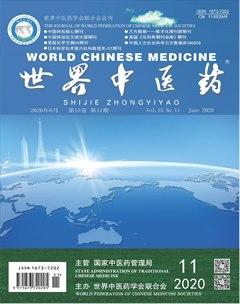拔罐療法的臨床及其生物學機制研究
陳勇 陳波 陳澤林 郭義 孟向文 徐枝芳 蒙秀東 裴瑩 張青穎 公一囡 李檸岑 吳越



摘要 本文系統總結了我們團隊在拔罐研究中所取得成果。考證了拔罐療法的源流發展;提出“針之理即罐之理”“天人地層次理論”和“象思維”應用于拔罐;明確了拔罐補瀉的操作方法,創立了推拿罐療法;總結了拔罐療法的適應病譜,開展優勢病癥的拔罐臨床療效觀察;機制研究發現,拔罐通過改善能量代謝,調節免疫等多途徑起效;并開發拔罐儀器,制定拔罐的相關標準,編寫拔罐教材與專著;創建了全國性學術組織,推動了拔罐療法的應用。
關鍵詞 拔罐;理論;拔罐技術;推拿罐;臨床;作用機制;標準
Abstract The results of the author′s team in cupping research were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s in the paper.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cupping therapy were checked.The theories of “cupping and acupuncture have the same mechanism”,“heaven-human-earth hierarchy theory” and “manifestation thinking” were proposed and applied in cupping therapy.The cupping reinforcing-reducing method was defined,the Tuina cupping therapy were founded.The indication spectrum was summarized.The clinical observation of cupping′s predominant disease was carried out.Experimental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cupping works by many ways including improving energy metabolism and regulating immunity.We have developed cupping instruments and cupping standards and compiled cupping textbooks and monographs.We have established a national academic organization to promot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upping exchanges.
Keywords Cupping; Theory; Cupping technology; Tuina cupping; Clinical; Mechanism; Standard
中圖分類號:R246.9文獻標識碼:Adoi:10.3969/j.issn.1673-7202.2020.11.026
拔罐療法歷史悠久,應用廣泛,因為其簡便廉驗深受人民喜愛。歷經數千年的發展,拔罐療法取得了較大的進步,例如拔罐的應用形式越來越豐富,現在已有的應用形式包括留罐、刺絡拔罐、閃罐、走罐、針罐、溫針罐、藥罐、水罐等[1]。但是拔罐療法缺乏系統的研究,例如拔罐的源流發展、指導理論、適應疾病譜、臨床療效和作用機制等研究未被重視,這些影響了拔罐療法的進一步的推廣應用。筆者所在單位是中國針灸學會刺絡與拔罐專業委員會的掛靠單位,團隊多年以來致力于拔罐理論、臨床、作用機制、罐具、臨床推廣等方面的研究。本文將對本團隊在拔罐研究中取得的成果進行總結,現將研究結果介紹如下。
1 拔罐療法源流考
1.1 考證了最早的拔罐療法采用水煮罐法 拔罐療法最早可以追溯到《五十二病方》中的角法,《五十二病方》曰:“以小角角之,如熟二斗米頃,而張角,系以小繩,剖以刀,其中有如兔,若有堅血如末而出者,即已”。“以小角角之,如熟二斗米頃,而張角”就包含了角法的操作工具、操作部位、吸拔方法及吸拔時間。“小角”是牛、羊、鹿等頭上的角,是當時角法的操作工具;“角之”是操作部位,用動物的小角觸抵病灶,據考證這里的“之”指的是“牡痔”;“如熟二斗米頃”說的是操作方法和吸拔時間,用水煮熱小角,即水煮角法,也叫煮熱角法,吸拔時間則大概像煮熟二斗米的時間一樣長;“張角”則是說操作完后,取罐時用一定的力將小角拔下來。這說明作為拔罐療法最早的角法,采用的是水煮角法來獲得負壓[2]。唐代開始出現竹罐,以水煮竹罐吸拔法為主。王燾的《外臺秘要》記載:“取三指大青竹筒,長寸半,一頭留節,無節頭削令薄似劍,煮此筒子數沸,及熱出筒,籠墨點處,按之良數數如此角之,令惡物出盡,乃即除,當目明身輕也”,就是最早關于水煮罐吸拔法的記錄。宋元時期竹罐完全取代了角制罐,元代在運用竹罐的基礎之上發展出最早的藥罐。清代因為陶瓷技術逐漸成熟,隨之出現了瓷罐,吸拔方法主要是火力排氣法。趙學敏的《本草綱目拾遺》中首次出現了“火罐”一詞,并沿用至今。
1.2 總結出走罐技術具有的五大作用 近代以來,隨著技術的不斷進步,出現了玻璃罐、真空抽氣罐、電罐、橡膠罐、間歇式拔罐裝置、多功能震動按摩拔罐器等多種新型罐具,拔罐方式也出現了留罐、刺絡拔罐、閃罐、走罐等各種方式[3],其中走罐法是從上世紀50年代發展起來的拔罐技術[4]。走罐,將2 400多年的拔罐技術從靜態拔罐到動態拔罐,能實現針、灸、藥、推、罐多種療法的綜合效果,非常值得推廣和發展[50]。后又發展出天人地三部走罐法,通過不同的走罐手法與走罐方案的結合,可產生溫灸、火罐、刮痧、按摩和藥物的不同的作用[11]。
1.3 證明拔罐療法是世界共同療法 我們不僅考證了中國拔罐療法的源流發展,也研究了其他國家拔罐療法的源流和現狀。拔罐療法在古埃及,古希臘,古印度等地區就有記錄,并一直被廣泛使用[5]。公元400年前,希羅多德記載了埃及醫生已經用拔罐放血療法治療疾病。伊朗同樣也運用拔罐療法,一千年前伊朗著名醫生Avicenna的著作《醫學經》是研究伊朗放血拔罐(或稱Hijamat)最早的資料。現狀,拔罐療法也已傳播到中東、歐洲等其他國家,受到世界各地人民的青睞。在中東地區,埃及、巴基斯坦、摩洛哥、沙特阿拉伯、伊朗、伊拉克、以色列、土耳其等國家均使用拔罐療法治療疾病,他們多使用刺絡拔罐療法,即稱之為Al-hijamah的療法[5]。在歐洲,拔罐療法是德國、捷克、烏克蘭、英國、荷蘭等國家的補充替代療法,抽氣罐和刺絡拔罐是常用的拔罐療法[5-7].拔罐療法是世界各國人民與疾病之間長期斗爭中的寶貴財富,也是人類智慧的結晶。拔罐療法在世界醫學史上起著重要的作用,是世界傳統醫學的共同財富。
2 提出“罐之理即針之理”,研究了拔罐療法的“天人地”層次理論和拔罐療法“象思維”法
2.1 罐之理即針之理 我們認為拔罐療法與針灸療法同屬于中醫的體表刺激療法,提出拔罐療法與針灸療法的作用機制有共通之處,罐法、針法同理。從理論同源、治神守神、辨證施力及辨證施術等角度進行了論述。體表是針刺和拔罐的作用部位,針破皮刺入,作用較深,可達皮、脈、肉、筋和骨,但拔罐不破皮,僅作用于皮膚,故相對來說,作用部位較淺。若吸力較大,也可作用于筋肉。由于罐口多較寬廣,故施術時作用部位可認為是以十二皮部為主,而針較細小,作用以經脈腧穴為主,二者理論同源皆以中醫理論為指導,只是應用實踐技術上有同有異[8-9]。
2.2 提出“天人地層次理論”應用于走罐 傳統醫學認為人體是按一定的層次結構組成的有機體。關于不同層次病證的針灸治療,《素問·刺要論》提出了基本原則:“病有浮沉,刺有淺深,各至其理,無過其道”。病有在皮脈肉筋骨的不同深淺層次,治療上也應注意力深淺的不同。陳澤林教授以《金針賦》“初針刺至皮內,乃曰天才;少停進針,刺入肉內,是曰人才;又停進針,刺至筋骨之間,名曰地才”為綱領,提出“力有大小,三才分布”的施治原則,即力的大小是施治淺深的關鍵,三才分布可以衡量治療效應的深淺。在此理論基礎上,陳澤林教授首次提出將天人地層次理論應用于走罐療法中,使走罐具有拔罐、溫灸、推拿、藥物和刮痧的作用[10-12]。天人地三部走罐法是指通過控制走罐的時間、速度、吸罐力的大小及通過不同的手法組合,使走罐的力作用于機體的不同層次,產生不同的臨床效果的一種走罐方法。天部走罐法的走罐時間短(5~10 min),走罐速度快(25~50 cm/s),吸罐深度淺(1~5 mm);人部走罐法的走罐時間較長(10~20 min),走罐速度較慢(10~20 cm/s),吸罐深度較深(5~10 mm);地部走罐法的走罐時間長(20~30 min),走罐速度慢(2~5 cm/s),吸罐深度深(10~20 mm)[11]。為達到天人地3個層次走罐的效果,陳澤林教授根據多年的臨床經驗對走罐技術進行創新,系統總結了15種走罐的基本手法,并制定了10種臨床常用走罐方案,豐富了走罐的操作手法。15種基本手法包括:響罐法、單罐單向走罐法、單罐雙向走罐法、螺旋走罐法、雙罐分段走罐法、雙罐往返走罐法、雙罐弧形走罐法、旋響復合走罐法、定點旋罐法、定點旋搖罐法、定點搖響罐法、定點振響罐法、定點推撥罐法、罐體溫熨法、蛇形走罐法。10種臨床常用走罐方案包括:肩胛“][”形方案、肩腰“][”形方案、肩脊“個”字方案、上焦“三角”方案、中焦“方形”方案、下焦“井”形方案、腰骶“八”字方案、四肢方案、面部方案、腹部方案[11-12]。
2.3 研究拔罐療法中的“象思維”
2.3.1 “辨象施治” 在中醫理論體系中,“象”無處不在,如“藏象”“脈象”“舌象”等[13]。中醫四診通過診察外在的“象”可以推導內在臟腑的變化。據《靈樞·本藏》記載:“視其外應,以知其內臟,則知所病矣”,《靈樞·論疾診尺》記載:“從外知內”,《丹溪心法》記載“欲知其內者,當以觀乎外;診于外者,斯以知其內。蓋有諸內者形諸外”,這就是說通過診查其外部的象征,便可知道內在的變化情況。人體之象,藏象是根本。陳澤林教授提出藏象表現在外的有皮、脈、肉、筋、骨五體之象[10]。而與拔罐密切相關之象,是皮象、脈象、筋象以及伴隨拔罐而出的痧象。所謂“皮象”,是臟腑功能在體表皮部的神色形態的反映,病理上表現為皮膚腠理的形態神色變化,如皮膚疏松或緊密、潰瘍點、皮疹、皮屑增多等;而皮象有色者或在體表施治吸拔力或摩擦擠壓力后所反應出來的皮象,我們則稱之為“痧象”。所謂“筋象”則是筋表露出來的顏色明暗色差、位置深淺、方向偏正、形態粗細曲直、性質急緩軟硬、感覺喜按或惡按以及溫度的寒熱溫涼等征象。皮象、痧象、筋象可反應病情的寒熱虛實及氣血陰陽盛衰。“辨象施治”理論就是根據“象”的性質特點與部位,分析病位病性,確定在臟腑、經絡、經筋、還是腧穴施以拔罐治療,以及拔罐的手法和刺激量的大小頻率等。
2.3.2 “度筋診病” 在“象思維”思維的基礎上,陳澤林教授提出“度筋診病”應用于拔罐,為拔罐的臨床診治提供依據。“度筋診病”是指揣度測量形體、筋骨、經筋以判斷機體狀態、疾病部位性質,從而采取相應的治療。若筋象的異常范圍小、硬度表現低,說明病程較短、病邪較淺;若筋象面積大、硬度高,說明病程較長、病邪較深。筋軟多屬熱證,筋硬多屬寒證、瘀證。根據“度筋”的表現判斷患者的狀態及疾病的性質,然后來決定施治原則,施治的手法、時間、療程等[10]。
2.3.3 “察痧辨病” 我們比較系統地研究了罐斑對診斷疾病的影響[14],提出了“察痧辨病”的概念[10]。“察痧辨病”是根據拔罐施治后的痧象來進一步判斷疾病的部位、性質等,可以為后續的治療方案及預后提供依據。比如背部心肺對應的位置出痧,說明心肺有問題。一般痧色鮮紅,呈點狀散痧,顏色淺淡,多為表癥,病程短,病情輕;若出痧較多,且點大成塊、呈斑片狀或瘀塊,痧色暗紅,多為里癥,病程長,病情重。痧色鮮紅為熱,痧色青暗為寒。鮮紅而艷,一般提示陰虛、氣陰兩虛,陰虛火旺也可出現此印跡。發紫伴有斑塊,一般提示寒凝血瘀;呈散紫點、深淺不一,一般提示氣滯血瘀,多出現在肝區及胃區;淡紫發青伴有斑塊,一般以虛證為主、兼有血瘀,如在兩腎處呈現則提示腎虛[10]。
3 提出拔罐補瀉的操作方法,創立推拿罐療法
3.1 拔罐補瀉的操作方法 針刺手法有補法和瀉法,郭義教授和陳澤林教授在臨床中均發現拔罐也有補法和瀉法[9,15]。《難經·七十八難》曰:“得氣,因推而內之,是謂補”,“動而伸之,是謂瀉”。在拔罐操作中,將罐體吸拔于腧穴機體之后,手持罐體,垂直按壓罐體,使罐力由外部向下向深部滲透,導氣內入,調氣補虛為補法;而在刺激量上,當吸附力輕,動作緩和,潤滑劑相對較多,推拿罐時間長,速度慢,罐口經過處以皮膚紅潤,不出瘀斑時也屬于補法,補法適用于久病老人、兒童及體質羸弱、病情偏于虛證者。拔罐操作中,手持罐體,向上向外提拉罐體,使罐力由深部向外擴散,引氣外出,運氣瀉實為瀉法;在拔罐刺激量上,當吸罐深度深,重按急摩,潤滑劑相對較少,推拿罐時間短,速度快,罐口下皮膚以明顯瘀痕為主時屬于瀉法,拔罐后在病灶局部的穴位或相應背部腧穴上通過留罐5-10分鐘加強刺激量,激發其穴位功能,促進其氣血運行,從而有利于病灶局部的疏通,以達到瀉實之功用,瀉法適用于新病、體壯、中青年及病情偏于實證者[10,15]。也可從拔罐迎隨、提壓和旋轉方向來定補瀉。罐法迎瀉、隨補,當依營衛運行和經脈往來為據,隨其循行逆順來進行走罐;罐法提按補瀉方面,補法以重壓輕提為主,引導陽氣入里,瀉法以重提輕壓為主,引導邪氣外出;罐法旋轉補瀉方面,拔罐時拇指向前左轉時用力重為補,拔罐拇指向后右轉時用力重為瀉[9]。
3.2 推拿罐療法 經過兩千多年的發展,拔罐療法經歷了從靜態的留罐法到動態的閃罐法、走罐法的過程[4]。陳澤林教授在臨床應用中發現“走罐”的推拉動作相當于推拿手法的推法和擦法,在應用拔罐罐具吸拔治療的同時,將罐具作為推拿按摩工具在軀體特定部位上施以特定推拿手法,這種療法既具有拔罐的吸拔作用,又將拔罐罐具作為推拿工具,在體表皮膚上動態吸拔罐具,是拔罐療法和推拿療法的有機結合,可使效應累積,實現1+1>2的效果,由此提出了“推拿罐療法”[10]。推拿罐療法分為:吸拔罐前的操作手法、吸拔罐后在罐體進行的操作手法和拔罐后配合主動運動或被動運動3個部分。吸拔罐前的操作手法包括:擊罐、叩罐、滾熨罐、點壓罐、點揉罐、摩罐;吸拔罐后在罐體進行的操作手法包括:閃罐、留罐、揉罐、推摩罐、擦罐、推罐、拉罐、搓罐、抹罐、按壓罐、振顫罐、拿罐、搖罐、刮罐、撥罐、拍罐、提罐、旋罐;拔罐后配合運動包括:拔罐后配合主動運動和拔罐后配合被動運動,拔罐后配合主動運動是施術者在實施推拿罐手法的同時,指導受術者主動活動肌肉,或者主動振奮精神活動,以調動受術者潛能。推拿罐配合被動運動包括:抖法、遠端搖動關節法、扳法、拔伸法等。
4 總結拔罐療法的適應病譜,研究拔罐優勢病種的臨床療效
臨床研究方面,我們系統總結了拔罐療法的臨床應用,按照國際標準歸類罐療(走罐、拔罐)的適宜病癥,制定拔罐療法適應病譜。我們采用回顧性期列研究,檢索知網中國期刊數據庫種拔罐療法所有臨床研究文獻,統計拔罐療法、走罐療法、罐療法治療疾病的文獻頻次、病例總數,采用循證醫學的方法和原則把文獻分類分級,根據世界衛生組織有關疾病和關于健康問題的國際統計分類(ICD10)把疾病分類,運用臨床循證醫學的原則與方法對文獻進行簡要分析。在拔罐療法適宜病癥的第一次研究中,我們共檢出有效文獻3 504篇,共計病例289 195例,共涉及19大類系統,病種363個[16]。在走罐療法適宜病癥的研究中,檢出有效文獻470篇,共計病例32 644例,共涉及16大類系統,130個病種[17]。1年后,在罐療(拔罐、走罐、藥罐等)適宜病癥的研究中,檢出有效文獻3 987篇,共計病例409 679例,共涉及20大類系統,456個病種[18]。
在總結拔罐適宜病癥譜基礎上,我們選擇了拔罐優勢病種如頸椎病、亞健康狀態、慢性疲勞綜合征等,應用隨機對照試驗客觀評價拔罐療效。刺絡拔罐療法治療神經根型頸椎病的臨床研究表明治療后患者疼痛程度普遍降低,頸部功能障礙及生命質量大幅度改善,神經根型頸椎病的臨床指標也有好轉[19-21]。走罐結合推拿治療椎動脈型頸椎病的臨床療效觀察試驗中,我們發現走罐配合推拿治療效果優于單純針刺治療[22]。走罐療法干預亞健康狀態臨床研究表明走罐療法對包括失眠、疼痛、腰痛、筋膜炎等在內的亞健康狀態有明顯療效[23-25]。定壓拔罐法干預慢性疲勞綜合征臨床研究發現,定壓拔罐可顯著改善慢性疲勞綜合征人群疲勞,睡眠,情緒等方面癥狀[26]。另外,我們還通過隨機對照試驗研究發現拔罐療法對肥胖、初期高血壓、慢性腰骶痛、慢性盆腔炎等疾病具有較好療效[27-34]。
5 開展拔罐起始動力學機制研究
拔罐療法與針灸療法同屬于體表刺激療法,都是通過刺激特定的經絡腧穴或體表部位而起到治療疾病的,因此在作用基礎與機制上應有相通之處,腸-腦-皮軸可能在其中發揮重要作用[35]。團隊在前期針刺作用機制研究中發現,首先引起體表刺激部位微環境的變化,使物理信號轉化為生物信號,局部相關信號分子相互作用、相互影響,使效應級聯放大,進而激活機體內神經-內分泌-免疫(NEI)網絡,產生整體調節效應。因此,我們認為拔罐療法可能也是通過局部相關細胞、因子的調節,激活機體內神經-內分泌-免疫(NEI)網絡,產生整體調節效應的[8,36]。經過研究發現,拔罐影響了穴位局部能量代謝狀態和神經-免疫調節。因此我們認為,拔罐可能通過改變局部的能量代謝和局部神經-免疫調節機制而起效的[37-38]。
5.1 拔罐起始動力學機制可能與局部能量代謝有關 我們的研究顯示拔罐后穴位局部的能量代謝狀態發生了改變,穴位局部溫度、血流灌注量、氧分壓可觀察到明顯的變化。拔罐健康人大椎穴觀察督脈穴表溫度,拔罐后督脈穴位皮溫升高,且5 min后升高最顯著,而后趨于平穩[39];用激光多普勒血流儀對健康人背部拔罐部位拔罐前后血流量進行掃描,發現拔罐可使局部組織充血,血流加快,血流量增高,且拔罐后血流量隨著時間而逐漸降低,到20 min時基本恢復至拔罐前水平[40-42];走罐后可引起局部經皮氧分壓升高,二氧化碳分壓先下降后緩慢回升。見圖1。這可能與增加局部血流量有關[43-44]。同時,我們發現拔罐后家兔外周血細胞因子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EGF)明顯升高,這也可能是拔罐擴張和改善局部微血管的分子機制[45-46]。基于以上實驗結果,我們認為拔罐可能是通過升高局部溫度→擴張血管→提高血流量→增加組織氧供及加快新陳代謝產生作用從而產生治療效應的。
5.2 拔罐起始動力學機制可能與局部神經、免疫調節有關 在拔罐大鼠耐缺氧效應平臺上,我們采用免疫組化檢測了拔罐局部包括P物質、組胺、五羥色胺等神經遞質的表達。見圖2。拔罐穴區局部P物質、組胺、五羥色胺明顯增加[28],拔罐促使穴位局部釋放神經遞質,可能是激活了穴位局部的神經調節。在拔罐大鼠耐缺氧平臺上,我們利用HE染色技術觀察拔罐局部炎性細胞的浸潤情況,見圖3,結果發現顯示拔罐組在組織間隙中可見紅細胞及大量炎性細胞浸潤[28]。在刺絡拔罐內毒素致熱家兔退熱效應平臺上,我們發現刺絡拔罐法退熱機制可能與提高抗炎因子水平,抑制中樞iNOS、COX-2蛋白表達水平[47],見圖4,和抑制炎性細胞因子水平,如IL-1β、GM-CSF、IL-6、TNF-α等水平,見圖5,調節機體免疫功能有關[48]。拔罐促進局部免疫細胞和免疫因子的釋放,激發穴位局部免疫調節。
6 促進臨床轉化應用,推廣拔罐研究成果
6.1 開發拔罐儀器 推拿罐療法需要在拔罐之后進行大量的手法操作,普通的玻璃罐質地較硬,大量的手法操作可能會對肌肉等組織造成損傷,針對這種情況,團隊開發了一種硬度合適的罐具——砭石罐。砭術是古代中醫的醫術之一,其關鍵因素就是砭石。砭石本身含有大量對人體有益的稀土和微量元素,有研究表明砭石可以顯著加快微循環的的血流速度,促進血液微循環,調理新陳代謝。以砭石為原材料研制罐具,不僅可以使患者的痛苦減少,促進血液循環,而且其本身的微量元素也有益于人體。砭石還經常用于刮痧,運用砭石罐進行推拿罐操作也可以達到刮痧的效果。砭石罐的應用使推拿、拔罐、刮痧3種療法合而為一,可以提高臨床療效,也可以促進推拿罐療法的推廣。同時,團隊的郭義教授深入研究玻黃銅的特性,研制了黃銅罐具。
6.2 制定拔罐標準 拔罐標準的研究也是團隊重要研究方向之一,團隊負責人郭義教授領銜主持了ISO/TC249項目:ISO/NP2221《傳統玻璃罐具》項目。由團隊指導完成的中華中醫藥學會團體標準《中醫治未病技術操作規范》中規范了拔罐操作[49]。目前團隊正在主持科技部重大專項課題“拔罐技術操作規范國際標準”的制定。
6.3 編寫拔罐教材與專著 除此之外,團隊將拔罐研究成果編寫成教材與專著,目前已出版《圖解推拿罐療法》,詳細介紹本團隊創立的推拿罐療法。同時,正在組織全國專家撰寫高等中醫藥院校創新教材和《中醫拔罐療法》,將本團隊的研究成果寫入教材中。團隊拔罐研究成果也已在本科生中開設課程,在《中醫拔罐療法》《拔罐與刺絡放血療法》選修課中介紹拔罐研究成果。
6.4 創建拔罐全國性學術組織,促進國內、國際拔罐交流 為更好的應用和開展拔罐療法研究,團隊負責人郭義教授牽頭成立了中國針灸學會刺絡與拔罐專業委員會。郭義教授擔任第一屆和第二屆的主任委員,陳澤林教授擔任第一屆和第二屆的秘書長并擔任第三屆的主任委員,陳波博士擔任第三屆的秘書長。中國針灸學會刺絡與拔罐專業委員會有會員500余人,每年舉辦多種形式的學術交流,創會以來共舉辦了10次全國性大會,參加國外刺絡拔罐學術交流3次,有力地推動了拔罐的國內外研究域應用。同時學會每年與日本刺絡學會聯合舉辦學術交流,多次講授推拿罐技術。團隊也在江西、四川等全國各地組織學術會議,與全國各地同行進行天人地三部走罐法、推拿罐療法、刺絡拔罐法交流。
7 展望
中國民間常說:“扎針拔罐,病好一半”,拔罐作為中外共同的療法,是具有深厚的群眾基礎的。我們團隊在拔罐研究中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較多成果。當然,要讓這種療法發揚光大,還有很多工作要做。希望在中國針灸學會刺絡與拔罐專業委員會領導下,同時在世界上熱愛傳統醫學的專家們的支持下,拔罐療法取得更大的突破,為世界人民的健康發揮更大的作用。
參考文獻
[1]El-Shanshory M,Hablas NM,Shebl Y,et al.Al-hijamah(wet cupping therapy of prophetic medicine)significantly and safely reduces iron overload and oxidative stress in thalassemic children:a novel pilot study[J].J Blood Med,2018,9:241-251.
[2]陳澤林.中國罐療法溯源——《五十二病方》角法研究[J].天津中醫藥,2013,30(2):87-89.
[3]張潔,李中正,李桂蘭,等.中國罐具發展簡史[J].湖南中醫雜志,2011,27(1):95-97.
[4]蒙秀東,齊婧蕾,祝秋梅,等.“走罐”源流考[J].亞太傳統醫藥,2019,15(2):71-73.
[5]陳波,郭義,陳澤林,等.拔罐——世界傳統醫學的共同財富[J].世界針灸雜志:英文版,2016,26(3):1-6,13.
[6]崔媛,陳澤林.歐洲拔罐療法的發展與現狀[J].中華針灸(連續型電子期刊),2014,(3):134-136.
[7]林為棟,王潁,孟向文,等.拔罐療法在世界各地的發展現狀[J].中醫藥導報,2016,22(18):6-8.
[8]陳波,王婷婷,余偉佳,邢立瑩,李檸岑,郭義,陳澤林.罐之理即針之理[J].中華中醫藥雜志,2017,32(9):4174-4176.
[9]吳越,李宛蓉,張闊,等.試述罐法針法同理[J].中醫藥學報,2018,46(3):1-3.
[10]陳澤林.圖解推拿罐療法[M].北京: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2017:24-30.
[11]陳波,陳澤林,郭義,等.罐療之走罐研究——天人地三部走罐法[J].中國針灸,2010,30(9):777-780.
[12]余楠楠,陳澤林,陳波,等.天人地三部走罐法的內涵釋解[J].上海針灸雜志,2015,34(3):260-264.
[13]杜旭,陳澤林.試論“筋象”與拔罐療法的“度筋論治”[J].中國針灸,2019,39(5):541-544.
[14]黃松,宋黎濤,盛偉華,等.磁共振平掃及波譜成像對新生兒膽紅素腦病診斷價值[J].中國實驗診斷學,2016,20(10):1685-1687.
[15]陳向紅,陳澤林,陳波,等.淺論拔罐療法補瀉——推而內之是謂補,動而伸之是謂瀉[J].中國針灸,2018,38(3):243-244.
[16]李霞,陳波,李春燕,等.拔罐療法適宜病癥初探[J].針灸臨床雜志,2012,28(10):44-47.
[17]于海龍,陳波,陳澤林,等.走罐療法適宜病癥淺析[J].天津中醫藥大學學報,2012,31(1):50-53.
[18]余楠楠,武虹波,劉佩東,等.罐療適宜病癥詳探[J].針灸臨床雜志,2013,29(7):66-70.
[19]藍秀蘆,孟向文.關于刺絡療法治療神經根型頸椎病療效評價的討論[J].中華針灸刺絡療法雜志,2011,12,7(2):45-47.
[20]孟向文,樸盛愛,朱成慧,等.刺絡療法治療神經根型和頸型頸椎病臨床初步研究,中華針灸刺絡療法雜志,2012,1(8):41-49.
[21]畢瓦可.刺絡療法治療神經根型和頸型頸椎病臨床初步研究[D].天津:天津中醫藥大學,2012.
[22]李飛,余楠楠,陳澤林.走罐結合推拿治療椎動脈型頸椎病療效觀察[J].山西中醫,2015,31(1):28-29.
[23]朱必偉,童登祿,陳澤林,等.督脈三部走罐法干預亞健康失眠癥臨床療效觀察[J].天津中醫藥,2013,30(6):336-338.
[24]王艷.拔罐治療慢性非特異性下腰痛的臨床研究[A].北京:中國針灸學會.2017世界針灸學術大會暨2017中國針灸學會年會論文集,2017.
[25]趙曉瑤,李飛,陳澤林,等.走罐結合刺絡拔罐及推拿治療腰背肌筋膜炎療效觀察[J].山西中醫,2015,31(5):27-28.
[26]蒙秀東,郭昊然,齊靜蕾,李檸岑,祝秋梅,陳波,陳澤林.定壓拔罐干預慢性疲勞綜合征相關性評價指標臨床分析[J].山東中醫雜志,2019,38(10):943-946.
[27]王艷.基于期刊文獻的拔罐療法疾病譜及拔罐治療NLBP的臨床研究[D].天津:天津中醫藥大學,2016.
[28]余偉佳.基于大鼠耐缺氧的拔罐療法時效-位效作用規律及機制初步研究[D].天津:天津中醫藥大學,2018.
[29]柳昌希.推拿罐療法干預血壓的臨床觀察及機制初步探討[D].天津:天津中醫藥大學,2019.
[30]蒙秀東.拔罐療法治療慢性疲勞綜合征的作用規律研究[D].天津:天津中醫藥大學,2019.
[31]齊婧蕾.基于蛋白組學及復雜網絡分析的拔罐耐缺氧作用機制研究[D].天津:天津中醫藥大學,2019.
[32]張嘉殷.拔罐治療單純性腹型肥胖的文獻及臨床療效觀察[D].天津:天津中醫藥大學,2019.
[33]李飛.推拿罐干預椎動脈型頸椎病的臨床療效及對頸部局部皮膚微循環灌注量的研究[D].天津:天津中醫藥大學,2019.
[34]程曉燕.基于期刊文獻的走罐療法疾病譜及走罐干預CPID合并盆腔積液的臨床研究[D].天津:天津中醫藥大學,2019.
[35]陳柳伊,弓明燕,陳澤林.對腸-腦-皮軸及其與中醫聯系的思考[J].中華中醫藥雜志,2019,34(1):275-277.
[36]Guo Y,Chen B,Wang DQ,et al.Cupping regulates local immunomodulation to activate neural-endocrine-immune worknet[J].Complement Ther Clin Pract,2017,28:1-3.
[37]梁友和,劉迪生,洪壽海,等.拔罐防治亞健康狀態整體調節機制探討[J].遼寧中醫雜志,2014,41(9):1886-1887.
[38]洪壽海,吳菲,盧軒,蔡青,郭義.拔罐療法作用機制探討[J].中國針灸,2011,31(10):932-934.
[39]李超群,孟向文,郭義,等.大椎穴拔罐前后對健康成人膀胱經穴表溫度變化影響的研究[J].針灸臨床雜志,2011,27(5):18-20.
[40]LIU Wei,PIAO Sheng-ai,MENG Xiang-wen,WEI Lian-hai,LIU Zhao.Effects of cupping on blood flow under skin of back in healthy human[J].World J Acupunct Moxibustion,2013,23(3):50-52.
[41]金蘭,劉陽陽,孟向文,等.拔罐對健康人體背部皮膚血流量影響的初步觀察[J].針灸臨床雜志,2010,26(11):4-5.
[42]趙義靜,劉佩東,陳澤林,等.不同參數督脈走罐對亞健康人體背部局部皮膚血流量影響的初步觀察[J].天津中醫藥大學學報,2015,34(1):18-22.
[43]孟向文,李超群,郭義.大椎穴拔罐前后對健康成人左肺俞及其旁開非經穴的氧分壓變化的影響[J].上海針灸雜志,2012,31(4):274-276.
[44]ZHAO Yi-jing,CHEN Ze-lin,ZHOU Dan,GUO Yi.Effect of sliding-cup along governor vessel on tcpO2 and tapCO2 in Mìngmén(GV 4)point of sub-healthy humans:observation on different cupping pressure[J].World Journal of Acupuncture-Moxibustion,2015,25(3):11-16.
[45]劉華朋,楊靜,朱成慧,等.拔罐療法對寒凝血瘀型家兔局部皮膚相關因子影響的實驗研究[J].吉林中醫藥,2018,38(1):76-79,前插1.
[46]朱成慧,孟向文,劉華朋,等.拔罐療法干預寒凝血瘀證家兔模型細胞因子的實驗研究[J].針灸臨床雜志,2017,33(2):58-60.
[47]裴瑩,陳澤林,金穎,等.刺絡拔罐法對內毒素致熱家兔的退熱作用及機制研究[J].中華中醫藥學刊,2019,37(7):1588-1592.
[48]裴瑩,陳澤林,金穎,等.刺絡拔罐法對內毒素致熱家兔血清細胞因子水平的影響[J].中華中醫藥學刊,2019,37(6):1385-1388.
[49]中華中醫藥學會.T/CACM1078-2008中醫治未病技術操作規范·拔罐[S].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19.
[50]王謐,李月,陳澤林.拔罐療法概述與走罐手法述要[J].天津中醫藥大學學報,2009,28(4):217-217.
(2020-03-10收稿 責任編輯: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