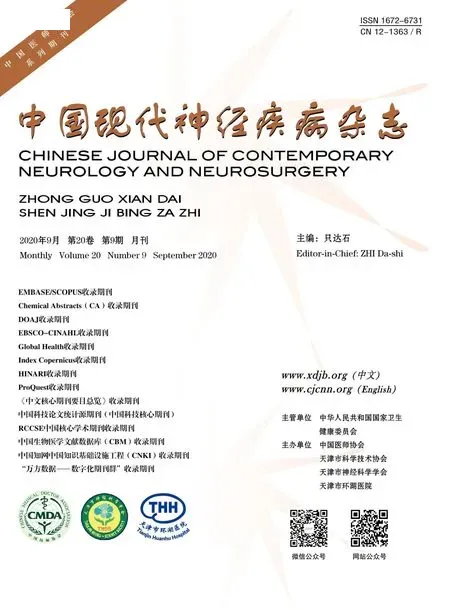免疫相關運動障礙臨床研究進展
石紅琴 孟環宇 梁華峰 陳晟
運動障礙作為臨床常見癥候群不僅是神經變性病的特點,同時亦是感染啟動免疫機制、神經系統自身免疫性疾病乃至免疫相關治療引發疾病的重要臨床表現。例如,Sydenham 舞蹈病(SC)或人類免疫缺陷病毒(HIV)感染所導致的舞蹈病已為人們所熟識,而由神經系統自身免疫性相關抗體所介導的運動障礙則有多種類型,包括富亮氨酸膠質瘤失活基因1(LGI1)抗體誘發的典型運動障礙面-臂肌張力障礙發作(FBDS),以及谷氨酸脫羧酶(GAD)抗體介導的僵人綜合征(SPS)和N-甲基-D-天冬氨酸受體(NMDAR)抗體介導的口-面部運動障礙等。除上述自身免疫性抗體相關運動障礙外,由細胞程序性死亡蛋白1(PD1)抑制劑或嵌合抗原受體T 細胞(CAR-T)療法等所誘發的運動障礙也逐漸引起關注。就發病機制而言,免疫相關運動障礙包括中樞性和周圍性(周圍神經和神經肌肉接頭)運動障礙兩類,其中以中樞神經系統免疫相關運動障礙較為常見。為了使臨床醫師更好的認識免疫相關性疾病、了解免疫調節治療與不同類型運動障礙之間的關系,本文對近年免疫相關運動障礙臨床研究進展進行歸納闡述,以供臨床參考。
一、免疫相關性疾病與運動障礙
1.免疫相關舞蹈病 舞蹈病是免疫相關運動障礙的常見發病形式,其舞蹈樣動作可由感染或自身免疫性腦炎等因素所誘發,兒童舞蹈樣動作的主要病因是Sydenham 舞蹈病;青年女性主要考慮系統性紅斑狼瘡(SLE)和抗磷脂綜合征(APS)相關舞蹈病,呈亞急性發病,表現為單側或雙側肢體舞蹈樣動作,18F-FDG PET 顯像提示紋狀體呈高代謝[1]。成年期發病的舞蹈病病因復雜,HIV 感染是感染性免疫相關舞蹈病較為常見的病因,因此對于無運動障礙家族史但疑似感染是致病原因的成年舞蹈病患者,應盡早施行HIV 檢測[2]。此外,由自身免疫性相關抗體介導的舞蹈病也是成年免疫相關舞蹈病的重要原因,其中副腫瘤性舞蹈病好發于男性,發病年齡較晚,病程中常伴有周圍神經病變和體重減輕[3],除Hu、Yo 抗體等臨床廣泛關注的副腫瘤相關抗體外,與小細胞肺癌(SCLC)、胸腺瘤、結腸癌、腎癌、淋巴瘤等密切相關的塌陷反應調節蛋白5(CRMP5)抗體也與其舞蹈樣動作有關,患者可伴視覺障礙[4]。常見的自身免疫性相關抗體還包括谷氨酸脫羧酶65(GAD65)、接 觸 蛋 白 相 關 蛋 白(CASPR2)[3]、IgLon5[5]和LG1 抗 體[6],這些抗體主要與系統性紅斑狼瘡的發病有關。
2.免疫相關小腦共濟失調 是一組由免疫介導的、呈急性或亞急性發病、快速進展的小腦共濟失調,包括副腫瘤性小腦變性(PCD)、GAD65 抗體相關性小腦共濟失調、麩質共濟失調(GA)等。(1)副腫瘤性小腦變性:是副腫瘤綜合征的臨床常見類型,尤其好發于Yo 抗體陽性的女性病例,可伴發乳腺癌、卵巢癌或其他婦科腫瘤。約有65%的患者在腫瘤確診之前即已出現軀干和肢體共濟失調、構音障礙、眼球震顫等中樞神經系統癥狀與體征,經針對原發腫瘤治療后癥狀可有所改善,但大多數患者預后不良,中位生存期為13 ~22 個月[7];根據文獻報道,亦可見于Yo 抗體陽性合并胃腸道腺癌的男性副腫瘤性小腦變性病例[8]。約有32%的副腫瘤性小腦變性患者Hu 抗體陽性,除累及小腦外,還可有邊緣系統、腦干、周圍神經、自主神經等受累表現,其中65%~75%患者合并小細胞肺癌,后者抗腫瘤治療和免疫調節治療效果欠佳,中位生存期僅7 ~13 個月[9]。電壓門控性鈣離子通道(VGCC)抗體相關副腫瘤性小腦變性僅見于男性,約81%的患者合并小細胞肺癌,44%存在Lambert-Eaton 綜合征臨床或電生理學表現,免疫調節治療反應欠佳,中位生存期約12 個月[10];而VGCC 抗體陽性的非腫瘤性小腦變性患者,免疫調節治療效果良好[11]。約有86%的Ri抗體陽性的副腫瘤性小腦變性患者合并有乳腺癌或肺癌,除表現為小腦共濟失調外,分別有36% ~50%的患者出現斜視性眼陣攣、24%出現頜-頸肌張力障礙或喉痙攣,中位生存期約69 個月[12]。此外,還有霍奇金淋巴瘤(HL)相關Tr 抗體、非小細胞肺癌和胸腺瘤相關CRMP5 抗體導致的副腫瘤性小腦變性的個案報告[13]。代謝性谷氨酸受體1(mGluR1)抗體與小腦共濟失調也有關,部分患者在其共濟失調發生之前即已出現味覺障礙,常伴發霍奇金淋巴瘤,免疫調節治療效果良好[14]。此外,一些少見抗體 如Homer3、CARP Ⅷ、Sj/ITPR1、GluR δ 2、PKC γ、CA/ARGHAP26、Nb/AP3B2 抗體亦可見于小腦共濟失調患者,可合并卵巢癌、乳腺癌、黑色素瘤、膽囊癌、肺癌等[15-17]。(2)GAD65 抗 體 相關 小 腦 共 濟失調:以50 ~60 歲女性好發,呈亞急性或慢性發病,臨床特點為共濟失調與癲發作,并且疊加僵人綜合征[18],常合并自身免疫性疾病,如1 型糖尿病、橋本甲狀腺炎(HT)等[19],糖皮質激素治療后血清和腦脊液GAD 抗體水平下降,癥狀明顯改善[20]。(3)麩質共濟失調:系一種對谷蛋白過敏的自身免疫性小腦共濟失調,常見于40 ~50 歲女性,呈慢性或隱匿性發病,軀干共濟失調明顯重于肢體,約50%患者可同時存在麩質敏感性腸病或伴局灶性肌陣攣、腭震顫等癥狀與體征,血清和腦脊液谷氨酰胺轉胺酶2 和6(TG2 和TG6)抗體陽性[21]。無麩質飲食是首選治療方案,其療效取決于臨床癥狀嚴重程度或小腦萎縮程度,因此一經確診應盡早啟動無麩質飲食[21]。
3. 免疫相關肌張力障礙以及帕金森綜合征
(1)基底節腦炎:臨床表現為孤立性皮質下功能異常,尤以運動障礙如肌張力障礙、帕金森樣癥狀或舞蹈樣動作為主,同時可以伴有嗜睡和精神癥狀。頭部MRI 基底節區T2WI 呈高信號,隨訪期間可見基底節區萎縮和膠質增生。基底節腦炎與多巴胺D2 受體(D2R)抗體陽性密切相關,若于疾病早期施行免疫調節治療,可有效改善臨床癥狀并使D2R抗體水平下降[22],但僅行糖皮質激素治療而未采取與免疫調節藥物聯合治療的患者則殘留神經精神后遺癥且D2R 抗體可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持續位于較高水平[23]。(2)面-臂肌張力障礙發作:是LGI1 抗體腦炎的特征性發作癥狀,表現為單側面部、手臂頻繁而短暫的肌張力障礙樣不自主動作,亦可累及下肢或軀干,每次發作持續數秒,每日發作數次至數十次。有學者將面-臂肌張力障礙發作歸為癲發作,但大部分患者發作期視頻腦電圖檢測不到節律性變化或樣放電[24],因此有學者將其定位于皮質下區域[25]。Flanagan 等[26]發現,面-臂肌張力障礙發作患者頭部MRI 可見發作對側基底節區異常信號,因此更傾向于該病是肌張力障礙而非癲發作。(3)抗NMDAR 腦炎:除精神行為異常、癲發作外,可伴發多種運動障礙,如肌張力障礙、帕金森綜合征等,其中以口-面部運動障礙最具特征性,表現為噘嘴、咀嚼、重復做鬼臉樣動作。抗NMDAR 腦炎好發于青年女性,易罹患畸胎瘤,也可繼發于中樞神經系統感染啟動的免疫反應,單純皰疹病毒(HSV)為其常見病原體,其次為流行性乙型腦炎病毒、EB 病毒、水痘-帶狀皰疹病毒(VZV)、人皰疹病毒6 型等[27-29]。若于單純皰疹病毒性腦炎(HSE)后出現運動障礙,更加提示單純皰疹病毒誘發抗NMDAR 腦炎,而非單純皰疹病毒性腦炎復發[29]。(4)副腫瘤性頜肌張力障礙和喉痙攣:是Ri 抗體相關副腫瘤綜合征的常見伴隨癥狀,發生率約24%,好發于女性,大多數患者合并乳腺癌或肺癌,病情嚴重者甚至可出現進食困難[12]。(5)副腫瘤性帕金森綜合征:主要表現為運動遲緩、姿勢不穩、肌強直、眼球運動障礙等,對左旋多巴治療反應欠佳,常見于Ma1/Ma2 抗體陽性的邊緣性腦炎,除帕金森綜合征外,還可表現為癲發作、快速眼動睡眠期行為障礙(RBD)、發作性睡病、構音障礙、猝倒發作等,MRI 呈現高位腦干,以及丘腦異常信號[30]。Ma2 抗體陽性常見于睪丸腫瘤患者;而Ma1 抗體則高表達于肺癌,其次是睪丸腫瘤,此類患者神經功能預后不良,對免疫調節治療反應較差或完全無反應[31]。Kelch 樣蛋白11(KLHL11)抗體與精原細胞瘤密切相關,KLHL11 抗體陽性的邊緣性腦炎主要表現為共濟失調和復視,與Ma2 抗體陽性的邊緣性腦炎患者不同,KLHL11 抗體陽性患者對免疫治療反應良好[32]。此外,亦有文獻報道LGI1 和CASPR2 抗體可導致帕金森綜合征[33-34]。2006 年,梅奧診所曾報告4 例GAD65 抗體陽性的帕金森綜合征病例,均呈現運動遲緩、垂直性核上性眼肌麻痹表現,此類患者更好發于非裔美國人,免疫調節治療對病情有所改善[35]。(6)HIV 相關帕金森綜合征:發生率約5%,表現為帕金森綜合征的HIV 陽性患者均存在嚴重免疫抑制現象,外周血CD4+T 細胞數目明顯減少[36]。2001 年,Hersh 等[37]曾 報 告1 例HIV 陽 性 的 帕 金 森綜合征患者采用高效抗逆轉錄病毒療法(HAART)治療后,外周血CD4+T 細胞數目恢復正常,病情明顯改善。
4.僵人綜合征 由梅奧診所1956 年首次報告,是臨床罕見的神經系統免疫性疾病,以軀干中軸肌和四肢肌僵硬、痛性肌肉痙攣為特征,常伴發自主神經功能障礙如大量出汗、心動過速等癥狀,女性發病率約為男性的5 倍[38]。該綜合征分為經典型和變異型兩種類型,后者包括僵肢綜合征(SLS)、伴強直和肌陣攣的進展性腦脊髓炎(PERM)[38]。僵人綜合征目前仍是一種臨床診斷,具備3 項臨床特征,即肌強直、痛性痙攣的臨床表現,激動肌與拮抗肌持續不自主放電的典型肌電圖表現,以及陽性的自身免疫相關抗體的血清學表現。與僵人綜合征相關的自身免疫性相關抗體有GAD65、甘氨酸受體α1(GlyRα1)、兩性蛋白(amphiphysin)、調節亞單位二肽基肽酶樣蛋白6(DPPX6)和Gephyrin 抗體[38]。經典型僵人綜合征最常見的抗體是GAD65 抗體,此類患者可同時合并腎細胞癌、胸腺瘤、淋巴瘤等,免疫調節治療聯合苯二氮類藥物可改善癥狀[39]。伴強直和肌陣攣的進展性腦脊髓炎以肌強直、痛性肌痙攣、腦干脊髓癥狀、自主神經功能障礙、刺激誘發肌陣攣為臨床特點,發病與GlyRα1 抗體密切相關,但該抗體亦可見于10%~15%的經典型僵人綜合征病例,若實驗室檢測顯示外周血GlyRα1 抗體陽性則提示免疫調節治療療效良好[40]。DPPX6 抗體陽性患者亦可以表現為伴強直和肌陣攣的進展性腦脊髓炎,持續積極的免疫調節治療可以改善癥狀與體征[41]。兩性蛋白抗體是誘發副腫瘤性僵人綜合征、僵肢綜合征和伴強直和肌陣攣的進展性腦脊髓炎的相關抗體,患者最常罹患乳腺癌[42],其次為非小細胞肺癌[43];此外,與兩性蛋白抗體相關的神經系統疾病還有周圍神經病、腦病、脊髓病和小腦共濟失調。與經典型相比,副腫瘤性僵人綜合征患者頸部和上肢僵硬更加顯著,糖皮質激素治療有效,且治療原發腫瘤后癥狀可明顯改善[42]。此外,Butler等[44]在1 例同時罹患僵人綜合征和縱隔腫瘤患者的外周血中檢測到Gephyrin 抗體,故認為該抗體也是介導副腫瘤性僵人綜合征的相關抗體之一。
5.免疫相關神經性肌強直 免疫相關神經性肌強直(NMT)系周圍神經過度興奮引起的一種自發性持續肌肉收縮,典型表現為肌顫搐、肌痙攣、假性肌強直,常伴有出汗增多;當合并自主神經功能紊亂、中樞神經系統功能障礙如睡眠障礙和精神異常時,則稱為Morvan 綜合征。免疫相關神經性肌強直是臨床最為常見的獲得性神經性肌強直,亦稱Issacs 綜合征。Morvan 和Issacs 綜合征均與電壓門控性鉀離子通道(VGKC)復合體抗體具有較高的相關性,尤其是LGI1 和CASPR2 抗體[45]。LGI1 抗體可見于Issacs 綜合征患者,更常見于邊緣性腦炎病例,患者在病程中可伴發面-臂肌張力障礙發作、低鈉血癥、近記憶力減退、睡眠障礙等癥狀,較少合并腫瘤,預后良好[6];CASPR2 抗體陽性主要見于Morvan綜合征或Issacs 綜合征,表現為邊緣性腦炎、帕金森綜合征、慢性神經病理性疼痛等癥狀,大多合并有胸 腺 瘤[6,46]。Irani 等[47]發 現,逾1/3 的Morvan 綜 合征患者合并胸腺瘤,其中一些患者可同時檢出AChR 抗體。
6.眼陣攣-肌陣攣綜合征 眼陣攣-肌陣攣綜合征(OMS)的特征性臨床癥狀為眼陣攣,即雙眼不自主、無規律、大幅度共軛快速眼動,尤以注意或追視物體時最顯著,當注視目標固定時眼陣攣減輕,伴發癥狀以共濟失調常見。研究顯示,兒童眼陣攣-肌陣攣綜合征可能與神經母細胞瘤相關[48];成人副腫瘤性眼肌陣攣-肌陣攣綜合征(POMS)與多種自身免疫 性 相 關 抗 體 相 關,諸 如Ri、Hu、Yo、Ma1、Ma2、NMDAR、CRMP5 抗體等,可合并非小細胞肺癌、乳腺癌、卵巢癌等[49]。2016 年,Armangué等[50]共報告3 例眼陣攣-肌陣攣綜合征合并肺癌病例,并且發現1 種新型的抗原決定簇——人類自然殺傷分子1(HNK-1)。眼陣攣-肌陣攣綜合征相關病原體包括HIV 病毒、肺炎支原體、巨細胞病毒、人類皰疹病毒6 型、EB 病毒、西尼羅河病毒、丙型肝炎病毒等[49],單獨應用糖皮質激素或免疫球蛋白或與抗菌藥物聯合應用均有效,表明眼陣攣-肌陣攣綜合征與感染激活的免疫系統炎癥反應有關。
7.其他類型免疫相關運動障礙 NF155 抗體被認為是慢性炎性脫髓鞘性多發性神經根神經病(CIDP)的致病性自身免疫性相關抗體,NF155 抗體陽性的慢性炎性脫髓鞘性多發性神經根神經病患者可發生感覺性共濟失調和震顫,部分患者病程中可合并出現中樞和周圍神經系統聯合脫髓鞘疾病(CCPD)[51]。研究顯示,約67% DPPX6 抗體陽性腦炎患者表現為中樞神經系統過度興奮癥狀與體征,尤以運動障礙癥狀最為突出,如肌陣攣、多動和震顫,其他表現還有腹瀉和(或)體重減輕、認知功能障礙、精神行為異常、癲發作等;患者對免疫治療反應良好[52]。IgLON5 抗體相關腦病的重要特征為運動障礙,包括步態不穩、共濟失調、構音障礙、舞蹈樣動作、口-面部不自主運動等,亦可出現睡眠障礙如嚴重失眠、非快速眼動睡眠期行為障礙、睡眠呼吸暫停等,多數患者對免疫調節治療效果欠佳[5]。
臨床常見運動障礙自身免疫性相關抗體及臨床特點參見表1。
二、免疫調節治療性相關運動障礙
1.免疫調節治療相關運動障礙 CAR-T 療法是一項新型精準靶向治療腫瘤的技術,神經毒性反應是其特有的藥物不良反應,雖然僅發生在部分細胞因子釋放綜合征(CRS)患者,但亦有極少數患者在無細胞因子釋放綜合征的情況下并發神經系統不良事件[53]。約有32%~64%的腫瘤患者于CAR-T 治療后5 ~7 天發生神經毒性反應,表現為震顫、運動障礙等,嚴重者可進展為局灶性神經功能缺損或全面性強直-陣攣發作(GTCS)等腦病[54-55]。PD1 是重要的免疫抑制因子,與組織細胞表面的細胞程序性死亡蛋白配體1(PDL1)相結合,抑制淋巴細胞功能,因此,PD1 抑制劑可通過阻斷與腫瘤細胞的PDL1 結合增強對腫瘤細胞的免疫反應。與PD1 抑制劑有關的神經系統并發癥發生率約4.2%[56],以神經-肌肉并發癥較為常見,亦有PD1 抑制劑導致運動障礙、小腦共濟失調的文獻報道[57]。
2.免疫重建炎性綜合征相關運動障礙 HIV 感染患者經高效抗逆轉錄病毒療法治療后,在其免疫功能重建過程中出現的臨床表現惡化現象,稱為免疫重建炎性綜合征(IRIS),發病機制尚未闡明,可能與機體免疫功能失調等多種因素有關。免疫重建炎性綜合征相關運動障礙主要表現為眼肌陣攣-肌陣攣綜合征,通常發生于CD4+T 細胞數目迅速增加的背景下或經高效抗逆轉錄病毒療法治療后,提示眼肌陣攣-肌陣攣綜合征可能是免疫重建炎性綜合征的一種特殊表現[58]。
三、小結
神經系統自身免疫性疾病的臨床表現多樣,特別是運動障礙的表現形式更加復雜,其病理生理學機制與傳統神經變性病導致的運動障礙不盡相同,治療方案更是多樣。臨床遇到呈急性或亞急性發病的運動障礙,更應考慮自身免疫性疾病所致。大部分自身免疫性疾病導致的運動障礙在消除病因后癥狀可以部分甚至完全改善,即所謂的“可逆性”。治療原則采取以免疫調節治療為主的綜合治療,有別于神經變性病所致運動障礙的“不可逆性”和“對癥治療”。

表1 運動障礙自身免疫性相關抗體及臨床特點Table 1. Autoimmune antibodies and clinical features of movement disorder
由于運動障礙是神經系統自身免疫性疾病重要的甚至是首發的臨床表現,因此提高對此類運動障礙的診斷與鑒別診斷能力有助于提升臨床醫師對神經系統自身免疫性疾病的認識。神經系統自身免疫性疾病相關運動障礙有可能將成為運動障礙家族中最特殊的“分支”,隨著相關研究的開展,其神秘面紗將逐漸被臨床醫師揭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