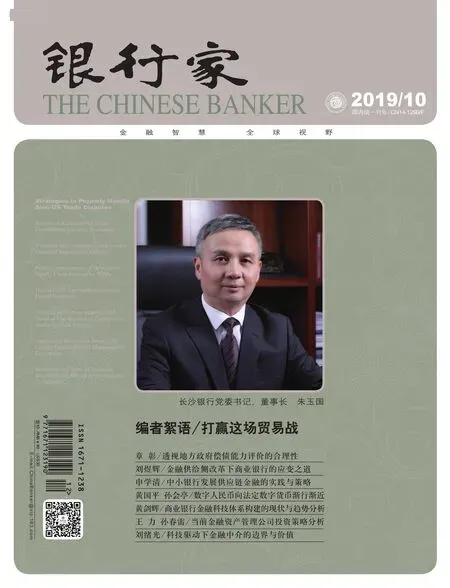再議資管新規:戰略、制度與文化
徐義國 王增武



2020年5月8日,中國銀保監會頒行《信托公司資金信托暫行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簡稱“資金信托新規”)。至此,與2018年4月27日發布的《關于進一步明確規范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指導意見有關事項的通知》(下稱“資管新規”)相配套的分部門細則的出臺告一段落(見表1)。對于資金信托的私募定位、非標投資比例以及服務信托和公益(慈善)信托的非資金信托例外條款,以及非標投資的封閉性和不同集合信托計劃不能投資單一項目等,市場上眾說紛紜,來自不同立場的觀點解讀和應對方略此起彼伏。
事實上,資管新規肇始于2018年3月28日的深改委第一次會議。習總書記在會議中強調:“規范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要立足整個資產管理行業,堅持宏觀審慎管理和微觀審慎監管相結合、機構監管和功能監管相結合,按照資產管理產品的類型統一監管標準,實行公平的市場準入和監管,最大程度消除監管套利空間,促進資產管理業務規范發展。”2019年2月22日,習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體學習時再次強調:“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強化金融服務功能,找準金融服務重點,以服務實體經濟、服務人民生活為本。要以金融體系結構調整優化為重點,優化融資結構和金融機構體系、市場體系、產品體系,為實體經濟發展提供更高質量、更有效率的金融服務。要構建多層次、廣覆蓋、有差異的銀行體系,端正發展理念,堅持以市場需求為導向,積極開發個性化、差異化、定制化金融產品。”通過會議我們可以很清晰地領會中央對資管行業的監管模式、機構體系、市場準入和產品取向等重大問題的發展思路,即新時代資管行業的指導思想與戰略定位。
概言之,對資管行業監管的總體要求是“大一統”,目標是實現宏觀審慎管理與微觀審慎監管相結合、機構監管與功能監管相結合。具體來看,合格投資者的界定、產品分類、投資方向、集中度、信息披露以及風險準備計提等均以資管新規的要求為基準,分部門的實施細則在此基準上進行微調。鑒于機構的稟賦差異,對不同機構的微調略有不同,其中最大的分歧或在非標投資的界定上。非標投資的界定是基于機構稟賦的業務差異所在,也是關于“是否統一”的爭議或詬病所在,更是資管新規及分部門細則進一步完善的空間所在。有關分類、業務、統計和評級等方面的建議,此文不再贅述,以下重點圍繞戰略、制度和文化三個視角展開。
踐行戰略指向。無論是從體量還是從改革開放以來的積累來看,就需求角度而言,資產管理行業都是金融行業的重要組成部分,2019年我國資產管理市場深度達到133.57%(見表2)。一些地方政府已將資產管理或財富管理納入政府推動的重點戰略,如上海“建設資產管理中心”和青島“打造財富管理中心”,并陸續出臺與之配套的多項舉措,如上海在2020年4月份推出的《海外資管機構赴上海投資指南》。眾所周知,新加坡是亞太乃至全球的資產管理或財富管理中心,其成長邏輯主要緣自于新加坡政府賦予資產管理或財富管理行業發展極高的戰略定位。因為對于執政黨——新加坡人民行動黨而言,財富管理不僅僅是一項經濟和金融業務,更是一項主權業務。財富管理是新加坡經濟戰略的一部分,是其在國內外取得成功的基礎,包括生物技術、先進制造業、“金融+醫療+教育”服務以及綜合度假村和賭場等。新加坡目前仍在奉行這一戰略,如在2019年的預算法案中,新加坡正在努力打造區域乃至全球的重要節點,如要在全球活動的重要領域擔當中立、可信的節點等。有鑒于此,深改委明確了資產管理行業的頂層架構,在具體的操作層面切實貫徹和落實這一戰略指向,如信托制度的優化和信托文化的弘揚等。
優化信托制度。監管統一的基礎是“法理共識”,根基則在于信托制度。基金法的上位法是信托法,銀行理財公募與私募兼營,其他資管類型則均定位為私募。分部門的實施細則均在某種程度上明確了來源于資管業務的資金、機構的固有資金和客戶的其他資金獨立的“信托性質”,但未明確其信托制度屬性,這或許正是進一步完善功能監管的空間所在。“資金信托新規”明確了服務信托和公益(慈善)信托不屬于資金信托。作為信托服務的主要服務之一——家族信托,自2012年首發至今,已歷經萌芽和醞釀階段,下一步可能進入爆發期。在前期的實操過程中已發現現有信托制度中存在不利于家族信托業務發展的要求,如登記制度。有鑒于此,以推動家族信托發展為例,信托制度及其配套措施需要進一步完善,包括明晰信托財產所有權、完善信托財產登記制度、嘗試信托持牌經營機制、落實信托財產稅收制度、強化家族信托保密制度和明確例外債權人范圍六個方面。另外,股票等證券作為家族信托未來重要的委托資產之一,是否也可配享《證券期貨經營機構私募資產管理業務管理辦法》中單一資產管理計劃享有的“非交易過戶”優勢,值得深思和探討。
弘揚信托文化。信托理念源于羅馬,信托制度源于英國,信托公司發端于美國,而信托文化則是在中華民族衍生發展。曾子曰“為人謀而不忠乎”,孟子曰“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楚游者”,皆個人信托之事也。“三綱五常”中“父為子綱”衍生的“長兄為父”也是一種委托代理關系,說的是父親過世后,長兄將承擔父親的責任,扶助及教育弟弟妹妹,從信托角度來詮釋就是“父親為委托人,長兄為受托人,弟弟妹妹為受益人”,受托資產則是家庭的物質資產或精神資產,如財產的分配或家族精神的延續等。在中國古代傳統中,托孤遺囑以指定監護人和委托管理家產為內容,承擔了維護家產和延續家庭的功能,最符合家族信托的要義。以三國時期劉備的“白帝城托孤”為例,委托人是劉備,受托人是諸葛亮,受益人是劉禪,信托資產為家族產業——蜀國政權;晉商的東掌制、財身股及號規等與信托制度、收益分配以及信托合約等存在異曲同工之妙;清末民初時期典型的家族財富管理——盛宣懷家族的愚齋義莊機制和李經方家族的五代傳承架構等都隱含家族信托的理念。從某種意義上講,始自范仲淹家族的義莊理念類同于時下國際盛行的私人信托公司(Private Trust Company,PTC)理念。以華氏義莊為例,和PTC對比來看,二者的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之間均存在諸多相同之處,其中特別重要的是義莊和PTC均把控制權維系在家族范圍內,如義莊的管理人需是義莊創辦人的嫡系子孫,而負責管理的PTC的董事會成員則可以是家族成員和家族的咨詢顧問人員,其中家族的咨詢顧問人員顯然在家族的“可控范圍之內”。這表明,中華文明的“道德論”和“集體意識”與西方文明的“物質論”和“個人主義”等文化差異決定了資管業務模式的本質區別。我們應該發展基于信義文化的“本土化”或“中國特色”的資管業務模式,如兩合公司的組織架構安排和東掌制的激勵約束機制等,而非“東施效顰”。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
——關注自然資源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