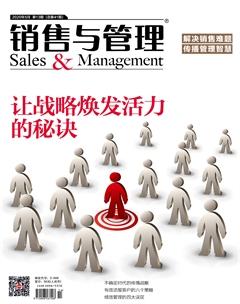探索式數字化轉型
麗塔·麥格拉斯 瑞恩·麥克馬納斯
你們公司的數字化戰略是什么?
這個簡單問題常常令傳統公司的CEO們驚慌失措。他們認為數字化技術及商業模式對現有的運營模式發起了挑戰,當然,這么想沒錯,但他們肩負的壓力往往令他們做出孤注一擲的決定——這種決定往往是錯誤的。
大型跨國電信服務提供商Veon就是一例。公司2017年上線的新數字化平臺是個龐大的項目,涉及阿姆斯特丹的100名員工和倫敦辦公室另外100多名員工。公司最初的想法是打造一個手機App,為用戶提供豐富的本地體驗,同時作為Veon商業伙伴(例如萬事達卡)的銷售渠道。管理層視該項目為首要工作。但這個App聲勢浩大地上線后,消費者卻反應冷淡,后續圍繞這一App打造新生態系統的計劃也隨之流產。項目失敗導致管理層人員大量離職、解聘,公司很多數字化項目也退回到試點階段,回歸基本戰略。
Veon仍然需要新的商業模式,但公司很明顯已經沒有足夠的資金去嘗試更多耗資巨大的試點項目。
也沒必要花那么多錢。巨大的威脅不一定要興師動眾去應對。相反,Veon及類似企業如果采用漸進式變革方式,效果會更好。這些企業應該始終保持對未來的展望,不斷尋找機會,將核心運營中有問題的流程數字化。解決這些問題的過程中,企業會了解到該使用哪些指標,修正哪些假設,在哪些方面引入新商業模式,誰是潛在的新競爭對手。吸取教訓的同時,企業對于競爭環境的理解以及長期目標也必然會發生改變。
這類針對戰略的學習方式已經有了一套既定流程,稱作探索式規劃(DDP)。本文作者之一瑞恩·麥克馬納斯(Ian MacMillan)在20世紀90年代,以產品創新方法論的方式介紹了這一流程。之后這套流程成為流行的“敏捷創業公司”的一種工具,用于在高度不確定的環境下創業。其核心是一個低成本的流程,可以快速驗證假設,獲得新信息,將風險降至最低。
接下來,我們會詳細介紹企業如何利用修改版的DDP迎接數字化挑戰,并逐步找到新商業模式。首先,我們來詳細分析一下,為什么傳統企業更適合采用按部就班的變革方式,而不是適用于初創企業轉向的“孤注一擲”。
在位企業的增量優勢
經濟學家一直思考企業存在的原因,以及更具體的,一家特定企業經營范圍內有哪些任務。20世紀30年代羅納德·科斯(Ronald Coase)率先提出一種思路,即在以下幾種條件下,市場交易無法令人滿意:要付出很大代價才能獲得所需商品信息,由于信息不對稱無法講價,執行協議成本很高或障礙重重,這種時候就需要企業介入交易活動。
直到近些年,企業和市場間的界限才逐漸被真正理解并確定。但是數字化技術改變了這一切,過去在企業中完成效率更高的一些工作,現在可以通過市場完成。阿里巴巴和亞馬遜等平臺提供了便利的渠道,可以將選擇供應商、洽談價格、執行合同、管理付款以及其他工作外包。
因此誕生于數字時代的企業高管和傳統企業的高管相比,對交易的結構化方式有著完全不同的假設。更重要的是,由于數字企業的構架不斷進化,管理者頻繁修正假設,直接面向消費者的行業(如床墊供應商Casper,剃須用品公司Harrys和眼鏡網站Warby Parker)不斷嘗試并調整,提出免運費、打包出售產品、加購送優惠等新服務。而通過分銷商銷售產品的在位企業根本無法使用這些技巧。而且數字化企業不需要中間商,即便規模較小也可以盈利。
關鍵是,初創企業可以在不損失太多價值的情況下,改變或調整戰略方向。這些企業往往不是資本密集型,也沒有太多員工。例如,Rooted的幾位創始人最初就在自己的公寓向消費者出售綠植,之后才搬入獨立辦公空間,并聘請員工。對這樣的企業來說,失敗的損失相對可控,除非發生在后期(或者投資人陷入不計代價求增長的魔咒,攫取所謂獨角獸企業累積的財富)。
然而傳統企業的員工、管理者和股東無法在不損失價值的情況下調整戰略。如果傳統企業的數字化轉型失敗,員工會失業,公司有形資產會大幅縮水。如果投資失敗,傳統企業的投資者不同于初創企業背后的風投資本家,并沒有高回報的投資作為緩沖用來彌補損失。
在位企業無法輕松改變戰略方向,幸好他們也不需要。大企業應當思考,自己能做什么小企業做不到的事情。初創公司幾乎總是傾盡所有資源投資一個創意,無法同時嘗試一個創意的多種版本,更不要說多個創意。大企業卻有足夠資源試驗多個創意,也更容易嘗試多種流程和運營,更有可能開發出一個主導模式。這也讓大企業更能有效地回應數字化挑戰。
德國金屬分銷商Kl?ckner公司就是例證。該公司CEO季斯波特·魯爾(Gisbert Rühl)想要打造服務于整個行業的數字化平臺,但他并不支持大爆炸式的變革,而是致力于在利用公司核心鋼鐵業務部門人才洞見和知識的同時逐步打造數字化能力。頭兩年,魯爾重點解決低效的人工流程,公司開設網上店鋪,設置合同端口,開發了訂單透明化工具和零部件管理應用程序,在此過程中掌握了足夠的知識,用于打造可以和客戶無縫互動的平臺。
Kl?ckner的案例讓我們看到在位企業的另一優勢——至少在采用數字化模式的早期是種優勢。在位企業的項目領導者了解客戶,且能夠挖掘此前交易的豐富數據庫獲得洞見。而初創企業的數字化往往由技術專家領導,更容易被新功能吸引,而非關注客戶需要的整體產品及服務組合。讓理解客戶的人來負責數字化工作,投資獲得回報的幾率更大。因此,Kl?ckner堅持所有項目重點關注如何幫助客戶更便捷高效地和企業溝通。當然這并非唯一目標,另一家企業也許會首先解決如何縮短回應客戶要求的時間。但無論什么目標,都應將技術視為業務機會,而不是將業務視為技術機會。
一旦接受了企業應當通過非顛覆的方式完成顛覆的思路,挑戰就巧妙地從“我們該支持什么新商業模式”變為更細致的問題,“我們該如何逐漸通過學習,找到適合公司業務的模式?”——方法就是DDP。
數字化情境
DDP有點類似逆向工程。在產品研發中運用DDP,第一步是想象你要創造什么東西,然后找出實現這件事所需的改變。但在數字化變革過程中,DDP的重點是徹底改造公司銷售產品的方式和現有產品的交付方式,以及設法利用新的數字化能力創造并交付新的價值。
以電力行業為例。數字技術就像顛覆其他很多行業一樣,顛覆了這個一度穩定的行業。過去,單一發電中心負責發電,并通過中控電網將電力輸送到千家萬戶。但有了新的技術之后,可以采用分散式小型發電站,利用多種能源發電并動態輸送。屋頂安裝太陽能電池板或花園有風車的家庭可以將多余的電力賣給電網,減少千家萬戶在發電設備上的投資,減少公眾對大型化石燃料發電廠的依賴。如果在位企業以為過去的商業模式可以預測未來的成功,很可能犯下大錯。通用電氣公司(GE)錯誤預測了人們對化石燃料發電廠的依賴,給我們留下慘烈的教訓。接著我們來看看采用DDP方式進行數字化轉型需要做些什么,一共有5個關鍵步驟。
1.定義運營體驗:數字化并非全部
進行數字化投資之前,先檢查一下公司運營中存在的問題。有沒有什么地方總是需要變通,有沒有哪個流程總是意外中斷、需要更多信息或請另一個人幫忙才能繼續下去?這些往往是數字化可以改進的領域。公司應當思考如何重新設計運營,通過技術優化服務和流程,讓一切變得更快速、成本更低或更便捷,從而增加價值。
在位企業零售商百思買集團(Best Buy)重新設計了企業運營,創造出純數字化企業無法復制的競爭優勢。2010年,亞馬遜發布一款比價App,這款工具和其他很多工具的作用,都是讓購物者能在實體店鋪體驗產品,然后在網上以折扣價格購買。這款App叫“買前驗貨”,差點斷了零售連鎖店的命脈,實體店鋪在地產、員工和庫存方面支出巨大,很難給出有競爭力的價格。這也是2012年百思買一個季度就損失了17億美元的原因之一。
百思買聘請休伯特·喬力(Hubert Joly)擔任CEO力挽狂瀾。喬力將戰略(以及商業模式)重點放在解決兩個問題:負面的比價銷售和不斷降低的運營利潤。為此,他設想出一個集人力、實體店和數字化為一體的企業——純數字化企業難以匹敵。首先,他思考百思買可以為顧客提供怎樣的體驗,以及更重要的問題:哪些地方還沒有運用數字化技術來協助實現這種體驗。
百思買的Renew Blue項目應運而生,由5部分組成:重振顧客體驗;改變供應商關系;生態和社會舉措投資;員工體驗;投資者回報。每部分都有相應的財務目標和試驗。
為改進員工體驗,百思買重點推行了提振員工士氣的舉措,例如恢復很受歡迎的員工折扣福利,為員工提供更密集的培訓。為吸引消費者,公司逐步在定價方面接近亞馬遜及其他電商——這一步需要付出極大的努力,徹底改革倉儲、軟件和供應鏈活動。但是因為顧客可以直接從店鋪買走產品,不必等待配送,也免去了昂貴商品網購的麻煩(例如放在門口被盜),百思買擁有了重要的優勢。此外,顧客還可以在網購后選擇送貨上門或到店自取。70%的美國人住處15英里以內就有一家百思買門店,所以這種方法很劃算。
百思買的新模式讓實體店鋪的高成本劣勢變為優勢。蘋果、三星和微軟等品牌,在百思買1000多個大賣場內開設了商鋪,本質上是為了租下店面展示自家產品和服務,讓線下購物者可以親自到店體驗。對于彼此激烈交戰的大型科技公司而言,百思買是中立方;互為競爭對手的谷歌和亞馬遜都在這里出售自家產品。最終,百思買投資建立了一支內部顧問團隊,讓這些訓練有素的全職雇員前往顧客家中幫忙解決技術問題,但不做銷售,目標是和顧客建立更緊密的關系。憑借這些,百思買逐步平穩地完成了數字化轉型。
百思買的案例說明,企業主動重新思考資產的使用方式以及與合作伙伴的互動方式是很重要的。公司之前的領導者并沒有發現與電商匹配價格的任何可能。但喬力挑戰了傳統的思維方式,促使公司重新設想了和供應商的關系(現在供應商在百思買店內租用商鋪),重新設計了供應鏈,公司的實體資產可以為新商業模式提供支持,與電子商務巨頭一爭高下。
2.關注具體問題:明確結果和進度衡量指標
任何數字化轉型戰略的關鍵問題都是,我們該如何使用數據和數字化能力,為客戶創造新價值?DDP流程可以將這一挑戰轉化為清晰的項目目標。
衡量新項目成敗的傳統指標一直是投資回報率(ROI),到今天也是如此。但是ROI無法幫助企業理解項目為客戶增加了什么價值,至少沒有直接體現。況且要準確計算ROI,企業需要預測投資和回報,但企業不知道的就是這幾項。企業要做的是,明確數字化項目應該帶來哪些具體改變,并找到密切相關的指標。
我們一般將這類信息匯總為一個“從……到……”的表格:定義問題,描述解決方案的效果,提出量化進度的方式。解決這些問題的過程中,原本的假設會得到檢驗和改進——這是DDP原則的關鍵。企業還可以看到迄今為止為了獲取新洞見而付出的代價,以及新洞見帶來的收獲。最終,公司會總結出某種類似ROI的指標。
Kl?ckner公司的終極目標是將公司的商業模式從庫存提價轉變為服務盈利模式。最初數字化項目很簡單,重點在于改善下單流程——例如將傳真下單改為網絡下單。在這些項目的幫助下,周轉時間和完成下單所需步驟等指標都有所改善。隨著公司在數字化方面知識和能力的不斷提高,項目目標也越來越宏偉。
當然,企業仍然需要一個指標用于衡量數字化變革的整體進展,我們推薦投資時間回報率(ROTI)指標。該指標計算方式是整體收益除以員工數量,邏輯是成功的技術投資應該讓公司用更少的人實現更多成就。例如,我們對比亞馬遜(數字化企業)和沃爾瑪(相對傳統的企業)的2018年年度報告數據。我們發現,亞馬遜的凈銷售額是2329億美元,全職和兼職員工人數共64.75萬人,每位員工的銷售額為35.9671萬美元。沃爾瑪的凈銷售額為4958億美元,員工230萬,每位員工銷售額為21.7852萬美元。相比之下,亞馬遜每位員工績效高67%。
3.定義競爭:廣撒網
如今行業邊界模糊不清,標準產業分類(SIC)幾乎淪為擺設。正因為如此,在位企業無法采用傳統的戰略制定方法做出關于邊界的預測。
我們建議,領導者不應將競爭領域看成一個相似企業聚在一起為顧客提供競品及服務的市場,而應將其視為戰略家口中的“競技場”。競技場由顧客需求而定,克萊頓·克里斯坦森(Clay Christensen)將顧客需求稱為“要做的事”,這一概念起源于泰德·萊維特(Ted Levitt),他認為鐵路公司應當將競爭對手拓寬到整個運輸行業,包括航空公司、巴士公司、卡車行業,甚至汽車業。如果鐵路乘客是一個市場,交通工具用戶則是競技場。
明智的原生數字化企業已經在這么做了。例如,奈飛(Netflix)已經表明自己不會僅限于和電視或電影競爭,爭奪觀眾時間;而是將觀眾除觀看視頻內容以外的所有休閑活動都視為競爭對手。公司理所當然地將傳統媒體公司視為對手,但也將雜志、書籍、播客和運動賽事視為競爭對手。
至此,你應該回頭檢查一下,自身企業所處的競技場是否適用于前兩步中制定的成果和成功指標。你的行業類型在競技場中,是否正在失去用戶份額,還是有一席之地?奈飛實現增長目標的潛力很大,因為觀眾整體觀看視頻的時間在增長,其中很大一部分來自網絡視頻。
4.尋找平臺:別忘了生態系統的影響
數字經濟時代,努力成為他人買賣商品的中間平臺,是企業很流行的戰略。這種商業模式很誘人,因為市場雙方一旦加入某個平臺,一般不會主動換。部分原因是網絡效應,用戶人數越多,平臺對單個用戶的價值越大。例如,使用愛彼迎這個平臺的房東和房客數量越多,平臺越能獲益,公司也一直不遺余力地確保供需雙方的忠誠。
平臺誘人的另一個原因是所需成本較低。運營一家傳統酒店要投資地產,維護房間,打造預訂系統,招聘員工等。愛彼迎則利用房東的生態系統提供上述所有內容,平臺擁有全部控制權的活動僅僅是匹配房東和房客,確保交易順利進行——且都在云端完成,因此可無限擴張。
為了了解是否存在平臺方面機會,我們采用的工具叫“顧客消費鏈”。原理很簡單:因為顧客在生活中要完成各種事項,經歷一系列體驗,首先是察覺到某個需求,思考如何滿足這種需求,然后享受整個服務過程,直到需要更換。在數字技術的幫助下,鏈條上很多環節得以在開放市場交易,企業因此構建起平臺。
對在位企業來說這似乎是壞消息。但在位企業有一張王牌:有很多資深技術人才或理解客戶問題的人才。這讓在位企業可以發現平臺方面的機會并構建起生態系統。在Kl?ckner,魯爾意識到一旦基本金屬貨物交易的過程實現了價格透明,摩擦大幅減少,競爭優勢將轉移到能夠提供卓越服務和解決方案的供應商身上。公司融合了數字部門平臺運營的新方式(例如和顧客共同設計產品),結合員工深度的專業知識,開發出更高價值的定制化產品和服務。
對企業來說,成為受歡迎的平臺并非易事。商業疆土中遍布失敗的“準平臺”,貌似萬事俱備,卻仍然未能成功。例如GE的Predix項目,初衷是希望成為工業物聯網的平臺。該項目未能推動客戶重視的數字化服務,卻為GE內部部門(而且是很多個部門)服務并深陷其中;而且,作為GE數字化(GE Digital)的一部分,該項目有盈利壓力,為了交差與客戶簽訂短期合同。此外,項目原本應該找到適合自身能力的地方后再慢慢發揮作用,但卻操之過急。
5.驗證假設:失敗也是經驗
DDP中較受歡迎的一個工具是“假設檢查表”。表格制作方法是:寫下幾個數字化項目需要經歷的里程碑,以及每個里程碑要驗證的假設,如果可能的話,還要把驗證這些假設的成本寫進去。這種方式的精妙之處在于,將討論重點從“我們犯錯了,真失敗”轉為“學到這點是否值得付出這樣的代價”。
我們來看一下Buffer在起步階段驗證假設的案例。Buffer主要提供的服務是幫助人們管理社交賬戶,規劃合適的活動推送時間。公司聯合創始人喬爾·加斯科因(Joel Gascoigne)最初想到這個創業機會,是因為他感到堅持發Twitter壓力很大,令人挫敗。他想驗證的第一個假設是,別人是否也覺得這件事是個問題,所以做了一個簡單的網站,只有兩個頁面。
第一頁的廣告語是“Buffer幫你持續發Twitter”。如果用戶點擊了網頁,會轉到下一頁,標題是“您來早了,我們還在籌備”。用戶如果對Buffer的服務感興趣,可以在頁面留下郵箱地址。多數人沒有這樣做,但有一些人留了。因此加斯科因在兩頁之間加了第三頁測試收費假設。同樣地,多數人對付費沒有興趣,但感興趣的人數足夠說服加斯科因打造這款產品。
接著他要決定產品的復雜程度及應用到哪些社交平臺,最終成型的產品非常簡單,一開始只支持Twitter賬戶。到2018年,和Buffer app綁定的社交賬戶已經達到140萬。
很多大企業采用了類似的“測試-學習”思維模式,而一些新服務的出現也讓試驗變得更容易,例如Alpha,用戶可以使用該軟件從潛在客戶那里獲得關于產品的快速反饋,無需做出不可逆的決定或者耗費大量資金。WellMatch公司是安泰人壽(Aetna)旗下的業務部門,公司通過試驗解決設計方面的分歧。公司前任首席產品官埃圖格·諾坎(Etugo Nwokah)表示,公司網站曾引發分歧:各團隊都希望能在首頁展示自己部門的內容。因此試運營的時候頁面很擁擠,用戶一頭霧水。公司不得不回到原點,重新設計,但仍然比推出正式網站后再修改更節省成本,風險也更低。
回報
數字化轉型很復雜,需要通過新方式逐步找到戰略。如果企業一開始就進行燒錢的大項目,自以為掌握了所有信息,公司內部傾向于規避風險、拒絕改變或者單純不喜歡這種項目的人很可能會群起而攻之。
探索式方法會幫助領導者避開數字化轉型常見的障礙,從成本不高的小項目開始不斷試驗,從中學習,為企業贏得早期支持者和采用者;然后快速推進,清晰展示財務績效指標受到的影響,幫助企業逐步梳理出可行的數字化戰略。你也可以通過數字化項目開啟組織變革。
本文作者麗塔·麥格拉斯長期在哥倫比亞商學院擔任教授,是世界知名的戰略專家,專注研究不確定和不穩定環境下的企業戰略。瑞恩·麥克馬納斯是Techtonic.io公司CEO,全球知名數字化商業模式、變革和生態系統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