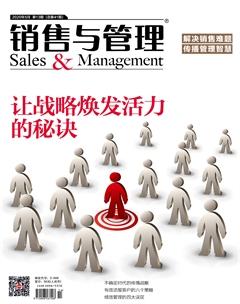組織的五個層次有助于修煉“內功”
房晟陶 左謙
所謂的練內功,大部分指的就是補“組織能力”的課。形勢不太好的時候,一部分企業終于有時間和意識“練內功”了。但形勢不好的時候練內功還來得及嗎?肯定不是所有企業都來得及。來不及的企業得壯士斷腕、丟車保帥、死馬當作活馬醫等。對于已經裸泳的企業,先練點外功穿上短褲,練內功的事看機緣吧。對于來得及的企業,冬天的時候沒有好好練內功,夏天的高歌猛進可就沒你的份了。
所謂的練內功,大部分指的就是補“組織能力”的課。但“內功”也不是說練就能練的,也得講究方法。有些練就是瞎練。
練“內功”的關鍵是組織策略
有些公司遇事就喜歡調整組織結構。領導高屋建瓴地考慮了過去、現在和未來,設計了新的組織結構,迅速宣布,個把月就部署到位。新組織結構的戰略意圖確實很重要,要是錯了的話很致命。但是,把戰略意圖想清楚了,從工作量上來說,充其量只是完成了1%,剩下的臟活細活累活領導就都嗤之以鼻地交給中基層了。領導層只做到這種程度,不僅算不上是練內功,連“外練筋骨皮”的水平都沒達到,基本屬于理個發、洗個澡的水平。真正的“內”如血液循環系統、內分泌系統、消化系統等,一點都沒觸及。
另外,一些公司遇事喜歡“調整人”和“整肅綱紀”。調整人無可厚非,形勢好的時候也會經常調整人。但是,形勢不好的時候,很多公司容易讓“酷吏”上位。什么叫“酷吏”?在企業的語境下,“酷吏”無非就是極端結果導向但很容易忽視價值觀的人。這些人的風格就是“雷厲風行”,善于“亂世用重典”,特別符合短期“整肅綱紀”的心理需求。有智慧的企業家一定要慎用“酷吏”。一旦大量“酷吏”上位,那就是“揮刀自宮”式地練內功了。
那么,該怎么練內功呢?練內功的關鍵和前提是更新你的“組織策略”。經歷了冷熱、起伏之后,一些根本性的組織問題才可以真正地被深入思考、認真討論。可以說,形勢不好的時候反而是產生真正的組織策略的機會期。對于一些年輕的公司來說,這是第一次產生真正的組織策略的機會期。要注意,這個機會期也不會長,因為好了傷疤就會忘了疼。那么,組織策略都包含哪些內容呢?

使命、愿景、價值觀的返璞歸真。沒遇到困難的時候,使命、愿景、價值觀是很容易得到擁護的。但形勢好的時候,這種擁護實際上只是不反對而已。經歷了起伏和冷熱之后,核心領導人以及核心領導團隊才能更認真地總結及反省使命、愿景、價值觀,真正找到想干、應干、能干的交集。
經營管理原則的豐富。缺乏經營管理原則支撐的使命、愿景、價值觀很容易就是口號和愿望。原則是用來指導如何處理實際工作中的具體問題的,比如如何處理刁鉆的客戶、如何對待供應商、如何處理長短期的平衡、如何對待競爭對手、如何對待創新中的錯誤等。這些都是員工在日常工作中會遇到的問題。對于這些問題,使命、愿景、價值觀往往遠水解不了近渴。經歷了起伏和冷熱,這些問題才會尖銳地出現,其重要性和必要性才可能被認真對待。這時候,經營管理原則才能真正地形成。
公司級競爭能力的選擇。是差異化產品、客戶親密,還是低成本?服務于什么客戶?增加什么價值?經歷了起伏之后,核心領導人及核心領導團隊才更愿意有所取舍并達成共識。
組織地圖/文化地圖。我們雖然是一個公司,但是很可能不是一個組織。我們有多少組織?我們允許亞文化嗎?我們有能力讓亞文化之間和諧共處嗎?不同組織靠什么凝聚起來?哪些組織需要去掉?
組織能力建設策略。如果用一個公式來表現:組織能力=f(人才,文化,系統,工具/設備/AI,X)。對于本公司,要想在下一個周期中取勝,組織能力建設的重點要素是什么?是人才、文化,還是系統?或者是工具/設備/AI?經歷了起伏之后,企業的領導層會對關鍵要素的排序以及如何組合(即如何設置這個F函數)有更清醒的認識。
人才策略。如果人才是本企業組織能力的關鍵要素,那么究竟是哪類人才?新階段的新標準是什么樣的?如何變革?如何建立能持續供應及培養這種人才的系統“功能”?
組織氣質。使命、愿景、價值觀可以保持穩定,但組織的氣質可以有階段性變化。現階段組織需要什么樣的氣質?比如,有“積極求勝”這樣一個價值觀,但氣質可以根據內外形勢選擇穩健或者敢沖敢闖。
系統。如果系統是本企業組織能力的關鍵要素,那么哪些是“戰略性組織系統”,需要優先及重點投入?
工具/設備/AI。哪些工具和設備需要迭代更新?哪些是公司發展所需要的關鍵技術能力?哪些關鍵業務環節可以被AI提升效率?要做出哪些投資?
組織想象。我們能為員工提供什么,不能提供什么?我們希望員工在組織里有怎樣的體驗?組織想象與所在行業并無必然聯系。它更多取決于核心領導人的價值觀:我想創造一個什么樣的小社會?與核心領導人的組織想象匹配的組織策略更容易得以施行。
核心領導人及核心領導團隊的學習成長。這是個重要的組織問題。核心領導人及核心領導團隊的能力就是組織的天花板。他們過去的學習方式有什么問題?如何改進學習方式及學習效果?核心領導團隊用什么樣的機制討論及決策組織問題?如何集體學習成長?
沒有以上這些對于組織策略的深入思考,“練內功”就是個口號而已,很容易停留在“外練筋骨皮”的狀態。如果你承擔著高管的職責,但對上面列舉的事情根本就是“無感”,那你確實應該加強學習。注意,在本文中我用了“組織策略”而不是“組織戰略”。這是因為組織方面的工作不是靠一兩個“大動作”就可以萬事大吉的,尤其是在形勢不好的時候。“策略”比“戰略”更符合組織方面工作的特點。
組織方法論的層次
本文從方法論層次的角度去解讀很多組織方面的挑戰,比如創始人兼CEO與CHO/人力資源副總裁(HRVP)難以同頻、對話,經常一拍兩散等現象。方法論錯層、缺層及同一層次的互不兼容,都會使高效的討論和對話難以產生。
我們試著把組織方面的方法論分為五個層次來構建一個簡單的“神經網絡”。組織方法論的層數(layers)不一樣,你處理組織問題的“神經網絡”(neural networks)的結構就不一樣,由此產生的“算法”(algorithm)自然就不一樣。一級問題視角及一級方法論,我們可以稱其為“創始人兼CEO層次”。
1.創始人兼CEO層次
創始人兼CEO首先關注的問題是“如何創建一個企業”,需要的是創建企業的方法論。如果用公式來簡單表達的話,創始人需要一個類似“企業=f(產品/服務,使命/愿景,技術,組織,資本,X)”這樣的創業方法論。創始人兼CEO要把產品/服務、資本、組織等不同類的要素組合起來成為一個整體。
在這個一級問題視角及方法論層次上,“組織”只是其中要素之一。要素之間有代償作用。如果其他要素如“資本”做得好,對“組織”這個要素的要求就會降低。這個一級方法論解決了“組織”這個要素在整體中的要求和定位問題。但要達到對“組織”這個要素的要求和定位,需要下一級的方法論。
2.首席組織官層次
二級問題視角及二級方法論,我們可以稱其為“首席組織官層次”。這個層次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建立或迭代組織”,需要的是建立或迭代組織的方法論。要回答的問題包括:誰來領導這項工作?什么是組織?什么是組織能力?建立組織要考慮哪些要素?建立組織與管理組織有什么不同?
如果用公式來簡單表達的話,首席組織官需要一些類似“建立或迭代組織=f(首席組織官,組織模型,組織系統,組織策略,變革藝術,創業精神及創作能力,X)”“組織能力=f(人才,文化,流程/機制/系統,工具/設備/ AI,X)”等這樣的組織方法論。
上一段這兩個公式里面的要素不像“企業=f(產品/服務,使命、愿景、價值觀,組織,資本,X)”這個公式里面的要素那么容易理解,所以還要解釋什么是組織系統,都有哪些組織系統,如何選擇本組織的關鍵組織系統,什么是組織模型,什么是組織策略,建立組織為什么需要變革藝術,建立組織為什么需要創業精神及創作能力等。
在這個二級問題視角及方法論層次上,“組織系統”只是其中要素之一。要素之間有代償作用。如果其他要素如“組織策略”“創業精神及創作能力”方面做得好,對“組織系統”的要求就會降低。這個二級方法論解決了對類似“組織系統”這樣的個體要素的要求和定位問題。但具體來說如何達到對“組織系統”這些個體要素的要求和定位,需要再下一級的方法論。
3.首席人力資源官層次
三級問題視角及三級方法論,我們可以稱其為“首席人力資源官層次”。順著二級方法論里舉的“組織系統”這個例子講,在第三層次要解決的問題就比如如何建立一個人才選育用留系統,如何塑造文化。這需要一個建立組織系統的方法論。
如果用公式來簡單表達的話,首席人力資源官(CHO)需要類似“建立組織系統=f(功能/目標,關系/連接,要素/部件,價值觀/原則,變革管理,X)”“人才選育用留系統=f(人才類型,人才標準,人才獲取,能力與潛力的關系,評價,評價與任用的關系,淘汰,標準與評價和淘汰的關系,X)”這樣的系統方法論。
這兩個方法論要回答的問題包括:為什么功能/目標對系統很重要?為什么只有要素形不成系統?為什么關系/連接很重要?價值觀與組織系統是什么關系?具體到人才選育用留系統,這個人才選育用留系統要達成什么樣的功能/目標?“淘汰”是個重要功能/目標嗎?它有哪些關鍵要素/部件,比如“標準”是關鍵要素/部件嗎?“評價”是關鍵要素/部件嗎?“人才獲取”是關鍵要素/部件嗎?它有哪些關鍵連接,比如“標準與評價和淘汰的關系”是關鍵連接嗎?
在這個三級方法論層次上,對人才選育用留系統來說,“人才標準”只是其中的單個要素。如果其他要素如“淘汰”“人才獲取”,關鍵連接如“標準與評價和淘汰的關系”做得很好,對于“人才標準”本身的要求就會降低。這個三級方法論解決了對“人才標準”等要素的要求和定位問題。但具體來說如何達到對“人才標準”的要求和定位,需要再下一級的方法論。
4.人力資源副總裁層次
四級問題視角及四級方法論,我們可以稱其為“人力資源副總裁層次”。順著三級方法論里舉的“人員標準”這個例子講,在第四層次上要解決的問題就是“如何建立人才標準”,這就需要關于“人才標準”的專業及工作方法論。如果用公式來簡單表達的話,人力資源副總裁(HRVP)需要類似“人才標準=f(通用素質能力,職能素質能力,專業能力,價值觀要求,職業序列及等級,X)”這樣的方法論。
在這個四級方法論層次上,對“人才標準”這件事情來說,“通用素質能力”只是其中的單個要素。要素之間有代償作用。如果其他要素如“職能素質能力”“價值觀要求”做得很好,對于“通用素質能力”本身的要求就會降低。這個四級方法論解決了對“通用素質能力”等要素的要求和定位問題。但具體來說如何達到對“通用素質能力”的要求和定位,需要再下一級的方法論。
5.人力資源總監層次
五級問題視角及五級方法論,我們可以稱其為“人力資源總監層次”。繼續第四層次的“通用素質能力”的舉例,在第五層次上要解決的問題就是“如何開發通用素質能力”,這就需要相應的工作及專業方法論。
如果用公式來簡單表達的話,人力資源總監(HRD)需要類似“開發通用素質能力標準=f(高績效員工訪談,領導人人才審美,下一階段戰略需求,實際使命、愿景、價值觀,外部同行業對標,聘請專業咨詢公司,X)”這樣的方法論。
問題視角和方法論的層次還可以向六級、七級分解下去,直至最后輸出、收口到每個具體的員工身上。實際上,還可以向上溯源。比如,也可以有零級的組織方法論,那就是創始人兼CEO對于人生幸福和成功的方法論了。
分層很重要,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分層。不同的分層會導致不同的“神經網絡結構”及“算法”。關于以上的分層,有人會挑戰,HRVP層次與CHO層次真的可以區分嗎?我認為這兩個層次是有明顯不同的。CHO必須是向一個獨立公司的CEO匯報的,而HRVP往往向一個大的分公司總經理匯報,比如向一個大公司里面的大老板或者500強外企中國區的總裁匯報。這兩種場景下的實質挑戰是很不一樣的。同理,CHO與首席組織官也是有明顯不同的。簡單來說,只是管理一個已經成形的組織,沒有經歷過“建立組織”階段的CHO很難實質性貢獻于首席組織官功能。
有些人還會問,在這種“神經網絡”里面,是不是必須在上一層次做好后才能到下一個層次?不是的,這就是系統的奇妙之處,這個“神經網絡”有很強的自適應能力。任何一個層次上的有質量的工作都可能促進相鄰層次的進化。比如,如果在第四層次的“人才標準”這個部件要素上做得比較好,不僅第三層次的“人才選育用留系統”會更有機會做好,第三層次中與“人才選育用留系統”并列的其他系統如“文化管理系統”“績效管理系統”都可能被帶動起來,最后使所有組織系統都加強。第三層次“組織系統”的整體加強又會向上影響到第二層次,促進與“組織系統”并列的“組織策略”的進化。如此種種,有很多可能,難以完全預測和控制。
這種組織方法論的分層及“神經網絡”可以解釋很多問題。比如,它可以解釋為什么創始人兼CEO與HRVP很難同頻、對話,經常一拍兩散。
想象以下場景:一個只具備一級問題視角而且一級方法論都還沒搞清楚的創始人兼CEO,與一個具備四級問題視角及四級方法論的HRVP,他們怎么才能進行建設性的討論和共創?難道靠溝通能力及人際技巧就能解決方法論的問題?甚至,能有一個四級問題視角及方法論的HRVP已經算是很好的了。對于創業小公司來說,能吸引一個五級問題視角及方法論的HRD就不錯了。一個擁有一級的視角及方法論者與一個擁有五級的視角及方法論者如何討論問題?能同頻及對話才怪。
如果只是錯層,還沒那么復雜,至少大家還承認有第二層、第三層。我觀察到的現象是,大部分創始人兼CEO以及資深的HRVP會結構性地忽略二級問題視角及方法論,很多人甚至連三級問題視角及方法論也會忽略。這樣,他們就從一級問題視角及方法論直接到了四級、五級問題視角及方法論。這種嚴重的缺層會導致“組織算法”上的粗糙和低效,使難以同頻及一拍兩散的現象更加嚴重。
怎么辦?我們可以想到的解決方案是:創始人兼CEO必須下探1-2個層次,掌握二級問題視角及方法論(COO層次),并對三級問題視角及方法論有所理解(CHO層次)。HRVP必須上探1-2個層次,掌握三級問題視角及方法論(CHO層次),并對二級問題視角及方法論(COO層次)有充分理解。很多HRVP也結構性地忽略了二級問題視角及方法論,試圖以四級、五級方法論解決二級問題。與此同時,也要對其他業務高管進行培訓,他們也需要理解二級問題視角及方法論(COO層次)。
理解了有什么用?理解了不一定會做對,但會減少無知無畏地做錯,以及互相甩鍋。這樣,創始人兼CEO下探,HRVP上探,其他業務高管伸手相助,大家共同實現首席組織官功能的概率就大大提高了。還有另外一個關鍵問題:除了錯層、缺層外,在同一層次的問題視角及方法論中,會不會也容易產生很多矛盾?是的,這也是非常可能的。
你還有可能是受你以前的組織經驗的影響。比如,如果你一直在一個投行工作,你肯定會非常理解“人才”的重要性,而對于“組織”對一個大型企業的重要性,你可能沒有直觀理解。或者,你以前是在一個偏資源型的房地產公司工作,你可能就會對“技術”對于企業成功的重要性沒有深刻認識。或者,你的主要組織經驗是在經濟企業。如果你曾在非營利組織或社會企業工作過,你就會更容易理解“使命/愿景”對于一個企業/機構的重要性,如此等等。
總結一下,無論是方法論缺層、錯層,還是同一層次方法論的互不兼容,都會產生很多組織上的矛盾及低效。實際上,這種現象在任何事情上都可能發生,只是在“組織”這種相對最沒有明確的“對錯”之分的事情上,更容易發生。在遇到這種事情的時候,建議當事人著重厘清及反省彼此在方法論層面上的不同及能力缺失,而不是一味地向“政治”及“態度”歸因。
最后,我們順便還可以討論另一個問題:是不是必須先成為HRVP才能成為CHO及首席組織官?我認為不一定。有志成為首席組織官的HRD,也可以去做一個獨立的小公司的HR Head。在這種崗位上的歷練會更快地幫助你獲得三級及二級問題視角,并倒逼你學習三級及二級方法論。當然,絕對不能忽視HRVP層面的能力訓練。不然即使有了CHO、首席組織官視角,也不容易實現其所應有的作用。
對于處于創業階段的創始人兼CEO來說,這一點意味著在尋找組織方面的伙伴時,你不必老想著從大公司尋找那種“資深人員”。盡管“資深人員”在經驗積累方面更接近CHO以及首席組織官,但他們在問題視角及方法論上也不一定能更快跨越四級HRVP視角。
另外,也可以考慮將建立組織方面的職責交給非HR人員。如果HR人員不能有二級、三級視角,讓在業務領域中體現出了二級、三級視角的業務高管轉做組織工作也是個不錯的選擇。問題視角及方法論上達不到二級、三級層次的HR,在四級、五級層面做得非常專業也只會事倍功半。
本文作者房晟陶是首席組織官創始人,龍湖集團原執行董事兼首席人力資源官,寶潔(P&G)原人力資源高級經理,25年來致力于研究組織、文化及領導力;左謙是首席組織官聯合創始人,龍湖集團人力資源部原副總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