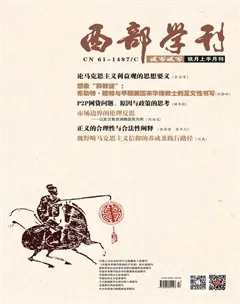想象“異教徒”:布勒特·哈特與早期美國來華傳教士的互文性書寫
摘要:早期美國來華傳教士的書報著作所構建的中國異教徒形象深刻影響著美國人對中國人的認知。十九世紀美國邊疆作家布勒特·哈特的異教徒書寫則與排華運動息息相關。通過分析二者的異教徒書寫,可以看到他們的異教徒書寫存在互文關系,且哈特在其書寫中挪用了早期美國來華傳教士的異教徒概念。哈特的《異教徒中國佬》一詩對早期美國來華傳教士的“拯救異教徒”話語進行了戲仿,這種戲仿因被誤讀而成為煽動美國民眾排華情緒的工具。在小說《異教徒李頑》中,哈特則對早期美國來華傳教士的“拯救異教徒”話語進行了改寫與解構,并以此挑戰了排華運動中的“驅逐異教徒”話語。
關鍵詞:來華傳教士;布勒特·哈特;《異教徒中國佬》;《異教徒李頑》;排華運動
中圖分類號:I3/7 ?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6916(2020)17-0039-06
一、引言
布勒特·哈特(Bret Harte,1836—1902年)是十九世紀美國現實主義小說家,曾供職于《大陸月刊》(Overland Monthly),他的作品多為描寫加利福尼亞州生活的短篇小說。除了詩歌《異教徒中國佬》(“The Heathen Chinee”,1870)和短篇小說《異教徒李頑》(“Wan Lee,The Pagan”,1874),他還寫了《咆哮營的幸運兒》(“The Luck of Roaring Camp”,1868)、《撲克灘放逐的人們》(“The Outcasts of Poker Flat”,1869)、《海盜島的皇后》(“The Queen of Pirate Isle”,1887)等作品。他的短詩《異教徒中國佬》出版后頗受歡迎,并深刻影響著美國社會中的中國形象。
(一)《異教徒中國佬》與美國的早期中國形象
一八七零年九月,布勒特·哈特在《大陸月刊》上發表詩歌《老實人詹姆斯的大實話》(“Plain Language from Truthful James”),后因詩中的“異教徒中國佬”(“The Heathen Chinee”)多次被傳誦而易名。這首短詩“被美國和英國的報紙廣泛轉載,《大陸月刊》的發行量因此大增,在它出版兩個月后,單是紐約一家新聞公司就賣出了一千兩百份”[1]。作為《大陸月刊》首位編輯的布勒特·哈特大概沒有想到這首他并不滿意的小詩會如此受歡迎,并不斷卷入政治和文化辯論當中。建議哈特將此詩發表的比爾斯先生(Mr.Bierce)回憶道,“過了好幾個月他才拋開對這些詩句不滿意的情緒,將這些詩句發表。事實上他不是很在意這首詩,對于讀者所讀出來的蘊意他感到好笑”[1]。《異教徒中國佬》一詩因被誤讀而使“異教徒中國佬”成為描述中國人的代名詞,也成為排華運動的重要宣傳讀物。聚焦并探討布勒特·哈特的詩歌《異教徒中國佬》被誤讀并在排華運動中發揮重要作用這一現象,有助于我們進一步考察美國的異教徒中國形象的生成和發展脈絡,更為深入地理解美國社會中的中國形象。
(二)國內外研究綜述
目前學界關于布勒特·哈特筆下的“異教徒中國佬”形象的研究取徑多樣、視角各異。國外學者特別是美國學者偏向于將《異教徒中國佬》一詩的誤讀置于歷史語境中理解。例如,泰拉·潘莉(Tara Penry)考察了《大陸月刊》所刊文章,指出對《異教徒中國佬》的誤讀不符合《大陸月刊》及其編輯哈特的立場和本意[2]。國內學者則更多地關注這一形象背后的東方主義思想。例如,朱剛認為通過突出語言差異,哈特突出了華人這一“他者”與白人的差異,加劇了美國的排華情緒[3]。學者們已經關注到了這首短詩的誤讀現象以及其產生的重要作用,但對于存在集體性誤讀的原因、哈特本人的中國觀以及其異教徒書寫與早期美國傳教士所構建的中國異教徒形象之間的聯系則少有人問津。筆者注意到他們的異教徒書寫存在互文性(Intertextuality),且哈特在其書寫中挪用了早期美國來華傳教士的異教徒概念。本文通過探究在傳教士異教徒話語深刻影響美國民眾的中國觀的語境下,哈特的異教徒書寫如何影響了排華運動,指出哈特的《異教徒中國佬》一詩對早期美國來華傳教士的“拯救異教徒”話語進行了戲仿,這種戲仿因被誤讀而成為煽動美國民眾排華情緒的工具,而在他的小說《異教徒李頑》中,哈特則對早期美國來華傳教士的“拯救異教徒”話語進行了改寫和解構,并以此挑戰排華運動中的“驅逐異教徒”話語。
(三)互文性理論闡釋
通過研究哈特與早期美國來華傳教士異教徒書寫的互文性,我們可以看到異教徒這一話語如何影響了哈特的文學創作,以及這一話語的傳續與變異是如何發生的。在進行論述之前,我們有必要對“互文性”這一概念加以界定。互文性(又稱互文本性或文本間性)這一術語由法國符號學家、哲學家、文學批評家朱麗婭·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在其《符號學》(Semeiotikè,1969)一書中首先提出,她認為任何文本都是對其他文本的吸收與轉換,文本與文本之間相互指涉,文本的意義由此產生。此后,有不少文學理論家對這個術語加以解釋,如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雅克·德里達(Jacques Derrida)、熱拉爾·熱奈(Gérard Genette)和米歇爾·里法泰爾(Michael Riffaterre),他們的闡釋拓展了這一理論的內涵。這一概念在當代文學理論中熠熠生輝,著名敘事學家杰拉爾德·普林斯(Gerald Prince)在其《敘事學詞典》(A Dictionary of Narratology,1987)給出了較為明晰的定義:
一個特定文本與它所引用、改寫、吸收、拓展或是總體而言進行改造的其他文本之間存在的關系,并且依據這種關系才可能理解該文本[4]。
程錫麟梳理了互文性在文學文本中的體現,包括引用語、典故與原型、拼貼(collage)、嘲諷的模仿(parody)以及“無法追溯來源的代碼”(巴特等人之語,即無處不在的文化傳統的影響)[5]。哈特在其文學創作中對早期美國來華傳教士的“拯救異教徒”話語進行了戲仿(即“嘲諷的模仿”)和改造,而其文學創作也體現了基督教世界中“拯救異教徒”話語和“驅逐異教徒”話語這兩種“無處不在的文化傳統的影響”。因而,文本之間的對話、書寫者之間的對話又將我們引向文化之間的對話。研究哈特與早期美國來華傳教士的互文書寫可以幫助我們把握中美文化之間復雜、多元的互動。早期美國來華傳教士的話語深刻影響著美國民眾對中國人的認識,這是哈特構建中國異教徒形象的重要背景,因此需要梳理早期美國來華傳教士的中國“異教徒”書寫,以理解哈特筆下的中國形象及其作品對排華運動的影響。
二、早期美國來華傳教士的中國“異教徒”書寫
布勒特·哈特的《異教徒中國佬》發表時,美國民眾已對遠在太平洋另一端的中國人有所認識,而他們的認識除了來自十八世紀傳入美洲大陸的中國商品和中國典籍英譯本之外,也有來自早期美國來華傳教士的書報著述所構建的中國異教徒形象。宗教不僅僅是一種信仰,更是一種認識世界的視角。十九世紀三十年代以來,早期美國來華傳教士便以基督教教徒的眼光打量中國“異教徒”,塑造“罪惡”的中國形象,宣揚以“基督教文明”來拯救中國“異教徒”,他們撰述并出版的刊物及論著深深地影響著美國民眾對中國人的認知。
(一)早期美國來華傳教士塑造的中國人形象
早期美國來華傳教士是美國人認識中國的眼睛,中國人的“異教徒”形象通過他們的書寫才更為充分地浮現出來,并對美國的中國觀產生深刻的影響。十八世紀中葉以前,來到北美的歐洲移民們忙于建設自己的家園,而對中國這個“由不信上帝的異教徒組成的遙遠國家”并不關心[6]。隨著物質條件的改善和政治環境的逐漸穩定,美國人開始從精美的中國商品、傳入美國的中國典籍英譯本和英國人的記述來了解中國。十八世紀末以來,歐洲的中國形象逐漸轉為負面,中國成為需要被“改造”的落后社會,這也影響著美國人的中國觀。與此同時,美國本土的宗教運動,以及鴉片戰爭后美國對華擴張促成了美國傳教士來華傳教。到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前,美國已經歷了兩次宗教“大覺醒”運動,強化了“上帝的選民”意識,而作為“上帝的選民”,便“有責任遵照上帝的旨意拯救世界”[7]。如此一來,按照“上帝的旨意”來“拯救”中國這個異教國度便成為基督教徒的責任,而這種以基督教文明來拯救中國“異教徒”的話語貫穿于早期美國來華傳教士的書寫當中,配合著美國的海外擴張,也影響著美國境內民眾的中國觀。
早期美國來華傳教士所呈現的“異教徒”中國形象是一種“罪惡的”“待拯救”的形象。這種形象的生成不僅源于傳教活動的需要,也與基督教的“原罪觀”以及“異教徒”這一符號所蘊含的價值體系息息相關。以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為代表的早期美國來華傳教士以《中國叢報》(The Chinese Repository)為陣地向美國民眾介紹他們眼中的中國。他們所呈現的中國人形象勤奮向上,但也迷信、無知、幼稚。因此,傳教士興辦學校,試圖以“基督文明”啟蒙中國人,改變中國人的精神面貌,使中國人皈依基督教。在早期美國來華傳教士的書寫中,中國人身上所體現的“罪惡”是時常可見的。例如,衛三畏曾寫道:“他們的對話中充滿了骯臟的詞語,他們的生活中充滿了不潔的行為……比肉體的罪惡更難以洗刷的是中國人的虛偽,以及伴隨著的罪惡、卑鄙的忘恩負義”[8]。在衛三畏看來,中國人從肉體到心靈都顯現著“罪惡”,他們“不講衛生”“道德低下”,而要改變這樣的面貌唯有依靠基督教的宗教信念和上帝的救贖,如此一來,傳教活動便具有了合理性和神圣性。對于“罪惡的”“待拯救”的中國形象的夸大既是出于傳教活動的需要,也源于基督教的“原罪觀”和“異教徒”這一符號所蘊含的價值體系。基督教徒之所以會將中國視為“罪惡”的化身,一方面是由于基督教徒原本就對“罪”有敏感而深刻的認知,他們認為人生來便是有罪之身,需要用一生的善行去彌補;另一方面是由于文化沖突和文化認同,任何兩種文化在剛開始相遇時都存在著難以互相理解的部分,一經環境激發便可能產生負面認知。再則,中國人對宗教的理解與基督教徒有著天壤之別,在基督教徒看來,不信上帝的便是“異教徒”,中國是一個“由不信上帝的異教徒組成的國度”,是罪惡和墮落的。在基督教徒看來,“異教徒”不僅僅是不信基督教的人,更是一個復雜的能指鏈,在《圣經》中,“異教徒=崇拜偶像、財寶眾多而又邪惡淫蕩的外邦人=蛇/龍=魔鬼/撒旦。他們是一體的,都是邪惡和墮落的象征,是上帝的敵人,也就是基督徒的敵人,理應將其誅滅而后快”[9]。從這一“邪惡和墮落的象征”來看,中國人是“罪惡的”,等待上帝的拯救。裨治文更曾在《中國叢報》發文呼吁“所有國家聯合起來共同行動”以化解中國人的“罪惡”,因為“這些罪惡危害著的不僅是一個國家,而是所有國家”[10]。
(二)早期美國來華傳教士中國觀對美國民眾的影響
早期美國來華傳教士的見聞和感悟通過刊物及論著深刻影響著美國人對中國人的認知。《中國叢報》第四卷的注記就表明該刊定期無償向印度、歐洲及美國的公共機構、媒體和個人寄送。伊麗莎白·馬爾科姆(Elizabeth Malcolm)亦曾指出,“當時西方大部分有影響力的期刊均得到了《中國叢報》的贈刊,如《北美評論》(North America Review)、《愛丁堡季刊》(Edinburgh Quarterly)、《威斯特敏斯特評論》(Westminster Review)以及《布萊克伍德雜志》(Blackwoods Magazine)等,這些刊物所刊登的與中國相關的文章,大都參考了《中國叢報》所載文章或是鳴謝《中國叢報》贈刊”[11]。在接觸渠道非常有限的情況下,早期美國來華傳教士的觀點和論述也就成了美國人認知中國的最重要渠道之一。除了《中國叢報》以外,傳教士的各種與中國相關的言論也在美國國土上產生重要影響,“由美國和英國的傳教士所生產的關于中國的‘專家證詞”以“東方專制主義”(Oriental despotism)和“亞細亞生產方式”(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的面貌出現在美國民眾的認知中和美國的報紙上[12]。在以自由和民主為主要價值觀的美國人看來,專制主義是束縛人性的落后社會制度,正是晚清政府的腐朽使民眾處境日益艱難,而亞細亞生產方式則在工業社會中因效率低下而導致落后和貧窮。這兩種面貌表明中國人身處苦難當中,需要民主、自由的精神和先進的生產方式,而傳教士幫助中國人改變這種狀態的方式就是傳播知識并以基督信仰洗滌中國人的精神世界。從布勒特·哈特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傳教士“拯救異教徒”話語對美國民眾的影響以及排華情緒與美國民眾對中國人“道德問題”的擔憂之間的聯系。
三、布勒特·哈特對傳教士異教徒書寫的挪用
早期美國來華傳教士所構建的中國形象成為哈特生活時代美國民眾認知中國人的深刻印記。不過,哈特卻并未以傳教士的基督徒/異教徒的二元對立視角來看待中國人。相反,他以一種近乎異教徒的觀察方式來認識中國人。單從文本內部來看,在《異教徒中國佬》一詩中,他對早期美國來華傳教士的“拯救異教徒”話語進行了戲仿,而在短篇小說《異教徒李頑》中他改寫并解構了這一話語,這樣的互文性書寫體現了哈特的中國觀以及基督教世界中異教徒話語的流變。
(一)《異教徒中國佬》對“拯救異教徒”話語的戲仿
《異教徒中國佬》這首簡短的敘事詩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詹姆斯(James)和他的朋友奈依(Nye)與華工阿信(Ah Sin)玩紙牌賭錢欲作弊騙取阿信錢財而反被阿信算計,阿信作弊被發現以后奈依動怒欲對其施暴。在《異教徒中國佬》這首詩中,哈特借敘述者對早期美國來華傳教士所宣揚的“罪惡的”“道德低下的”中國形象進行了戲仿。詩中的華工以“Ah Sin”為名顯示了基督教的影響力和敘述者的宗教身份。從他對華工的名字的看法,可以看出這位敘述者也秉承著“原罪”觀,認為“異教徒中國佬”是“戴罪之身”:
他的名字叫阿信(Ah Sin);
我不否認
這個名字
所含的蘊意;[13]
詩中的敘述者一開始就將阿信的名字與基督教中的“Sin”聯系起來并“不否認”此名之后的“蘊意”,說明這個時候敘述者已經預設了詩中的華工的“罪孽”,并通過呈現華工作弊的不道德行為引導著讀者對此做出價值判斷。對詩中華工之罪的預設也可以看到早期美國來華傳教士話語的影子,正是這種預設使得敘述者總向他的朋友奈依提起詩中華工“帶有孩子氣”的笑容,這種“帶有孩子氣”的笑容對他們來說既是不成熟的表現,也是極具欺騙性的偽裝,而敘述者講述這個故事的目的便是揭露這種偽裝:
請聽我來講一講,
我說的絕對是實話。
說到歪門邪道
或是詭計多端,
異教徒中國佬絕對是個中高手。
且容我慢慢道來。[13]
敘述者用“實話”講述這個故事的目的在于說明華工擅長“歪門邪道”且“詭計多端”,而這個故事講述的十分成功,到結尾處他已經“對此深信不疑”。敘述者對其朋友奈依的作弊行為不加以譴責,卻將華工妖魔化,而奈依也從一個作弊欲騙取華工錢財的人成了一個“被中國廉價勞工毀了”的受害者。至此,哈特對敘述者話語的諷刺體現得淋漓盡致。事實上,早在一八六三年四月,哈特便在他的文章中這樣評論中國人:“他們大都誠實、守信、純樸、勤勉”,同時他譴責了排華運動對華人所造成的不公正待遇[14]。這也表明了詩中敘述者的態度并非哈特的真實態度,哈特只是借敘述者對早期美國來華傳教士所宣揚的中國異教徒形象進行了戲仿。而哈特也非虔誠的基督教徒,“根據他的著作和他所發表的信件,我們可以判斷,他不是一個對宗教應該處理的人類存在的神秘問題思考得那么多或關心得那么多的人”[1]。哈特從小就表現出對宗教的滿不在乎,為哈特作傳的麥爾溫(Henry Childs Merwin)舉了一個生動的例子:哈特兒時閱讀《天路歷程》(Pilgrims Progress)只覺得其中的角色十分好笑,而對他們的朝圣精神沒有太深的感觸。相反,哈特是一個近乎“異教徒”的人,“事實是,布勒特·哈特具有異教徒的那種道德上的冷漠和精神上的寧靜,而且作為一種必然的伴生物,他對人的生命和命運的膚淺看法是屬于異教的”[1]。哈特的這種異教徒一般的特質也影響了他看待世界的方式。與早期美國來華傳教士不同的是,他并不認為中國異教徒需要上帝的拯救,也不試圖以“高尚的道德”啟迪中國人。這使二者的異教徒書寫顯示出對立性,這種對立的維度在《異教徒中國佬》中只能看到星星點點的蹤跡,而在哈特后來寫的《異教徒李頑》中則更加清晰地顯現出來。
(二)《異教徒李頑》對“拯救異教徒”的改寫與解構
在《異教徒李頑》這篇小說中,哈特以主人公李頑(Wan Lee)的人生經歷折射了早期美國來華傳教士“拯救異教徒”話語如何推動了殘酷的排華運動。小說的主人公李頑被其教父送到一個傳教士所辦的學校,并寄居在一個寡婦家里,其女是一位與李頑年紀相仿的基督徒,她試圖改變李頑的宗教信仰和道德意識:“正是這個聰明、活潑、天真、無邪的孩子走進了這個男孩的心靈深處,喚醒他的道德敏感性,讓他改變多年來一直對社會教誨和神學家的倫理道德無動于衷的狀態”[15]。這種“喚醒”和“改變”的欲望有著基督教傳教士“拯救異教徒”話語的影子,而這種想法植根于女孩的思想中也體現了“社會教誨”(the teachings of society)和“神學家的倫理道德”(the ethics of the theologian)的滲透作用。這個小女孩在這種觀念的影響下也想教化異教徒小男孩李頑,“這個小女孩很開心她能在他沒有意識到的情況下以基督善心改變他,所以他們倆相處得很好”[15]。但事實上李頑一直將自己的陶瓷神像藏在衣服里,這也表明了李頑宗教信仰方面的不可同化性。這種基督教的宗教信仰非但沒有讓他得到“拯救”,反而讓他喪生:“死了,我尊敬的朋友,死了——在不尋常的一八六九年,被一群毛頭小孩和基督教學童用石頭砸死在舊金山的街上”[15]。傳教士“拯救異教徒”是為了精神上征服異教徒,使之皈依。而當中國異教徒顯示出無法被基督教“高尚的道德”所教化的特質之時,精神感化便轉為暴力毀滅。故事的最后,手里緊握菩薩瓷像的李頑最終被基督教孩子用石頭砸死,而瓷像也被砸得粉碎,“那是李頑的陶瓷神像,被基督教的偶像破壞者用石頭砸碎了”[15]。
哈特的小說表明,早期美國來華傳教士所宣揚的“拯救異教徒”話語根植于美國民眾的意識當中,連未諳世事的小女孩也試圖通過基督文明改變李頑的道德觀念,但同時,哈特又改寫了這一話語,用李頑的死消解了基督教話語的崇高性,也顛覆和解構了以“基督文明”來拯救中國人的話語。在哈特的異教徒書寫中可以看到“拯救異教徒”根植于美國文化當中,而早期美國來華傳教士的異教徒話語也通過哈特的書寫實現了傳續與變異。
四、布勒特·哈特的異教徒書寫對排華運動的影響
從文本內部看,哈特在其作品中對早期美國來華傳教士異教徒話語進行了戲仿和改寫,但將他的作品放在排華運動的大語境中來理解,則能看到在傳教士話語深刻影響美國民眾的語境下,哈特的《異教徒中國佬》被誤讀的原因以及在哈特對排華運動中“驅逐異教徒”話語的挑戰。
(一)《異教徒中國佬》助燃排華情緒的歷史語境
前文提到哈特的《異教徒中國佬》在排華情緒高漲之時存在全國性的誤讀現象。《異教徒中國佬》這首短詩在美國國內掀起軒然大波是哈特始料未及的,但卻非完全出于偶然或是讀者對詩歌韻律本身的喜愛。這首詩的流行與民眾的排華情緒緊密相連,“幾乎每個人的背心口袋里或錢包里都夾著這幾行詩的剪報。每個人的嘴唇上都掛著這些詩句,其中一些最重要的詩句在眾議院中被朗誦,聽者報以熱烈的掌聲”[1]。自發表以來這首短詩也不斷被重印、漫畫化、戲仿,以及被政壇人士援引以支撐其反對中國移民的主張,助長排華情緒。
事實上,這首短詩在《排華法案》(Chinese Exclusion Law)通過之后仍具有影響力,一八八八年民主黨副總統候選人艾倫.瑟曼(Allen Thurman)在競選期間曾引用這句話來證明自己反對中國移民”[14]。《異教徒中國佬》一詩存在集體性誤讀的現象不僅僅源于華工大量涌入美國所造成的就業問題,更是因為中國“異教徒形象”在美國民眾的潛意識里扎下了根。在華工威脅到美國工人尤其是愛爾蘭工人的工作機會時,中國“異教徒”形象更是成為驅逐華工的重要依據。正如唐海東指出的那樣,雖然愛爾蘭移民自踏入美國國土后一直受到排斥,但是與華工相比,他們具有許多優勢,比如說,白皮膚、基督教信仰、完整的家庭以及充分的政治發言權和話語權[16]。擁有這些優勢的愛爾蘭工人在與華工的工作競爭當中運用政治資源和輿論的力量將華工塑造為“黃賭毒俱全、善于欺詐、道德墮落、習俗怪異、難以同化、冷漠隔絕、為微薄工資不惜違背就業準則、嚴重威脅白人家庭生存的異教徒”[16]。再加上早期美國來華傳教士的異教徒話語對美國民眾的影響和政治宣傳的需要,排華情緒不斷高漲,在這樣的情況下,《異教徒中國佬》便被用作排華運動的宣傳讀物。
(二)哈特對排華運動中“驅逐異教徒”話語的挑戰
一八七四年,哈特發表短篇小說《異教徒李頑》之時美國已發生過多次排華暴亂,民眾排華情緒日益高漲。面對高漲的排華情緒和《異教徒中國佬》被誤讀的情況,哈特以《異教徒李頑》挑戰了排華運動當中盛行的“驅逐異教徒”話語。首先,他對排華暴動的理由進行了批駁,“在大事接連不斷的那年當中有兩天是會被舊金山的人們長久地記著的——那兩天里一大群公民聚集起來殺害了一群手無寸鐵的外國人,他們殺這些外國人是因為他們是外國人,因為他們是屬于其他種族,有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膚色,且能夠掙到他們應得的錢”[15]。在哈特看來,因華工的到來而引發美國工人的就業危機并不是排華運動最重要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因為中國人是種族和宗教他者,與美國民眾格格不入。
類似地,針對華工大量涌入美國會威脅美國民眾的就業機會的擔憂,衛三畏曾根據其對中國人和中國移民的了解,撰寫《中國移民》(Chinese Immigration,1879)為中國人作了一番辯護,他寫道,“過去四十五年的華人移民總數,還不能與當時六個月內來美的歐洲移民之數持平”[17]。而對于華人移民增長的趨勢,他繼續分析道,“現在的華人數量增長,要比開放初期少得多。三十年過后,這片上帝之區依舊被新教子民所占領”[17]。如此看來,對于異教徒侵入的擔憂是排華情緒高漲的重要原因,當衛三畏在為中國人辯護力挽排華狂潮之時仍不忘提醒美國民眾“三十年過后,這片上帝之區依舊被新教子民所占領”。在《異教徒李頑》中哈特批評了政治家鼓吹驅逐異教徒的現象,他寫道,“有一些著名的政治家——我覺得把他們的名字寫在這里都令人羞愧——開始認為憲法當中保障公民和宗教自由的條款是一個錯誤(the passage in the Constitution which guarantees civil and religious liberty)”[15]。通過批判排華暴動和鼓吹驅逐中國人的政治家,哈特挑戰了排華浪潮中盛行的“驅逐異教徒”話語,但哈特的聲音在風起云涌的排華浪潮中并沒有產生大的反響。
《異教徒李頑》發表之后四年,也就是一八七八年,美國國會決定制定《排華法案》。經過多輪激烈辯論,一八八二年《排華法案》正式通過。雖然哈特發表這篇小說之時《排華法案》還沒有正式生效,但通過立法以驅逐異教徒中國人的呼聲已頗為強烈。異教徒中國人的“道德低下”“不講衛生”與“不可教化”等特質共同構成了排華運動支持者的“驅逐異教徒”話語,而哈特對這一話語的挑戰體現了排華運動不僅僅是一場就業機會的矛盾,更是一種對不可被同化的異教徒中國人威脅基督教徒“道德”的擔憂,但哈特的話語在當時排山倒海的排華浪潮當中并未被揭示和接受。
五、結語
文明與野蠻、基督教徒與異教徒之間的二元對立是西方世界認識中國人的重要維度,這種認知方式深刻影響著中美文學文化關系,推動了排華暴動的發生。十九世紀三十年代以來,當美國經濟建設趨于繁榮時,美國的傳教事業擴展到了中國。早期美國來華傳教士通過《中國叢報》等報刊以及著述向美國民眾展示中國人的面貌和狀態,但他們往往將中國描寫為野蠻的、不信上帝的國度。他們宣揚以“基督文明”拯救中國“異教徒”于水火之中,顯示“基督文明”高于非基督文明的優越姿態,隱含著西方優于東方的權力關系。早期美國來華傳教士的“拯救異教徒”話語對美國民眾的認知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哈特的詩歌《異教徒中國佬》出現集體性誤讀并助推排華浪潮也顯現了這種話語在美國國土的重要影響力。雖然在這首詩歌中哈特只是對早期來華傳教士所建構的“道德低下”的中國異教徒進行了戲仿,反映了美國民眾對中國“異教徒”的負面認知,但他后來所創作的《異教徒李頑》更加明確地改寫和解構了“拯救異教徒”話語,并挑戰了排華浪潮當中的“驅逐異教徒”話語。哈特揭示了基督教視角下美國民眾存在對中國人宗教信仰不可同化的擔憂是排華情緒高漲的重要原因,也揭示了排華運動中盛行的“驅逐異教徒”話語因違反美國憲法“保障公民和宗教自由的條款”而顯示出其脆弱性。“拯救異教徒”話語和“驅逐異教徒”話語所影射的是西方世界征服他者的需求,是東方學式的知識生產的重要話語策略。哈特對這兩種話語進行了挑戰,其實也無意間顛覆了文明與野蠻、基督教徒與非基督教徒的二元對立及背后隱含的權力關系。
參考文獻:
[1]Henry Childs Merwin.The Life of Bret Harte[M].Boston: Houghton Mif.in Company,1911.
[2]Tara Penry.The Chinese in Bret Hartes Overland:A Context for Truthful James[J].American Literary Realism,2010(1).
[3]朱剛.排華浪潮中的華人再現[J].南京大學學報,2001(6).
[4]Gerald Prince.A Dictionary of Narratology[M].Nebraska: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87.
[5]程錫麟.互文性理論概論[J].外國文學,1996(1).
[6]姜智芹.鏡像后的文化沖突與文化認同:英美文學中的中國形象[M].北京:中華書局,2008.
[7]劉澎.當代美國宗教[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
[8]Samuel Wells Williams.The Middle Kingdom[M].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1883.
[9]陳兵.基督教文化傳統、哥倫布與英國歷險小說中的土著形象[J].外國文學,2007(3).
[10]Elijah Coleman Bridgman.Negotiations with China[J].The Chinese Repository,1835(9).
[11]Elizabeth Malcolm.The Chinese Repository and Western Literature on China 1800 to 1850[J].Modern Asia Studies,1973(2).
[12]Eric Hayot.The Hypothetical Mandarin[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
[13]Bret Harte.The Heathen Chinee[M]//Benson G.The American Image of China.New York:Fredrick Ungar Publishing Company,1979.
[14]Gray Scharnhorst."Ways That Are Dark":Appropriations of Bret Hartes "Plain Language from Truthful James"[J].Nineteenth-Century Literature,1996(3).
[15]Bret Harte.Wan Lee,The Pagan and Other Sketches[M].London:George Routledge and Sons,1876.
[16]唐海東.異國情調·故國想象·原鄉記憶——美國英語文學中的中國形象[D].上海:復旦大學,2010.
[17]Samuel Wells Williams.Chinese Immigration[M].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879.
作者簡介:許靜吟(1995—),女,漢族,廣東揭陽人,單位為廣東外語外貿大學英語語言文化學院,研究方向為英美文學和中外比較文學。
(責任編輯:朱希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