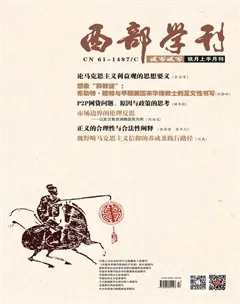鄉村振興視閾下推進少數民族傳統道德轉化問題探析
楊秀瓊 任健
摘要:黔南苗族傳統倫理道德是苗族社會歷史發展進程中逐漸流傳下來的調節該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和穩定的一種規范和行為準則。在戀愛、婚姻家庭方面,表現為贊成自由戀愛、重視婚姻家庭的穩定;在勞動方面,表現為重視勞動道德,強調勤勞對生活的意義;在社會公共生活中,表現為重視公共道德;在與自然關系上,表現為敬畏生命、尊重自然規律和熱愛人居環境的倫理道德觀念。在現代化的進程中,由于黔南苗族地區經濟結構的變遷和社會轉型、人員流動性加大以及傳統道德功能滯后于生活實際等方面的因素,使黔南苗族傳統道德在調節社會關系時出現困境。在鄉村振興戰略的背景下,加強黔南苗族地區的道德建設,推進黔南苗族傳統道德的轉化,需要通過與現代道德元素相融合,營造良好的道德建設的氛圍,發掘苗族鄉賢在道德建設中的引領示范作用及加強黨的建設。
關鍵詞:鄉村振興;少數民族;傳統道德;轉化
中圖分類號:D648 ?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6916(2020)17-0147-04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了以“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1] 為總要求的鄉村振興戰略,明確了中國鄉村發展的目標。在民族地區實現鄉風文明,需要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加強少數民族群眾道德教育,又要注意挖掘少數民族傳統道德文化中既有的優秀思想觀念、人文精神、道德規范,充分發揮其在凝聚人心、教化群眾、淳化民風中的作用,以推動民族地區的道德建設。貴州黔南是苗族群眾主要聚居區域之一,在該地區實現鄉村振興目標,要進一步充分挖掘黔南苗族中優秀傳統道德文化資源,以助力鄉村振興,提升該地區的道德水平,推動貴州黔南苗族地區的鄉風文明建設。
一、黔南苗族傳統道德的特征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指出:“人們從他們進行生產和交換的經濟關系中,獲得自己的倫理觀念。”并強調“一切以往的道德觀念歸根到底都是當時社會經濟的產物”。[2] 少數民族道德是少數民族在社會歷史發展進程中,以善惡觀念作為評價尺度,通過社會輿論、傳統習慣和少數民族成員內心信念等方式維系的,調節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關系的規范和行為方式的總和。少數民族道德為各民族提供了既定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并起著維護民族內部團結統一的作用,它反映了少數民族的經濟關系,而經濟關系實質就是利益關系,這就是說,少數民族道德反映了少數民族的利益關系,而利益關系決定著道德的內容和評價標準。隨著社會經濟結構的發展變化,少數民族道德的內容評價標準相應地得到補充、更新、調整和完善。同時,由于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亦會造成民族道德的多層次性。
苗族是中國西南地區人口較多的少數民族,第6 次全國人口普查的資料顯示,苗族人口在全國總人口排名中占第6 位,約有940 萬人。其中,貴州境內居住的苗族人口有400 多萬,占了全國苗族人口總數的二分之一。目前,居住在貴州黔南的苗族,人口約有59.9 萬,分布在黔南12 縣市,其中人口3 萬以上的苗族主要分布在都勻、福泉、三都、貴定、龍里和惠水等縣市。黔南境內的苗族屬于漢藏語系苗瑤語族苗語支,分屬湘西方言(東部方言)、黔東方言(中部方言)和川滇黔方言(西部方言),其傳統節日主要有“四月八”“鼓藏節”“吃新節”“苗年”等。由于黔南苗族群眾常年居住于自然環境相對惡劣的石漠化嚴重的偏遠山區,高山冷寒、土地貧瘠的山區、丘陵與高山邊緣的壩子區以及邊遠的河谷地帶深山區,造成黔南苗族生產力發展水平較低,自然經濟廣泛存在于各苗族村寨中,甚至有的苗族村寨在新中國成立前糧食尚不能完全自給,每年四季都要用一部分時間到鎮或附近地區去“打雇”,以解決口糧不足問題[3]。在這種自然環境下生存的黔南苗族村寨,呈現傳統中國鄉土社會的一個側面,形成了具有地域特點的苗族傳統倫理道德觀念。
在戀愛、婚姻家庭方面,苗族贊成自由戀愛、重視婚姻家庭的穩定。婚姻是兩性的結合,是組成合法家庭的前提。家庭是婚姻的結果,承擔著生育和撫育功能。唯物史觀認為,人類的生產包括兩大類:一是物質的生產與再生產,二是作為人類自身的延續與生產。婚姻家庭是延續人類發展的主要途徑。婚姻家庭的維系不僅需要完備的法律體系,還需要相應的倫理道德觀念對婚姻家庭加持。家庭的性質、結構、功能及倫理觀念與一定的社會生產方式相關,家庭倫理道德是調節家庭成員利益關系的行為規范。在苗族的戀愛觀中,苗族倡導戀愛自由,允許男女青年通過“游方”等形式定情。在婚姻關系中,苗族男女青年多采取自愿或父母同意的基礎上締結婚姻關系。此外,還存在姑表婚形式,它以延續舅家子嗣為前提,通過姑家女兒嫁與舅家兒子的婚姻形式。在家庭關系中,普遍采取一夫一妻的父系家庭制,家庭內分工雖有不同,但相較于漢族傳統,其地位基本平等。在家庭倫理道德上,普遍有尊老愛幼、孝敬父母、長幼有序、禁止亂倫的傳統,在生活上對老人有特殊照顧。如在喜宴中有長輩或老者入座,雞頭、雞肝等需獻與長輩或老者,然后小輩方可食用雞肉,以表示對長輩或老者的尊重。
在勞動方面,重視勞動道德,強調勤勞對生活的意義。勞動道德是人們在生產勞動中應遵守的規范和行為準則。歷史上的苗族生產力水平落后,在個體勞動中強調勤勞對生活的意義,苗族女子到一定年齡便要自己制作女紅,把勤勞看作是成家立業的根本。對于慵懶之人,輿論上投以鄙夷的目光。在集體勞動中,提倡相互幫工。
在社會公共生活中,重視公共道德。在一些苗族村寨中,人們為了生產、生活的需要,都制定有相應的村規寨約,村規寨約以本村寨、本民族優秀的道德觀念和道德標準為前提,緊密聯系實際,把道德教育和一定的戒懲結合起來規范行為準則。村規寨約在民族村寨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和權威性,是民族道德意識的體現,是一種少數民族民間的法。村規寨約在貴州黔南的一些苗族村寨中表現為“議榔”,如貴州三都的排燒苗寨,民風淳樸,民間“議榔”組織特色濃厚,寨內很少發生偷盜現象[5],這說明“議榔”在苗族村寨的內部穩定方面發揮獨特的作用。
在與自然關系上,形成了一套關于人地關系的倫理道德觀念,表現為敬畏生命、尊重自然規律和熱愛人居環境的倫理道德觀念。由于歷史、地理、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原因,在一些苗族村寨中保留著視為神物的樹、泉、林、山、湖等自然靈物,相應地也就有一套完整禁忌,這些禁忌實際上展現了苗族道德意識,它規范著人與自然的關系。
綜上所述,黔南苗族的傳統道德觀念反映了苗族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維系了苗族傳統社會內部穩定和團結,起到了精神紐帶的作用,展示了苗族的內部團結。在苗族發展進程中,苗族傳統道德觀念融化于個體內心中,成為個體的價值觀念、思維模式、心理狀態、內心信念及自身實踐的精神動力,推動了個體的道德實踐。
二、黔南苗族傳統道德面臨的挑戰
新中國成立后,黔南苗族經濟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黔南苗族與其他民族共同為社會主義服務,黔南地區的各民族都共同面臨著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歷史任務。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濟實現了前所未有的跨越式發展,在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國家推動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將對解決“三農”問題,夯實農村發展的經濟社會基礎,全面決勝小康社會,整體推進我國現代化進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產生重大影響。當下,在我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歷史進程就是要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宏偉目標,就是社會全面轉型、升級的過程。按照唯物史觀的觀點,轉型首先是從物質生產方式(即經濟關系)開始的,與之相適應的思想、觀念、倫理道德等上層建筑亦隨之變化。在這種背景下,農村正在由鄉土社會走向后鄉土社會,在自然經濟條件下形成的黔南苗族倫理道德觀念受到沖擊,調節苗族社會關系時出現困境。
第一,市場經濟發展加速了黔南苗族地區經濟結構的變遷和社會轉型,沖擊了黔南苗族傳統道德觀念存在的利益基礎。傳統苗族村寨由于自然地理、交通等因素的影響,經濟發展較為緩慢,經濟結構單一,造成了苗族村寨生產力水平相對落后的情況。建國后,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建立,我國政治經濟關系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全國人民的道德觀念和價值取向也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改革開放后,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得到進一步發揮,市場通過“看不見的手”使經濟運行遵循價值規律的作用,供求關系得到滿足。在市場作用下,包括黔南苗族在內的各地的少數民族都被納入市場經濟發展軌道中,納入到快速發展的現代化進程中。黔南苗族在此背景下加速從傳統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從封閉社會轉向開放社會,從落后的自然經濟走向市場經濟,這意味著作為黔南苗族傳統道德存在基礎的自然經濟正在加速解體。
第二,人員流動性加大,加速了黔南苗族地區人口的空心化,使傳統道德調節的對象——人在逐漸減少。費孝通先生認為,傳統的農業社會本質上是一個鄉土社會。鄉土社會的特點之一是人口缺乏流動性。一般情況下,人們是生于斯、長于斯、老于斯、死于斯,由此形成了彼此相互熟悉的、流動性較小的熟人社會。決定熟人社會人口發展的婚姻關系,自有其運作機制。苗族傳統的人口生產主要是通過姑表婚、村寨內不同姓相互締結婚姻關系或附近相鄰村寨間相互締結婚姻關系等進行。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市場機制配置資源力度加大,人的生產積極性得到調動,人們對改變自身的生活狀態,對美好生活充滿了更多的愿景。在這樣一種大背景下,少數民族村寨的民眾走出鄉村,外出務工,流入城市,創造美好生活的意愿更加強烈。自20 世紀90 年代以來,農村逐漸形成的打工潮加速了少數民族群眾走出民族村寨、走出大山的步伐,村寨中的青壯年勞動力大多選擇外出打工,甚至進城定居,以尋求更美好的生活。在他們走出村寨后,黔南苗族村寨中留下的大多是老年人、中年婦女和留守兒童,這些人成為當地苗族社會中的留守一族,而本應成為苗族村寨發展主力的青壯年則外出務工,成為我國成千上萬打工大軍中的一員。苗族村寨發展的潛力被抽空,傳統倫理道德得以維系的根基被動搖。
第三,傳統道德功能滯后于生活實際。傳統少數民族村寨的道德關系建立在土地為核心的基礎上,農民依賴土地的產出獲得生活成本,并以一定的土地為中心建立個體的交往關系,在交往關系基礎上形成了一定的地緣—血緣共同體,并在這種共同體中形成生活世界,獲得生活意義。隨著市場化深入、青壯年勞動力外出打工,農村原有的社會關系被打破,造成的后果之一便是村民的土地情結淡化,這標志著傳統農耕觀念的解體。由于新的生產方式興起引發少數民族村寨運行結構的變遷,使傳統道德發生一系列變化,進而碎片化、邊緣化。以婚姻家庭道德為例,隨著80 后、90 后、甚至00 后逐漸長大成人,年青人對于配偶的選擇面,相較于父母輩,不再局限于相互了解的熟人社會,甚至選擇來自省外的男女組建家庭。其中,受教育女性外嫁的意愿表現得更為強烈,受教育男性在外地工作娶外地女子增多,經濟條件較差、家庭負擔較重的大齡未婚男性的數量增多。這表明,隨著經濟的發展,年青人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苗族青年的婚嫁觀念正在逐漸改變,苗族傳統婚姻道德觀念已滯后于苗族青年實際。
三、以“鄉村振興”為契機,推動黔南苗族傳統道德的轉化
在推進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我們正在推進一場前所未有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歷史活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黔南苗族傳統倫理道德只有在這場偉大的社會歷史變革中實現現代轉型,才能有如鳳凰涅槃般得到重生。這是一場艱難而又必須要完成的現代轉型,為此,必須搶抓機遇,利用國家對民族地區政策優惠,結合自身實際,推動黔南苗族傳統倫理道德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有機融合,實現鄉風融合的目標。需要說明的是,傳統向現代轉換是繼承性發展、創造性轉換的過程,目標是傳統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實現再造,這需要找到傳統與現代的契合點,為傳統注入新的活力,同時,揚棄不合時宜的要素。轉換的核心是實現個體的思想觀念、道德意志、思維方式、行為模式、心理意識的躍遷,并最終實現人的現代化。在推動鄉村振興過程中,《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的發布,無疑為黔南苗族傳統倫理道德轉換指明了方向。
第一,在分析黔南苗族傳統道德實際狀況的基礎上,明確其歷史定位,發掘其具有現代社會相容性的元素,與現代道德相整合。應該看到的是,黔南地區苗族的傳統道德觀念既有傳統美德和對良好道德秩序的向往,也摻雜著封建迷信,對于摻雜封建迷信的道德禁忌應該加以剔除。在現代化進程中,對有助于促進黔南苗族經濟社會發展的道德觀念,應加以吸收并轉化為自身道德意識的一部分。與此同時,要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公民基本道德規范為基礎和前提,融入黔南苗族地區道德建設,實現傳統道德與現代道德觀念的融合。
第二,創造良好的道德建設的氛圍。道德是在社會生活實踐中形成的并以善惡為標準的客觀價值,其功能的發揮在于人們內心形成向善的道德理想。要在推進道德建設的進程中,將先進的道德觀念轉化為人們內心的道德意識,并在生活中形成道德自律從而自覺實踐。同時,針對不同群體開展道德養成教育。對于青少年開展強化義務教育和職業教育,普及科學文化知識,提升他們理性認知世界的能力;對于留守婦女,普及科學文化知識,提升他們的科學文化素養。加大黔南苗族地區基層民主政治建設力度,推進政治文明建設。著力改善民生,加大精準扶貧力度,調整農業產業種植結構,增強苗族群眾的增收渠道,為苗族地區道德建設夯實經濟基礎。推動先進文化下鄉,形成先進文化與地方文化水乳交融的局面。
第三,重視黔南苗族鄉賢在道德建設中的引領示范作用。鄉賢文化是中國歷史上一種獨特的文化現象。在國家權力未達鄉村之時,鄉賢成為普通民眾與政府溝通的橋梁,是鄉村秩序的執行者和維護者。歷史上的鄉賢,大多為品德高尚、處事公道正派之人,他們所做的大多為修橋鋪路、教化地方、捐資助學等事,以自己的言行引導周邊民眾傾心向化、從德向善,同時組織地方的公共活動。因此,這些鄉賢多受人尊敬,成為地方的領袖,對引領地方文化發展、推動經濟繁榮起到促進作用。在當下,黔南苗族社會中,鄉賢的主要來源主要為改革開放以來成長起來的財富精英、鄉村社會中舊有德高望重且處事公道之人及農村“兩委”干部。對于財富精英而言,他們是改革開放以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走出鄉土成長起來的人,他們有回歸鄉土,參與本鄉本土的公共事務建設的意愿,他們仍然存在家鄉情結,希望自己的家鄉變得更加美好,所以會積極主動地投入到鄉土建設中。從鄉村走出的財富精英對于未走出大山的人而言,他們展示了對鄉土之外的世界的駕馭能力,對于鄉土社會中的其他人而言具有巨大的吸引力,由此,這些人成為鄉土社會中人們羨慕和崇拜對象,他們回到鄉土后有一種自然的感召力;對于自然領袖而言,自然領袖通常是黔南苗族社會中德高望重、能言善辯、通曉當地歷史的人。他們通過參與和維護村寨各種公共事務中發揮自己的作用和影響力,如制定村規民約、評判本地山林、田地糾紛,調解家庭矛盾等,他們在熟人社會中存在著天然的感召力。對村“兩委”干部而言,他們是鄉村中的黨員和干部,是國家意志在鄉村的執行者。在推進鄉村振興的進程中,他們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在推進鄉村振興的進程中,要通過凝聚財富精英、自然領袖的力量和鄉村“兩委”干部的力量,發揮他們的引領示范作用,共同推進苗族社會的道德建設,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黔南苗族社會中生根發芽。
第四,在黔南苗族地區強化基層黨組織的引領作用。在推進鄉村振興中,需要進一步加強黨的領導,其中包括思想道德建設的領導。在黔南苗族地區推進鄉村振興戰略,實現黔南苗族傳統道德向現代道德的轉化中,需要切實加強黨的領導,提升思想引領的水平,引導民族傳統道德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相適應。既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以黔南苗族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表達,又使黔南苗族傳統道德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煥發新的生命,發揮調節苗族社會關系的作用。
四、結語
黔南苗族傳統道德是黔南苗族在其自身發展進程中長期積累起來的精神財富,是苗族先民處理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關系中,逐漸形成的苗族優秀傳統文化的體現。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進程中,需要賦予黔南苗族以新的內涵。在找尋苗族傳統道德觀念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契合點過程中,需要把握二者的辯證關系,唯有如此,才能讓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廣大的黔南苗族群眾接受,又使黔南苗族道德煥發新的生機,從而更好為促進苗族經濟社會發展,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服務。
參考文獻:
[1]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EB/OL].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2/04/c_1122366449.htm.
[2]馬克思, 恩格斯.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M].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3] 貴州省民族宗教事務委員會, 貴州省民族研究所. 貴州“六山六水”民族調查資料選編·苗族卷[M]. 貴陽: 貴州民族出版社,2008.
[4] 吳正彪, 吳進華. 黔南苗族[M]. 北京: 中國文化出版社,2009.
作者簡介:楊秀瓊(1981—),男,苗族,貴州凱里人,黔南民族醫學高等專科學校社科部副教授,研究方向為少數民族文化與思想政治教育。
任健(1980—),男,仡佬族,貴州正安人,哲學博士,貴陽學院陽明學與黔學研究院研究員,碩士研究生導師,研究方向為中國哲學、中國文化。
(責任編輯:王寶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