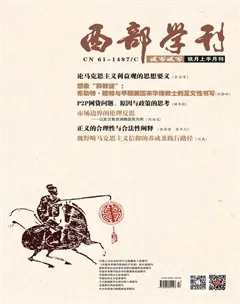正義的合理性與合法性闡釋
岳海湧 童書元
摘要:合理性是正義的屬性之一。正義的合理性在于它能夠對正義的必然性和可行性做出說明和論證。為正義辯護,即為人們的合理觀點尋求令人信服的根據或證據,使人們的正義主張既具有說服力和正當、充足的理由,也使得正義既有客觀性又有理性和邏輯的力量。因為正義的合法性需要多數人的同意或認可,因此它能夠成為一個國家權威的源泉和基礎。正義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的關系是辯證的:正義的合理性是正義的合法性的前提和基礎,正義的合法性是正義的合理性的“中介”或實現的手段。正義具有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使得它必將逐漸成為人們普遍接受的具有共通性的價值觀念和規范。
關鍵詞:正義;合理性;合法性;價值
中圖分類號:D08 ?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6916(2020)17-0114-04
從柏拉圖到羅爾斯,在西方思想史上,關于正義的內涵,不同時代、不同思想家因其觀察視角的不同,而有著各異的看法和不同的理解。由于人們所處的歷史條件和文化背景的差異,正義也被不同地域、不同信仰的人們賦予不同的內容,從而形成了不同的正義觀。理論上多元化的正義觀恰恰有利于豐富和從某個角度加深人們對正義的理解。實踐證明,自古至今,正義之所以為大多數人所崇尚,在于正義觀念的內涵更具有其內在的一致性。
無疑,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問題,能否及時而準確地發現并把握該問題,決定著一種理論的價值和生命力。正義問題橫跨哲學、倫理、政治、法律、宗教、經濟、社會以及心理學等范疇。從不同的角度深化理解和思考那些具有永恒性的問題,則有助于我們理解其意義和價值,如培根所說的:“我們就可以在思想上得到真理,而在行動上得到自由。”正義即屬于永恒性的問題之一。
在學術界,人們從合理性和合法性的角度對正義進行的研究尚不充分。以下我們做一番考察,以求加深對正義的認識。然而,正義像任何一種社會現象一樣,只有在它高度發展、充分得以展示時,才有可能被全面、正確地認識。
一、合理性與正義
從文獻來看,正義的觀念淵源眾多,理性即其中之一。社會契約論和自然法學派的主要觀點之一即認為,存在著一種完全出自理性的普遍正義,但這種正義必須是由具有理性的人共同認可并加以遵行,因而對他們的要求是相互的。如同盧梭所指出的:“當正直的人對一切人都遵守正義的法則,卻沒有人對他遵守時,正義的法則就只不過造成了壞人的幸福和正直的人的不幸罷了。”[1]
在黑格爾看來:“抽象地說,合理性一般是普遍性和單一性相互滲透的統一。具體地說,這里合理性按其內容是客觀自由(即普遍的實體性意志)與主觀自由(即個人知識和他追求特殊目的的意志)兩者的統一,因此,合理性按其形式就是根據被思考的即普遍的規律和原則而規定自己的行動。這個理念乃是精神絕對永久和必然的存在。”而“凡是合乎理性的東西都是現實的;凡是現實的東西都是合乎理性的。……最關要緊的是,在有時間性的瞬即消逝的假象中,去認識內在的實體和現在事物中的永久東西。”[2]我們可演繹黑格爾的這兩段話的意思如下:事物中蘊含著理性,理性具有必然性和普遍性的屬性,它是可被認識的,而人是有理性的,因此通過人這一中介,對理性的認識即是理性自己對自己的認識。合理性即是事物中理性的趨向——必然展現其自身內在的本質和規律,這一展現其自身內在本質和規律的力量是不可阻擋的,因而是一定會成為現實的。對理性的把握既要通過概念也要通過實踐——理性外化的現實。這里的關鍵在于,“現實的”①具有雙重屬性:假象和真相。因為真正現實的東西是合理性(vernünftig)的東西實現的環節,所以它有著存在的理由,例如事物的“合法性”即是這樣的一種存在現象。對正義的認識也是如此。正義是合乎理性的,它的內容或內在的價值也是由其具有的必然性和普遍性而能夠被人們認識和把握或展現自身成為現實的。由于非正義的現實即是不合理性的現實,是由于其“合法性”的假象或非法性的真相造成的“現實”,所以,“合乎理性的”正義必然展現其自身的“合理性或正義性”而終將成為正義的現實。
而“正義觀念能否被視為是理性以及它的合理對象,以及它是否能夠被認為是一個值得人們持久不斷關注的問題呢?”[3]回答是肯定的。事實證明,人們對正義的內容側重不同或對其要素進行先后抉擇,就會產生不同的實踐后果。那種對正義的否定或懷疑以及對正義具有某種制度的客觀效力的社會事實的忽視則會導致實踐中的“不正義”。就政治正義來看,不合理性的政制和行使的權力,如專制、極權遲早會走向終結。就法律正義而言,20世紀初的法律實證主義者,尤其是分析法學家試圖阻止對法律的性質和目的進行哲學或思辨的思考,并試圖把法理學的探究范圍嚴格限制在對國家制定和執行的實在法進行技術分析方面的實踐后果時,對那些強權即有理的信奉者們則是大行不正義之道的有力的理論支持。例如,希特勒上臺和法西斯政權及其法律雖是“合法的”和“現實的”,但其不具有合理性而僅僅是一種具有“瞬即消逝的假象”性質的存在。由于法律實證主義無力從理論上駁斥暴政是不爭的事實,因此,當在正義和實在法之間發生不可調和的沖突時,有必要承認完全無正義的法律必須讓位給正義。
至于理性的內涵,在西方哲學史上各派各家的主張迄今也是眾說不一。但是無論如何,把理性作為判斷正義的一個標準這一點是值得肯定的。從實際應用來看,理性的作用在于甄別真偽、辨別是非。
由于建立在理性基礎之上的真理具有客觀的實在性,可以為一切具有理性的人認可和遵循,所以在公共事務上沒有人有權抱著不合理的意見而隨心所欲。從蘇格拉底和智者的時代可以看出,否定了理性的統治,使任何別的見解——任憑個人混亂的感覺、主觀的幻象、奇想和欲望居于理性之上,結果都將顛覆真理的客觀性質,而陷于懷疑主義和相對主義。因此,就“人是萬物的尺度”來說,這一尺度也應該是指合乎理性而言。
正義的合理性要求對正義的必然性和可行性做出說明和論證,以解決對正義的信仰和理解之認識問題。為正義辯護,即為我們的合理觀點尋求令人信服的根據或證據,使我們的正義主張具有說服力和正當、充足的理由,使得正義既有客觀性又有理性或邏輯的力量。換句話說,如果我們的主張和行為要讓他人贊同和認可,當然需要向他人說明自己的主張和行為的正當性。只有在一個完全缺乏平等和正義觀念的非理性——例如有權即有理,正義即強者的利益的社會里,人們才無須向他人證明自己的行為的合理性或正當性。所以,無論是正義還是真理,只有訴諸說服,以理服人,而不能訴諸權力甚至暴力,能夠體現這一點的應該是一種值得稱道的合理性的社會狀態。韋伯的“社會行動理論”把這一現代社會的現象稱之為世界歷史過程的合理化,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則視之為“社會的理性化趨勢”的一部分。
在西方語言中,正義一詞本身即有正當、合理、正確的、恰當的、規律的、合理的或正當的道理的含義。
按一般性的理解,人們開誠布公地講理,自由、平等地論辯,合乎邏輯地推理,以尋求共識,而后信守約定等等這都是有理性的表現。正如波普爾所說的:這種源自古希臘人的西方理性主義傳統,是批判討論的傳統,它試圖通過反駁命題或理論來考察和檢驗它們,體現了思想自由和討論自由的價值[4]。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就正義的平等對待方面而言,按照經濟學關于經濟人的假設,和非理性的、急功近利的、甚至損人的利己主義者相比,理性的利己主義者能夠理解正義的必要性。這是因為他認識到,只有依靠正義的觀念和制度,交易者之間才能達到可持續的互利共贏的目的;而維持正義制度的前提是,有得必有失,享受權利,承擔責任。因此,有學者指出:“一旦人們必須向別人證明自己的行為的正當性,某些類型的私利,例如嚴重或明顯損害他人的私利,就很難以合理的方式得到辯護。”[5]
總之,為使普遍正義觀所內含的合理性為大多數人們所接受并得到踐行,如同羅爾斯主張的,要尋求重疊共識。他相信,“就民主社會的公民所能得到的而言,這是政治統一和社會統一之最合乎理性的基礎”。在他看來,“作為公平的正義具有政治正義觀念的三個特征,這一個特征有助于使它獲得一種理性的重疊共識的支持。這三個特征都會促使不同的統合性觀點來贊成它。這些統合性觀點可以是承認良心自由和支持基本憲法自由的宗教學說,也可以是同樣承認和支持它們的各種自由主義的哲學理論,諸如康德和密爾的哲學理論”。[6]
二、合法性與正義
若著眼于不同的領域,正義在道德領域是指人的行為不違反道德義務;在法律領域通常是指人的行為符合法律規則而不違反法律規則或法治,也指一種形式上的平等;而在宗教領域則指肉體應當歸順于靈魂;在政治領域則通常是指制度和人的行為的合法性。具體而言,政治合法性研究的是政治系統與民眾之間統治與服從的關系。
針對人的社會行為規則、社會制度而言,正義是一種公正合理的體制。這些正義的規則、制度在最廣泛的主體范圍內具有普遍可接受性,因而具有普遍同意性或認同性,也即合法性。以此為基點,羅爾斯在其《正義論》中提出了一種稱之為“作為公平的正義”的正義觀念。他認為,最合乎理性的正義原則是這樣的原則,即在公平的條件下它們會得到人們的一致同意。
“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7]。與法律實證主義認為正義就是合法律性即服從國家制定的實在法不同,從正義的政治角度看待合法性是關于法律的終極價值問題。政治正義則是按照對“正義”的認同和對共同的利益的認同而言的,從政治正義的視角來看,合乎正義的法律或“良法”才是法律。
政治正義通常指專門的政治機構在協調政治關系、矛盾與治理社會時所確立的一套被人們共同認可和普遍接受的公平而正當的標準與行為方式。
在對正義的認識上,與哲學注重研究正義與合理性問題相對應,政治學則著重探究正義與合法性的問題。亞里士多德認為,人之所以是最優秀的政治動物,是因為他是理性的和道德的動物。對人來說的最好的生活方式是實踐的或政治的生活。他說:“政治學上的善就是‘正義,正義以公共利益為依歸。”[8]而“政治的公正是以法律為依據而存在的”。[9]
社會契約論認為,不論最初的社會是否是從契約中產生的,未來的政府和權威只能靠同意或認同建立起來,或是從互利的契約中獲得合法性。從歷史上看,合法性的概念在革命、民族主義和選舉等形式中得到集中體現。就革命的合法性而言,洛克的辯護是有力的,他曾雄辯地指出:“擺脫一種由暴力而不是由正義強加于任何人的權力,縱有背叛之名,但在上帝面前并不是罪行,而是為他所容許和贊同的事情,即使靠暴力取得的諾言和契約起著阻礙的作用。”[10]120他還說:“要人們為了和平而不反抗暴政,因為這會引起紛亂或流血,正如羔羊不加抵抗地讓兇惡的狼來咬斷它的喉嚨,誰會認為這是強弱之間值得贊許的和平呢?……究竟是壓迫還是抗命最先導致混亂,我想讓公正的歷史去判斷。”[10]138
簡而言之,人們之所以應該服從政府或法律主要是因為一個國家民主的存在或公民享有平等的政治權利。因為歸根到底,一個政府的合法性只能從個人自愿讓予自然權利或自治權的同意中取得,在這里,同意是一個核心概念。而政府的合法性關系到政府在其中得以運用的制度體系本身的正義性,如此,一個社會才能夠保持在有秩序的狀態中,也才有可能建立法治政府。正是因為任何社會都不存在政府的合法性得到普遍承認的現象,所以才有政府更迭和反政府行為的存在。只有當合法性政府體現了正義原則時,才可擁有公正的參照點而據以判斷人們的一種行為是否“合法”。而政治上公正的行為就是政府和公民雙方都不違犯事先表示已經同意的規則,例如民主和法治以及人權保障的行為。它所涉及的是對賦予規則以合法性所必需的協議,這往往表現為法律和政策。由此,規則就獲得了合法性,因而也就可以成為判斷政府的行為是否公正以及政府要求公民如何行為的根據,這一切都取決于人們同意的具體規則是什么。體現為法律領域的法律正義即指構成法律的行為規則總和的內容在最廣泛的主體范圍內具有可接受性和可贊同性。例如,如果在立法時,在民主的基礎上最廣泛的主體都參與了立法制定,并對法案表示了接受、贊同,所通過的法律就是正義之法或“良法”,法律的實施也就更有保障。
有關制度正義或公正問題的研究,現代公共選擇理論的代表G·布倫南和詹姆斯·M·布坎南的觀點值得人們重視,他們在《規則的理由》中指出:“要考慮公正問題,就得研究規則問題。”[11]126“假如規則確實可以讓人們形成正當合理的預期,則公正的問題就必然迎刃而解。從這一意義來說,規則必然是與公正密切相關的;公正的行為,大致而言,就是遵守通行規則的行為。”[11]113
羅爾斯在他的新著《作為公平的正義》(2001年)中進一步論述了他曾經在其《正義論》(1971年)中提出的合乎理性的正義原則和重疊共識的觀念。他認為,“作為公平的正義的理念必須以這樣一種方式來加以規定,即這種方式應該是政治的,從而有別于與之平行的統合性學說的理念。在理性多元論的事實是既定的情況下,如果作為公平的正義(或者任何政治觀念)想要獲得重疊共識的支持,我們就必須同各種不同的觀點打交道。”[6]4而“在一個由公眾承認的政治正義觀念加以有效調節的秩序良好社會里,每一個人都接受相同的正義原則。這樣,這些原則提供了一種可相互接受的觀點,只有從這一觀點出發,公民關于基本結構之主要制度的要求才能夠被加以裁定。秩序良好社會的一個本質特征是,它的公共的政治正義觀念為公民建立了一個共享的基礎,以使其相互證明他們的政治判斷:在所有人都認定是正義的條款的基礎上,每個人都同其他人進行政治上和社會上的合作。”[6]35
總之,正義的合法性是一個國家權威的源泉和基礎。在現代,尊重和保障人權使一個國家的主權具有合法性。國家只要按正義原則保護個人的權利,也就能夠獲得合法性。
三、應正確認識正義的合理性與正義的合法性的關系
正義的合理性條件是自足的,并不以少數人還是多數人是否同意或認可為轉移,但正義的合法性是需要多數人的同意或認可的。一般而言,正義的合理性與正義的合法性的關系在于:正義的合理性是正義的合法性的前提和基礎,正義的合法性是正義的合理性的“中介”或實現的手段。抽象地看,只有在正義的條件下,也即賦予合法性正義的屬性時,正義的合理性與正義的合法性才是內在一致的,也正因為如此,正義才真正具有生命力。但在現實社會,僅就合理性與合法性本身而言,它們之間并不存在一致的關系。與具有單純屬性的合理性不同,由于現實的合法性具有雙重屬性:合于理性的合法性和不合于理性的合法性。就后者來說,例如,在按照多數人決定的民主制度下,其不合理的政治決定的判斷時常是依賴于投票人多數票的合法性而不是基于專業知識和正確意見的基礎之上。這往往導致所謂“多數人暴政”的問題。因此,正義的合理性與合法性則時常顯得相互脫離:或者正義的合理性(如正義的理論和觀念)在先而合于正義的合法性(對正義的合理性的認可和同意)滯后,或者不合于正義的合法性(例如認可和同意不具有合理性或不正義的主張和做法或制度)存在而正義的合理性缺位。但它們最終會達到一致的:正義的合理性終究會獲得正義的合法性的支持和體現,不合理性的合法性遲早會遵循正義的合理性。它們之間一致和不一致的關系也恰恰印證了黑格爾的“凡是合乎理性的東西都是現實的;凡是現實的東西都是合乎理性的”這句具有雙重二律背反性質的至理名言。
注 釋:
①德語“wirklich”一詞具有“真實的”“真正的”“確實的”和“實際存在的”等含義,它通常與“ideal”(想像的、合乎理想的)一詞相對。因此,“wirklich”側重于“實際存在的”之義,而事實上這種存在并非總是“合理的。
參考文獻:
[1]盧梭.社會契約論[M].何兆武,譯.北京:商務印書館, 1985:48.
[2]黑格爾.法哲學原理[M].范揚,張企泰,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1:254.
[3]E·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M].鄧正來,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258.
[4]波普爾.猜想與反駁——科學知識的增長[M].傅季重等,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502.
[5]慈繼偉.正義的兩面[M].北京:三聯書店,2001:133.
[6]約翰·羅爾斯.作為公平的正義[M].姚大志,譯.上海:三聯書店,2002.
[7]約翰·羅爾斯.正義論[M].何懷宏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1.
[8]亞里士多德.政治學[M].吳壽彭,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5:148.
[9]亞里士多德.尼各馬科倫理學[M].苗力田,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102.
[10]洛克.政府論:下篇[M].葉啟芳,瞿菊農,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
[11]杰佛瑞·布倫南,詹姆斯.M·布坎南.憲政經濟學[M].馮克利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作者簡介:岳海湧(1963—),男,漢族,甘肅靖遠人,中共甘肅省委黨校科學社會主義教研部教授,研究方向為政治哲學史。
童書元(1982—),女,漢族,山東煙臺人,中共甘肅省委黨校科學社會主義教研部講師,研究方向為政治學理論。
(責任編輯:朱希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