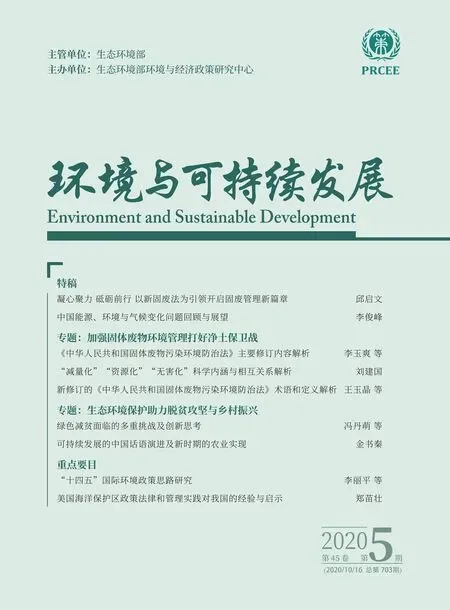新型城市群綠色轉型能力測度與評價研究
宋旭,劉全齊,于成學,孫莉
(1.生態環境部環境發展中心,北京 100029;2.廣東財經大學國際商學院,廣州 510320)
在傳統經濟發展模式下,區域經濟發展的活力還沒有得到充分發揮,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也將受到嚴峻考驗,那么區域經濟發展的模式也需要發展。隨著我國在2019年先后出臺了《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和《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規劃綱要》兩個關于新型城市群發展的重要文件,區域經濟發展也將走進新時代,加強新型城市群的建設也被提上了日程,對新型城市群綠色轉型協調發展能力的測度與評價研究也成為一個新的研究方向并日益增多。但目前對這些研究進行系統歸納的文獻還不多,因此,分析并歸納這些文獻對全面、正確理解新型城市群綠色轉型協調發展能力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1 新型城市群的概念、特點及其評價
1.1 相關概念的界定
1.1.1 新型城市群的概念界定
現有文獻主要是從城市規模、經濟、交通、信息網絡及其相互關系等方面界定城市群的內涵。比如,姚士謀等(2006)[1]認為城市群是指在一定的地理范圍內,大量性質和規模不同的城市形成以個別或幾個大城市為核心,依托一定的自然環境條件,借助于現代化的交通運輸網和高速信息網絡,增進城市相互聯系的相對完整的城市集合。王娟(2014)[2]認為城市群是在一定的人口集中區域內具有高度內在關系的新型城市集群。黃征學(2014)[3]認為城市群就是以一個或幾個有較強競爭力的城市為主,借助各種基礎設施,形成較高經濟與社會關聯度,具有合理空間與職能等結構的城市“綜合體”。也有學者從內在聯系的內容上對城市群的內涵進行了拓展。比如,魏麗華(2015)[4]認為新型戰略性城市群主要是指通過建立有效的協調與創新機制,發掘各種內外優勢,達到產學研、科技與經濟、創新驅動與產業發展相輔相成的目的,并促進經濟、社會、生態協調發展,在產業布局、發展規模與建設時序方面統籌安排,具有美好發展愿景的城市集合體。本文認同姚士謀等人的觀點,認為新型城市群是指在一定的區域范圍內包括一定數量的不同規模、產業和發展潛力的城市,以一個或多個大城市作為區域經濟的中心,依靠各自的優越條件,以便利的交通網絡和先進的互聯網技術為基礎,形成一個各有特色、優勢互補、協調發展的區域城市共同體。
1.1.2 綠色轉型的概念界定
國內外學者并未就綠色轉型概念做出界定。姜明生和姜艷生(2008)[5]認為綠色轉型的本質是一種經濟、社會與生態協調可持續發展的轉型。劉純彬和張晨(2009)[6]對資源型城市綠色轉型內涵進行了一般性分析。但有學者認為綠色轉型是實現綠色發展的前提,石敏俊(2017)[7]認為綠色發展包括幾個方面的內容,一方面經濟發展不能以犧牲環境為代價,必須構建人與自然和諧并存與發展的新局面,另一方面是樹立“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正確生態發展觀,促進資源的可持續利用。李俐佳和王雪華(2017)[8]認為綠色轉型是指為了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目標,必須倡導生態文明建設理念,發展循環經濟,轉變發展模式,做好綠色管理。因此,本文認為綠色轉型強調發展方式的轉變過程,從傳統的過度資源浪費、污染環境的發展模式向資源節約循環利用、生態環境友好的科學發展模式轉變,是由人與自然相背離以及經濟、社會、生態欠協調的發展形態,向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以及經濟、社會、生態協調發展形態的轉變。
1.1.3 綠色轉型能力的概念界定
目前,關于綠色轉型能力的評價較多,但還缺乏對綠色轉型能力概念界定的研究。界定好綠色轉型概念有助于正確理解綠色轉型能力的概念。由于理解綠色轉型的視角不同、綠色轉型的方式不同以及綠色轉型的階段不同,可以從多方面來理解綠色轉型能力。因此,本文認為綠色轉型能力可以理解為在發展方式轉變的過程中,從傳統的過度浪費資源、污染環境的發展模式向資源節約循環利用、生態環境友好的科學發展模式轉變的一種能力,是由人與自然相背離以及經濟、社會、生態欠協調的發展形態,向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以及經濟、社會、生態協調發展形態的轉變能力。總之,綠色轉型能力強調發展要從觀念、方式、模式、形態等方面進行轉變。
1.2 新型城市群的特點
為了更好地理解新型城市群的涵義,為我國新型城市群建設提供參考和建議,很多學者對國內外主要新型城市群的特點進行了研究。比如,李炳超等(2019)[9]分析了歐美和亞洲創新型城市的主要分布特點,對倫敦、新加坡、巴黎、中國香港等城市的排名情況進行了比較分析,得出一些啟示并提出相關的建議。李雪濤和吳清揚(2019)[10]用熵值賦權法研究我國珠三角等城市群時發現,這些城市群的發展指標中表現最好的是生態城鎮化發展指標,其次是土地和社會經濟發展指標,最后是人口的城鎮化指標。在城市群的綜合發展水平方面,珠三角城市群表現為第一,第二是長三角城市群,第三是京津冀城市群。在各城市群內部也是表現不一。比如,珠三角城市群中,廣州和深圳的城鎮化水平最高;長三角是以上海為城鎮化水平最高的地區;京津冀也是以京津為城市群的領頭羊。城市群之間及其內部的發展并不均衡,協調度不高。錢瀟克和于樂榮(2019)[11]用變異系數法構建了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評價指數并對長三角城市群的城鎮化水平進行了評價。
根據已有的研究,結合當前新型城市群的發展實際,本文認為新型城市群具有如下特點:(1)城市群之間及其內部的發展水平不一,沒有良好的協調度;(2)各城市群在發展過程中,呈現出生態城鎮化指標水平較高,土地和社會經濟發展指標次之,人口城鎮化指標層次較弱的狀況。
1.3 新型城市群評價指標體系
王艷秋等(2012)[12]構建了TPE復合系統模型,從經濟、社會、資源、環境、科技5個方面構建了資源型城市綠色轉型能力評價指標體系,用熵值賦權法確定了相關權重,并用該指標體系評價了大慶市的綠色轉型能力,結果較理想。宋林書等(2019)[13]以產業生態化理論為基礎,利用哈長城市群2000—2017年的相關數據,構建了相應指標的系統動力學仿真模型。該研究認為,創新型工業能夠顯著促進區域經濟可持續發展;在生態環保上的投資能夠提升地區經濟的發展,但提升幅度并不大;相比而言,大力發展新興產業在促進產業生態水平和地區經濟提升方面的效果更好;創新型工業產業生態化發展與區域經濟可持續增長是正相關的。
2 綠色轉型能力測度與評價
通過對已有文獻的閱讀和整理,發現綠色轉型能力測度與評價的方法、模型和指標體系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主要方面(見表1)。
從表1可以看出,現有文獻在研究綠色轉型能力的測度與評價問題時,主要做法分為三個步驟:首先選擇一定的理論基礎,包括協調發展理論、新增長理論等;其次在分析相關理論的基礎上形成一個指標體系,而且這個指標體系通常具有層次多、范圍廣的特征;最后利用指數法和熵值賦權法進行相應計算并構建相關模型以便分析實際問題。這說明在研究新型城市群綠色轉型協調發展能力測度與評價方面已形成了比較成熟的理論和方法,對于深入開展相關研究具有很大的借鑒意義。而在研究具體的城市群過程中是可以適當發展這些理論、研究方法和模型,為生態文明建設提供良好的理論基礎和方法論。
3 綠色轉型能力建設
綠色轉型能力建設是城市群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關于綠色轉型能力建設的研究還不集中。有從評價角度分析的,如Kuai等(2015)[36]從產業的規模、結構和效率三個方面,利用系統動態模型對各種規劃方案進行了評估。該研究認為,應該把控制產業規模放在城市群轉型措施的首要地位,其次是調整產業結構以及推進相關技術進程的發展。Wang(2015)[37]用DEA方法從改變和發展兩個系統動態評估了區域綠色轉型能力。Shao等(2016)[38]基于超對數生產函數和1994—2011年上海32個產業部門的面板數據,采用隨機前沿分析法,綜合前沿技術結構動態演化和技術變革方向動態演化方法估算生產要素產出彈性和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率。有從風險角度闡述的,如Brown和McGranahan(2016)[39]考察了城市信息經濟帶來綠色經濟的優勢和劣勢,以及給脆弱信息居民和工作者帶來的風險。有從治理效果角度研究的,如杜龍政等(2019)[40]從治理轉型的角度進行研究,認為不同治理類型對企業創新存在不同的影響作用,這也導致創新階段差異化特征有所不同;再利用Global-Malmquist-Luenberger生產率指數評價了2001—2016年中國30個省份的工業綠色競爭力,全面檢驗了環境規制、治理轉型與中國工業綠色競爭力的關系。結果表明,中國環境規制對工業綠色競爭力的影響呈現U型曲線的趨勢。Li等(2019)[41]基于2005—2014年微觀層次的企業面板數據,采用DEA模型和Malmquist-Luenberger指數模型方法計算中國鋼鐵行業企業的環境治理效率。結果表明,中國鋼鐵行業企業的環境治理效率總體水平較低。也有從綠色金融方面著手分析的,如Huybrechs等(2019)[42]主張用系統和權力敏感性的方式理解綠色微金融對可持續性轉型的潛在貢獻。

表1 綠色轉型能力測度與評價指標體系、模型、方法、理論及參考文獻
此外,綠色轉型能力建設還考慮到城市協同問題,部分學者已經進行了相關的研究。如米鵬舉(2019)[43]研究珠三角城市群空間結構與區域治理模式協同演化過程發現,它們存在“不協同—協同—不協同”的螺旋協同演化的路線。董微微和諶琦(2019)[44]利用熵值賦權法和變異系數法對相關城市發展差距綜合指數和分類指數進行測度。結果顯示,京津冀各城市發展差距逐步縮小,其中綠色發展和開放發展差距明顯縮小,協調發展、創新發展和共享發展上的差距有所加大。關溪媛(2019)[45]運用TOPSIS方法和灰色關聯法構建距離協同模型對2009—2017年的相關數據進行研究。結果顯示,其發展度普遍不高,協同度表現不穩定,沒有顯著增加協同水平;經濟協同度可以促進經濟發展度。胡艷等(2019)[46]運用2007—2017年的數據,利用協同創新空間聯系引力模型、協同創新空間關聯模型和空間滯后模型,分析了城市群協同創新發展的動態變化特征及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發現長三角城市群整體的協同創新空間聯系持續提高且有區域差異性;長三角城市群協同創新的空間集聚現象凸顯,有顯著的空間溢出效應,通過直接效應、間接效應和總效應促進地區經濟增長,反過來促進區域一體化進程。張建華等(2019)[47]從收入協同和技術協同的角度分析了中國長江經濟帶城市協同發展的現狀。研究結果表明,長江經濟帶城市存在顯著的技術協同發展關系,收入上存在一定的區域性差異并呈現周期性波動的特點。李雪松和齊曉旭(2019)[48]模擬了長江中游城市群差異化協同發展的動態演化過程,并評估了長江中游城市群差異化協同發展情況。研究結果顯示,2000—2017年,長江中游城市群差異化協同發展水平處于提升通道,它是推動長江中游城市群協同有序發展的內在驅動力,各個城市的差異化協同發展水平大相徑庭。
4 結 語
通過系統梳理國內外文獻發現,國內外關于綠色轉型研究仍然多以區域、單一城市、產業層面為主,鮮有針對城市群綠色轉型的實證研究,多以資源型城市為研究對象,主要是關于綠色轉型能力的評價研究。現有研究方法主要通過不同評價指標和數學模型方法來實現綠色轉型水平的測度,具體做法是通過熵值賦權法、TOPSIS、DEA模型和Malmquist-Luenberger指數模型等方法和模型,構建相應的評價指標體系開展綠色轉型能力評估。由此可見,現有研究缺乏方法的有機整合,評價指標選取也基本是基于壓力—狀態—響應框架的拓展,沒有從根本上體現綠色轉型的本質。還有一部分學者通過效率測度來衡量綠色轉型水平,即所謂的綠色發展效率和綠色生態效率,研究方法多是基于全要素生產率框架,但投入—產出要素選取無法充分突出“綠色”特征,與傳統全要素生產率模型無異。城市群是城市發展到成熟階段的最高空間組織形式,對城市群綠色轉型的全要素生產率進行系統研究符合國家區域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總體要求。但是,對城市群協同發展能力的測度和評價的文獻還不是很多,關于綠色轉型能力建設的研究就更少,這也為未來的綠色轉型研究提供了契機并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