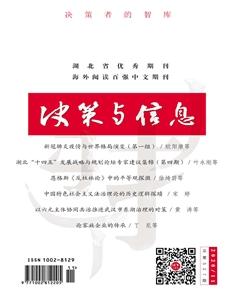從疫情中的博弈看新國際秩序
翁詩杰
新冠肺炎疫情(簡稱“疫情”)的全球暴發,不管是天災,還是人禍,固然是一場百年一遇的災難浩劫,但同時也是一次全方位的慘痛考驗,讓人類社會在面臨生死存亡之際,能夠以變應變。一方面適應新常態以圖生存,另一方面痛定思痛,思考整個國際秩序的重塑。
一、疫情測試和考驗了什么?
(一)疫情測試了各國(不分貧富強弱)的治理水平,尤其是反應在醫療保健領域、面對災難的應對能力、中央與地方的協調等。
(二)疫情考驗了區域性組織,如歐盟、東盟、非盟等的協作、應變能力。
(三)疫情也測試了國際性組織,如世界衛生組織(WHO)、世界貿易組織(WTO),甚至包括聯合國及其安理會的協調、馳援能力的執行力。并等同檢視了現階段負責全球治理的相關主要機構的能動性。
(四)疫情還是對西方國家主導、并以多邊主義為主軸的全球一體化,展開的一場前所未有的嚴峻“抽考”,考驗現有的全球治理水平和國際秩序。
二、疫情面前的國家反應典型
疫情同時測試出人性、民族性格、社會習性,乃至一個國家的格局,堪稱是一面“照妖鏡”。值此疫情仍在肆虐之際,綜觀各國對疫情的反應,可粗略歸納如下:
(一)以舉國之力防控疫情的擴散,寧可選擇以非常手段短暫犧牲國家經濟發展、個人生活自由等,以阻緩疫情外擴,為他國乃至世界爭取更充裕的時間空間來防控疫情——盡管中國這次首當其沖,可它樹立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典范。
(二)當本國受疫程度趨緩,不忘將自己應疫經驗、醫護人員、醫用物資等馳援境外多國抗疫一線,體現“天下一家”、人類命運共同體精神的典型例子,仍非中國莫屬。
(三)中國受疫之初,一些西方國家以種族、體制、文化的偏見與傲慢看待疫情,以為這只會殃及黃種人、亞裔人,與己無關,故此漠然視之,而致錯失防控疫情的時機。待疫情蔓延至自己國家時,毫無防備、驚慌失措的國家多在歐、美。
(四)武漢疫情暴發之初,那些期待中國經濟受到重挫,進而阻緩中國崛起勢頭的“幸災樂禍”,首推美國。美國執政當局如此,主流媒體也不逞多讓。
(五)面對本國疫情日趨嚴重,為了本身的政治利益(如:尋求競選連任、紓緩國內民情輿論壓力等),而不惜甩鍋卸責,將疫情污名化、政治化,劍指中國,甚至折騰出天價索賠的荒唐鬧劇。美國朝野政客已是始作俑者,還有歐洲若干國家,乃至亞洲另一個人口大國的某些政客、精英、媒體也跟著起哄。
三、百年變局的新趨勢
在這一片紛擾當中,構建百年變局的新趨勢,已在疫情的催化下逐漸涌現, 沖擊著既有的國際秩序。這大致可概括如下:
(一)在特朗普“美國優先”的政策下,美國自我放棄領導全球性的防控抗疫。這也是自二戰以來,美國首次缺席全球性的聯合行動。它讓美國的一眾盟友感到群龍無首,無所適從。現有的全球治理體系也逐漸出現領導真空。
在這種情況下,國際社會愈發迫切需要團結與合作,以面對當前和日后的全球危機,譬如氣候變化或其他可能發生的流疫。同時,這也會引發世界對美國領導全球的角色反思,以及加速國際組織對全球治理機制尋求變革的步伐。
(二)中國的“抱疫馳援”,不管是基于國家利益和地緣政治考量,或是歸因于“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智慧,都體現出一個大國當仁不讓、敢于擔當的角色;也同時為未來的全球治理體系提供一個迥然不同的互鑒互惠互利、共商共建共享的模式。
(三)現有的全球一體化,過多聚焦和建立在經濟GDP追求競逐的基礎上,卻不能在災難流疫面前發揮國際合作、守望相助的作用。從G7、G20、歐盟、非盟乃至東盟等,疫情當前,盡顯“各掃門前雪”的本色與無奈,使一眾區域性或跨國組織多淪為空泛的清談平臺。在疫情當頭,人類大家庭理應“抱團自救”,回歸到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理性省思。
(四)疫情暴發后,全球的醫用物資供應鏈過度倚賴中國,這讓歐美各國驀然驚覺。在當前新一輪的“防華、反華”思維的彌漫下,疫后多國、尤其是西方發達國家,預料會重新部署本國的醫用物資供應鏈,乃至整頓整個公共衛生體系。這將會形成一種嶄新的戰略布局。
(五)弱小國家與許多發展中國家礙于多方面資源的匱乏,疫情的暴發進一步暴露出他們對國際合作的期待與依賴,這為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提供了深耕的沃土。
四、中國的機遇與挑戰
這一輪新的變局對中國來說,既是機遇,也是嚴峻的挑戰。中國的“抱疫馳援”體現了大國擔當的本色,也以行動印證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更為全球治理模式提供了新的選擇。這一方面有助于中國在國際重大議題上開拓更大話語權的空間,但另一方面也引發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模式”的疑慮和排斥。西方媒體對中國“兼善天下”的美意,已漸次由起初對所謂“中方的公關宣傳,志在擴大影響力”的冷嘲熱諷,發酵為針對“輸出中國治理模式”的疑慮,甚至是無限上綱地扭曲為“輸出極權體制”。目前西方媒體針對中國的“輿論圍剿戰”已經全面開打,冷戰時期的意識形態號角再次吹響。
因此中國對這場席卷全球的戰“疫”所取得的重大勝利,必須倍感珍惜,善加經營。面對西方國家的甩鍋卸責、抹黑污蔑,有關“馳援抗疫”義舉的闡釋, 不妨將之定位在通俗易懂的“同舟共濟”的人道主義基礎上,而不要作為批評、對比西方治理模式和社會體制的根據。
有道是“打鐵還須自身硬”。中國的當務之急應該是努力厚植本身的軟實力,積極扮演好作為大國的國際角色,而不必競逐所謂全球治理的領導角色,以免坐實西方國家所謂“意圖輸出中國模式”的指責和圈套。中國要始終堅持互鑒互惠互利、共商共建共享的對外交往方向,面對全球性危機的考驗時,要始終如一敢于擔當,有所作為。
與此同時,中國宜把握這百年變局的機遇,適時調整“一帶一路”倡議的戰略布局,如以“重整醫護體系”為出發點,借“一帶一路”為載體,按親疏遠近、戰略考量的排序,選擇性地向外提供自身在疫情防控和公共衛生體系建設方面的成功經驗,尤其是要加大幫助弱勢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力度,這更是刻不容緩。其實“醫護外交”可作為中國拓展軟實力的另一試金石,只要運用得當,其地緣政治紅利,當非經濟效益所能比擬。
五、結語
“一帶一路”倡議發展至今,已不純然只是由中國人講中國故事。它既然是體現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載體,就要歡迎更多中國境外的聲音,共同唱響這一曲屬于世界大家庭的新時代樂章。
(作者系馬來西亞新亞洲戰略研究中心主席、馬來西亞前交通部長、前副議長)
[責任編輯:鄒立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