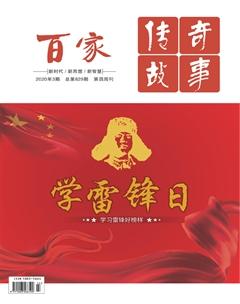平民化的呈現與生活傳達
郭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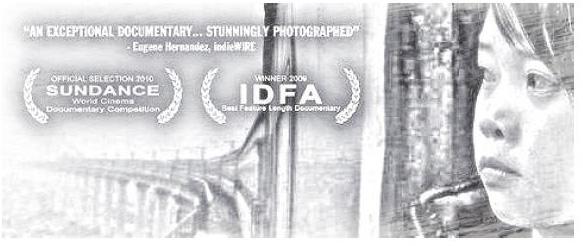
摘要:20世紀90年代紀錄片再度崛起,走平民化路線,喜歡拍老百姓。《歸途列車》即是平民影像崛起并在某種程度上將其推向極致的一部紀錄片。該片由范立欣導演,通過跟蹤記錄農民工一家的現實生活片段折射出轉型時期中國農民工的生存景況。
關鍵詞:紀錄片;《歸途列車》;平民化
一、回家的路總是充滿艱辛
該是回家的時候,廣州火車站外黑壓壓的人頭攢動,里三層外三層地擠滿了鏡頭,遠看就像鄉下人家禾場上鋪曬的五谷雜糧,鏡頭推近,滿滿的全是一臉無奈、疲倦、驚慌、焦躁、騷動、急切……
他們絕大部分都是農民工,只是想買張回家的票,卻如此之難。為何買張票這么難?答案很簡單,僧多粥少。有人曾提議再多修幾條鐵路,多開通幾路火車來改善“回家難”的問題。顯然,此舉無異于揚湯止沸。下面我們不妨從后現代主義的視角談談這個問題。
所謂后現代,核心理論是解構主義,作為一種廣泛的社會思潮,后現代對本體性進行解構,即解構傳統哲學對社會的認識。后現代認為世界是平面化的存在,無具體的本體,沒有本質,沒有規律性,零散的,偶然的,無中心。“無中心”是要討論的關鍵詞。
中國人歷來就是“中心論者”,以天朝自稱。古人就有“天圓地方”之說,“方”是有中心的,而“中國”一詞也是因為站在“中心”的立場上來命名的。
城市化建設跟工業化、后工業化是聯系在一起的。但是國家現在的城市化建設卻按照傳統的思維圍繞一個“中心”發展經濟,這樣必然跟現代的社會格局產生沖突。一個城市所能承載的人口數量總是有限的,試想,當超過城市所能承載數量十倍、百倍的人奔著一個城市蜂擁而至,勢必導致人口飽和甚至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廣州就成了這樣一個“中心”,這是我國在發展過程中出現的顯著問題,亟待解決,而絕不是增設幾條鐵路就能解決問題的。
二、生產性勞動者的雙重“剝削”
導演在片中借火車上的一個農民工的口吻道出真相:“比如說,我們公司生產球拍,每一款球拍都是外國的品牌,比如說Prince和Head都是美國的,我們中國沒有自己的品牌。我們只是一個加工大國,西方國家提供訂單,我們則全力以赴為他們完成所有訂單,賣出去的價格不菲,而我們老板和民工所得到的利潤是微薄的。”“我們這個是發往國外的,我們做的(褲子)腰這么大(用手比畫著說),兩個人都穿得下,四十幾碼的,中國人哪有穿四十幾碼的褲子?”
社會中的勞動者分為生產性勞動者和非生產性勞動者,生產性勞動者供養非生產性勞動者,而中國的農民工就是生產性勞動者,提供生產勞動。而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多以服務行業為主,生產性工業主要在第三世界或欠發達國家里。
在后殖民主義的全球化語境下,發達國家將資本、政治理念、文化觀念等以不對等的形式輸入給發展中國家,而并不直接將其變成殖民地。發達國家憑借自己技術的優越性,將資本輸入中國,使中國成為一個巨大的工廠,廣大農民工僅為了生活而拼命干活,這是一種經濟殖民行為,這是一重“剝削”。
與此同時,從片中我們可以看到,農民工的居住條件、伙食等待遇非常差,生病了也沒有保障(現在已有了)。農民工是極廉價的勞動力。為什么待遇那么差?這不得不讓人反思二次分配的問題。
二次分配的初衷是出于社會公平的考慮,但農民工的勞動力價格很便宜,為節約支出,老板不用考慮員工是否生病,孩子是否讀書,是否贍養老人等問題。相反,給農民工安排集體宿舍,吃大鍋飯,不提供醫保。農民工勞動力的廉價是建立在對農民工的“剝削”之上的,這是第二重“剝削”。
三、女兒在爸爸面前稱“老子”而挨打
片中有個激烈沖突,看得讓人心揪。女兒麗琴因為在父親面前自稱“老子”而慘遭父親一頓痛打,在場的奶奶、媽媽、弟弟無一人勸架,都一致覺得爸爸做得對,女兒在爸爸面前自稱“老子”實在不可容忍。
在城市里人的關系建立在金錢利益基礎上,而在農村建立在宗法倫理基礎上。自孔子以來中國就提倡家族倫理,“克己復禮”,家庭宗法觀念代代相傳,深入人心。從君臣、父子到夫婦的一整套嚴格的倫理關系神圣不可侵犯。而麗琴在父親面前稱“老子”,實屬不孝,亂了祖宗的章法。這不禁讓我們聯想到《茶館》里那位太監說的話:“誰要是壞了祖宗的章程,誰就得掉腦袋。”在媽媽爸爸眼里,麗琴“不聽話”。所謂的“聽話”,到底聽誰的話?并不是聽真理的話,而是要聽爸爸媽媽長輩們的話。其實在某種程度上,他們口中的“聽話”是要求順從、服從。麗琴不順從爸爸媽媽的意思,所以就是“不聽話”。從中我們不難看出家庭專制的影子,這是自古就有的一個傳統,即凡事都講“禮”,這已經滲透到老百姓的意識當中。
四、為鄉村寫一首牧歌
片中影像在光的使用上我們可以看到,在城市中的取景多為灰色調或暗色調,給人一種壓抑、苦悶、茫然的心理暗示。而在鄉村的用光上多為綠色調,甚至暖色調的紅色、黃色,渲染了一種安謐平和的視覺感受。兩相比較,不難看出導演流露出對城鄉不同的態度:厭惡城市,卻為鄉村寫下一首牧歌。
影片剛開始呈現的四川回龍村的樣貌,就是小姑娘背著竹簍,踏過小橋,迎著朝霞,踏著土塄,掠過秧苗,映著碧水去地里采摘薯蔓的畫卷。此后,片中又投入了大量的鄉村獨有的意象:彎曲的土巷、瓦當下的細流、在青青稻穗上搭織的蜘蛛網、在尖尖麥芒上停歇的蜻蜓、隨波飄蕩的浮萍、秧苗上的露珠、黃澄澄的苞谷、墨綠色的竹林等,宛然一曲離世隱居的牧歌,寄寓了導演的鄉村情懷。苦心營構了一個逃離都市的世外理想桃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