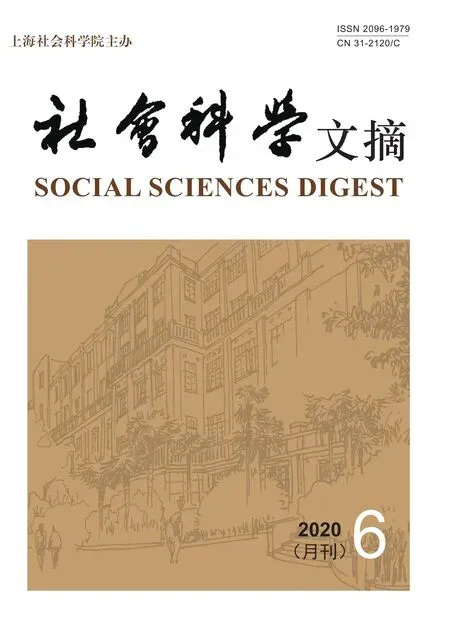國際關系研究的心理學路徑探析
文/喬亮
國際關系研究心理學路徑的發展現狀
國際關系研究的心理學路徑發展到今天,已經成為國際關系理論譜系中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對于心理學路徑方法的認知度和討論度也十分熱烈,然而在實際的使用度和研究度上卻還是相對不足。國際關系研究的心理學路徑處于一種表面上紅火而實際上很冷門的“主流的邊緣”的尷尬狀態。
20世紀五六十年代,科學行為主義革命在西方興起,并迅速發起了與傳統經驗主義的學術論爭。這兩者最大的分歧就在于研究方法路徑上的迥異。科學行為主義反映了戰后新科學技術迅猛發展的大時代背景,為國際關系研究帶來了方法論上的革命。這種新的范式強調國際關系研究是一種跨學科的研究,主張不光要運用政治與歷史的傳統方法,更要仿效自然科學的研究路徑,建立“科學的理論”。正是在這種科學、綜合、跨學科研究的方法論要求下,心理學相應方法和概念也繼經濟學、社會學等之后,被引進到國際關系學的研究中來,加入了科學行為主義革命中。
經過約半個世紀的發展,心理學路徑的范式和相關研究在國際關系學科中發展很快,產生了包括學會、雜志在內的一大批成果,甚至一些理論學派帶有明顯的心理學痕跡。譬如以瓦萊麗·赫德森等學者為代表的外交政策分析學派(FPA)就十分強調包括心理學分析在內的綜合性跨學科分析,并且衍生出諸多分支理論學派,如斯普勞特夫婦的“環境”理論、歐文·詹尼斯的“小團體迷思”、羅伯特·杰維斯的認知心理學模式等等。
同時,國際關系理論史上的第二次論戰,即科學行為主義與傳統經驗主義之爭,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國際關系學界內部一直存在的對于研究路徑上的差異。在這其中,英國和歐洲大陸在很大程度上就深受心理學研究路徑的影響,從而和美國國際關系學界形成了所謂英美研究風格上的顯著差異。斯蒂芬·史密斯在其所做的關于英美國際關系分析的十點比較中就提出,“英國注重國際關系中的獨特性和行為的個人特點,美國注重國際關系中的普遍性和行為的一般規律”,“英國認為‘本能’‘直感’和‘想象’大于‘前提’‘推斷’和‘理論’,美國反之”。這種分歧在隨后美國國際關系學界逐漸掌握更大的話語權和范式主流后,就演化為所謂國際關系“主流性范式”同“替代性范式”之間的爭論。
可以看出,心理學路徑在國際關系研究中已成為重要的研究路徑之一。然而心理學在科學行為主義革命中卻沒有獲得像決策論、博弈論等那樣廣泛的運用和巨大的影響,在行為主義路徑占據主流地位的時代里,心理學路徑依然是“主流中的邊緣理論”。心理學路徑在國際關系研究中的興起發展狀態與其“主流中的邊緣”地位構成了鮮明的對比。究竟何以最終形成了今天這種“不冷不熱”的奇妙狀態?一種原因就是美國國際關系學界逐漸掌握話語權,從而導致博弈論、統計模型這樣的方法范式壓倒性地超過英國(以及歐洲)以個人分析為核心的社會、心理學范式,使得后者處于相對邊緣和暗淡的地位。另一個原因或許在于冷戰的爆發和核恐怖的升級,使得謝林等人的博弈論這類的剛需理論更加為各國的軍政和智庫所青睞,而心理學路徑則被認為過于唯心化、“玄學化”,沒有取得前者那樣的主流性應用地位。
國際關系研究心理學路徑的研究核心
國際關系研究的心理學路徑同大多數“主流”或常規型國際關系理論范式不同的最突出一點,就是其研究分析的是個人層次,核心研究對象是個人及其特性。
個人以及人性的概念,再度回歸社會科學的研究范疇,有著一個漫長曲折的過程。尤其是在國際政治領域,這一排斥性偏好尤為明顯:國際關系的觀念自17世紀黎塞留紅衣大主教以來,就被看成是“現實主義的”和“國家利益至上的”,國家成為唯一的考量對象。這樣的觀念有著更深層次的科學哲學土壤:中世紀經院哲學以降,個人即被開始視作一種抽象概念,本質上不同于政治社會及其具體操作。在這個大背景下,從人性最深層次的心理學層面出發分析個人的特質性的行為,對于以往的國際關系研究而言,本身就是一個極具挑戰性的嘗試。
在20世紀下半葉,個人開始重新出現在國際政治學者的視線內,而首當其沖的就是對身居要位或對國際政治進程具有重大影響力的政治人物所進行的探究。在經歷了長時間有關結構與進程等范式的爭論后,人們普遍出現了一種理論的“審美疲勞”,轉而開始憧憬這樣一種理想狀態,即能夠用微小的代價——從個人的角度——來輕松發現社會的變化。按照詹姆斯·羅森諾的假設,個人(尤其是處于國家權力中心和決策中心的政治家們)會毫無疑問地認定自身在世界政治舞臺上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并且也會對在這個由自己出場的舞臺上如何確定自己應有的地位和角色十分感興趣。因為自身的所作所為總是重要的,所以會很大程度上憑借自身對外部事物的看法與評估來決定自己的動作與行為。正是在這樣的語境下,以個人為研究對象的心理學才能夠得到發揮作用的合適空間。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的觀點為例,人由于在成長過程中所遭遇的挫折和沖突,會逐漸在自身形成一種調節沖突、緩解焦慮的心理防御機制。這種防御機制具體包括:壓抑、否認、投射、退行、置換、抵消、合理化和幻想等。眾多實例表明,諸如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論這樣的心理學路徑,對于從個人心理視角去解釋或預測其行為,有著重要的作用與價值。
在結構層次上,對于國際政治系統的分析領域,也同樣證明了心理學分析的可行性和有效性。邁克爾·尼柯爾森從結構角度對于個人對國際系統的影響進行了分析,他將國際系統模擬為簡單的幾種模型:純粹的等級系統、純粹的相互作用系統、混合的現實主義系統以及復雜型系統等。在設定了角色、信息渠道等變量后,尼柯爾森提出了“參與之悖論”,如有一角色欲對系統的演變產生影響,它必須在不同的行為間選擇,不同的選擇會導致截然不同的結果。然而當今的國際系統又是異常復雜的,這使得預測更是難上加難。系統的成員越少,性質越單一,系統就越有秩序,特定行為的后果就越易于被預見;相反,系統越是向眾多成員開放(即所謂的參與),系統就越難被預測,行為目的就越難奏效。這樣的分析模式,恰好符合了心理學路徑融匯入國際關系研究領域的基本要求,即在一個有秩序的系統中關注系統中心(通常往往就是一國政府的首腦或接近權力中心的人物)的心理狀態和變化,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學者理解其行為的背后動因,理解其政治操作的風格和偏好,以及較為準確地預測其未來的政策走向。
國際關系研究心理學路徑的典型研究案例
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發展,心理學路徑相關研究已經逐漸豐富,日益成為一種被人們廣泛討論的獨特范式,這其中就包括美國學者雷蒙·波爾特的研究文獻《性格與外交政策:斯大林的案例》,這是一個極富代表性的研究案例,形象地詮釋了心理學研究路徑是如何具體應用于國際關系領域研究的。
波爾特指出,在國際關系研究中,傳統的或現實主義的理論關于利益與國家的解釋是有效的,但是延伸到更深層次的個人層面,任何人都會處在一個等級制的組織設置中,受到各種思維的影響,在解釋“為什么會這樣?”這個深層問題上,顯然傳統的或現實主義的理論是不夠有效的,而心理學路徑在這方面則具有其獨特的解釋優勢。心理學研究路徑的基本意義及其應用原則在于,當決策者處于一個正規的官僚決策系統中時,那么心理學對于決策者的衡量在大多數時間里都是可以剔除的;但是,如果決策者的個人性格在決策過程中會使其做出明顯有別于正常情況下的行為,那么傳統理論就必須考慮心理學所獨具的作用了。波爾特在研究成果中關于不同方法的比較性研究,有助于使人們對心理學路徑的優勢有進一步的了解。
而尼柯爾森的相關分析表明,心理學路徑在國際關系領域的應用,一定程度上恰恰需要這樣的結構,即系統的成員和性質需要比較簡單,以更容易預見特定人物之特定行為的后果。波爾特在研究中同樣遵循了這一要求,對于斯大林時期的蘇聯國內政治進行一定程度上的闡述,增強心理學路徑的有效性。蘇德戰爭爆發前,本就缺乏復雜官僚決策層的蘇聯進一步受到斯大林政治改革運動的影響,官僚層的決策能力受到一定影響,斯大林成為了掌握蘇聯內政外交的最高核心決策者,系統成員和決策性質被空前地簡化了,客觀上為心理學研究路徑提供了一個絕佳的環境與平臺。
波爾特所采用的研究框架,是經典的弗洛伊德動力精神學的“投射理論”,即為將自己的想法、動機和欲望投射到別人身上,斷言別人也有這種想法、動機和欲望。偏執性精神障礙即為一種典型的具有投射行為的心理障礙,現代衛生心理學認為“偏執性”心理特征的原因有遺傳因素,與此同時,受到成長環境的影響同樣很大。其特點是頑固的、呈結構系統性的、嚴密的“妄想”,而整個人格則表現為完好無缺。臨床表現上最為突出的特點,就是迫害妄想和夸大妄想互為因果、相互影響。患者往往會認為自己將要或正在做偉大的事情,別人正因為妒忌他的能力而對自己進行迫害,并因此采取暴力攻擊手段,以挫敗對方的“陰謀”,在病理激情及狂熱的驅使下,甚至采取極端的手段。波爾特從斯大林的童年環境開始枚舉事實,包括斯大林對于國內政治的行為和態度,一系列歷史事實的列舉和分析都力圖合乎心理學上對于偏執性患者的臨床和病理診斷標準,最終證實了斯大林具有偏執性心理障礙的設想。至此,波爾特實現了他運用心理學分析國際關系所需要的基本背景要求:極度簡化的決策體系和符合心理學診斷標準的系統決策人(同樣也是心理疾病的患者)。在此基礎上,他提出了一個屬于心理學范疇的理論觀點,即偏執性心理障礙患者對于外界刺激的反應方式,就在“情緒平穩、可控—脆弱—沮喪、極度壓抑—策劃反擊、重建權威”四個階段間循環。
這一理論假設用于類似于斯大林這樣的國家政治決策核心人物身上,就可以較容易地分析出他做出某些舉動的原因,或者比較準確地預見到他未來的決策,這對于國際關系研究意義重大。波爾特將心理學關于偏執性心理障礙的循環模式理論,同國際關系研究較好地結合在了一起,并且對于一直以來缺乏有效解釋的斯大林1939年對德外交和對波戰爭政策的原因,做出了令人較為信服的解釋。
國際關系研究心理學路徑的發展前景
波爾特和其他一系列應用心理學路徑的研究案例表明,心理學路徑在國際關系領域是可行的,并且通過合適的切入點,可以較為有效地解決相關國際政治問題,而這些問題又常是傳統或現實主義理論很難做出令人信服之解釋的領域。傳統理論路徑往往很難在這些案例中找到合適的突破口,過分死板地將“利益”“權力”等概念套用到案例中,得出的結論也是削足適履,漏洞百出。例如,斯大林在戰爭期間對于英美盟國反復的不信任和所謂的“搖擺”政策,基于現實主義視角的解讀大都不盡如人意,而心理學視角則根據當時斯大林位于蘇聯決策核心的政治地位和偏執性心理特征的背景,提出斯大林較為不信任他人的性格特征,由于當時特殊的國內政治狀態,幾乎鏡像般“投射”于蘇聯的外交政策中,因而才導致斯大林乃至整個蘇聯的對外行為展現出一種西方人看來的所謂多疑、反常乃至神秘。顯然,這樣的解釋相對于傳統的現實主義視角是比較具有說服力的,至少在相當程度上是一種值得人們參考的重要意見。
但是另一方面,從波爾特的文獻中,我們也可以窺見一些重要的問題,即心理學路徑有著自身較為苛刻的適用范圍和理論局限,正是這些潛在缺陷導致了心理學研究路徑在火熱的行為主義革命中,始終只扮演了一個不溫不火的“邊緣性”角色,遠遠沒有像博弈論等其他方法那樣,為學者們和國際關系學界所廣泛采用,也沒有創造出能夠支撐其成為一種新的“主流”理論范式的足量研究成果。
心理學路徑的理論缺陷(或者說理論局限)大致有這樣幾個較為明顯的方面:首先,心理學研究路徑對于得以應用的案例背景條件要求過于苛刻。這體現在大背景(環境)和個體兩個方面,“參與之悖論”中所提到的復雜的現實結構,成為心理學方法應用的巨大障礙之一,波爾特自己也承認蘇德戰爭爆發時的蘇聯決策系統是一個“偶發的、罕見的個例”,這個系統是極其理想化的。而國際關系的現實卻是日益復雜的國際系統,系統越是向眾多成員開放(即所謂的參與),系統就越難被預測,行為就越難奏效。其次,信息不對稱也是造成心理學路徑難以廣泛應用的重要原因,而這個在國際關系研究中普遍存在的困難,反過來卻成為博弈論研究法盛行的關鍵因素之一。
以心理學為視角研究政治家行為的方法,也受到許多質疑。羅伊·梅德韋杰夫在研究“斯大林主義”的過程中,特別關注了斯大林的心理癥狀問題。羅伊通過研究也認為斯大林患有精神心理疾患的假設是可以某種程度上得以確定的。但是羅伊也利用事實尖銳地指出,盡管斯大林的病理變化具有明顯的偏執性心理障礙的一些特點,但是令人確信的是,斯大林絕對是有責任能力的人,他的所有國內國際政策都是在理智狀態下縝密、謹慎地決策出來的。羅伊認為,如果僅僅用心理疾病來解釋諸如斯大林的政治行為,那么在政治哲學和正義范疇內是難以令人信服的,并且缺乏對人基本的尊重和反思精神,是對道德和人本主義原則的踐踏。換句話說,作為心理疾病患者的自然人,其行為表現和責任能力,是不可同從事具體國內外政治行為的具有心理病患傾向的政治人相等同的,用所謂心理疾病或精神病人來給斯大林這位歷史上偉大的無產階級政治家進行草率定性,是斷然不可取的。
綜上所述,可以得出一個基本的結論,在行為主義革命中,心理學的研究路徑以其獨特的視角和方法為國際關系領域帶來了新的清風,在解釋和預測國際事務中,盡其所能地發揮了自己獨特的優勢,同時,也由于自身較高的應用門檻,受到了諸如信息不對稱、國際形勢日益復雜多變和外交大眾化等現實條件的限制,造成心理學研究路徑在國際關系研究譜系中不冷不熱的特殊而尷尬的局面。
心理學脫離哲學范疇已經有一個多世紀的時間了,在今天隨著實驗科學越來越多地融入心理學領域,心理學已經發展成為一門介于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之間的中間學科。可以想見,這種中間地帶學科的特性,在本質上是有益于心理學在國際關系領域的進一步應用和發展的。要解決當下心理學路徑在國際關系領域不冷不熱的局面,應該進一步提高實驗型心理學與國際關系學科的融合,定性或定量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心理測試與模擬,將有助于國際關系學者們把握研究對象心理發展的大方向,為國際關系研究提供有益的幫助。在這一點上,國內政治學領域已取得了不小的進步,例如,路透社/佐格比關于每屆美國總統大選的選民心理分析和民意測驗,已經達到了相當精確的程度,成為了選戰民調的重要風向標。這至少證明心理學和政治學之間尚有巨大的融合空間,那么從屬于政治學的國際關系學科研究也不會例外,國際關系研究的心理學路徑方法具有廣闊的發展空間和理論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