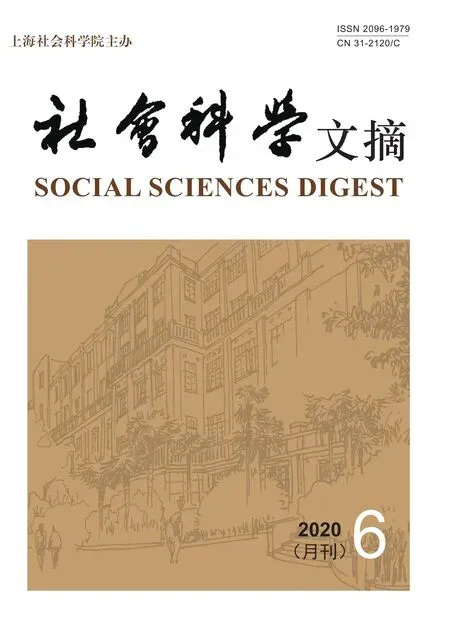尚未觸發(fā)的“修昔底德陷阱”與美國對華政策
文/潘蓉 肖河
理論改進:在恐懼與戰(zhàn)爭之間
鑒于中美間的“全領域”摩擦正愈演愈烈,因此雖然“修昔底德陷阱”這一概念在中國一直飽受批判,但是仍然具有頑強的理論生命力。坦率地說,中國學界過于迫切地嘗試證偽“修昔底德陷阱”。要么訴諸于中國的某種特殊單元屬性,例如中國的和平主義戰(zhàn)略文化;要么訴諸于國際環(huán)境的某種體系屬性,例如經濟相互依賴、網絡化、大國的核恐怖平衡以及集體安全體系。然而,上述批判都不能成功推翻其兩個核心假設:第一,崛起國實力的迅速增長會引起守成國的恐懼;第二,基于恐懼,守成國會采取包括預防性戰(zhàn)爭在內的“破壞性”政策。在第一點上,部分中國學者側重于強調美國“不應”恐懼中國。然而即使“不應該”,恐懼也完全可以單方面地“無理”存在。在第二點上,中國學者側重于否定戰(zhàn)爭發(fā)生的可能性,從而一舉推翻整個假設。然而,冷戰(zhàn)中固然美蘇之間沒有爆發(fā)直接戰(zhàn)爭,但對于蘇聯(lián)而言其結果并不美妙。因此,戰(zhàn)爭危險的“排除”并不能解構“修昔底德陷阱”的核心關切,這也正是總是要反復討論這一“不受歡迎”的概念的根本原因。
在守成國的恐懼到與崛起國的戰(zhàn)爭之間,還存在著很多中間階段。學術界對“修昔底德陷阱”的批評和改進集中于重新分析原本被忽略或者簡化了的從和平到戰(zhàn)爭的過程,以及戰(zhàn)爭以外的其他破壞性競爭。這些改進沒有否定“修昔底德陷阱”的核心關切:守成國會對崛起國在實力上的接近感到恐懼,從而引發(fā)極具破壞性的對抗反應。從學術傳統(tǒng)上看,艾利森關于恐懼導致戰(zhàn)爭的論斷接近預防性戰(zhàn)爭理論(Preventive War Theory)學派。該學派強調守成國對實力逼近的崛起國的最可能反應是發(fā)動預防性戰(zhàn)爭。不過,相反研究則認為國家在面對長期衰落時,會通過內部動員(internal mobilization)提升長期經濟潛力。經驗研究也顯示,收縮戰(zhàn)略對于守成大國而言既可能,也可欲。關于國家戰(zhàn)略行為的理論是理解“修昔底德陷阱”表現(xiàn)形式的關鍵。在該議題領域,偏好預防性戰(zhàn)爭和內部制衡的兩個學派給出了大相徑庭的答案。從現(xiàn)有趨勢來看,需要拓寬對“修昔底德陷阱”的理解,把具有嚴重破壞性的雙邊對抗政策納入其中。
前提判斷:美國的對華政策是恐懼驅動嗎?
(一)國際政治中的恐懼
在改進了“修昔底德陷阱”的理論機制后,接下來要做的是判斷中美兩國是否陷入了更廣義的陷阱,以及雙邊關系在這一陷阱中發(fā)展到了何種階段。為此,首先需要仔細審視中美關系是否適用于“修昔底德陷阱”的前半段邏輯,即美國是否因為雙方實力的拉近而恐懼。
恐懼是諸多國際理論中的關鍵概念,如何應對恐懼更是國際政治中的基本問題。然而,大部分理論在談到恐懼時,更多側重于分析恐懼的來源,而非直指內涵。羅伯特·杰維斯(Robert Jervis)就認為恐懼是一種心理上的反應功能,源自對其他行為體意圖的不確定性。然而,其無法說明何種不確定性才會導致恐懼。顯然,將所有對他國意圖的不確定感都視為恐懼不符合常識。在理查德·勒博(Richard Lebow)看來,這種“界線不明”導致了國際關系學界對恐懼概念的濫用,將很多并非恐懼驅動的行為錯誤歸因。勒博認為事實恰恰相反,包括卷入世界大戰(zhàn)在內的很多國家行為是出于追求榮譽的精神(spirit)考慮,而非出于克服恐懼的安全考慮。針對恐懼的上述“泛化”問題,本文傾向于采用嚴格定義,將恐懼限定為行為體(在這里是國家)對于是否能確保生存(to survive)的不確定性。
毋庸質疑,當前美國對中國的整體看法正日趨負面,這源于彼此間遙遠的“秩序距離(order distance)”和在單元層次上的異質性。這種負面情緒正隨著中國實力的增長而增強。不可否認,中國實力的增長會讓美國對中國的異質性日益無法忍受,認為中國正在與其在國際上爭奪影響力與合法性。但是從情緒的物質基礎和美國的行為來看,這種反感情緒還不至于使美國認為其社會及其生存方式正處于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更多是一種利益和榮譽上的競爭心理。
(二)恐懼的物質基礎
歸根到底,僅有對其他行為體意圖的不確定性不會產生恐懼。只有當對方具備足夠的物質能力時,這種不確定性才會真正威脅到生存,恐懼才會出現(xiàn)。此外,影響一國威脅感知的最重要因素并非只有總體的凈實力(net power)大小,還涉及權力的構成。某些力量要比另一些力量更容易招致恐懼。不過,雖然力量差距本身是客觀存在,但是對差距的評估卻具有主觀性。由于評估者對各因素的重視程度不同,使得美國學術界和政策界在“中國的實力是否正在迅速接近美國”這一基本問題上都難以取得共識。
國內生產總值(GDP)和國家能力綜合指數(shù)(CINC)是衡量國家實力的最常用標準。按照給予基本物質能力(例如軍事人員)更多權重的CINC計算,中國早已超過美國,并且優(yōu)勢還在繼續(xù)擴大。因此,學術界普遍認為該數(shù)據(jù)在設計上存在問題。按照更權威的GDP來計算,中國與美國的差距也在迅速縮小。然而,以邁克爾·貝克萊(Michael Beckley)為代表的學者認為,只有當兩國間的絕對能力差縮小時,才能認為較強的一方趨于衰落。而在衡量絕對能力時,人均GDP和技術能力最為重要。從這一角度看,美國沒有衰落,中國在當前和未來很長時間內都很難構成對美國的挑戰(zhàn)。很多學者在關鍵判斷上與貝克萊大同小異,那就是雖然中國的經濟總量正在接近美國,但是相比以往的崛起國和守成國,中國與美國的技術差距更大,難以動搖美國在物質能力上的單極優(yōu)勢。
從上述辯論中可以看出,美國確實感知到了中國絕對實力的迅速增長,但并不認為中國在關鍵領域縮小了層次差距,并不認為中國的物質能力已經對美國的生存方式構成挑戰(zhàn),更遑論“生存性威脅”。
(三)美國的對華心理感知
如果中國還不是令美國恐懼的安全上的敵人的話,那么當今美國如何看待中國呢?就特朗普政府而言,就是比敵人(enemy)、敵手(adversary)或者反對者(opponent)情感色彩更弱的對手(rival)和競爭者(competitor)。在安全領域,競爭者的定位也沒有對中國帶來實質的安全壓力。中美雖然已經陷入一定程度的安全困境,但是這還沒有轉變?yōu)橐粓龈邚姸溶妭涓傎悺C绹质侨绾慰创斍芭c中國的經濟競爭?是勝負難料還是游刃有余呢?在政策表述上,由于次貸危機的后續(xù)影響,奧巴馬時期的美國在經濟領域被中國趕超的危機感要更強。到了特朗普執(zhí)政時期,這種“危機感”基本從美國的官方表述中消失了。特朗普多次宣稱美國經濟正處在“史上最強大的時期”,擁有“最好的就業(yè)率和股票數(shù)值”。盡管對這一說法不乏批評,但是總體上仍然反映了美方更加強大的自信。歷史上看,中美貿易摩擦和20世紀80年代的日美貿易摩擦相比,更是有質的區(qū)別。當時,日本是美國在半導體等最高技術領域的直接競爭對手,而中國現(xiàn)在還處于全球價值鏈的中下游,中國企業(yè)更多是美國企業(yè)的利益延伸而非競爭對手。以此而言,與中國的“貿易戰(zhàn)”并非美國因經濟衰落而發(fā)動的一場經濟“預防性戰(zhàn)爭”,相反是要借助強勢經濟擴展在華經濟利益,屬于“擴張性行為”。
由于單元層面的異質性,中國的實力增長引起了美國的關切甚至是反感,但是美國并不認為中國對美國的生存和生存方式構成威脅。特朗普政府處理中美貿易摩擦的方式,也并不符合恐懼驅動的行為模式。換言之,當前中國可能還沒有發(fā)展到足以驗證這一理論邏輯是否正確的地步。
“碎片化”與“追求經濟收益”:經濟摩擦中的美國行為模式
(一)“制華”不是美對外政策軸心
首先可以確定,即使將“修昔底德陷阱”的理論假設放寬——從守成國和崛起國爆發(fā)直接戰(zhàn)爭延伸到冷戰(zhàn)競賽,中美兩國仍然沒有觸發(fā)這一陷阱。其原因并非某種特殊的單元和系統(tǒng)屬性在起作用,而是中國的實力并未增長到讓美國恐懼的地步。從行動上看,壓制中國并非是當前美國外交的軸心,甚至不是唯一的重要目標。回顧冷戰(zhàn),美蘇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表現(xiàn)就是將遏制對方作為外交政策中壓倒一切的出發(fā)點,經常過高估計世界形勢變化的重要性及其與對手的關聯(lián)。正因如此,冷戰(zhàn)中爭奪最激烈、破壞性最強的部分都發(fā)生在實際上并不那么重要的第三世界國家,例如古巴、越南、安哥拉、非洲之角和阿富汗。然而,這種“偏執(zhí)”的戰(zhàn)略思考方式才是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中的大國的常態(tài)。
特朗普政府顯然不具備上述“偏執(zhí)”。固然,特朗普政府在貿易問題上對中國施加了空前壓力,但是他的目標不僅僅是中國。一方面,歐盟、日本、加拿大、墨西哥還有印度都是特朗普關稅戰(zhàn)的目標;另一方面,美國又主動退出了包括環(huán)太平洋伙伴協(xié)議(TPP)在內的多邊協(xié)定,同時威脅退出世界貿易組織(WTO)。這種做法使得美國無法構建出針對中國的“包圍網”,給予了中國在多邊舞臺爭取伙伴的機會。這說明壓制中國并非是美國政府外交政策的終極落腳點,而只是差不多重要的多個目標中的一項。雖然中美之間的競爭加劇,但是美國的整體外交政策并沒有以“制華”為軸心協(xié)調起來。
當今的美歐關系尤其表明美國的對外政策并未以“制華”為串聯(lián)軸心。美國一方面要求歐洲各主要國家在安全、政治和經濟領域追隨美國、對華施壓,另一方面又在關稅、北約等議題領域上頻頻挑起沖突,大大削弱了前一努力的效果。這從側面說明美國雖然視中國為競爭者,但是在威脅感知上并不強烈,并不愿意為壓制中國而安撫、利誘最重要的潛在合作伙伴。
(二)追求經濟收益是美對華經濟政策重心
除了未能聚焦中國,美國政府的對華經濟政策也不是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守成大國應該采用的政策。其核心訴求是擴展在華經濟利益,而不是寧可犧牲自身經濟利益,也要破壞中國經濟積累。以此而言,中美還沒有進入旨在破壞對方經濟、作為安全沖突序曲的經濟戰(zhàn)。
那么,美國又是出于什么目的在經濟和科技領域向中國施壓呢?邏輯上有兩種可能:第一,美國將中國視為經濟和科技上的真實威脅,認為中國已經動搖了美國的經濟和技術優(yōu)勢,因此需要發(fā)動“預防性戰(zhàn)爭”;第二,美國并未將中國視為經濟和科技上的真實威脅,只是希望堵住“漏洞”,保證從經濟和科技優(yōu)勢中獲得的利益能夠最大化。現(xiàn)實狀況可能處于理論上的兩端之間。中國學者通常更強調前一種可能,美國對中國的經濟打壓就是基于對兩國未來發(fā)展趨勢正日益不利于自身的“悲觀預期”。
然而,美國學術界和政策界的主流并不認為自身在科技創(chuàng)新上相對中國“失速”,相反優(yōu)勢還日益鞏固。中美貿易摩擦開啟時,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出臺了一份《關于中國技術轉移、知識產權和創(chuàng)新活動、政策和實踐的調查結論》。該報告并未強調中國企業(yè)在技術上的競爭,而是主張美國企業(yè)無法“公平”進入中國市場,損害了原本可能產生的貿易利益。從美國在經貿戰(zhàn)線上“心有旁騖”的做法可就可以看出,“預防”中國未來在經濟和科技上超越美國的考慮可能一定程度存在,但是并非主導動機。
美國當前對華政策的壓力和訴求都高度集中在經濟領域,在美國社會具有最廣泛共識的核心關切還是所謂“政府補貼、產業(yè)保護主義、濫用發(fā)展中國家待遇等貿易規(guī)則、強制技術轉移和知識產權竊取”等經濟議題。在中美兩國達成的“第一階段(Phase One)”貿易協(xié)定中,美國取得的主要實質“成果”包括中國承諾未來兩年從美國購買2000億美元的農產品,向美國銀行和信用卡公司開放金融市場,承諾加強知識產權保護。這對于試圖限制中國產業(yè)發(fā)展的鷹派來說,無疑是一場“失敗”。美國的這一選擇說明,現(xiàn)階段其意在以對抗性方式(挑起貿易戰(zhàn))謀取在華經濟收益。“殺敵一千,自損八百”只是美國實現(xiàn)目標的方式,而非目標本身。
改變中國的國內和國際行為,讓中國更接近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一直是美國對華戰(zhàn)略的核心。為此,美國一直在正反兩方面執(zhí)行對沖政策。過去,美國在經貿領域以看好、接觸中國的“做多”為主,防范主要體現(xiàn)在政治和安全領域。現(xiàn)在,美國將防范的主要陣地轉移到經貿領域,就中國經濟體制的發(fā)展方向提出了廣泛的“結構性改革”要求。2019年12月13日,美國國務院負責東亞暨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戴維·史迪威(David Stilwell)發(fā)表演講表示,如果“實事求是”地看待中美關系的歷史,就會發(fā)現(xiàn)“美國決策者多次向中華人民共和國伸出友誼之手,但卻沒有得到回報”。不論這一論述本身是否正確,其突出的著眼點和特朗普一樣,就是要求中國“回報”美國,而非打擊中國。
結論:尚未觸發(fā)的“陷阱”及其危險
“修昔底德陷阱”是一個既符合一般常識又具有相當學術潛力的概念。雖然其“恐懼導致戰(zhàn)爭”的簡單化論述招致了很多批評,但是并不能僅憑這一點就抹煞其學理上的價值。更何況,如果只能用“是與否”來回答,當前中美關系的發(fā)展趨勢更多是證實而非證偽這一概念。現(xiàn)實的發(fā)展告誡我們,絕不能輕易斷言“修昔底德陷阱”的邏輯是錯誤的,或者完全不適用于當今時代的中美關系,不能忽視其潛在的破壞力。
不過,即使“修昔底德陷阱”的邏輯有合理性,也不能輕易斷定中國近三十年的迅速發(fā)展就已經觸發(fā)了該作用機制。當前,美國對中國的經濟成長確有擔憂,但是正如“中國崩潰論”和“中國威脅論”一直以來都旗鼓相當所顯示的那樣,美國對自身的經濟發(fā)展模式和效果仍然充滿信心,遠遠談不上對自身的相對衰落持有“不可逆轉”的悲觀態(tài)度。從美國在對華經貿政策中的具體措施來看,其也更多是以高風險方式追求絕對收益,而不是以謀取零和的相對收益為目的。因此,沒有充足證據(jù)表明當前的中美貿易摩擦是“修昔底德陷阱”全面展開的第一階段。
然而,中美之間的“修昔底德陷阱”尚未觸發(fā)也不必然是一個好消息。反過來說,兩國在經貿和整個雙邊關系上都還有很大的惡化空間。如果不能管控好摩擦和沖突,找到新的雙方都認可的平衡點,擴大共同的國際秩序基礎,那么伴隨著中國綜合實力的進一步增長,或者美國陷入顯著衰退,就可能迎來“修昔底德陷阱”的真正展開。要想避免這一前景,需要做的不是拒絕承認“修昔底德陷阱”的邏輯,也不可能是“反其道而行之”,畢竟中國不可能為了避免美國產生恐懼而拒絕縮小與美國的實力差距。而是要認識到即使“修昔底德陷阱”邏輯的本身是成立的,其也并非是決定兩國的關系的唯一邏輯。正如想要讓成熟的蘋果不落向地面,要做的不是否定地心引力,也不是不讓蘋果成熟,而是可以利用網兜等人類的智慧工具。屆時,只要努力確保影響中美關系的其他作用機制發(fā)揮更大作用,那么仍然可能在相當程度上抵消“修昔底德陷阱”的負面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