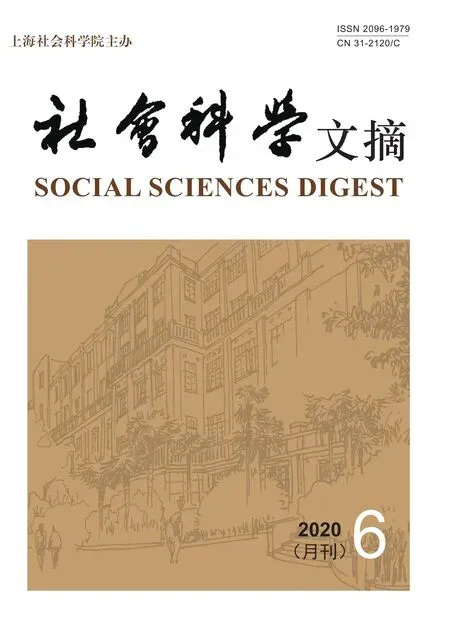憲法與民法典關(guān)系的四個(gè)理論問(wèn)題
文/童之偉
基本民事主體表述為“公民”還是“自然人”更合適
所謂民事主體,是指具有民事權(quán)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權(quán)利、承擔(dān)民事義務(wù)的行為者。基本民事主體,是指在兩種或多種民事主體中,處于居首的、最重要的位置的那一種。《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民法典(草案)》(以下簡(jiǎn)稱《草案》)第2條規(guī)定:“民法調(diào)整平等主體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組織之間的人身關(guān)系和財(cái)產(chǎn)關(guān)系。”顯然,“自然人”被表述為基本民事主體。
現(xiàn)在似乎一般認(rèn)為,《草案》確定基本民事主體是定位于“公民”還是“自然人”已不是問(wèn)題,因?yàn)椤恫莅浮返?條的規(guī)定是對(duì)我國(guó)《民法總則》的承襲。其實(shí)這個(gè)問(wèn)題并沒(méi)有這么簡(jiǎn)單。《草案》有什么必要將“公民”改為“自然人”呢?這是一個(gè)即使在民法學(xué)界也未真正形成共識(shí)的問(wèn)題。
我國(guó)民法典將基本的民事主體表述為“自然人”,對(duì)法治實(shí)踐也許不會(huì)有明顯阻礙,但從法律體系應(yīng)以憲法為基礎(chǔ)形成內(nèi)部和諧統(tǒng)一整體的客觀要求來(lái)看,肯定是不合適的。因此,我國(guó)民法典最好在采用“自然人”概念的同時(shí),將基本的民事主體表述為“公民”。這在技術(shù)上很好安排,可采用“公民和其他自然人”并舉的表達(dá)。可以說(shuō)將基本民事主體表述為“公民”比表述為“自然人”更合適。為了進(jìn)一步說(shuō)明這個(gè)道理,下面筆者再作三個(gè)方面的補(bǔ)充論述。
1.《草案》對(duì)基本民事主體的表述與《憲法》相關(guān)內(nèi)容脫節(jié)。《草案》第1條至第9條,每條都包含“民事主體”的規(guī)定。在中國(guó)憲法的框架下,民事主體中的自然人首先是公民,主要也是公民,但《草案》全文沒(méi)有“公民”二字或?qū)嶋H上指代公民的名詞(如本國(guó)人),甚至也沒(méi)有同公民或本國(guó)人形成對(duì)照的“外國(guó)人”之類(lèi)的名詞。所以,從外觀上看,這些條款就不是根據(jù)中國(guó)憲法形成的。
就主體和內(nèi)容而言,憲法保障的公民人身權(quán)利、財(cái)產(chǎn)權(quán)利在范圍上含蓋了民法保障的人身權(quán)利、財(cái)產(chǎn)權(quán)利。要明白這一點(diǎn),關(guān)鍵在于合理理解憲法、公法和私法在一國(guó)法制體系中的分工。基于權(quán)利與權(quán)力的劃分,一國(guó)法律體系中的全部法律可相應(yīng)地分為三類(lèi),由此形成不同于法律二元分類(lèi)傳統(tǒng)的法律三元分類(lèi):一是憲法(或根本法),它是公法和私法共同的根本法,從制定法制度的國(guó)家立法的角度看,它在很大程度上相當(dāng)于公法和私法的立法大綱;二是單純調(diào)整人身和財(cái)產(chǎn)領(lǐng)域具體權(quán)利—權(quán)利關(guān)系的法律,即私法或曰民商法;三是既調(diào)整具體的權(quán)力—權(quán)力關(guān)系,又調(diào)整除人身和財(cái)產(chǎn)方面的具體權(quán)利之外的其他具體的權(quán)利—權(quán)力關(guān)系的法律,即公法。采用這種與傳統(tǒng)的法律二元分類(lèi)法不同的法律三元分類(lèi)法,對(duì)合理說(shuō)明當(dāng)代很多法律現(xiàn)象(尤其是憲法與部門(mén)法關(guān)系方面的現(xiàn)象)非常重要。
憲法保障的人身權(quán)利的主體如果表述為“公民”,民事權(quán)利中人身權(quán)利的基本主體就應(yīng)該表述為“公民”;同理,憲法保障的基本權(quán)利的主體如果表述為“人”,民法典中民事權(quán)利的基本主體就應(yīng)該表述為“人”或“自然人”——德國(guó)憲法(基本法)與當(dāng)今的《德國(guó)民法典》就是按這個(gè)原則配套的。憲法保障財(cái)產(chǎn)權(quán)利與私法、公法保障財(cái)產(chǎn)權(quán)利的關(guān)系的原理也是如此,憲法從根本上、原則上保障公民財(cái)產(chǎn)權(quán)利,私法和公法分別從細(xì)節(jié)上以各自的方式具體保障個(gè)人的財(cái)產(chǎn)權(quán)利。如果中國(guó)民法學(xué)者看不到這一點(diǎn),編纂中國(guó)民法典時(shí)簡(jiǎn)單化地追隨《德國(guó)民法典》,其后果極可能是紙面上寫(xiě)著編纂民法典以本國(guó)憲法為根據(jù),客觀上卻以德國(guó)憲法為根據(jù)而并不自知。
2.將基本民事主體表述為公民有其現(xiàn)實(shí)必要性。《草案》產(chǎn)生上述憲法性瑕疵的關(guān)鍵,是其第2條將民事主體的范圍或種類(lèi)簡(jiǎn)單表述為“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組織”,而未對(duì)自然人、法人作憲法角度的細(xì)分。將基本的民事主體定位于公民并對(duì)自然人作公民與其他自然人(外國(guó)人、無(wú)國(guó)籍人)、本國(guó)法人與外國(guó)法人之區(qū)分,能杜絕民法典可能遺留的后患,而且有利于民法典的傳播和理解。
3.憲法差異決定中國(guó)民法典表述民事主體不能效仿德國(guó)。德國(guó)憲法與中國(guó)憲法不同,在德國(guó)憲法中,“人”是基本權(quán)利的首要主體,其次才是公民。與德國(guó)憲法不同,中國(guó)憲法基本權(quán)利的首要主體是“公民”,這從我國(guó)《憲法》第二章的標(biāo)題“公民的基本權(quán)利和義務(wù)”就能看出來(lái)。在中國(guó)憲法中,“人”不是基本權(quán)利的主體。《草案》在民事主體范圍的安排上,由于追隨《德國(guó)民法典》以自然人為中心的做法,實(shí)際上使得與《草案》對(duì)接的憲法并不是我國(guó)《憲法》的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權(quán)利和義務(wù)”,而是德國(guó)憲法的第一章“基本權(quán)利”。《草案》總則部分民事主體“自然人”應(yīng)當(dāng)改為“公民”(中國(guó)人),從而回到我國(guó)憲法的效力范圍內(nèi)來(lái)。筆者相信,民法學(xué)者們并不是要故意舍棄中國(guó)憲法而對(duì)接德國(guó)憲法,而是因?yàn)椴患颖鎰e地追隨《德國(guó)民法典》,不幸讓民法典偏離中國(guó)憲法的“接口”,像《德國(guó)民法典》一樣,對(duì)上了德國(guó)憲法的“接口”。
基本民事主體若表述為自然人,應(yīng)否將其區(qū)分為公民和其他自然人
退一步說(shuō),如果我國(guó)立法者難以接受上述憲法邏輯,堅(jiān)持在民法典中將一般民事主體表述為自然人,那么,將外國(guó)人納入自然人范圍,在民法典總則編中加以規(guī)定,而將特殊人格指向外國(guó)人,由民法分則(或特別法、特別規(guī)范)加以例外性地規(guī)定,應(yīng)該也是可以的,只是在邏輯上的整體性、協(xié)調(diào)性會(huì)差一些。
《草案》為什么應(yīng)該對(duì)自然人、法人作公民、外國(guó)人、中國(guó)法人和外國(guó)法人的區(qū)分呢?這應(yīng)該從民法典編纂的主權(quán)屬性來(lái)解釋。對(duì)自然人應(yīng)作公民與外國(guó)人的區(qū)分,而不應(yīng)完全無(wú)保留地賦予所有自然人平等的民事權(quán)利能力。然而,筆者檢索《草案》后發(fā)現(xiàn),其全文沒(méi)有出現(xiàn)過(guò)一次“公民”“本國(guó)人”之類(lèi)的名詞,這不是實(shí)行制定法制度的國(guó)家編纂民法典的通常做法。近現(xiàn)代大陸法系國(guó)家的民法典對(duì)民事主體,如自然人,都區(qū)分本國(guó)人和非本國(guó)人。易言之,《草案》不區(qū)分本國(guó)公民與外國(guó)人,并不是沿用其他大陸法系國(guó)家成熟做法的結(jié)果。《草案》對(duì)自然人完全不作公民與外國(guó)人之區(qū)分的做法,也不合乎中國(guó)民法的傳統(tǒng)。
民事主體內(nèi)部是權(quán)力關(guān)系還是權(quán)利關(guān)系
一國(guó)法律體系或法制體系所使用的術(shù)語(yǔ)體系應(yīng)該是和諧統(tǒng)一、層次分明的。這個(gè)術(shù)語(yǔ)體系的基礎(chǔ),應(yīng)是本國(guó)的憲法。按此要求來(lái)衡量,《草案》中有的用語(yǔ)明顯與我國(guó)《憲法》的規(guī)定和精神不相符,其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用“權(quán)力機(jī)構(gòu)”“職權(quán)”來(lái)描述法人內(nèi)部組織的地位和功能的做法。“權(quán)力”與“職權(quán)”是相聯(lián)系的,前者主要通過(guò)后者在憲法、法律中獲得具體表現(xiàn)。
1.用“決策機(jī)構(gòu)”取代“權(quán)力機(jī)構(gòu)”可補(bǔ)救與憲法不兼容的缺憾。《草案》總共在8個(gè)條款中10次使用了“權(quán)力機(jī)構(gòu)”一詞,都與我國(guó)《憲法》的規(guī)定和精神不相符合。在我國(guó)《憲法》中,權(quán)力實(shí)際上是我國(guó)《監(jiān)察法》所稱或人們?nèi)粘Kf(shuō)的“公權(quán)力”的同義詞,是以各級(jí)財(cái)政預(yù)算等公共資源支撐的公共利益在憲法上,從而在法律上的表現(xiàn)形式。我國(guó)《憲法》第2條規(guī)定:“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的一切權(quán)力屬于人民。人民行使國(guó)家權(quán)力的機(jī)關(guān)是全國(guó)人民代表大會(huì)和地方各級(jí)人民代表大會(huì)。”如果民法典稱股東會(huì)之類(lèi)組織為“權(quán)力機(jī)構(gòu)”,那么,它的“權(quán)力”就是“一切權(quán)力”的構(gòu)成部分,是屬于人民的,而在人大制度下,人民由全國(guó)人大和地方各級(jí)人大等國(guó)家權(quán)力機(jī)關(guān)代表。因此,從憲法角度看,股東會(huì)之類(lèi)組織根本不享有任何權(quán)力,《草案》將股東會(huì)之類(lèi)組織稱為“權(quán)力機(jī)構(gòu)”會(huì)擾亂憲法與民法典的正常關(guān)系,不利于國(guó)家的健全法治秩序的形成。
此外,由于民法典調(diào)整作為平等主體的公民、其他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組織之間的人身關(guān)系和財(cái)產(chǎn)關(guān)系,民事主體雖包括機(jī)關(guān)法人,但機(jī)關(guān)法人到了民事關(guān)系中,地位與公民、法人是平等的,都是私法關(guān)系的主體,只能擁有人身權(quán)利和財(cái)產(chǎn)權(quán)利,并無(wú)“權(quán)力”的存在空間。因此,民事主體及其權(quán)利,無(wú)論是將不同權(quán)利主體組合在一起還是將不同權(quán)利組合在一起,都是“私”的組合,不可能產(chǎn)生代議民主、人大制度等“公共”意義上的權(quán)力主體和權(quán)力內(nèi)容。在民法領(lǐng)域用“權(quán)力機(jī)構(gòu)”來(lái)描述民事主體中的內(nèi)部組織,也不符合漢語(yǔ)的表述傳統(tǒng)和習(xí)慣,最好將“權(quán)力機(jī)構(gòu)”全部改為“決策機(jī)構(gòu)”或“全權(quán)機(jī)構(gòu)”。編纂民法典,是堅(jiān)持本國(guó)法制體系的話語(yǔ)系統(tǒng)和民族語(yǔ)言的立場(chǎng)、消除民法條文中違逆我國(guó)具體情況的域外影響的一個(gè)良好的契機(jī),應(yīng)該避開(kāi)“權(quán)力機(jī)構(gòu)”這個(gè)名詞,而采用“決策機(jī)構(gòu)”或“全權(quán)機(jī)構(gòu)”的說(shuō)法。
2.有些情況下用“職能”“職位優(yōu)勢(shì)”比用“職權(quán)”合適。《草案》有7個(gè)條文中8次出現(xiàn)了“職權(quán)”一詞。然而,它們實(shí)際上是民事主體的一種私權(quán),不具備憲法文本規(guī)定的權(quán)力或職權(quán)的公共屬性,因而不應(yīng)稱為職權(quán)。從我國(guó)憲法中職權(quán)與權(quán)力的關(guān)系的角度看,“職權(quán)”是國(guó)家機(jī)構(gòu)的權(quán)力即公權(quán)力的具體存在形式之一,不適合用來(lái)表述民事主體所屬的組織機(jī)構(gòu)的職能,因?yàn)楹笳叩膶傩匀匀皇敲袷聶?quán)利,不是公共權(quán)力,盡管它表現(xiàn)為個(gè)人的財(cái)產(chǎn)權(quán)的聚合組織,并且在組織內(nèi)部發(fā)揮管理作用。
上述問(wèn)題,看似名詞術(shù)語(yǔ)運(yùn)用之爭(zhēng),好像是小事,實(shí)則上是涉及我國(guó)法制體系統(tǒng)一的原則問(wèn)題。《憲法》第5條要求,“國(guó)家維護(hù)社會(huì)主義法制的統(tǒng)一”。在社會(huì)主義法律體系初步形成的今天,立法時(shí)使用與憲法中的概念有實(shí)質(zhì)性沖突的術(shù)語(yǔ),對(duì)社會(huì)主義法律體系的統(tǒng)一難免造成一定程度的實(shí)際損害。編纂民法典時(shí),如果有可能,這些術(shù)語(yǔ)應(yīng)基于我國(guó)《憲法》一并理順才好。
憲法之下人格權(quán)利與公權(quán)力如何平衡
在憲法與民法關(guān)系方面,一些法學(xué)界人士在自媒體上對(duì)人格權(quán)利與公權(quán)力之間的關(guān)系表現(xiàn)出兩種不無(wú)矛盾的認(rèn)識(shí)傾向,對(duì)此,亦可結(jié)合《草案》的審議作討論,爭(zhēng)取形成共識(shí)。一種認(rèn)識(shí)傾向認(rèn)為,《草案》規(guī)定的有些內(nèi)容(如人格權(quán)保障)在我國(guó)《憲法》規(guī)定的公民基本權(quán)利部分找不到足夠的依托;另一種認(rèn)識(shí)傾向認(rèn)為,《草案》受我國(guó)《憲法》相關(guān)條款約束似乎失去了一些作為民法典應(yīng)有的私法特性。筆者認(rèn)為,只要正確理解憲法,并且在技術(shù)上處理得當(dāng),就不會(huì)有憲法妨礙民法典充分保障民事權(quán)利的問(wèn)題和憲法使民法典失去民法特性的問(wèn)題。
1.關(guān)于民法典充分保障人格權(quán)的憲法根據(jù)。關(guān)于人格權(quán)保障,我國(guó)《憲法》第38條只規(guī)定:“公民的人格尊嚴(yán)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對(duì)公民進(jìn)行侮辱、誹謗和誣告陷害。”那么,《草案》可否將人格權(quán)保障作大范圍擴(kuò)充呢?在法德等歐洲制定法國(guó)家,法理、憲法、民法在權(quán)利保障方面具有同源性,內(nèi)部融合程度比較高。從20世紀(jì)20年代開(kāi)始,社會(huì)主義國(guó)家的民法把這個(gè)原則移植過(guò)來(lái)了。這很有必要,但是包括我國(guó)在內(nèi)的社會(huì)主義國(guó)家的經(jīng)典法理、憲理和憲法從來(lái)不包括“人生而平等,具有某些與生俱來(lái)的、不可轉(zhuǎn)讓、不可剝奪的權(quán)利”等內(nèi)容。因此,我們的民法原則與憲法原則及其支撐性法理不具有同源性。與此相類(lèi)似,我國(guó)《憲法》列舉公民基本權(quán)利的性質(zhì)往往并不十分明確。如果假定個(gè)人本源性的基本權(quán)利是先于憲法、與生俱來(lái)的,只是通過(guò)選舉、制憲把個(gè)人權(quán)利的一部分轉(zhuǎn)讓給了國(guó)家機(jī)構(gòu),那就很清楚,憲法列舉的只是強(qiáng)調(diào)個(gè)人權(quán)利中的一部分,表示國(guó)家愿對(duì)這一部分權(quán)利承擔(dān)保障義務(wù)。所以,列舉并不否認(rèn)未列舉的權(quán)利,只要有可能,國(guó)家愿意盡可能多地承擔(dān)保障它們的義務(wù)。
2.憲法并不要求民法典承擔(dān)公法功能。《草案》主要包含三個(gè)隱蔽地向國(guó)家行政機(jī)關(guān)授予征收、征用的權(quán)力或職權(quán)的條款,即第117條、第243條和第245條。它們的性質(zhì)主要在于授予國(guó)家行政機(jī)關(guān)征收、征用和處理相應(yīng)善后事宜的權(quán)力,很大程度上不屬于民法條款,或許放在某部憲法相關(guān)法或行政法中比較合適。
退許多步說(shuō),上述三處涉及征收征用組織、個(gè)人的不動(dòng)產(chǎn)的規(guī)定即使不得不置于民法典中,也應(yīng)切實(shí)體現(xiàn)《草案》第4條、第6條規(guī)定的“民事主體在民事活動(dòng)中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和民事主體從事民事活動(dòng)應(yīng)當(dāng)遵循“公平原則”等要求。無(wú)論如何,應(yīng)當(dāng)防止地方政府利用征收集體土地賺取差價(jià)等不平等、不公平的做法。在這些方面,民法典無(wú)論寫(xiě)上多少“公平、合理”都沒(méi)有意義,是否公平合理事實(shí)上只能由國(guó)家機(jī)關(guān)單方面確定。民法典的制定者如果想拿出“公平、合理”的解決方案,就應(yīng)該具體規(guī)定被征收的不動(dòng)產(chǎn)在若干年內(nèi)價(jià)格增值后的分享比例,或者在國(guó)有和集體的土地的使用權(quán)有償轉(zhuǎn)讓方面規(guī)定平等上市權(quán),如此等等。無(wú)論如何,應(yīng)該不給地方政府壟斷土地使用權(quán)一級(jí)市場(chǎng)留下空間。
3.民法典宜在憲定人格尊嚴(yán)保障方面更有作為。在數(shù)字化時(shí)代,個(gè)人隱私權(quán)保護(hù)面臨歷史上從來(lái)沒(méi)有遇到過(guò)的來(lái)自公權(quán)力部門(mén)、其他組織和其他個(gè)人的嚴(yán)峻挑戰(zhàn)。然而,《草案》保護(hù)隱私權(quán)的主要條款對(duì)個(gè)人隱私權(quán)的保護(hù)力度似乎與當(dāng)今的這種挑戰(zhàn)不相稱。《草案》上述條款對(duì)隱私權(quán)保護(hù)力度不夠。這首先表現(xiàn)為將“隱私”的外延界定得比較狹窄,只限于“私密空間、私密活動(dòng)、私密信息”。privacy一詞有兩重含義:一是某人不受干擾的獨(dú)處狀態(tài);二是某人的秘密(secrecy)。生活中人們對(duì)中文“隱私”一詞的理解也對(duì)應(yīng)于英文privacy,是雙重的。國(guó)外在法律上使用privacy(隱私)一詞偏重第一層含義。相對(duì)而言,《草案》對(duì)“隱私”是基于其第二重含義(即秘密)來(lái)定義的。如此一來(lái),就將一這就使得打擾個(gè)人獨(dú)處狀態(tài)的做法合法化了。筆者認(rèn)為,應(yīng)按“隱私”一詞的第一層含義來(lái)定義人格權(quán)中的“隱私”權(quán)。
此外,同樣重要的是,今天人們生活在各種各樣的攝像、錄影和人臉識(shí)別設(shè)備的鏡頭下,人格權(quán)受到的威脅前所未有。因此,對(duì)于這些數(shù)字設(shè)備的使用,《草案》原本可以從其擁有主體、使用的空間范圍和保留個(gè)人影像資料的時(shí)間長(zhǎng)度等多個(gè)方面,從民法的角度作些必要的限制和規(guī)范。遺憾的是,《草案》并未作出應(yīng)有的努力。
4.民法典應(yīng)促進(jìn)民事主體發(fā)展權(quán)利的實(shí)質(zhì)平等。《草案》規(guī)定“國(guó)家實(shí)行社會(huì)主義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保障一切市場(chǎng)主體的平等法律地位和發(fā)展權(quán)利”。需要關(guān)注的是,《草案》幾個(gè)后續(xù)條款對(duì)財(cái)產(chǎn)關(guān)系的處理,似乎仍然留有一些計(jì)劃經(jīng)濟(jì)時(shí)代公有財(cái)產(chǎn)受特殊保護(hù)的痕跡,不盡合情合理。“公有制為主體”已經(jīng)體現(xiàn)在我國(guó)憲法、法律將全社會(huì)基礎(chǔ)性的和最重要的經(jīng)濟(jì)資源都劃歸國(guó)家所有的制度中,屬于公民私人所有的財(cái)產(chǎn)在財(cái)產(chǎn)總量中的比例本來(lái)就相當(dāng)?shù)汀T诖藸顩r下,國(guó)家沒(méi)有必要在漂流物、埋藏物、隱藏物、個(gè)人遺產(chǎn)等小事上居于比個(gè)人更優(yōu)越的獲取地位。就拾得漂流物、發(fā)現(xiàn)埋藏物或者隱藏物而言,如果所涉財(cái)產(chǎn)不是特別巨大、不具有重要?dú)v史文化價(jià)值,而拾得者、發(fā)現(xiàn)者又比較貧困,那么基于民事主體法律地位平等和發(fā)展權(quán)利平等的原則,法律為什么不能規(guī)定漂流物、埋藏物、隱藏物歸拾得者、發(fā)現(xiàn)者個(gè)人所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