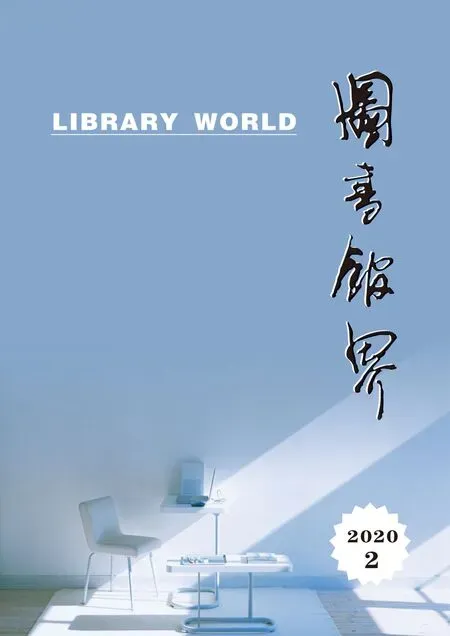共生學科服務“知識共生模式”預設
——真人圖書館方案
吳云珊
(廣西師范大學圖書館,廣西 桂林 541004)
1 共生學科服務
“共生學科服務”是將學科服務建立在供需雙方交互協同基礎上,以共生界面、共生模式、共生單元和共生環境四個要素為基本理論框架的新興理論[1]。“共生學科服務”理論,重新審視了“學科服務”的復雜性和特殊性,為學科服務的可持續發展開辟了嶄新的理論探索之路。
2 知識共生模式
“知識共生”是筆者基于“情報共生”[2]提出的概念,指在一定知識領域內,異類知識個體按一定共生模式形成相互依賴的知識關系或認知共同體。依據“共生學科服務”理論,“共生模式”是建立學科館員和學科用戶之間一切“共生關系”的關鍵。學科館員和學科用戶之間“知識共生”是開展共生學科服務的基本前提。要建立二者的“知識共生關系”,關鍵要在二者之間構建適合的“知識共生模式”。
所謂“知識共生模式”是指建立和維系認知共同體的方式。在學科館員和學科用戶之間尋求適合的知識共生模式是積極實踐和驗證共生學科服務理論的要求,也是積極推動學科服務向可持續、高品質、良性方向發展的體現。
3 真人圖書館
2000年誕生于丹麥哥本哈根的“活體圖書館”(Living Library),2010年更名為“真人圖書館”(Human Library,HL),因其獨特新穎的“閱人”方式于2008年被我國各界關注。如今作為“不斷生長的有機體”,真人圖書館的價值在不斷被挖掘——各級學校圖書館、公共圖書館、民間組織和商業組織紛紛開設各式各樣的真人圖書館,利用其的特殊形式達到隱性知識轉移[3]、閱讀推廣[4]、文化傳承[5]、閱讀療法[6]、人際交流[7]、知識服務[8]、文化扶貧[9]等目的。真人圖書館是否還能成為共生學科服務的“知識共生模式”呢?
4 真人圖書館的知識共生優勢
為學科服務尋求“知識共生模式”,目的是在一定學科領域內建立、維系“服務者”學科館員和“被服務者”學科用戶之間相互依賴的知識關系,建立以“服務”為前提的學科館員和學科用戶在本學科領域的“認知共同體”。因此,學科服務的知識共生模式既要保持學科館員作為“服務者”、學科用戶作為“被服務者”的關系,又要實現知識的高效能共生——實現知識的偏利性雙贏交互、常規化深度交流、全類型高效轉移和混沌序協同生成。
4.1 真人圖書館實現知識偏利性雙贏交互
根據初景利教授的定義,學科服務具有個性化、專業化、知識化的特征[10]。要做好這項服務,學科館員不僅要有圖情知識,還要有學科知識;不僅要有學科知識,還要能隨著學科的發展不斷更新原有的學科知識;不僅要能不斷更新原有的學科知識,還要能針對不同服務對象的需求整理個性化的學科情報。學科館員“可拓展的學科知識”和“個性化學科情報”從哪里來?最直接的渠道就是從其要為之服務的學科用戶中來。在學科服務過程中,“服務者”和“被服務者”即“學科館員”和“學科用戶”的知識必須“雙向流動”、利益必須“二者兼顧”,學科館員的“圖情優勢”和學科用戶的“學科優勢”才能得以“優勢互補”“螺旋上升”。
傳統的學科服務交流方式,如走訪、咨詢等,偏重“學科用戶提出需求、學科館員回饋需求”,學科館員通過知識勞動輸出優勢知識,滿足學科用戶的學科需求,使學科用戶單方面受益,但學科館員自身的知識結構卻沒有得到優化。長此以往,學科館員將知識虧空嚴重,無法提供高質量的服務。顯然傳統的學科服務知識交流模式無法實現學科館員和學科用戶的“雙贏”,學科服務無法良性發展。
真人圖書館模式可改變這種情況。真人圖書館實行“主題式借閱”,每次借閱都圍繞一定的主題進行。“學科館員”標簽下的真人圖書可以根據自身特長設置每次的借閱主題,學科用戶可以根據自身的學科需求自行選擇借閱主題,與有可能幫助自己解決問題的學科館員真人圖書交流。這樣有兩個好處:一是“不平衡”不改變“服務”定位,二是“雙向”實現雙方知識結構“雙贏”。1)“不平衡”不改變“服務”定位。“服務”就是以被服務者的需求為中心,服務者付出和輸出,被服務者接收和吸納。與作為讀者的學科用戶相比,學科館員真人圖書在其借閱主題下的知識儲備更為豐厚,知識外溢性更強,因此知識輸出更多。例如,借閱主題是“校外學術資源的獲取”的學科館員真人圖書,在公共圖書館資源、機構知識庫和開放期刊等開放獲取資源、慕課、文獻傳遞、漫游賬號等方面的知識涉獵要遠遠廣于作為真人圖書讀者的學科用戶。因此,真人圖書館的知識交流模式是不平衡的,真人圖書的知識輸出要高于讀者,這與“服務”的定位是一致的。2)“雙向”實現雙方知識結構“雙贏”。與作為真人圖書的學科館員相比,作為真人圖書讀者的學科用戶在該“借閱主題”下的知識儲備雖然稍少,但依然有一定的知識儲備;知識外溢性雖然稍弱,但依然存在知識外溢性;知識輸出雖然稍少,但依舊有知識輸出。例如,與借閱主題是“校外學術資源的獲取”的學科館員真人圖書交流,學科用戶或許在小眾學術資料獲取和篩選方面也有經歷和心得,可使學科館員真人圖書受益。真人圖書館讓學科館員在其作為“服務者”的定位不變的情況下,一改傳統知識交流“一邊倒”的弊端,實現了學科館員和學科用戶之間知識的“不平衡雙向流動”。這種不平衡的雙向知識流動對于學科館員和學科用戶來說都是必不可少的生存之本:來自學科館員的知識是學科用戶教學、科研的利器;而來自學科用戶的知識則是學科館員不斷充電、高質量開展學科服務工作的源泉。學科館員和學科用戶之間的“不平衡雙向”知識交流實現了交流雙方的“偏利性雙贏”,使交流雙方“知識共生”形態悄然而顯。
4.2 真人圖書館實現知識常規化深度交流
可持續開展的高品質學科服務需要在學科館員和學科用戶之間營造一種“知識以太(ether)”,即:無時不在、相互依存的“知識共生關系”。如何營造這種“知識以太”呢?一要注重知識交流的“廣度”,“面”要鋪開,覆蓋所有的學科館員和學科用戶;二要注重知識交流的“深度”,“點”要深入,進行以解決問題為目的的深度交流。1)學科服務是一項少數人為多數人服務的工作,學科館員數量遠遠低于學科用戶數量。學科服務向來要求學科館員和學科用戶加強聯系,號召學科館員動起來,走出圖書館、走進院系、嵌入學科用戶的科研團隊,但讓少數人通過頻繁走訪,深度嵌入多數人,實踐上難以實現。傳統學科服務只能覆蓋部分重點學科用戶和團隊。2)學科服務是一項難度較高的工作,要切實解決用戶的問題。要解決問題,必須要先深入地了解問題、探討問題。學科館員單槍匹馬工作,往往很難解決用戶“多樣化”的問題。這也是當今圖書館界提倡“學科團隊”的緣由——由若干學科館員組成“團隊”,以協作方式取長補短才能滿足某個學科用戶或團隊的“多樣化”學科需求。為此,筆者要引入“學科館員群體”和“學科館員個體”兩個概念。所謂“學科館員群體”,是“學科館員個體”的集合,類似生物學上的“種群”。這個知識種群更多強調學科館員的“共性”,即同時具備圖情知識和學科知識的圖書館專業技術人員。但學科館員也有個性。相同“知識種群”下的不同學科館員有不同的特點和特長,如同為學科館員,有的擅長查新,有的擅長授課;有的文獻計量分析能力很強,有的則課題服務能力很強;有的側重關注理工科、有的側重關注人文社科……學科館員團隊作業,解決問題的能力得到加強,但人力卻更顯不足。
真人圖書館憑借其常規化的“按需讀人”和常態化的“深度會談”解決以上問題。1)“按需讀人”常規化。真人圖書館模式將學科館員變成一本一本帶有“標簽”和“內容簡介”的真人圖書,將每個學科館員的特長公之于眾,學科用戶或者教研團隊可以按需借閱。再輔之以“預約方式”和“在線視頻對話方式”,實現“高頻次借閱”和“異地借閱”,讓“讀人”常規化。只要了解各位學科館員真人圖書的服務期限,提前預約,想借誰就借誰,想什么時候借就什么時候借,且一個用戶可以借好幾本書。這就實現了學科用戶和學科館員群體之間“經常性”的知識交流。而學科館員真人圖書按時上架,面向所有的學科用戶,交流的都是自己擅長的內容,完全可以“少數人覆蓋所有人”,有效解決人力不足的問題。根據自身需求選擇交流對象,相當于學科用戶為自己量身定制了“個性化的學科服務團隊”,為自己構建了“個性化知識共同體”。2)“深度會談”常態化。“深度會談是在會談雙方之間產生一股來回往返的知識流,實現隱性知識螺旋式上升地來回轉移,達到產生新思想、新觀點的效果。”[3]在文化等各種因素的影響下,國內大多數真人圖書館與分享會、報告會、沙龍等區別不大,都是一對多的講座交流形式,抓住了“以人為書”的基本概念,卻沒有抓住“閱人”的本質,筆者暫且稱之為“第一代中國化真人圖書館”。第一代中國化真人圖書館并沒有真正發揮真人圖書館的核心價值,造成真人圖書館在中國一度走下坡路。筆者在以往的研究中發現,真人圖書館的核心價值在于“主題式深度會談”[11],通過“主題式深度會談”達到傳播隱性知識、消除歧視偏見、滿足交流需求、傳承文化等目的。在工作實踐上,筆者曾嘗試通過減少每次借閱的讀者人數、設立獨立的借閱空間等方式減少干擾,為真人圖書的借閱盡量營造利于開展深度會談的環境,促成深度會談,取得一定效果。實踐證明,異類知識個體在真人圖書館可以自由組合,異類知識種群在真人圖書館可以自發交叉,深度知識交流在真人圖書館可以隨時開展,知識共生系統在真人圖書館完全可能自覺形成。
4.3 真人圖書館實現全類型知識高級轉移
“學科知識”指以學科劃分的專業領域知識,及在某專業知識領域開展教學、科研、組織、管理、交流等所用到的知識。學科服務是一種“知識服務”。研究學科服務的“知識共生模式”,是研究學科服務中“知識轉移”“知識轉化”和“知識效用”的問題。研究這些問題,需要關注知識的性質和知識轉移的難易程度。盡管知識可以從不同維度進行分類,但基于知識轉移的難易程度這個研究視角,筆者在此僅依據波蘭尼的觀點[12],將知識分為“顯性知識”和“隱性知識”來討論。“顯性知識”是以書面文字、圖表和數學公式加以表述的知識;“隱性知識”是存在于人腦當中、難以言傳的知識,主要通過頓悟、師徒傳授、內隱學習、隱喻、象征、講故事、深度會談等方式獲得[13]。學科服務中涉及的學科知識應該既包括學科館員在該學科領域所有的顯性知識和隱性知識,也包括學科用戶在該學科領域所有的顯性知識和隱性知識。根據倪延年[14]的研究,知識傳播發展有四個階段層次:第一階段層次是通過動作和姿態傳播;第二階段層次除了通過動作和姿態傳播,還加入了語言傳播;第三階段層次除了通過動作、姿態、語言傳播,還加入了文字(文獻)傳播;第四階段層次,在第三階段層次基礎上加入了綜合各種工具的以教育為形式的知識傳播。也就是說,最高層次的知識傳播,是集動作、姿態、語言、文字(文獻)、綜合各種工具以教育為形式的知識傳播。
結合波蘭尼對知識的劃分和倪延年對知識傳播層次的劃分,真人圖書館是一種能實現顯性知識和隱性知識“全類型知識”,集動作、姿態、語言、文字(文獻)、綜合各種工具以教育為形式的最高層次知識傳播的模式。借助這種模式,學科館員和學科用戶可以實現“全通道”的知識共生。所謂“全通道”,指知識轉移的所有途徑。從人汲取知識的途徑看,包括“看、聽、嗅、嘗、觸”這5個動作。1)真人圖書館能同時調動人的視覺、聽覺、嗅覺、味覺、觸覺五個感官。感官通道全開的個體接觸,通過觀察、模仿,全面獲取各類信息,篩選出相關信息進行選擇性組合和比較,發生頓悟。學科館員真人圖書與學科用戶讀者在真人圖書館模式下“面對面”。“面對面”,可以看到文字、文獻、圖片、視頻、動作、姿勢、神態,聽到語言、聲音,聞到氣味,嘗到味道,摸到實物,感受到對方的語氣、傾向、喜惡、潛意識、思維方式,捕捉到對方的思維火花。真人圖書館模式不僅可以幫助學科館員和學科用戶進行顯性知識轉移,還讓他們嘗試高難度的隱性知識轉移,這是傳統的學科服務知識交流模式所欠缺的。真人圖書館為學科服務打開了“全類型知識轉移”的全部感官通道,在輕松的交流中發生無意識的內隱學習,是一種旨在實現知識共生的高級知識傳播模式。2)真人圖書館讓知識的傳遞距離變為最短。真實生活中的“面對面”,讓不同的“知識體”進行“活體接觸”,通過“視、聽、嗅、味、觸”五種感受,即時傳遞零次信息,進行最直接的知識交流。學科館員和學科用戶屬于不同的知識群體,二者是異類知識體。借助真人圖書館模式,二者將知識傳遞距離縮小到最短、傳遞頻率提高到最高、傳遞效能擴大到最大,極有利于在二者之間建立知識共生關系。
4.4 真人圖書館實現混沌序知識協同生成
“新知識生成”即“知識創新”。學科館員和學科用戶分屬于不同知識群體,其個體是“異構知識體”。學科館員和學科用戶之間需要通過不斷生成新知識、促進雙方知識增量來建立“異構知識共同體”,保持長久的知識共生關系。因此,學科服務的“知識共生模式”不僅要實現知識的“轉移”和“利用”,還要實現新知識的“生成”。根據SECI知識轉化模型[15],“知識轉化”有四種基本模式——社會化、外化、組合化和內化。“新知識生成”是不同類型知識(包括顯性知識和隱性知識)和不同知識體在相互作用中,不斷轉移、演化、應用和創造的動態過程。
真人圖書館的“主題式借閱組合”和“深度會談”是其獨具特色的知識交流模式。學科館員和學科用戶借助這種知識交流模式,可以提高彼此的信任感,常態化地讓彼此的顯性知識和隱性知識在相關學科范疇下進入“混沌”狀態,通過“協同”運動,從無序變為有序,生成新知識,極大提高知識共生效率。1)“主題式借閱組合”讓不同知識體的知識“混沌化”,而“深度會談”捕捉混沌態知識隨機碰撞的瞬間火花從而生成新知識。所謂“混沌”,指“混沌學(Chaos)”中確定論系統的一種動力學行為方式,不是“有序”,也不是“混亂無序”,而是“混沌序”——不規則、不穩定、隨機、非周期、異常復雜的有序進化的歸宿。“混沌學”主要研究不穩定、不規則以及分形構造的系統現象[16]。混沌本質是系統的長期行為對初始條件的敏感性,如“蝴蝶效應”,一只蝴蝶在巴西扇動翅膀,可能會在德州引起一場龍卷風。確定論系統有“外隨機性”和“內隨機性”兩種隨機性。“外隨機性”指外部環境的不定性對系統運動產生干擾所形成的隨機性;“內隨機性”是系統內部自發產生的隨機性[16]。“混沌”的基本特征是“內隨機性”。真人圖書和讀者都是個性化的動態知識體。真人圖書館模式很好地保持了二者的“內隨機性”,使二者的知識在真人圖書館模式下混沌融合。同一本真人圖書,在同一個主題標簽下,面對不同的讀者,可讀的內容不完全相同;即使同一本真人圖書,面對同一位讀者,在不同的時期、情緒、環境下,可讀的內容也不盡相同。同理,同一位讀者,借閱不同標簽的真人圖書,他回饋真人圖書的信息、知識也不同;同一位讀者,借閱同一本真人圖書,在不同的時期、情緒、環境下反饋給真人圖書的信息、知識也不同。當學科館員成為真人圖書,學科用戶成為讀者,二者所具有的學科知識、信息知識、生活常識、職業歸屬等異構知識自然處于混沌狀態。混沌狀態是“無序”和“有序”兼容的不穩定狀態,既可以向“無序”發展,也可以向“有序”發展。如果天馬行空地“閑聊”,則混沌態知識向“無序”方向發展、生成知識傾向較弱;如果“深度會談”,則混沌態知識向“有序”方向發展、生成知識傾向較強。真人圖書館讓不同“知識體”的各種類型(顯性和隱性)知識通過“主題式借閱組合”隨機接觸,各類知識看似處于不規則、不穩定、隨機、非周期、異常復雜狀態,其實并非一團亂麻,而通過“深度會談”隨機作用,朝著“借閱主題”這個目標頻繁轉移、內化、外化,形成更高層次的“有序態”,即新知識。真人圖書館借閱主題下不經意的一句話有可能改變一個學科的發展方向。2)外參量“主題式借閱組合”驅動下,不同知識體“協同”作用,通過序參量“深度會談”確定有序化程度,生成新知識。所謂“協同”,指“協同學”中系統從無序到有序轉變的規律和過程。“協同學”是關于多組分系統如何通過子系統的協同行動而導致結構有序演化的自組織理論,是研究協同系統從無序到有序的演化規律的新興綜合性學科[16]。外參量指控制參量,是環境對系統的影響因素,包括物質或能量的輸入。序參量,是協同論的核心概念,指在系統演化中從無到有的變化,并能指示出新結構形成的參量。序參量主宰著系統演化的整個進程,決定著系統演化的結果[16]。“主題式借閱組合”是真人圖書館的外參量。“交流主題”將真人圖書知識體和讀者知識體有目的地組合在一起,促使二者知識協同運動、循環再生。“借閱時間”和“借閱環境”影響和控制著真人圖書和讀者的交流深度:交流時間越長,交流環境越隱秘,交流越容易深入。借閱時間和借閱環境的變化驅使真人圖書借閱經歷一系列臨界點,導致序參量的出現。“深度會談”是真人圖書館的序參量。當在相對獨立而安靜的環境中經過一定時間按約定主題自由閑談后,普通聊天轉為目標明確的“深度會談”,知識高頻地進行著雙向流動,舊知識不斷被新知識替代、改變、豐富,知識體原有知識體系出現不穩定性,不穩定性充當了新舊結構演替的媒介,不穩定性使舊結構的瓦解、新結構產生,新舊知識結構完成演替,新知識生成。“主題式借閱組合”使不同知識體知識混沌、協同作用,“深度會談”捕捉瞬息新知識火花、有序演變,從而不斷形成新知識,新知識又繼續混沌、協同作用形成新的知識火花,進而繼續有序演變形成新知識……真人圖書館模式讓學科館員知識體和學科用戶知識體在進行著周而復始、螺旋上升的知識生產基礎上建立相互依存的知識共生關系。
5 結 語
真人圖書館以其可控的主題式借閱、明確的“身份定位”、五感全開的“借閱形式”、超短的“轉移距離”、自由的“借閱組合”、獨特的“創新模式”和最具價值的“深度會談”,實現知識偏利性雙贏交互和常規化深度交流和全類型和混沌序知識的高效轉移和協同生產,是不可多得的一種知識共生模式,可以作為學科服務知識共生模式的優選方案付諸實踐、接受實踐檢驗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