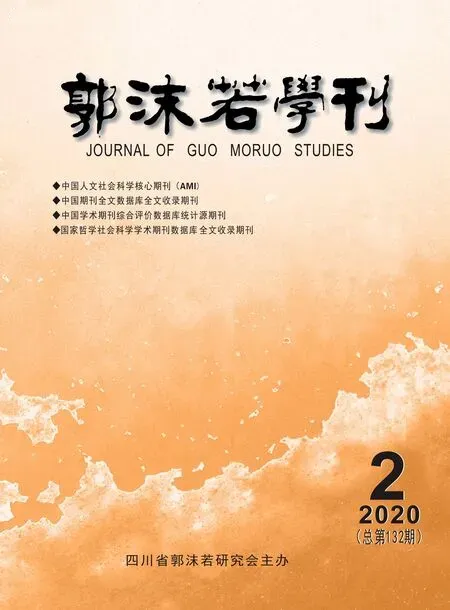郭沫若又一首寺字韻詩考
蔡 震
在“盧溝橋事變”80周年紀念之際,曾有一首郭沫若的佚詩被披露出來,是郭沫若1939年書贈一位日本九州帝國大學校友的詩。因是一件文物,所以并無整理出的文本及相關資料刊出。該詩無題,詩文及落款如下:
九大今中小野寺,誘和慣寫怪文字。
我輩恨之澈骨深,學部雖殊心不異。
同窗健者來巴岷,聚談同樂氣訚訚。
可憐孺子號龍象,俯首附敵如犬馴。
流芳遺臭各千載,薰蕕一器難同在。
今晨聞刺丁默邨,明朝定死周佛海。
侈談南闕貴公卿,聞警何人最心驚。
防毒外衣兼面具,此公不便書其名。
廿八年除夕九大同學團年會席上戲作剛侯同學囑為之書①據題詩手跡釋讀,錄入。
詩所以能披露出來,是因為得到郭沫若贈詩的“剛侯同學”的子女將其作為抗戰文物,捐贈給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九大”,即日本九州帝國大學。剛侯,閔剛侯,法學家,江蘇南匯人,生于1904年。閔剛侯1932年畢業于東吳大學,次年留學日本九州帝國大學,主攻法學。所以與郭沫若是先后期校友。閔剛侯畢業回國后1937年在上海做執業律師。抗戰期間,在重慶負責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工作。新中國成立后,閔剛侯任最高人民法院秘書長、司法部副部長,民盟第三屆中央常委、組織部部長、秘書長,1971辭世。
郭沫若創作中的佚詩,尤其是舊體形式的佚詩比較多,需要不斷發掘整理。而這一首在詩文披露于世后,需要特別做一些考察,因為它不只是郭沫若在抗戰時期的一首詩歌作品,而且包含了一些抗戰期間的歷史文化信息。
閱讀該詩,首先會注意到這是一首用寺字韻作的詩,而且作于1939年,那么對于郭沫若的舊體詩創作,應當是一個值得單獨記述的事情。
“當年重慶詩人盛行用寺字韻,疊相唱和,成為風氣。余亦偶為之,今僅存此一首。”這是郭沫若在1959年編輯詩歌集《潮汐集·汐集》時,為輯錄的一首用寺字韻作于1939年9月的《登烏尤山》所寫的題注。1965年2月25日,郭沫若為一幅手寫于1940年1月的書卷題寫了一段跋語。這幅書卷是當年他為于立群所寫,書錄了自己所作的七首(包括《登烏尤山》)寺字韻詩。跋語寫道:“三十五年前在重慶曾為寺字韻十三首,此卷存其七首,余六首如石沉大海矣”。(“三十五年”應系“二十五年”筆誤)②《郭沫若書法集》,四川辭書出版社1999年11月。顯然,這幅書卷是在1965年時才翻撿出來的,所以郭沫若編《潮汐集》時并沒有看到它。但書卷除了七首詩的文本,沒有任何其它信息。這些情況說明,對于當年(1939年)曾創作過十三首寺字韻詩的事情,郭沫若自己其實已經記不得究竟了。
一年之內用寺字韻創作了十三首詩,僅就數量而言,這應該也是郭沫若抗戰詩歌創作一個值得關注的內容。但除了《登烏尤山》一首發表過,郭沫若書錄的七首寺字韻詩是作為書法作品刊出的,其中另外六首詩作實際上并未被注意,也從未被提及。所以,我竭力想找尋全部十三首寺字韻詩,并做整理,研究,特別是那些還不為人知的篇目。之后,我曾撰寫了《郭沫若用寺字韻詩作考》一文(發表于《郭沫若學刊》2011年第3期),梳理、考訂了當時能夠找到的那些詩篇的文本、創作時間、創作背景等情況,并整體考察了其創作的意義。在將該文收入《郭沫若生平文獻史料考》書稿,出版社已錄排出校樣之際,又找到兩首郭沫若作于1939年12月31日的寺字韻詩《疊用寺字韻贈別西北攝影隊》,遂將詩文附錄于該篇文末。①參見蔡震:《郭沫若生平文獻史料考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7月。該文收入書中題作《抗戰期間用寺字韻作佚詩考》。
算上這次被公之于世的這一首題贈閔剛侯的詩作,郭沫若所說的十三首寺字韻詩,已經能見到十一首了。
郭沫若書贈閔剛侯的這首詩沒有篇題,不妨名之為《寺字韻書贈閔剛侯》。詩用了敘事感懷的方式,詩文中包含了這樣一些值得關注的歷史信息:
廿八年,即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是年郭沫若在重慶主政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除夕,這里應是按照日本公歷紀年的說法指12月31日。此時郭沫若身在重慶,所以詩是寫在重慶的,“九大同學團年會”應該也是在重慶舉辦的。九大,即日本九州帝國大學的簡稱。九大的同學校友能在年末舉辦一次年會(日本稱團年會),應該平時也是有個相互聯系、聯絡感情的同學會這樣的組織吧。在郭沫若生平史料中有關這方面的史實,倒是初次見到,需要繼續留意。
詩文首句中的今中,即今中次麿,是九州帝國大學政治學教授,曾為閔剛侯的授業導師;小野寺,即小野寺直助,是九州帝國大學醫學教授,曾為郭沫若的授業導師。從詩句的意思看,今中次麿、小野寺直助當時應該都是遵照日本軍部的意旨,在報刊上發表過“誘和”之類的文字、文章的。那時,曾在九大求學,畢業后回國工作的中國留學生當有相當數量。而且他們回國后,大都從事著不一般的工作,像郭沫若、閔剛侯一樣。日本侵略軍顯然是力圖以這樣的宣傳,引誘這些有留學日本背景的中國知識分子像周佛海、周作人那樣“附逆”,服務于日本對中國的侵略。
“我輩恨之澈骨深”,顯然,郭沫若對于今中、小野寺們發表“怪文字”的這種行徑是非常痛恨的。其實在流亡日本期間,郭沫若與小野寺是有來往的(包括通信),但抗戰改變了原有的師生關系。不過到了戰后,郭沫若1955年率中國科學代表團訪日的時候,在福岡,他與小野寺又恢復了師生情誼②參見劉德友:《隨郭沫若戰后訪日》,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8年9月。。那么從這首詩中,我們實際上可以看到在戰爭中人際關系(特別是郭沫若這樣有留學與亡命日本背景的日本人際關系)所發生的變化。
郭沫若留學九州帝國大學醫學部,閔剛侯就讀于法學部,在渝的九大“同窗”會是畢業于九大各個學部的學友,大家的愛國情懷是心心相印的,所以詩中謂“學部雖殊心不異”。
“今晨聞刺丁默邨”句,當指1939年12月21日中統特務刺殺丁默邨未遂之事。丁默邨與下句所寫的周佛海均為大漢奸。刺殺事件的發生恰在除夕九大同學團年會之前幾天,“今晨”倒未必實指具體日期,而是與“明朝”相對,詛咒漢奸們的最終下場。
南闕,指1939年9月,汪精衛在南京與北平偽臨時政府主席王克敏、偽維新政府主席梁鴻志協商,達成在南京成立偽中央政府的協議并付諸施行。
將《寺字韻書贈閔剛侯》與之前我所整理出的郭沫若那些寺字韻詩放在一起,可以清楚地看到該詩也是在同樣的抗戰時代背景下所創作的。它真切地抒發了作者的抗戰情懷,“直接、間接地記錄或反映”了發生在1939年間的時事,是“記錄了一段歷史的一組詩”之中的一首。
但這其中也有一點存疑之處:《寺字韻書贈閔剛侯》與之前找到的《疊用寺字韻贈別西北攝影隊》,為何沒有納入郭沫若當年用寺字韻詩的排序中去呢?就郭沫若1940年1月為于立群手錄的書卷而言,有可能他只是從1939年所作13首寺字韻詩中選錄了七首并做了排序,但記述了故宮文物西遷之事的那首“書奉”馬衡的寺字韻詩,就是落款作“十二用寺字韻”。也就是說在“七用寺字韻”與“十二用寺字韻”之間,應該有“八用寺字韻”、“九用寺字韻”……那么,是不是有這樣的可能:這三首詩題或跋語未明確列入十三首排序的寺字韻詩,是郭沫若當年在十三首寺字韻詩之外的創作?當然,這也就意味著還應該有多篇寺字韻詩尚為佚詩,且仍塵封在歷史中。
中國文人在文化交往中,用某字韻這種形式唱和,是舊體詩寫作所獨有的創作方式,是文人之間的一種風雅之事,很多時候難說什么微言大義。但在抗戰期間,就不盡然了,雖然也有為友朋之間雅聚而作,譬如,郭沫若與沈尹默等一班文友曾在宴席之間以沖字韻詩相互唱和。但郭沫若這十余首用寺字韻創作的詩,就如他所說:“在我的想法,目前正宜于利用種種舊有的文學形式以推動一般的大眾。”①郭沫若:《由“有感”說到氣節》,1937年8月30日上海《救亡日報》。事實上,舊體詩詞寫作,是郭沫若抗戰詩歌創作的主要方式。盡管有朋友勸他不要作舊體詩,但他“覺得做舊詩也有做舊詩的好處,問題該在所做出的詩能不能感動人而已”。②郭沫若:《由“有感”說到氣節》,1937年8月30日上海《救亡日報》。郭沫若曾在一次演講中說道:“隨著抗戰的號角,詩歌便勃興了起來,甚至詩歌本身差不多就等于抗戰的號角。”③郭沫若:《中國戰時的文學與藝術》,1942年5月28日、29日重慶《新華日報》。他就一直在吹響著這只號角。